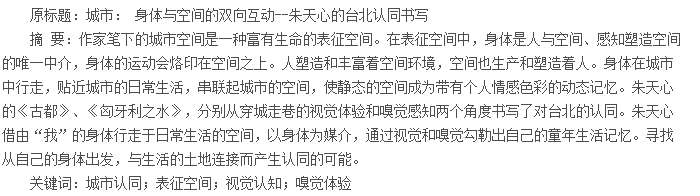
众多的城市叙事中渗透着地理学意义上的城市和个人的城市体验、想象。爱德华·索亚提出第三空间的概念,认为城市是兼具真实与想象的地方。作家们在城市的不断书写中总是会融入自己的特殊记忆体验,一种借由身体与环境的互动而产生的体感经验。
列斐伏尔将社会空间划分为三个环节: 空间实践 (spatial practice)、空间表征 (representations ofspace)和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列斐伏尔认为表征的空间是具有象征性的,“表征的空间是有生命的:它能说话。它拥有一个富有感情的核心或中心: 自我、床、卧室、住所、房屋;或者,广场、教堂、墓地。它包含着激情行动以及生活场景的中心,这直接暗示着时间。结果它可能被以各种方式描述:它可能是方向性的、情景性的或者关系性的,因为它本质上是性质上的、灵活的和能动的”.
爱德华·索亚在列斐伏尔的基础上针对表征空间进一步阐述,“实际的表征空间把真实的和想象的、物质和思维在平等的地位上结合起来……这是反抗统治秩序的空间,这种反抗的空间是从属的、外围的和边缘化了的处境产生出来的。”由此可见,表征空间与空间表征是不同的,空间表征更多倾向于全面、官方、历史的空间,而表征空间更多的是个人体验、私密的空间,是城市使用者的空间。表征空间是空间中的使用者通过个人私密的身体与想象力,把现有的空间变成一个“被直接活着”的空间,是具有生命的,具有感情核心的空间。表征空间充满着真实与想象及符号化,充满着意识形态的痕迹,是受各种资本主义,种族主义等具体实践的空间。
在没有官方的空间表征和历史知识的中介之下,通过叙述者的身体和想象,呈现的是一个私人化、私密性的表征空间。针对列斐伏尔的表征空间,德塞都更进一步提出身体行走是贴近城市生活、贴近城市空间的实践方法。借助于身体在城市中的交叉和移动,城市中静止不动的各种场所串联成为一个网络,这个网络中透露出城市生活的种种轨迹,也许会过于零碎化、片段化,但相对于城市地图那样的“在线”城市空间,行走保持了城市实践的本色---日常性和不确定性。身体取代了大脑,取代了官方出版的地图地理知识。身体在城市中行走,贴近城市的日常生活,串联起城市的空间,当行人与不同的场所相遇时,这个场所对于这个人而言就被激活了,带有了个人的情感记忆,静态的场所成为动态的空间,成为实践的空间。城市在不同的行人脚下变得丰富复杂起来,而这个城市空间也成为人无法重复的实践空间。任何一次的行走都会成为带有个人情感认识的空间之旅。
一、穿城走巷的视觉体验
城市的书写往往通过不同的人游走于城市,借由身体与环境的互动产生的体验而形成记忆。记忆书写是书写个人在时间与空间中移动所留下来的痕迹,因此,身体在时间与空间中的变化和体验是形成个人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自己根本上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与居所的生产”,而“生产的空间性过程开始于身体……开始于总是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中的、作为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的人类主体”.
人塑造和丰富着空间环境,社会空间也生产和塑造着人。身体成为人感知塑造空间的中介。“身体并不是一个自然的、去历史的、中性的客体,它是一个穿越历史、地理、文化经验,并且与感官所构成的经验互相交织而成的实体的界面。”由此葛洛兹针对身体的概念,提出了多元身体类型的场域,她认为“身体的概念包含所有的可能性的类型,并不仅仅是某一个典型代替了所有身体的可能性。”
在身体的各种感官体验中,乌尔曼将感官渠道按照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的关系分为触觉、温觉、嗅觉、听觉、视觉六个渠道。身体与城市的互动也涉及到多种感官体验,包括视觉、嗅觉、听觉、味觉和触觉,这些感官经验都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身体成为“我”认识世界的方式,世界也通过身体成为自我认知的途径,主体的形成与身体的经验息息相关。在众多的身体体验中,无疑视觉的体验是最直接最具象的一种。
穆时英霓虹灯下的狐步舞者,以曼妙的舞姿感受和消费着殖民舶来文化的上海,战乱年代的香港让聪明的白流苏当了一回乱世佳人,万千风情的香港也随着白流苏与范柳原在浅水湾和太平山顶若即若离勾心斗角的爱情游戏展开。胡兰成的嫡传弟子台湾作家朱天心,也试图以身体为媒介来感受批判后现代的台北。朱天心的《古都》以身体行走对比了90 年代后现代台北的丑乱和日本京都的恒常温馨,以及 70 年代台北的温馨原乡。朱天心的《古都》主要讲述了两个故事,“我”与好友 A 约定在京都见面,而 A 没有赴约,“我”独自在京都的游历;“我”回台北后被当做日籍游客,拿起日式台北地图重新游台的经历。无论是京都还是台北的游历,都交织着“我”对京都和台北的记忆和想象。在京都,“我”按照川端康成所写的《古都》中千重子和苗子的路线,重游了京都。“我”在四条桥上俯望着鸭川畔一对对不怕冻的情侣,穿过祇园,走上白川南通看两岸的植柳和垂樱,在通往清本町的巽桥上回忆起 5 岁的女儿曾为鱼儿争食大为紧张,拾级上八阪神社,最后从西行庵、菊溪亭的巷子左转东大谷祖庙前,拦腰进圆山公园,回忆起自己曾经在此边吃喝边讲阪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的事迹给女儿听。“我”借由身体的行走重走了京都,唤起了对京都的温馨记忆。与温馨恒常的京都相比的是,“我”重游台北时,记忆中的温馨台北被现实中的后现代商业化所消解。
“我”尾随森鸥外和外公的散步路径穿越三线道路的东线,坐上开往淡水的旧客车,分别经过大正町、三桥町、宫前町、圆山町、台湾神社,一路上司机一直吃票,车飞过关渡隘口,只是沿途再没有了百年茄冬,多的是路边的大广告招牌,最后在黄槿下车,看入海口处人们钓鱼,感慨现在的榕园咖啡好贵。从满是小摊吃客的甘州街走到太平町,发现红砖洋楼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摩天大楼,中街更是被各种南北干货行塞满。叙述者把殖民地图与现在的台北街道重叠,台湾神社变成了圆山饭店,台湾总督官邸建成了 总统府 ,二二八圣地现在是黑美人酒家……江畔已无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倒是有可能会有浮尸。京都和台北已经不再是官方地图上的京都台北,是带有叙述者个人体验的表征空间。城市因身体的穿城走巷而富有叙述者独特的个人色彩。官方《(台湾志略》)记载的剑潭是: 位于台北基隆河沿大直山麓之曲流处,有树名茄苳,高耸障天,大可数抱,峙于潭岸。相传荷兰人插剑于树,生皮合,剑在其内,因以为名。然而对朱天心而言,剑潭是“五岁时,穿戴整齐的由父母第一次带你去动物园儿童乐园,看到满天都是五彩气球、吹泡泡和音乐,各式各样小吃摊的香味和叫卖”《(古都》),是一个又大又繁华的嘉年华广场。同样地,爱国西路和信义路南岛遍见的茄冬,是青春时期女校男校常议的楚河汉界,是少男少女进行身体探索的掩体。
在表征空间中,身体是人与空间的唯一中介,身体的运动会烙印在空间之上,身体会与空间产生自然的亲密感。就如巴什拉所说“一旦‘二十年后’再回到出生时的那一栋‘永难忘怀’的房子,我们依然可以重新掌握住‘生平第一道阶梯’的肌肉反射,我们绝不会在那个高起来的台阶上绊倒……最小的门栓带来的感觉也依然驻留在我们的手上”.
巴什拉形容的那种空间与身体之间互相铭刻的感觉,在朱天心的小说中也有表现:“你们像回到家似的熟门熟路拾级而上。渡船口正对的窄巷,石阶缝里永远长着润青应时的野草,只差没向二号和四号的人家喊一声: 我回来啦”.城市叙事涵盖了时间和历史向度,是个人经验的再现和想象。通过身体在城市中的穿城走巷,让停留于城市地图的空间表征成为带有个人丰富体验的表征空间。
二、嗅觉地景的构筑
17 世纪的法国理性主义把理性视为检验一切的标准,认为包括嗅觉在内的感觉都是不可靠的东西。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打破理性主义的唯理论,重新强调感觉在认识论中的重要性。狄德罗充分肯定了感觉在认识论中的作用,“在生物界,触觉分化为无穷无尽的方式和程度,在人身就叫做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知觉。他接受各种印象,让这些印象保留在他的感官中,然后用字眼来区别他们,并且就用这些字眼或用形象来追忆它们”.
在人类的历史上,嗅觉被认为是最原始,最本能的器官,也是最常被忽视的器官。古希腊人认为嗅觉比视觉低级,嗅觉更多的属于是动物的特殊功能,而不是人类的特征。因此“许多学者将嗅觉置于感觉分类体系的最下层”.但是“科学家经过研究认为儿童的第一感觉是嗅觉,人类生命起始时,并非先看到白天的阳光,而是先闻到扩散于子宫液体的生命气味”.
婴儿第一个发生作用的感觉器官是嗅觉,通过嗅觉的经验,感觉到自我的存在,这证明人类的嗅觉经验早于视觉经验。婴儿离开母体之后,开始接触周围的环境,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转移,气味给了“我”嗅觉的经验,同时也给了“我”由嗅觉引起的记忆。嗅觉是一种即时性的经验,“嗅觉无法为我们建构一张具体的地图,但是嗅觉给我们线索,告诉我们某个环境曾经发生过的事件,以及与此时间相关的人、事、物”.
视觉引起的视觉地图由颜色、距离感组成,触觉地图由感受到的不同物体的形状、温度和质感组成,而嗅觉由不同气味的引诱而产生,因此嗅觉地景依赖的是记忆和想象,通过嗅觉产生的多是虚化的空间。由于气味没有形体,本身是一种虚无和空白,嗅觉地景往往是借由想象和回忆而产生。
中国古典文学《红楼梦》以香味来区分人物的性格,各种香味对应着主人公特有的性格,王熙凤房间的辛香对应其泼辣的性格,潇湘馆的木竹清香与林黛玉冷漠高傲的性格相合。如果在《红楼梦》中味道还只是区别人物性格的一个媒介,那么在帕·聚斯金德的《香水》中,嗅觉已经成为主人公格雷诺耶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格雷诺耶拥有灵敏的嗅觉,即使不掌灯也能“嗅”清道路,并以嗅觉来与人打交道,并预知危险,“从他吸入格里马气味的头一次呼吸中即知道,他只要稍有反抗情绪,这个人完全会致他于死地。”
通过嗅觉,作者展示了 1738 年世界上最臭的巴黎: 圣丹尼大街和圣马丁大街,两侧的小巷里人口那么密集,房屋鳞次栉比……地面的空气像漂浮在潮湿的运河上一样,充溢着各种各样的气味。人和牲口的气味,饮食的蒸汽和疾病的毒气,水果味儿,石头味儿……近年来随着城市文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作品试图以嗅觉来表达对城市的体验和认知。台湾作家朱天心的《匈牙利之水》以嗅觉作为认知台北的媒介,以具体的物件唤起特殊的嗅觉体验,以引起对台北的各种回忆和重新的认知体验。
朱天心的《古都》是以身体行走来表达对 90 年代后现代台北身份认同的断裂,而其《匈牙利之水》则是以嗅觉来书写对老台北眷村的回忆和认知。《匈牙利之水》讲述两个偶然在小酒馆相遇的中年男子,凭着香水香料的嗅觉刺激,重启记忆之门,进而沉浸于往日时光,“闻”出了已经遗忘的过去。“而嗅觉又刺激出听觉、味觉及触觉的快感,造成一种象征主义式感官交错的效果。”
A 酒鬼似的抓着个空酒杯,晃荡着向我走来,笑咪咪的先为自己的鲁莽抱歉一声,随后真正非常鲁莽的问我“:你怎么会有这种味道?”“香茅油!我有三十年没闻过了---”A深深吸着气。
香茅油就像是普鲁斯特的玛德莲蛋糕,摸一摸这阿拉丁神灯,记忆便倾泻而出。由香茅油“我”忆起妻子在雨季为防白蚁,用香茅油涂遍衣柜。A 因香茅油忆起了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台北,“那时候,整条街上日日夜夜都是香茅油的味道,我到大了才知道是熬了外销到日本去的”.20 世纪 60~70年代正是台湾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以外销为主的经济模式,渗透到家家户户。当时的 行政院院长 曾经提出“客厅工厂”的概念,即将小手工艺加工变成家庭作业,使每个家庭都参与到外销制造中来。在当时外销盛行“客厅工厂”,家家户户绣亮片串珠子补贴家用。同样由气味,“我”还记起,“当时妹妹为了收集金银财宝,硬要我带着她去玩伴家串门子,那时候家家的妈妈们都在做绣珠绣线的女红,有人定期来发材料和工钱,贴补家用。很多人不会绣,珠子亮片因此常常散落地上,我妹就不动声色的捡拾它们,充满了耐心,她完全相信有一天聚拢到某个数量,我们家就会‘发财喽'! ”
故事一开始的“我”是一个活于现在,没有过去的人,回忆对“我”而言太沉重。然而 A 却一点点卸下“我”内心的心防,重新启动了“我”的嗅觉机制。“我”不知不觉也开始从气味想起童年往事。由服务生身上的异味,我想起了和妹妹一起吃妈妈炒的咖喱饭,这幅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触发了作者对原乡的渴望,并重温了儿时家庭的温暖。
由栀子花的香味“,我”想起了小学一年级人人桌面上的宝藏盒: 儿时的可爱天性,将一切都视如宝贝,栀子花、香水铅笔皮,甚至臭烘烘的奶牙都是值得展示的真品。这些没有价格的“微小”东西,在一切以价格衡量物品价值的“消费主义时代”实在是微不足道。却让 A 内心泛起童年的喜悦和温馨。
与香茅油和栀子花引起的温馨记忆相比,“我”由绿色葡萄籽召唤起的儿时回忆,却带着诸多死亡的阴影。“我”童年居住过的眷村被迫拆迁,儿时的玩伴脸孔也日渐模糊,这份哀伤转化为死亡的阴影。在大逃难一样的迁村中,丢失了一些人口。有七个兄弟姐妹的孙家,在拆迁搬家中丢失了孙囡囡。
经常出没在荒草场的流浪汉也没有下落,而“我”一直问自己,当年自己到底有没有和后来变成绑架犯的刘 XX,一起杀了这位流浪汉。这种对死亡的可怕阴影和记忆始终笼罩着“我”,“朱天心借着这篇故事哀悼眷村的特殊人文生态环境随着都市化日渐消失。”
通过相关材料和感官的嗅觉、听觉、视觉产生的催化作用,主体开始搜索记忆之旅。但由于气味是通过空气相互作用的,是即时性的,很容易消失、移动,“我找遍了台北的香水店、百货公司、真品平行输入店、精品店、委托行……没听过这牌子的没听过,好些年没卖过的没卖,香茅油,它可能绝版了。”香茅油的绝版,是嗅觉媒介的绝版,等同于失去了某一种嗅觉,也就等同于失去了某种记忆。作者巧妙地用气味的存在与消失,表明了记忆的丢失与寻回的不可得。在文中,作者还借 A 之口,说“阿滋海默症患者(通常所说的老年痴呆)通常在失去记忆时,同时也失去嗅觉”.由此也从反面印证,失去嗅觉,因而失去记忆的人,就如老年痴呆患者,死亡提早来临,失去记忆,就如将死之人。
嗅觉经验是与环境相互交融的经验,在《匈牙利之水》中,朱天心借由“我”的身体行走于日常生活的空间,以身体为媒介,通过嗅觉勾勒出自己的儿时玩伴和童年生活趣事。重新处理了过去记忆之中的矛盾和断裂之处,处理了“我”对台北老城眷村的回忆和认知,寻找从自己的身体出发,与生活的土地连接而产生认同的可能。
作者笔下的城市空间是一种带有个人体验的表征空间,是富有感情的所在,是空间中的使用者通过个人私密的身体与想象力,把现有的空间变成一个“被直接活着”的空间,是具有生命的,具有感情核心的空间。在身体对空间感知的各种途径中,身体的行走与视觉成为感知空间的两种重要途径。《古都》、《匈牙利之水》分别让主人公以穿城走巷和嗅觉回忆的方式书写了对新旧台北的认同。《古都》中的“我”行走在圆山公园和八阪神社上,用身体感受京都的静美平和,回台后“我”坐车经过关渡隘口,穿梭在 90 年代台北的摩天大楼之间,置身后现代的台北,“我”如桃花源中的武陵捕鱼人,缘溪行,忘路之远近,最终在绕城行走后,发现记忆中的台北已消失,于是“这是哪里?---,你放声大哭”.《古都》以穿城走巷的方式表达了作者对于 90 年代新台北的无法认同。而在《匈牙利之水》中,作者借助笔下两个人物,通过气味引起的嗅觉地景,再现了记忆中眷村台北的样子。由香茅油的气味,A 想起在60~70 年代外销时代的台北,“我”想起和妹妹去别家客厅捡珠子的故事;由服务生身上的异味,“我”想起了小学月考后,和妹妹一起吃妈妈炒的咖喱饭;由栀子花之香“我”想起了小学一年级人人桌面上的宝藏盒。这种带有儿童时期的温馨记忆,是对眷村时期台北的深刻认同和怀恋。而由绿色葡萄籽召唤起的眷村被迫拆迁,朋友失散,眷村大家庭的瓦解记忆带着诸多恐怖的阴影。朱天心借着这个故事哀悼了眷村的特殊人文生态环境随着都市化日渐消失。在认同眷村台北的同时也在拒斥着后现代商业化的台北。
参考文献:
[1](法)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London: Blackwell Ltd.,1991.
[2](美)爱德华·索亚著,陆扬等译。 第三空间[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美)爱德华·索亚著,李钧译。 后大都市: 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4]Elizabeth Grosz Volatil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Feminism[M]. Bloomington:Indiana UP,1994.
[5](法)巴什拉著,张 婧译。 空间诗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6](法)狄德罗,伍蠡甫主编。 论戏剧艺术[A]. 西方文论选(上卷)[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7](荷兰)派特·瓦润等著,洪慧娟译。 嗅觉符码:记忆和欲望的语言[M].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
[8](德)帕·聚斯金德著,李清华译。 香水-一个谋杀犯的故事[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9]王德威。 老灵魂的前世今生(古都)[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10]黄锦树。 从大观园到咖啡馆: 阅读/书写朱天心[A]. 古都[M]. 台北:台北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