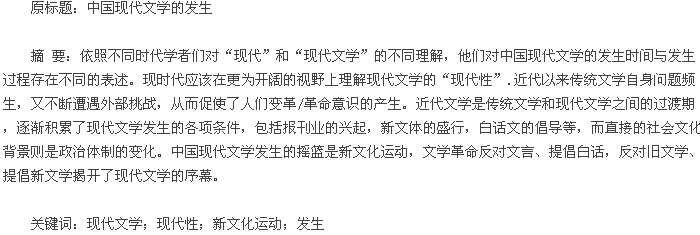
一、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身处
21世纪之初,回顾中国现代文学,首先应该思考的问题之一是,什么是“现代”.“现代”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性的名词,也是一个包含价值判断的形容词。我们可以说世界各国都置身于“现代”,也可以说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现代”.为什么在相同的时间段里存在着“现代”程度的差异?这说明“现代”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平衡性。由于这种不平衡性,“现代”就不是随着时间的河流自然涌到我们眼前的一个“历史的码头”,而是一座需要主动进入和主观建构的历史城堡。由于“现代”概念的双重含义,便产生了对于“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的林林总总的复杂理解和阐释。
世界各国进入“现代”的时间和方式都是不同的,这与工业文明的兴起、理性启蒙的普及、人类愈来愈组织化的生活模式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我们必须在“人类现代文明”的总体框架之下来看待和学习中国现代文学,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从而进一步去探索中国现代文学至当代文学的演变规律。
中国现代文学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和怎样“发生”的,这并不是一个具有“标准答案”的客观真理,而是依照对“现代”和“现代文学”的不同理解各有不同的表述。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周作人在他的着名演讲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认为:“我们可以这样说:明末的文学,是现在这次文学运动的来源,而清朝的文学,则是这次文学运动的原因。”[1]30他还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1]48最后总结道:“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1]58周作人的意思是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不过是数千年的中国文学长河里“言志派”和“载道派”起伏消长的又一个回合而已。
于是产生了胡适之的所谓“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所以,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异点无非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加外来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则又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1]
现代文学的主将之一郭沫若认为:“中国新文艺,事实上也可以说是中国旧有的两种形式--民间形式与士大夫形式--的综合统一,从民间形式取其通俗性,从士大夫形式取其艺术性,而益之以外来的因素,又成为旧有形式与外来形式的综合统一。”①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说过:“我认为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是旧文学底正当的发展。”②这些意见都偏重于认为“现代”是“过去”的自然演变。现代文学也无非是文学史上的又一次“改朝换代”.而文学革命的发起人之一胡适却认为“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从文学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国的文学实在不够给我们作模范”,所以“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着做我们的模范”③.现代文学的着名理论家胡风认为: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的一个新拓的支流。那不是笼统的“西欧文艺”,而是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以及浪漫主义)文艺;在民族解放的观点上,争求独立解放的弱小民族文艺;在肯定劳动人民的观点上,想挣脱工钱奴隶的运命的、自然生长的新兴文艺④.他们代表的意见偏重于认为现代文学具有崭新的特质,所谓“现代”,不能从中国自己的历史中去孤立地理解,而要与世界、与“西洋”联系起来。如此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包含了“中国”和“世界”两种因素。其“现代性”既是中国历史的自然演进,又是中国与世界碰撞交融后的自我更新。因此这就产生了从不同立场出发的对中国现代文学性质的不同阐述。王瑶1951年出版的第一本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式教科书《中国新文学史稿》,运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指出: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开始的。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上的斗争和表现,用艺术的武器来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新文学的提倡虽然在五四前一两年,但实际上是通过了“五四”,它的社会影响才扩大和深入,才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底有力的一翼的。[2]
其后由唐弢、严家炎主编的教育部统编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明确指出:历史驳斥了那些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说成只是明朝“公安派”、“竟陵派”的继承和发展,或是西欧资产阶级文艺的“一个新拓的支流”等不符事实的言论。无产阶级领导并以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这两种力量为中坚,保证了我国现代文学具有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性质。[3]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力图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
1987年,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等人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该书认为“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都是中国社会大变动,民族大觉醒、大奋起的产物,同时又是东西方文化互相撞击、影响的产物,因而形成了共同的整体性特征”.他们根据对鲁迅、周作人文艺思想的理解,把现代文学的性质概括为“改造民族灵魂”.但是该书1998年出版修订本时,却进行了另一种概括,明确指出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修订本最为引人注目之处是在每个“十年”都增加了一章对通俗文学的论述。这显然是与20世纪最后十余年间对“现代化”理解的学术背景有关的。严家炎最早采用“现代化”的观念来看待整个现代文学,影响了一代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到90年代基本落实,新文学研究和现代通俗文学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为新的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现在,我们可以在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上理解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这是一种“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但是不止于此;这是一种“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但是不止于此;这是一种表达现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文学,但是不止于此。这是伴随着并促进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学,这是三千年诗文大国自我扬弃变革的文学,这是组织和建立现代中华民族与现代中国的文学,这是走向世界舞台去实现光荣与梦想的文学……但是,可能还不止于此。
二、现代文学发生的必要性
现代文学之所以能够发生,其首要前提必然是传统文学出现了重大的问题,遇到了重大的挑战。传统文学自身的问题早已潜伏并不断滋长,而当它遭遇到来自外部的挑战时,这问题便被急速推入人们的视野,从而促使了变革/革命意识的产生。
中国传统文学发展到清朝后期,在内容、观念、文体、语言等诸方面,都愈来愈落后于时代的需求,愈来愈陈陈相因,生气凋零,既无力发挥组织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国民文学”功能,也无力光大中国文学固有的美学风范。从文体类型上看,传统文学的核心是诗文。清朝后期的正统诗文,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或者说进入了“衰变期”.明朝以后中国文学里最有成就的类型实际上是小说、戏曲,而小说与戏曲却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旁门左道。文体类型的“金字塔”等级观念,一方面严重束缚着小说、戏曲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使正统诗文原地踏步,无路突围。无论学唐学宋,正统诗文从总体上看,都远逊前代,乏善可陈。“代圣人立言”的创作观念和盲目推崇考证之学的不良风气,使文学的主体性日益萎缩。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文章规范之学”和遍布天下的八股文教育体系,将中国传统文学鲜活的精华,风干成枯瘦死板的一些教条,文学几乎演变为“破题游戏”.事实上晚清的各种文字游戏--如灯谜、诗钟、酒令--的确是精彩空前,仿佛在昭示着古汉语艺术的回光返照。而在真正的文学作品里,这种远离现实口语的文言,却越来越捉襟见肘,词不达意,越来越需要写作者付出长期的艰辛才能运用得体。
面对传统文学的窘境,不乏有识之士呼唤改革并力图突破。从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到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都表现出传统文学“突围”的努力。但是,在传统的内部要进行彻底的变革不但是万分艰难的,而且必然是视野局促的。将“地球”“火车”这些新名词写进“七律”“古风”这类传统诗歌,并不能解决传统文学的问题,不但遭致保守势力的嘲骂,连改革者自己也觉得不是正路。太平天国借助特殊的政治背景,曾经颁布《戒浮文巧言 谕》,指出“文以纪实,浮文所在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要求文字“一一叙明,语语确凿,不得一词娇艳,毋庸半字虚浮。但有虔恭之意,不须古典之言”.洪秀全为此还特意把《字典》改为《字义》。但是太平天国的诗文与清代的改革派诗文一样,加强了通俗性而减弱了文学性。比如洪秀全的《劝戒鸦片诗》:“烟枪即铳枪,自打自受伤,多少英雄汉,弹死在高床。”这显然不是文学变革的金光大道。
通俗性是现代性的要素之一,但是现代性所要求的通俗,必须是以不牺牲思想性、艺术性为前提的。在传统文学的观念中,雅和俗判若鸿泥,高雅的文学是为雅士服务的,通俗的文学是给“小民”娱乐的。雅士要领导和统治小民,“上智与下愚不移”,所以两种人需要有两种不同的读物。而现代性要求全体国民在理论上拥有相同的读物,这读物不是为了确定阅读者个体的社会等级,而是为了使所有读者产生共同的文明图景想象,从而结成民族共同体这样一个“同心集团”.所以,在古代,阅读《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是两种境界,两个层次。而在现代,不过是两种需求,或者是两种工作。因此,传统文学就面临着一场重新整合文体格局和语言功能的“脱胎换骨”的大抉择。
差不多与传统文学意识到自身的变革需求的同时,外国文学就开始了对中国文学的冲击。这种冲击由于不像军舰大炮的物质冲击那般剑拔弩张,来势汹汹,所以在很长时间内不大引人注意。
第一种是传教士用白话翻译的《圣经》和用白话写成的宗教读物。由于语言的通俗和思想的“异端”,这些读物具有极强的传播力,其传播速度和传播效果大大超过古代传入中国的佛教读物。最有力的结果是,由“拜上帝会”组织的一场农民起义竟然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太平天国政权。虽然最终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汉族士大夫集团消灭了太平天国,但清朝通过这次“中兴”,实际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第二种是外国人在中国组织的一些文学活动,比如租界里的戏剧表演,外国侨民的文学阅读等。这些活动的影响范围比较小,但是那种直接组织受众的方式和效果,却给中国的目击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中国最早的现代话剧,就是受此启迪而萌芽的。上海有个着名的外侨剧院--兰心大戏院,中国话剧的早期功臣徐半梅、郑正秋等经常去那里看戏。郑正秋在那里认识到中外戏剧的区别:“他们才是假戏真做,中国人在台上则有假戏假做的表示。”⑤外国人组织教会学校的中国学生演出宗教剧,则对中国传统戏曲产生了独特的冲击力。早期话剧家汪优游说:“这种穿时装的话剧,既无唱工,又无做工,不必下功夫练习,就能上台去表演,自信无论何等角色都能扮演,对新剧大感兴趣。”[4]戏剧的高雅和普及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这对中国人重新认识戏剧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启示。
第三种是外国文学作品的大规模翻译。以林纾为代表的小说翻译虽然标榜“古文笔法”,但实际上已经不能不受到外文原着的思想观念和艺术观念的影响。这些“异域奇闻”直接改变了中国人的“外国想象”,也直接改变了中国人对小说地位的看法,也正是在这些小说的巨大影响之下,才发生了清末的“小说界革命”.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对小说戏曲地位的贬低,直接导致对民众的贬低并进而导致国家的贫弱。因此,重新为中国文学排序,至关重要。
问题与挑战,促使中国传统文学在观念、语言等方面认真反省。不变革,不但不能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就连文学自身也前途渺茫。代圣人立言该结束了,为自己说话该开始了。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能够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这一点,现代文学发生的必要性就存在了。
三、现代文学发生的文化背景
现代文学并不是直接顺着传统文学大河奔涌的方向“鲤鱼跳龙门”的。近代文学是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漫长的过渡期。在这半个多世纪的过渡期中,逐渐积累了现代文学发生的各项条件,其中重要的有:报刊业的兴起,新文体的盛行,白话文的倡导,而最直接的社会文化背景则是清王朝的结束和民国的建立。
报刊作为大众传媒的登场,是现代化社会信息沟通方式的标志。本雅明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开展的。报刊不仅是现代文学作品的载体和园地,而且逐渐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的组织者、策划者乃至领导者。报刊使文学创作真正成为一种“艺术生产”,直接导致了“职业作家”的产生。在传统文学生产时期,单凭文学写作谋生是很难想象的,文学创作一般都是士大夫和官僚的闲情韵事,曹雪芹写出万人景仰的《红楼梦》,他自己却竟然“举家食粥”,贫病而死。报刊的出现,改变了作者、出版者和读者的关系,在三者之间建立了稳定的经济逻辑。
在清朝后期,中国缓慢地开始了自己的报刊业。综合各种统计资料,可以发现,到洋务运动时期,报刊业开始突飞猛进,全国达到几十种,到20世纪初,已经超过100种,进入民国,则超过了500种。
报刊的发展,直接影响了文体。黄遵宪倡导的“诗界革命”和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是从创作的角度要求革新文体,振兴文学。而报刊的发展则把读者有机地组织进文学生产的流程,报刊文体要求明确、清晰、有力。于是就产生了最具代表性的报章文体--梁启超的“新文体”.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自我概括为:“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5]
这里梁启超明确地强调“读者”,此话透露出现代文学一个重要的特质:重视读者。能够对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的文字,是现代文学的好文字,而不是像传统文学那样,经史子集,家法森严,不考虑读者的接受反应,只从创作角度对文学进行价值分类。不尊重读者的报刊是无法在现代社会里生存的,因而,孤芳自赏的文学也必定不会是现代文学的主流。梁启超新文体中的几个要素:通俗,自由,明快,热情,后来就成为现代文学的主要文体特色。
白话文的倡导,发轫很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就有一些学者开始思考书面语和口语相一致的问题。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说:“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6]这个“简易之法”一是进行汉语的拼音化探索,二是推行白话文。拼音化的现实基础薄弱,所以发展比较缓慢,而白话文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久远的历史积淀,所以发展比较快捷。当时的翻译外国小说,就既有文言译本,也有白话译本。
1898年裘廷梁发表了《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字者,天下公用之留声器也。”从开启民智的角度要求用白话来普及文字:“有文字为智国,无文字为愚国;识字为智民,不识字为愚民。”封建专制国家采取愚民统治,所以“文与言判然为二”,而今要发扬国人的“聪明才力”,则应该“崇白话而废文言”.文章列举了白话的八大好处:省目力,除骄气,免枉读,保圣教,便幼学,练心力,少弃才,便贫民。这是新旧双方都可接受的一种号召。
提倡白话文的另外一支重要力量是报刊的编辑者。被誉为“通俗文学之王”的包天笑在维新运动期间就办过一份《苏州白话报》,与《杭州白话报》相呼应。
1917年1月,包天笑创办了《小说画报》,在《编者例言》中指出:“小说以白话为正宗,本杂志全用白话体,取其雅俗共赏,凡闺秀、学生、商界、工人,无不咸宜。”《小说画报》的发刊词曰:鄙人从事于小说界十余寒暑矣,惟检点旧稿,翻译多而撰述少,文言伙而俗语鲜,颇以为病也。盖文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学,复而为俗话之文学。中国先秦之文,多用俗话,观于楚词墨庄,方言杂出,可为征也。自宋而后,文学界一大革命,即俗话文学之崛然特起,其一为儒家禅家之语录,其二即小说也。念忧时之彦亦以吾国言文之不一致,为种种进化之障碍,引为大戚。若吾乡陈颂年先生等奔走南北,创国语研究会到处劝导,用心苦矣,然而数千年来语言文字相距愈远,一旦欲沟通之,夫岂易易耶!即如小说一道,近世竟译欧文,而恒出以词章之笔,务为高古,以取悦于文人学子,鄙人即不免坐此病,惟去进化之旨远矣。又以吾国小说家不乏思想敏妙之士,奚必定欲借材异域?求群治之进化,非求诸吾自撰述之小说不可。乃本斯旨,创兹《小说画报》,词取浅显,意取高深,用以杂志体例,以为迟懒之鞭策,读者诸君其有以教诲之乎!天笑生识。
古人的楼似乎从来就不是作为一种实用价值而存在的事物,而是为了人们的审美需求而存在的一个边缘、神秘而开放的空间,它既不需要承担储存各类闲杂物件的责任,也不提供睡眠和生活的功能,相对于更加实用的房、屋而言,楼是一种边缘的真实。然而,它却是古人...
摘要龙应台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崛起的台湾知名作家,在台湾颇具影响力,因此她的作品及其引起的社会关注都值得我们去深入的研究。龙应台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多重的社会角色,这些都为她的文学创作注入了丰富的元素,每一个不同的社会身份都为她当时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