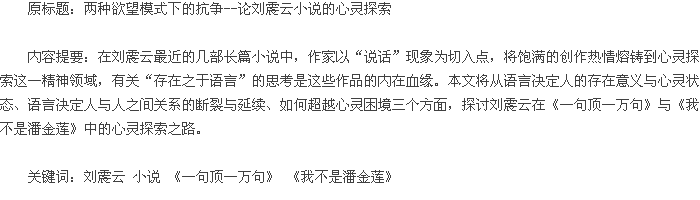
有论者指出:“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刘震云是一位把中国文学传统中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讽刺艺术和以《官场变形记》为代表的暴露艺术发挥到极致,同时又兼具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哲学的反讽意味的小说家。”这样的评价是贴切的,讽刺、暴露与反讽当然是研究刘震云创作的重要切入点,但刘震云的创作却又很难单以几个关键词来概括。
“说话系列小说”是刘震云新世纪以来的主要创作成果,从《一腔废话》到《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直至《我不是潘金莲》,“说话”、“交流”成为刘震云这一系列作品中的核心内容:《手机》通过现代通讯工具给都市人带来的困境,展示了人与人“交流”的困难及虚伪,对人物灵魂进行冷峻的逼视;《一腔废话》在黑色幽默的语言大杂烩中表现了沟通、交流的疲累和隔绝,揭示了人类的心灵困境;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以“说话”为叙事本体,挖掘出日常生活中的偶然与荒诞,发现语言交流不畅带来的心灵隔阂是造成个体孤独、恐慌的根源这一“现代人内心的秘密”;在洞悉了“说话”对于改变人物命运的种种可能性,勾勒出琐屑驳杂世态表象下的生存本相和精神重负之后,《我不是潘金莲》试图以一个有关坚持和追寻的“西绪弗斯神话”唤醒人们沉睡、麻木的心灵,实现对于现实的精神救赎。在这批小说中,作家以“说话”为切入点,将自己饱满的创作热情熔铸到心灵探索这一精神领域。刘震云的心灵探索常常在生命存在的维度上展开,内化为对人类生存困境及个体存在意义的追思。《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无疑将作家的思考推向了新的广度和深度。
从《我不是潘金莲》出版伊始,学界就有其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姊妹篇”的说法。从两部作品共同关注的“说话与存在”的主题、主人公一直“在路上寻找”的叙述主线、小说揭示的具有存在主义意味的人生之无助、孤独和荒谬来看,二者是有内在联系的,但两部作品又各自有所侧重。《一句顶一万句》以“说话”的行为、内容彰显人物性格,展示生活的琐碎,揭示语言之于存在的隐喻性阐释,在一串串看似偶然和荒诞的日常生活细节中将“说话”这个我们每天实践、亲历和不断延续的最平常的行为演绎成惊心动魄的将近百年的难解之谜,心灵无所依托的孤独感是小说传达的生存本相;而在《我不是潘金莲》序言部分那个颇有传奇性的故事里,李雪莲为了以严肃的态度澄清一件事、纠正一个被人强加的标签、证实一句话、一个说法奔走20年而不得,最终在荒诞中感受到不被理解且“无路可逃”这一无可消除的生之痛苦。在这部小说的正文部分,前任县长史为民却潇洒地以游戏的态度消解现实的种种无奈,超越了生命的沉重与虚无,展示了面对孤独和“生之痛苦”时的解脱之道。我认为,《我不是潘金莲》是对《一句顶一万句》中存在主题的发展和超越,而两部作品都涉及的“存在之于语言”问题是二者之间的内在血缘。
一
一直以来,存在与语言都是西方哲学的两大课题。学界公认,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由生存论向语言学的转向,即从前期对“存在”的本体论反思到后期对“语言”的探究。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指出:“语言是存在的家。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中。思想者和做诗者乃是这个寓所的看护者。”
这是海德格尔后期语言本体论的一个重要结论。事实上,海德格尔对于语言的探讨立足于语言之“体”,强调语言的非工具性、非逻辑性和对人生的普遍性意义,仍然在生存论的范围之内。
海德格尔认为,语言具有命名的力量,即语言给物命名,从而使物物化,将物召唤在场。他指出:“只有在合适的词语从而就是主管的词语命名某物为存在着的某物,并且因而把当下存在者确立为这样一个存在者的地方,某物才存在。”
在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风景线上,《心灵史》与《穆斯林的葬礼》(以下简称《葬礼》)格外引人注目。这两部佳作都出自回族作家之笔,前者是硬汉子张承志所写,后者是奇女子霍达所作,他们在同一母体文化、同一民族情结的牵引和驱策下,建构了回回人的艺术世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