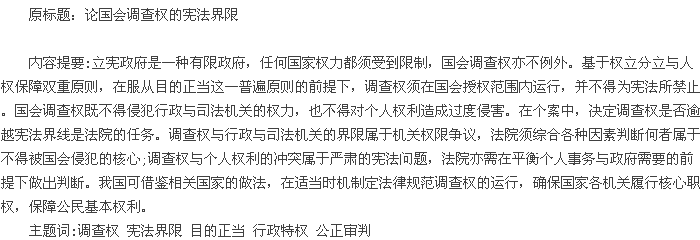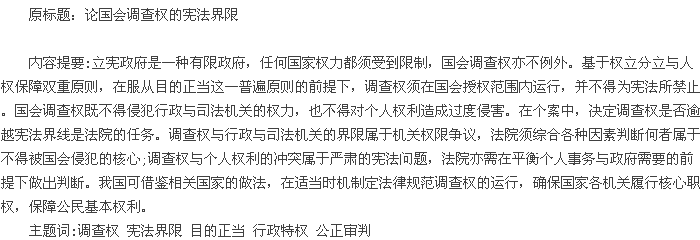
无论作为独立权能抑或辅助权能,调查权的行使皆有可能导致个人资料与国家秘密外泄,抵触其他机关的权限,严重者有危及国政之虞,动摇国家根本。基于权立分立和人权保障双重原则,立法机关的调查权既不得干预其他机关权力的正常行使,亦不得过度侵害个人权利,故调查权行使须有一定的范围与界限。国会调查权通常在三方面受到限制:其一,调查必须是在合法的目的与范围之内;其二,国会无权调查专属于其它权力机构的事项;其三,国会无权调查公民的私事。在个案争议中,判断调查权是否逾越宪法界限是法院的职责。
一、一般原则:目的正当
目的正当与否是判断任何公权力运行的基准,它是指公权力采取的手段与达成的目的之间是否具有妥适性。法律保留之比例原则就是关于立法机关限制基本权利的手段与目的关系的理论,包含三方面内容:其一,限制基本权利的目的必须是正当的;其二,限制手段与目的具有关联性,限制手段有助于目的之达成;其三,采用所有限制之中侵害最小之手段。在描述公权力采取手段与目的关系方面,最为着名的当属“麦卡洛诉马里兰州”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的判词。
在1819年的McCulloughv.Maryland(麦卡洛诉马里兰州)一案中,针对联邦是否有权在马里兰州设立国有银行,马歇尔认为,根据宪法第1条第8款国会的“必要且适当的权力”,设立银行是国会一项“默示的宪法权力”,是联邦运行宪法授权职责的一种手段,具有正当性。他阐述道:“如果目的是合法的,如果它又是在宪法所规定的范围内,那么,一切手段只要是适当的,只要是明显适合于这一目的,只要从未被禁止过,并且是与宪法的文字和精神相一致,就都是合乎宪法的。”在涉及征税权的判例中,联邦最高法院不断适用目的与手段的关联性考察国家权力的合宪性,认为如果国会设立税收是作为国家增加岁入的手段,则其目的正当,如果税收设立的目的是作为惩罚方法,该目的不具有正当性。在1922年的Baileyv.DrexelFurnitureCo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决国会制定的“童工税法(ChildLaborTaxLaw)”因将税收作为惩罚雇佣童工的公司的手段,其目的不具有正当性而违宪。该判决确立的原则体现在其后一系列涉及税收法律的案件中。这说明,目的正当不仅适用于基本权利限制,凡涉及国家权力的运行,皆存在目的正当与否之考量。在1927年的McGrainv.Daugherty一案中,最高法院驳回了低等法院的裁决,申明国会的调查是正当的。最高法院认为,虽然“宪法并未明确地授予国会以调查权,但是根据宪法第1条第8款的‘必要和合宜’条款,国会有权行使与其立法权相关的权利。……而国会要实行调查,其唯一的正当目的就是调查能辅助立法。”
目的正当包括实体与程序两方面内容。实体正当指调查是否为了辅助立法、运行监督,及就公众关心的问题查明真相;程序正当指调查是否在国会授权的范围内,是否被宪法禁止或者超越了宪法设立的权利保护界线。
首先,调查目的合法。法院在判断国会调查是具有正当目的时,主要视调查对象是否与国会行使立法权相关,调查所得的信息是否有助于国会立法方面的考量,如果符合这两个条件,法院就会认为调查目的正当。
早期,法院将国会调查目的严格限定在立法辅助方面。法院警告说,调查权仅仅用以辅助国会立法,调查必须与国会的立法任务相联系并且是为了促进国会立法任务的实现。判断调查目的是否正当须进行利益衡量。在调查政府机构乃至总统时,法院在考察调查对于总统确保相关信息和交往机密性的影响,及对总统正常履行宪法赋予职能影响的情况下进行衡量。根据衡量的结果,如果总统不交出相关材料,国会将无法有效履行其立法权能。“总统能够证明交出相关材料将会妨碍他履行正常职务,那么就应由国会承担说明责任”。
在对司法机关进行调查时,法院须判断调查是否逾越界限侵犯了宪法保障的司法独立原则,影响公正审判。在调查个人事务时,法院需在权衡个人隐私与政府需要的前提下,判断调查权是否逾越界限侵犯了宪法保护的个人权利。
其次,调查授权范围内的事务。两院或者参议院授权调查委员会一定范围内的事务进行调查,调查委员会只有对在授权权限范围内的事务进行调查的权力。
早期的调查须与国会立法目的有关,并且是为了促进国会立法任务的完成。由于调查目多样性,国会调查并非总是服务于立法,只要在国会两院授权调查事务的范围内,调查就是合法的。目前,国会调查用以实现一系列重要目的,包括确保行政服从立法目的,提高政府效率、有效性以及政府对经济的运营,评估项目实施,阻止行政机构侵犯立法权与立法特权,调查被指控的恶劣行政、政府的专断、任性、滥用、浪费与欺诈行为,评估机构与官员管理与执行项目目标的能力,评估立法的新需要,审查与决定财政优先事项,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告知公众有关政府如何履行其公共职责。只要属于国会授权调查范围内的事务,调查就符合目标。实际上,调查委员会一旦获得授权,确立了调查的管辖与权威,根据被授权调查范围内事务的相关性,调查范围是持久和广泛的。
最后,宪法未予禁止。由于调查势必披露个人资料和信息,根据权利保障原则,调查须在服从于立法目的的前提下,在国会参众两院授权调查事务的范围内进行,禁止为了披露本身而披露。调查自身不能成为目的,它必须与国会的合法任务相关。
修正案赋予个人的正当权利用来限制国会针对个人的调查,纯粹曝光他人私事的调查是不被允许的,法院认为,就“就国会功能而言,国会没有在缺乏正当性的情况下披露个人私人事务的普遍权力,国会也非法律执行和审判机构”。在1953年的UnitedStatesv.Rumely一案中,法院申明了三点:第一,需要查明国会授权调查的范围;其二,须在国会授予的调查权与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与出版自由之间进行平衡;其三,法院在无可回避的情况下有权决定国会权力的界线,避免减少第一修正案确立的保护。该案被告Rumely是一个名为“立宪政府”组织负责销售特定政治倾向书籍的秘书,国会“调查院外集团活动委员会”要求他披露购买大量书籍并予分发者的姓名,Rumely予以拒绝,委员会提起指控,国会对他课以罚金和监禁。法院明确了国会调查权的范围,认为国会授予“调查院外集团活动委员会”的权力与第一修正案所确保的言论与出版自由形成竞争,在此情况下须予权衡。国会对被告课以罚金和监禁的行为侵犯了被告的言论与出版自由。法院谨慎地阐明了自身立场,认为这是一个严峻的宪法问题,只有在不可回避的情况下才适合由法院裁决。在此之前,法院有责任避免标明国会权力的界线或者去除对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认为只有通过这种自我限制,法院才可能避免伤害那些遵守的但偶尔背离的所信奉的原则。
二、双重机关权限争议:权力分立
依据权力分立原则,各国家机关权力不得相互干预,调查权与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有一个适当的界限问题,这在理论上属于机关权限争议。
由于个案裁判中判断各种权力的边界是法院的职责,这在客观上又引发了法院与国会及行政机关的权限冲突。
(一)行政特权(ExecutivePrivilege)
调查权与行政权有一个适当的界限业已得到公认。美国理论认为,国会调查权与行政权的界限可分为四个方面:第一,行政机关如认为资料的提供有碍于国家利益时,均得拒绝;第二,有关军事和外交上的机密,得拒绝回答或提供文件;第三,根据三权分立的精神,得以“行政特权”宣布其为机密或根本拒绝接受调查;第四,凡非大众关切之事项,皆可不认为国会所应调查者。
日本国政调查权与行政权之界限,不论独立全能说或辅助全能说,均一致认为国会得借调查权之运作而对内阁行政权享有广泛之监督批评权能,惟仍需恪守日本宪法上的三权分立原则,故国会对于调查行政机关行为的合法性、妥当性之际,却不得径行撤销、停止行政处分。
针对国会调查,美国总统提出了行政特权这一概念,用以对抗国会调查与法院命令。在此情形下,判断何为行政特权是法院的任务。法院须综合各种因素判定何者构成行政特权,以此确立调查权的界限。
作为美国法上的一个概念,行政特权既可以作为判断国会法律是否侵犯行政权的标准,也可以作为抵制国会调查权的有力手段。虽然该权力很早被前几任总统包括华盛顿、杰佛逊行使,但并未形成一个确切概念,法院从未对此作出清晰的界定。美国着名政治科学家罗奥尔·伯杰(RaoulBerger)在其着作《行政特权:
一个宪法之谜》中指出,行政特权是“总统利用其宪法职权拒绝向国会提供情况的一种权利,是总统在履行义务时必不可少的法律手段”。总统可以通过签发行政命令的形式,禁止任何政府职员接受国会调查委员会的质询。在2009年的HouseCommitteeontheJudiciaryv.Miers.一案中,瑏琐法院重审国会获取信息的广泛权力及实施该权力的办法,驳回总统的行政特权主张。在该案中,总统主张行政特权,授权绝对出庭豁免,免于前总统助理在委员会出庭回应传票。在该案的裁决中,地区法院支持国会向前总统助理签发传票权。针对行政机关主张该案不得在法院受审,法院确立了自身管辖权,承认国会具有双重诉讼资格或者诉权,及基于宪法第一条有关“调查权”的默示诉因。法院总结道,“毫无疑问,国会有权———来自第一条的立法功能———发布并且执行传票,以及(获取)符合该传唤目的信息的相应权利”。法院裁决被传召的官员应作证,特定文件应予披露,政府的上诉应予撤回,地区法院的意见应予支持。
在1974年的UnitedStatesvNixon一案中,尼克松使用行政特权这一概念对抗独立检察官的调查及法院的命令。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WarrenBurger)代表法院作出了三项判决:第一,特别检察官有权对总统提起诉讼;第二,行政特权保护的内容须涉及国家军事和安全机密,但当这些磁带被视为犯罪证据时,不受行政特权的保护;第三,有关宪法争论,法院负有最后的责任,总统交出的材料是否与调查罪行有关非由总统来决定,而是由法院来决定。
该案不仅涉及调查权与行政权的关系,还是一个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竞争问题。在确立何者构成行政特权,最高法院颇费周折,其论证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包括方法、原则与战略的转变。法院须对三方面问题予以判断:首先,何为行政特权?行政特权的具体内容包括哪些?其次,行政特权与司法权之间的界线何在?最后,谁有权决定何者构成行政特权?
第一个问题包含了肯定与否定两方面内容。在行政特权提出之后不久,部分法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核心职权”一词。从肯定角度而言,行政部门的核心职权包括宣战、掌管外交权和否决权。布伦南认为,虽然核心职权公式有些含混不清,并可能被扩大使用范围,但只要将含义限定在外交、军事和国家机密的范围之内就没什么害处。从否定一面来看,需界定何者不属于行政特权,这关系到总统主张的保护范围。法官认为,谈话内容既已成为犯罪阴谋的一部分,就不应该受到行政特权的保护”,总统主张的录音带包含国家秘密的理由就不能成立。至于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线,首席法官认为既然本案关系到行政与司法部门的竞争,那就要进行权衡,弄清每一个部门的核心职权。行政部门的核心职权包括宣战、掌管外交权和否决权,司法部门的核心职权之一是为了保证进行刑事审判,要能够取得一切证据。
最后一个问题涉及谁有权决定何者构成行政特权。该问题有趣而微妙,法院在多个调查案件中申明自身谨慎但无可回避的判断权限和职责。因为行政特权不仅仅是行政部门用以对抗国会调查权的凭借,在个案中将转变为政府需要和法院职责之间的平衡,法院不得不面对行政部门对自身管辖权的质疑。由于首席法官最初将问题定位于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竞争上,判定何者为两种权力的核心成为一个问题。斯图尔特在撰写意见书的过程中转移了视线,将行政部门与司法部门之间的平衡转变为宪法问题。他不喜欢“核心职权”一词,认为这一概念过于笼统、宽泛,将成为总统为自己辩解的借口。除了包括首席法官提到的宣战、外交和否决权,行政特权还包括总统“在他的宪法作用的核心履行职责”所应有的什么职权。“这恰好是尼克松的要求。尼克松正是根据这样的广泛定义来对抗传票的。这类言辞可以支持尼克松所作的辩护。”
斯图尔特改变了论证的逻辑,用正当程序概念取代了“核心职权”一词。根据宪法,权利法案的第五条、第六条都规定须用证据确保正当程序与公正审判。“在公正处理刑事案件审判中必须按照正当的法律程序,这就需要证据”。如此,尼克松的要求成为直接与宪法规定的权利法案、实行法治的义务及正当法律程序对立起来的概念,行政特权遭遇宪法挑战。斯图尔特甚至据此认为,“首席法官只迷恋于根据法律进行审判”,“极端缺乏对基本宪法问题的关心”。
这一论证原则最终体现在首席法官伯格代表法院发布的意见书中。伯格援引马歇尔大法官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所阐明的观点“阐明法律完全是司法部门的职责和责任”,法院有权决定何者构成行政特权,这是“一项无法与行政部门共享的责任”。
(二)正当程序与公正审判
调查权与司法权的关系涉及国会在授权范围内对司法权的调查应在何种限度内进行。美国关于调查权与司法权的界限可分为三方面:第一,批判判决之调查。对判决的批判不可避免地涉及司法独立,可能影响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不得对指挥诉讼等法院活动加以调查或评论。第二,有罪探索之调查。为了达到违反法律加以起诉的目的而收集证据的行为不属于议员的权限。如果调查的目的在于针对个人的有罪探索,法院如已做出判决,则其调查无效。第三,议会与法院就同一事实并行调查。如果具有适法之目的,对于事实之调查,如系争之问题为司法部管辖内引起的,国会可就同一事实并行调查。
鉴于调查权与司法权的界限属于机关权限争议,根据权力分立原则,须在界定司法权本质属性或者核心职权的前提下确定调查权是否逾越宪法界限,侵害司法独立。何谓司法权的本质属性或者核心职权?法院的工作是审判,包括“审”与“判”两方面。“审”指事实认定,“判”指在认定事实的基础上适用法律予以裁决。正当程序为司法权的核心,排除在调查权范围之外;司法独立应为法官在依据程序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过程中经由独立判断形成的内心确信,如果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没有违反法律程序,其所认定的事实及做出的裁决须排除在调查范围之内。日本学者认为,“宪法规定的国会调查权须受司法独立原则的限制,且就司法独立的实质内容而言,不仅法官不受其他机关的指挥与命令,还须保证裁判官的法的确信形成自由。”
在U-nitedStatesvNixon一案中,针对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竞争,最高法院的法官达成了一致认识,认为司法部门的核心职权之一是为确保刑事审判而取得一切证据。证据是事实认定的基础,目的是为了保证审判的顺利与公正。实践中,美国法院在判例中确立了司法“核心职权”的判断标准,认定只要能合理推定具有妨害倾向的行为构成对审判独立的侵害。
在1929年的Sinclairv.UnitedStates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使用严格标准审查国会对法院的调查行为。原告HarryF.Sinclair与另一人Fall被指控共谋欺诈,在该案审理过程中,Sinclair等人指控组成陪审团的12人中有一名陪审员存在不当行为,并雇用侦探对一些陪审员和他们的亲人、邻居与朋友进行监视和调查,该案被判定陪审员的审判无效。上诉法院判定Sinclair等人妨害该刑事起诉的司法正当进程,应判处蔑视法庭罪,当事人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Sinclair等人辩护的主要事实与理由是:第一,自己被政府派出的代表监视,陪审团受到了政府施加的影响;为了发现不法影响的行为,将陪审团置于观察下是合理而正确的;公民与政府享有同等监视他人的权利与特权。
第二,Sinclair等人从未意图接触陪审员或干涉陪审员的意见,陪审员也表示没有感到被跟踪或监视。法官否定原告的辩称,认为私下调查会破坏法院自我保存的权利,跟踪行为无疑侵害了司法行为的忠实与公正。陪审团作为法庭必要部分具有重要的职能,是判定罪行成立与否的主体,能够平静地通过获知事实作出判断是扞卫法律所必要的。如果允许私人侦探跟踪,陪审员将失却平静并使法院保护自身的权力变得软弱无力。
判决依据司法规则(JudicialCode)第268条规定的“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手段妨害审判独立”,法官在判决中援引了ToledoNewspaperCo.v.UnitedStates一案的先例。在该案中,一个发行量很大的报纸对审判发表了干扰言论,虽然法官或陪审员并没有看到该报纸,但法官最终判定该报纸妨害审判公正,理由是报纸的评论具有妨害司法公正的行为倾向。
法官在本案判决中提出一个关键性问题,即“错误行为”与“干预结果”何者作为标准来判定是否违法?法官认为,行为倾向即为标准,是否对陪审员构成了实际影响并非必要要件,并据此判定本案的调查人员有罪。该案明确了何者构成审判独立的认定标准,即能够合理推定具有妨害倾向的行为即构成对审判独立的侵害。
前述两个案件的意义在于确立了“合理推定具有妨害倾向的行为”作为界定司法核心职权的公式,明确了司法独立是否受到侵犯的司法判断标准。所谓妨害倾向,是指调查行为可能对审判公正产生不良影响。
根据调查权界限的一般理论,目的正当是判定调查权运行合宪与否的重要根据。就调查权与司法权的关系而言,任何影响法院公正审判的调查行为应被视为超越界线,构成对司法独立的侵害。法院审判活动的核心在于“审”和“判”。前者认定事实,后者适用法律,两者俱属于司法的核心职权,不容干预。在第一个案件中,雇佣侦探调查陪审员行为已经危及司法独立之“审”即事实确定。根据美国的司法制度,陪审员负责认定事实,法官负责适用法律。完整的审判是由陪审员认定事实与法官适用法律两部分组成的,跟踪与调查陪审员无疑可能影响法院确定事实之公正性,危害“司法独立”。在第二个案件中,在案件未审结之前,报纸对案件的评论亦有可能影响法院事实认定,有危及司法独立的倾向。
日本浦和充子案提供了判断司法核心职权是否受到国会调查权侵犯的实际例证。1948年,在东京浅草一家小吃店工作的已婚女子在杀死三个女儿自杀未遂之后自首,检察机关以杀人罪起诉充子,东京浦和地方法院以杀人罪判处充子有期徒刑3年,缓期执行5年。检察机关未提起抗诉,充子杀人案正式结案。
日本国会参议院法委会认为浦和地方法院对充子杀人之罪判处乃量刑过轻,是受子女为父母财产传统观念影响的轻视人权行为,实属不当,传唤主审法官牛山毅等案件相关人士展开调查。1949年3月30日,参议院法务委员会发布关于浦和充子案件的调查报告,报告对案件的事实认定与量刑均作出干涉。日本最高法院表示强烈异议,认为参议院法委会对刑事案件的调查,超出了《宪法》第62条规定的国政调查范围,属违宪行为。参议院认为,“国政调查权是基于国家最高机关的性质而为的,对司法权亦具有监督权”。
学界认为,出于维护宪法规定的司法独立之需要,国政调查权在司法权领域的行使应受限制,尤其应禁止如下三种调查:第一,如果调查的唯一客观目的在于探查个人的有罪性,由于此种调查不在调查权范围内,所以不得实施;第二,不论是判决确定与否,如果调查会对法院判决造成批判,即使出于立法等目的,由于侵害司法独立,原则上不得实施;第三,如果调查涉及法官判决案件过程中的诉讼指挥,由于侵害司法独立,也不得实施。
日本学界维护司法独立的批评只是对美国理论的重复,最高法院的推理更加切合司法权的本质,与美国法院确立的审判独立的司法判断标准较为接近。因为无论是对个人的有罪探查,还是对量刑轻重的批判,均触及审判权的核心,是对司法独立原则之违反。“日本宪法规定,只有二审的高级法院有权决定地方法院的事实认定或量刑正确与否,别的国家机关不应进行任何干涉”。
最高法院认为这是一种宪法破坏,理由是“如果国会拥有对判决进行这样事后审查的权限,对最高法院作出的判决正确与否也可进行议论,极端情况下,国会对事关宪法的最高法院判决的再审查也将可能。这不是宪法的破坏又是什么呢”前述分析表明,国会行使调查权的范围必须适当。就浦和充子案本身而言,鉴于事实认定与适用法律量刑是法院的责任,判定当事人有罪与否、罪刑轻重是独立审判之“判”的核心内容,不属于调查权的范围。调查权固然是国会的宪法权力,司法独立亦为日本宪法的一项原则。当相邻两项权力发生竞争时,须不得影响各自权力之本质。参议院法务委对刑事事件的调查,是逾越国会调查权范围的违宪之举。
三、个人权利保护:利益平衡
调查需要证人出庭作证,交出文件,对个人基本权利进行限制。在针对个人的调查中,一方面需界定调查权的范围,另一方面需认定调查权是否逾越界限,过度侵害个人宪法权利。私人事务受宪法保障,保障国家安全,阻止暴力或武装颠覆属于政府的正当利益。
法院需在个人事务与政府需要之间进行权衡。在调查中,下列权利属于国会的界限:不得自证其罪、言论与出版自由、文件搜查与扣押、质证,及隐私权等。前几项权利属于美国权利法案明示的权利,涉及第一、第四、第五和第六修正案。隐私权并非宪法的明示规定,而是一项普通法上的权利,即法院在判例中创制的个人宪法权利。
(一)不得自证其罪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该项权利并非绝对,在适用并制约调查权的行使的同时,又受到调查权的限制。国会可以强迫证人作证或者出示证据,否则调查权就失去意义。最高法院肯定国会对拒绝作证的当事人课以藐视罪的权力,认为宪法已赋予国会该权力。在1821年的Andersonv.Dunn一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当事人自愿提供的信息并不总是准确完整的,因此采用一些强制手段来获取必要信息就是必要的”。1857年的国会法案将藐视国会认定为一种轻微刑事罪行,由联邦法院进行审理,这是对普通法上藐视罪的一种补充。1978年的政府道德法案赋予参议院及其委员会可以在哥伦比亚特区地区法院使用民事强制传唤的权力。该权利在对抗国会强迫证人作证过程中包含以下几点:
首先,该项权利的主体受到限制。不得自证其罪在本质上是个人的,只适用于自然人,不适用于法人,公司、合伙、工会和其他人为组织不能主张改项权利。其次,援引该项特权不需要特殊的言辞关联。证人既不需要作出特别的言辞表示,国会也不需要告知证人第五修正案的权利,只要提及第五修正案就可以认为证人主张该权利。如果不确定证人是否事实上援引该特权拒绝回答,国会应指示证人阐述反对回答的原因。第三,宣称该特权须基于对自证其罪的合理担心。国会可以质疑证人宣称该项权利的有效性,但却不能要求证人阐述其所担心的事情在刑事案件中所产生的准确后果。第四,证人可以放弃该项特权。第五,国会可以授权证人刑事豁免,强迫证人作证。国会可以免除证人证言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刑事后果,不得作为自证其罪的言辞证据。
(二)言论自由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诉冤请愿的权利”。调查权属于国会在授权范围内的正当行使,个人权利受宪法保护,如何容纳竞争的两个宪法原则是法院的职责,法院需在个人权利与国家利益之间进行衡量。调查权对公民第一修正案权利的限制须依据正当程序。
实践中,第一修正案与调查权的关系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在涉及第一修正案问题时,法院给予证人的权利是相对的,而非像第四修正案那样是绝对的。法院认为,涉及第一修正案的国会调查永远是一个在私人与公共利益的衡量问题,须视具体情形而定。在1959年的Barenblattv.UnitedStates一案中,法院进行了利益衡量,认为如果政府利益明显超过个人利益,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利就并未受到侵害。
法院一旦认为在特定情况下政府利益优于个人利益,个人就须作证或提交相关信息。第二,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是不确定的。如何平衡取决于法院在特定案件中对个人隐私与国家获取信息需要之间的权重。法院强调调查权的需要、国会授权调查的范围及国会立法目的。实践中,法院从未依据第一修正案推翻国会确定的藐视罪,但法院严格解释委员会的授权范围以便回避抵触第一修正案,支持援引第一修正案的证人回应州立法委员会的质疑。
第三,国会回避牵涉第一修正案。言论与新闻自由是美国社会最为敏感的问题,国会在调查过程中如有涉及第一修正案,往往采取回避的办法,以免引起更大的政治风暴,具体做法是尽量不对拒绝作证的当事人课以藐视罪。第一个例子是1976年国会道德委员会对情报遴选委员会最终报告草案泄漏事件的调查。被泄漏的草案包含遴选委员会长达一年对CIA及其他情报团体的组织、运行及监督情况,不确定是否公布的秘密信息,及对CIA背叛行为的讨论等。国会道德委员会向四个媒体代表发出传票,其中包括DanielSchorr,认定DanielSchorr从遴选委员会成员中获取该报告的复印件并予公开。虽然道德委员会认为DanielSchorr公开报告的行为没有顾及国会禁止公开涉及国家安全的高级秘密信息属于蔑视,其公开报告的行为应受指责,但却拒绝对其拒绝披露信息来源的行为课以藐视。第二个有关第一修正案的争端是特别小组委员会对国会州际和对外贸易委员会的调查。调查宣称名为“thesellingofthepentagon”的电视新闻纪录节目产品中使用了欺骗性的镜头编辑。在调查过程中,委员会传唤了CBS的总裁FrankStanton,命令他向小组委员会交出与节目有关的“不适用的镜头”。FrankStanton拒绝提供传唤所要求的材料,小组委员会一致投票藐视传唤,委员会全体成员建议对FrankStanton课以藐视罪。经过广泛辩论,下院拒绝采纳委员会的报告,而是投票让委员会重新决定。若干成员担心批准藐视将会对媒体引起可怕后果,不合宪地将政府卷入到对媒体的规制中。
最后一个例子是1999国会对托马斯提名最高法院法官的确认听证。一位女教授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秘密宣誓,指控提名人对她实施了性骚扰,秘密宣誓泄露给国家公共电台的记者NinaTotenberg。确认通过之后,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命令参议院有关规则与行政委员会任命了一个独立顾问小组负责调查泄漏的来源。顾问小组传唤了NinaTotenberg,NinaTotenberg宣称根据第一修正案记者享有特权,拒绝传唤。顾问小组建议参议院委员会课以藐视罪。负责裁决特权主张的主席和少数高层拒绝了这一要求。主席认为课以藐视将会对媒体产生可怕的后果,且可能当需要打开更多门时却关闭了一扇门。其他高层成员认为没有法律先例处理在第一修正案确保的媒体自由与国会强迫作证与根据调查权获取文件的固有权力之间的明显冲突。这些例子一方面说明国会不愿意揭发媒体,另一方面说明国会承认记者的宪法特权。一些学者认为该领域记者特权的理论基础是不正确的,即使该特权的基础有效,它们也不会重于政府在国会调查中的利益。
(三)文件扣押与正当搜查
美国宪法权利法案第四条规定:“人民保护其人身、住房、文件和财物不受无理搜查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非有合理的根据认为有罪,以宣誓或郑重声明保证,并详细开列应予搜查的地点、应予扣押的人或物,不得颁发搜查和扣押证”。第四修正案用以对抗国会过于宽泛的不合理传唤。国会获取和扣押文件的传唤必须是为了正当立法服务,或者与监督相关联。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法院给予国会该领域的宽泛权威。第二,证人负责拒绝传票的证明责任。最高法院认为,传票范围的充分或者过度因调查性质、范围与目的而异。传票的描述须使申请人确知何仲特定文件是需要的,并做出相应选择。如果证人有合理理由反对国会传召,不能服从国会提交文件的要求,证人须提出根据。法院认为:“如果申请人对传票所要求的文件有所怀疑,或发现它是不公正的负担,或发现其所要求的文件与调查无关,如果可能,证人有权并且应该建议小组委员会何处可以便捷地补救”;证人不能提交文件不能被课以藐视罪。第三,第四修正案是否适用排除规则是不确定的。排除规则适用于国会调查权依情形的精确事实而定,国会调查委员会命令扣押的不合法文件不能在随后相关的刑事指控中被认定为证据。如果国会通过另外一个调查机构不合法的文件扣押,并且发出了传唤,该传唤是否有效并不明确。
(四)质证
美国权利法案第六修正案规定:“与原告证人对质;以强制程序取得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并取得律师的帮助为其辩护。”在国会调查中,国会寻求信息和证人保护其隐私权之间始终存在着潜在的利益冲突。德国国会自身也曾滥用调查权,严重损害了公民的自由权利。早期由于国会调查是在一种没有电视传媒宣扬的相对低调的氛围中进行,经常允许证人召唤其他证人和对反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证人的权利受到侵犯。
(五)隐私权
隐私权属于美国法院的创制,是个人一项普通法上权利。在针对个人的调查方面,普通法上的隐私权是限制国会调查权的重要手段。在1880年的Kilbournv.Thompson一案中,法院强调国会无权要求个人公诸个人私事。强迫个人就有关个人隐私的事项作证属于司法权力,而不属于立法权力。在其后的Sinclairv.UnitedStates一案中,法院认为一旦个人事项关乎合法的国会调查时,则不属于隐私。
四、借鉴与启示
调查权属于权力机关行使的一项宪法权力,人权保障与权力分立原则要求该权力须在一定范围内运行。虽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基础不属于三权分立,但宪法规定权力分工,保障公民各项基本权利。我国各级权力机关在行使调查权的过程中,亦须在服从目的正当的前提下,在宪法和法律规定及各级人大常委会授权范围内从事调查,既不得超越授权范围,亦不得从事宪法禁止事项的调查。
根据权力分工原则,立法机关的调查不得侵犯其他国家机关的核心职权,包括行政、法院与检察机关的职权。属于行政职权核心的军事、外交等涉及国家安全的事项不属于调查权的范围,影响法院独立审判的正当程序应排除在调查权之外。由于制度差异,美德等国将检察机关作为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调查权之于行政权的界限适用于检察权。根据我国宪法,检察机关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各级人大调查权亦不得触及检察权的核心,影响检察独立。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人身自由、住宅自由、人格尊严等基本权利,各级人大在调取文件档案、要求证人出庭作证过程中不得非法扣押公民文件、搜查公民住所、泄露公民个人隐私,以及强迫公民自证其罪。
为确保各级权力机关运行调查权的同时其他国家机关权力正当行使及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我国可参照美德等国的《藐视法》,在适当之机制定单行法律,完善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议事规则,明确调查权的宪法依据、目的、范围、程序、界限、法律责任等,具体化宪法调查权的内容,确保调查权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序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