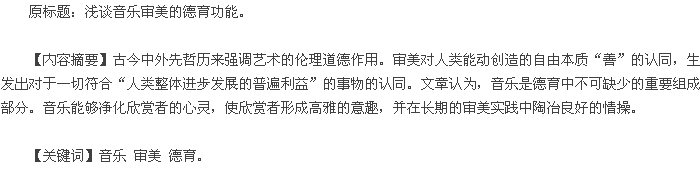
中国艺术历来强调伦理道德的作用,认为音乐“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也倡导“音乐净化论”.音乐的本质是一种有自己特质的审美事物。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美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创造活动及其成果对人的自由的肯定形式,美感则是对这种自由的感性直观所引起的一种特殊的精神愉快。”①同时,人类的实践都有一定的社会目的,只有这种社会目的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利益相一致,才具有客观历史的价值,这样的目的性的活动才是善。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美既然是一种人类生活的感性的实践创造,是一种对人的自由的肯定,它就不可能脱离善。正是对人类能动创造的自由本质之善的认同,生发出对于一切符合“人类整体进步发展的普遍利益”的事物的认同,欣赏美的和谐而追求社会的和谐,美之善与道德之善汇同一体。因而,先哲们认为音乐要美才可达善,要用音乐之美去陶冶欣赏者的情操。音乐审美性的本质是其能够作用于欣赏者道德领域的根本前提。
毕达哥拉斯学派之所以认为音乐能够促进“灵魂的净化”,是因为“声音在灵魂中得到反响,灵魂与声音是和谐一致的,就像两个并排而立的竖琴一样,弹拨其中一个的时候,另一个便会发出共鸣”②,这就是“情感的方式”.当欣赏者被音乐所感动的时候,音乐中的内在气质、高尚境界与欣赏者的心灵发生碰撞,欣赏者的灵魂便会由感化而达到净化。但要加上一个前提,即这个“声音”必须是审美的、情感高尚的,并且是为欣赏者的审美经验所接受的。音乐中所表现的情感可以满足欣赏者的期待,给予欣赏者希望,以其所充盈着的博爱之情平复没有爱的非道德的不平衡心理。
音乐艺术由于是审美的,所以使欣赏者生理上的舒适感与心理上的满足感相互交融,从而达到身心的和谐与平衡。这种满足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娱乐,还是对情感韵味的感动,对精神哲思启迪的震撼。而恶常常是生发于人没有满足、缺少爱与冷漠无情的状态下。
《美学与社会犯罪》一书引证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观点认为,人生而自由,但这种自由却必然受到社会的限制,人的欲望无限,但社会只能有限地满足人们的欲望,它是有条件的,“正是这种自由与必然、有限与无限的历史性冲突,导致了犯罪的发生”.③而审美关心的是事物的形式,不触及占有利害关系,不关心功利内容,审美活动能够在其所创造的美的理想境界中帮助人与社会达成协调,人们在审美的想象中平复身心的欲望,承载着社会规范的理智与追求个体需要的意志在美的氛围中和谐统一,于是“人人都可能犯罪,人人都需要审美”.②从这种意义上讲,美能生善。而这也并非绝对,需要主客体之间的互动沟通,并且是长期的互动。
欣赏者在欣赏音乐时所选择的总是对自身来讲具有审美新鲜的音乐,即在欣赏者审美经验范围内的作品。在“审美饱和”之前,音乐对于欣赏者具有吸引力,其所认同的有价值的音乐能够自然而然地激发起他们内心的某种冲动或某种情感。而“审美饱和”一旦产生,欣赏者便会选择新的音乐作品。在这种主客体之间的长期互动下,音乐能够潜移默化地陶冶人的情操也便具有了现实意义。当然,欣赏者选择什么样的音乐,钟情于什么样的音乐,能够与何种音乐达成共鸣,与其个人文化修养、音乐素质、生活经历、审美趣味等多种因素有关,“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同时,音乐是否能够陶冶人的情操还要看欣赏者选择何种欣赏方式,如果只是作为消遣,而不用音乐性的思维去体验它的形式美,那么音乐只能够让欣赏者神经放松、消遣娱乐,或许至多能够暂时达到让欣赏者举止平和,却与修身无关。一个热爱生活、热爱美,渴望寻求音乐所带来的精神满足的人,必将会在长期的审美实践中陶冶出良好的情操。
既然音乐的审美性如此重要,作为高雅音乐的创造者与传播者--作曲家、演奏家应当担当起提升人们的审美趣味与精神境界,缔造人类精神文明的历史使命。作为欣赏者,应当主动提高自己的审美趣味与艺术修养,追求审美的人生,力求成为具有健全人格的人。
而娱乐刺激都是一些浮光掠影的低级趣味,如泡沫一般最终留下空无一物。审美才是人类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人人都需要审美。
音乐是德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蔡元培所倡导的“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所谓“美育”,就是通过各种美好的事物对人进行熏陶,以达到“诗意的人生”.美育的最终结果无不渗透包含着德育。在音乐欣赏中,欣赏者应当力求在音乐作品的选择上将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起来。要使音乐与欣赏者的实际生活相结合,把美的音乐渗透到生活中。音乐欣赏要使欣赏者的情绪体验与逻辑思维相结合,使欣赏者在接受审美享受的过程中,激发出高尚的情感。
音乐教育既要挖掘深刻的艺术内涵,又要让欣赏者了解音乐表现的技能和技巧,从而使欣赏者成为意趣高雅的人。
参考文献:
[1]陈炎,李有祥。审美与犯罪--一种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J].宝鸡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7)。
[2]许可。试论党报公益广告的真善美[J].中国报业,2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