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拟剧论是欧文·戈夫曼社会学的重要构成, 它包含表演、剧班、区域、不协调角色、角色外沟通和印象管理等六大要素。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 戈夫曼对拟剧论作了结构性微调, 淡化剧场的隐喻和行动者作为操控者的形象, 并对阐释社会世界的拟剧论持保留态度, 将它视为权宜性的认知工具。学术界对拟剧论通常存在三种误解:在本体论层面, 将戏剧等同于现实;在认识论层面, 认为拟剧论是一种保守的理论, 并将面对面互动视为零和博弈;在方法论层面, 将拟剧论视为诠释社会生活的唯一视角。这些解读均有失偏颇, 对戈夫曼而言, 拟剧论既是隐喻, 也是对现代性的另类批判, 同时亦构成分析日常生活的独特视角, 它呈现的微观系统并不乏道德感和互动仪式。
关键词:欧文·戈夫曼; 拟剧论; 印象管理; 自我; 道德;
作者简介: 王晴锋, 男,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南亚社会研究。;
收稿日期:2019-05-31
基金: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齐美尔以货币哲学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秩序观及其对当前社会整合的启示” (项目编号:TJSR17-005);
Constitutions, Misinterpretations and Morality of Goffman's Dramaturgy
Wang Qingfeng
Institute of Global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Dramaturgy is the main content of Goffman's sociology, which includes performances, teams, regions, discrepant roles, communication out of character and impression management.In the late 1950 s, Goffman adjust the structure of dramaturgy:weaken the drama metaphor and the actor's image of manipulator, meanwhile have reservations to the dramaturgical explanation of social life, just treated as a temporary tool.There are three misunderstanding of dramaturgy:ontologically, regard drama as reality;epistemologically, regard dramaturgy is conservative and see face-to-face as zero-sum game;methodologically, regard dramaturgy as the only explanatory perspective of society.These explanations all are biased.To Goffman, dramaturgy is metaphor, is another way to criticize modernity, meanwhile the unique perspective to analysis social life.The micro-system presented by Goffman has morality and interactional ritual.
Keyword:Erving Goffman; Dramaturgy; Impression Management; Self; Morality;
Received: 2019-05-31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是拟剧论的创始者,他创造了一整套新的术语来探讨面对面互动系统。事实上,社会生活的拟剧隐喻并非戈夫曼所独创,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从莎士比亚到冯德尔(Vondel)等剧作家的文本中,“世界是一个大舞台”的隐喻颇为普遍。戈夫曼的贡献在于第一次将拟剧的隐喻系统化和理论化,并以这种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社会生活。正是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1956年版/1959年版)一书中,戈夫曼提出了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的拟剧论阐释,表明日常互动的重要特征是拟剧表演,对行动者如何进行印象管理进行了精妙的论述。如今戈夫曼的着述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引证来源,拟剧论也成为当代表演理论的思想源泉。与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等社会学家不同,戈夫曼的着作读起来并不艰深晦涩,但由于其表达的意义并不完全表露在字里行间,因而更值得仔细解读和品味,否则对他的理解容易流于表面和庸俗化,忽略其隐藏在背后的真实意图。本文试图重返戈夫曼的经典着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主要探讨拟剧论的构成、前后的结构微调以及人们对它的常见误读,最后阐明拟剧论的道德意涵。
一、拟剧论的构成
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戈夫曼试图发展出一套拟剧论的术语和框架,用于分析人们共同在场的面对面互动。通常而言,一种独创性的理论必须突显其特殊的理论成分,而戈夫曼主要从表演、剧班、区域、不协调角色、角色外沟通和印象管理等六个方面展开论述,这也是拟剧论的六大构成要素,其他还涉及戏剧角色、剧本、舞台和道具等。戈夫曼从情境的角度对“表演”这一核心概念作了宽泛的定义,它是指“既定的参与者在既定的场合以任何方式对其他参与者产生影响的一切活动”[1]15。在论述“前台”这个概念时,戈夫曼又进一步解释道:“我使用的‘表演’一词指的是个体在持续在场的观察者面前发生的所有活动,这些活动将对他们产生某些影响。”[1]22在戈夫曼看来,观众或观察者是以特定的参与者及其表演作为参照点进行表演的。
戈夫曼认为,前台具有一整套抽象的、模式化的期待,它是“拟剧实现”的领域,帮助表演者在既定的互动中传达出他们希望传达的信息。拟剧实现体现了表意性行为与其结果之间存在的沟壑,比如,课堂上的学生为了表明自己专心致志而特意端正就坐、身姿前倾并目不转睛地盯着老师。然而,学生的这种高度专注性的剧场表演本身可能使他无法集中精力聆听上课的实际内容。成功的前台表演需要在剧组和受众之间达成某种共识,即视前台为唯一的现实,否则表演将难以为继。在前台与后台之间还存在“保护性通道”。表演者会采取掩饰、隐瞒和伪装实践,使自我呈现与角色期待保持一致。成功的表演还需要剧班合作,因此,至少在剧班内部,成员之间不是相互欺诈的,他们荣辱与共、合舟共济。观众与演员之间也会默契合作、共同维持表演,在特定的场合,表演者与观众之间还可以互换角色。面子工夫是印象管理的重要形式,人们总是希望在他人的角色期待中呈现出能够胜任和充满自信的形象。表演可能被“理想化”,即与某种文化的一般性规范和价值完全吻合;同时也存在否定性的理想化。由于个体的社会地位大多通过符号表现出来,因此表演者经常出现歪曲地呈现自我的情况,即“误传”。此外,演员还需要与关注对象保持一定距离,以神秘化自己的角色。戈夫曼探讨了四种角色外的表演形式:缺席对待,如贬损性地谈论因缺席而影响剧组凝聚力的听众或演员;舞台闲聊,主要谈论表演的技术问题;剧组共谋以及行为重整等。
印象管理是拟剧论的重要构成,它具体包括三种实践形式。第一,防御性属性与实践,即表演者运用防御性实践保护自己的情境定义。它首先表现为拟剧忠诚,表演者必须接受某种道德义务,对剧班与表演保持忠诚,不会背叛剧班的秘密。拟剧忠诚切断了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情感纽带,通过在后台塑造关于观众的无人性形象,使表演者能够豁免道德与情感的愧疚而进行欺骗,在这种情形下,表演者的道德支持主要来自由表演者构成的共同体内部。其次是拟剧性规训,受过规训的表演者能自我控制、恪守角色,防止在角色扮演过程中出现失礼或过失。他言行谨慎、考虑周到、镇定自若,避免不当的暴露或破坏“运作共识”[1]10,并及时对其他剧班成员的失当行为进行补救和掩饰。拟剧性规训经常表现为表演者的面子管理。最后是拟剧性审慎。慎重的表演者在舞台表演过程中谨小慎微,预先对可能发生的偶然情况有充足准备,包括选择忠实的、受过良好训练的剧班成员和不会制造麻烦的观众以及适时根据现场信息作出调整使表演符合情境定义或预先进行排演等。日常生活中的拟剧性审慎无处不在,例如,当老师接近教室门口时故意放慢脚步,以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重新调整姿态。拟剧忠诚、拟剧规训和拟剧审慎都是剧班成员必须具备的特征。
第二,观众和局外人采取保护性实践协助表演者保全他的表演与情境定义。观众和局外人会主动远离后台区域,当局外人即将进入可能会被视为“不适当的闯入者”的区域时,他会事先通过各种方式(如敲门、干咳等)提醒在场者,从而推迟或阻止这种侵入,使在场者迅速恢复适当的表意性。当互动不得不在局外人面前进行时,局外人会巧妙地表现出不参与或毫无兴趣的表象。作为表演之构成的观众必须遵守一整套复杂的礼仪,如向表演者给予恰如其分的关注和兴致、克制可能造成失礼的言行、避免当众出洋相等。当表演者因失误导致希望塑造的形象与暴露出来的现实之间产生不一致时,观众会机智圆滑地忽略这种失误,与表演者达成合谋以帮助其摆脱困境。总之,观众运用的保护性实践在维持表演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第三,表演者必须对观众与局外人的圆滑得体给于配合才能使协助得以可能,从而使他们施行的保护性措施为己所用,这需要表演者经过一定的训练以及审慎的态度。例如,处于某个物理位置的局外人可能无意中听到谈话内容,但他会刻意表现出忽略和漫不经心的姿态,即表现为“在场的缺席者”。为了协助这种巧妙的撤离性姿态,那些感到可能被偷听的互动参与者会从他们的谈话和行为中省略任何会加重局外人负担的内容,同时泄露出半秘密性的信息,表示他们并非完全不信任表现出“在场撤离”状态的局外人。这种“投李报桃”的互动模式有两个要点:首先,表演者必须对各种示意和线索有着敏锐的感知,因为只有通过这些暗示,观众才能提醒表演者当下的表演无法令人接受,因而必须迅速改变以保全互动情境;其次,即使表演者误呈了事实,他也必须符合误呈的规则,以避免使自己陷于连那些最配合的观众也难以施与解救的窘境。
尽管表演者、观众甚至局外人采用各种印象管理技术共同维持互动的情境定义,但是仍然可能发生各种意外,观众也可能无意中瞥见表演幕后的场景。在这些意外事件中,观众往往能获得比发现各种秘密更重要的经验。总之,社会情境是一个相互监控的场域,生活世界充满着剧场表演和印象管理。角色扮演者躲在各种表演面具背后,一场绝好的表演真假难辨、甚至能够以假乱真。
二、拟剧论的结构性微调
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里大量使用戏剧术语和表演隐喻, 正因如此, 拟剧论世界中的互动参与者往往给人以伪善、造作和欺诈的印象。然而,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有两个不同的版本。1956年, 它的第一个版本由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出版。1959年, 它又同时由英国的企鹅出版社 (Penguin Press) 和美国的锚链出版社 (Anchor) 出版。时隔三年, 这两个不同的版本之间发生了一些细微但重要的变化。1959年的版本不仅在内容上有所扩增, 而且对某些观点作了修正。在1959年版的《导言》中, 戈夫曼增加了关于信息的“给予” (give) 和“流露” (give off) 的区别。互动参与者主动给予信息, 而信息的流露则是无意间表达的, 它是不由自主、无法完全掌控的, 而行动者给予的信息相对具有更大的确定性。这一区别对于理解行动者的动机甚为关键。戈夫曼主要关注个体在互动过程中信息流露的沟通形式, 即“更戏剧性的、情境化的类型, (或者) 非言语的、可假定为非意图性的类型, 不管是否故意策划这种沟通”[1]4。换句话说, 戈夫曼关注的是情境化的个体行动之非意图性过程及其结果。戈夫曼并不是刻意将面对面的互动系统描述为勾心斗角的激烈竞技场, 而恰恰是世人给戈夫曼造成这样的印象。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而言, 拟剧论“并非一种操控他人的策略, 也不是剥削和利用他人的手段, 而是一种真实的沟通行为”[2]533。
在1959年的版本中,戈夫曼还在第一章“表演”部分增加了“真实与造作”(Reality and Contrivance)这一小节。而在全书的结尾部分,又增加了“舞台表演与自我”(Staging and the Self)。同时,戈夫曼对自我进行了更加详细的阐述。对此,菲利普·曼宁(Philip Manning)认为,早期的拟剧论视角隐含着戈夫曼的“双自我命题”,即操控性的自我和表演性的自我[3]341,自我主要呈现为社会互动中的操控性欺诈者。而在新的版本里,戈夫曼修改了原先关于自我的理解,从而试图改变过于强调愤世嫉俗的自我形象。在结尾部分,戈夫曼还将个体分成两个基本的部分,即“作为表演者的个体”和“作为角色表演的个体”。作为表演者,个体是“一位卷入在过于人性的(all-too-human)舞台表演任务中苦不堪言的印象制造者”1。而作为“角色”,通常是作为仪表不凡、风度翩翩的人物,他要表现出表演赋予人物角色的独特精神内涵[1]252。正是由于戈夫曼意识到这两个不同的自我,即“作为角色表演的自我”和“作为表演者的自我”,才使他在1959年的版本中作出重要修正[4],也即从愤世嫉俗和操控性的自我(它无法充分阐释面对面互动的复杂性)转向更具信任和仪式化维度的自我。
虽然这些扩充的内容占全书的比例不大,并且也未改变全书的结构,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戈夫曼关于行动者是见利忘义、自私自利的面具操控者的观点,而重新返回到社会生活的面子、仪式等阐释立场上。大体而言,1956年版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偏重于舞台表演的操控性,它关于“生活是一场骗局”的意味更加浓厚。在1959年版本中,戈夫曼有意识地改变算计性的行动者模型,互动参与者不再是只顾私欲,行动也不再是绝对的以工具理性为导向[5]70。与此同时,原先对拟剧论较为乐观的态度消失了,戈夫曼转而强调“舞台语言与面具终将撕下”以及关于概念性“脚手架”的论述:
宣称“世界是一个大舞台”,这对于那些熟悉其局限性并对它的呈现表示宽容的读者而言,实在是老生常谈,因为他们知道,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轻易地向自己表明不必过于严肃地对待它。剧场里上演的行动是相对人为的幻象,这是被承认的;与日常生活不同,对角色表演而言,它不会发生真实或实际的东西。[1]254
在1959年版本的最后,戈夫曼对拟剧论显示出谨慎的态度,指出它仅是社会分析的其中一种视角,但这并不意味着戈夫曼否定拟剧论的价值。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之前,戈夫曼已经充分意识到并强调愤世嫉俗和仪式信任是日常互动系统的一体两面。在他的博士论文以及之前发表的论文中,戈夫曼已提出关于面对面互动的两种阐释,即强调操控与印象管理、强调仪式和妥协互让。戈夫曼后来仍然不断地回到关于面对面互动的信任这一主题。
概而言之,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的两个不同版本中,戈夫曼从三个方面做了重要修正。第一,他改变了马基雅维利式个体形象,淡化关于剧场的隐喻和行动者作为愤世嫉俗的操控者的片面形象。这种修正不仅质疑了个体是躲在公共面具背后的算计性形象,同时也对阐释社会世界的拟剧论视角表达了保留态度。这一修正体现出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具有能动与被动的特征,也结合了博弈与仪式的隐喻。第二,增加关于自我的论述,自我通过表演成为社会性的存在,并具有强烈的情境性特征。第三,重申拟剧论作为权宜性的认知阐释工具。由于很多学者忽略了这两个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别,导致对拟剧论的理解产生偏差,诸如阿尔文·古尔德纳(1970)[6]、尤尔根·哈贝马斯(1984)[7]90等人对戈夫曼的批评事实上都是基于1956年的版本,并且一直延续着这种先入之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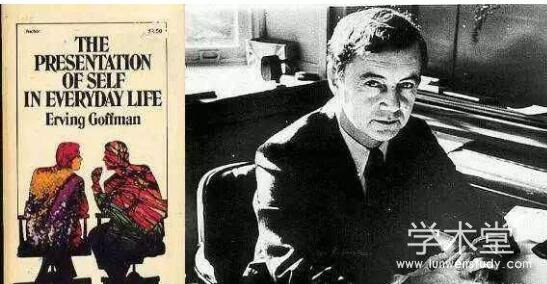
三、对拟剧论的三种典型误读
戏剧既是社会关系的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内容。在拟剧论中,戈夫曼无意像礼仪专家那样指导人们如何举止优雅、言行得体,也不像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那样追溯文明的起源及其进程。确切而言,拟剧论是关于互动的技术性分析。然而,自从戈夫曼提出拟剧论以来,就遭到很多批评和非议。学界对戈夫曼拟剧论的批评可归纳为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个层面,对此,本文分别加以阐述并相应地作出回应。
第一种是本体论误解。这种观点批评戈夫曼的拟剧论过于夸大个体行为的虚饰性或戏剧成分,将戏剧等同于现实本身,拟剧论表述的已经不再是社会现实“犹如”戏剧,而是现实“就是”戏剧。因此,戈夫曼用于阐述社会生活的拟剧论已不是隐喻,而是本体。在这些批评者看来,戈夫曼持“拟剧本体论”的立场[2]533。持此类批评意见的人在用拟剧论解释某一现象时,往往将其还原成戏剧隐喻本身,而不是向前推进社会理论。他们甚至尚未分清楚戏剧与拟剧论之间的区别:戏剧是虚构的,而拟剧论则是一门沟通的技艺。在戈夫曼那里,拟剧论是现实生活的极端表现形式,它通过角色扮演将现实世界与舞台世界相比照。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扮演着不同的人物角色,并通过剧本化和社会化将这些角色内化,这正所谓“戏如人生、人生如戏”。然而,舞台戏剧仅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呈现形式,它并非事实的全部。戈夫曼曾举例美国中产阶级的女孩跟男友约会时会故意表现得笨拙不堪,他借以说明女孩的表演并非完全是她个人的诡计、矫揉造作或欺骗,而是按照“年轻的美国中产阶级女孩”这一社会身份所隐含的价值观行事,并且她的男友、她自己以及周围其他人都认可了这一行为表现方式。类似地,戈夫曼在探讨角色外的沟通行为时指出,“剧班表演并非对情境自发地、即刻地反应,它并非倾注了整个剧班的精力,也没有构成他们唯一的社会现实”[1]207。在《框架分析》中,戈夫曼也对拟剧论的隐喻进行了纠正,称“并不是整个世界都是舞台[8]1。也就是说,舞台表演没有穷尽所有事实,它还有“未上演的事实”,即个体属性之外的社会特征。
第二种是认识论误解。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认为戈夫曼早期的论着将面对面互动视为零和博弈,或是充满欺骗性的表演。行动者通过表演、印象整饰操纵他人的感知,从而制造某种印象,表演的旨趣始终是自身而非他人[9]171。从这种观点看来,拟剧论呈现的现代人是缺乏是非观念的骗子和道德商贩,他们阴险狡诈、唯利是图。哈贝马斯亦将戈夫曼的行动者理解为投机取巧、虚情假意的行为操控者[7]90。总之,在这些批评者看来,日常生活是一场骗局、一出戏剧,戈夫曼描绘了一个尔虞我诈、人人自危的现实世界。因此,戈夫曼被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进而将他关于人类行为的有限博弈模型扩展到一切人类行为。另一种认识论误解认为拟剧论是保守的,它缺乏社会批判意味。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是古尔德纳,在他看来,戈夫曼社会学的这种特征与20世纪50年代消极的政治氛围密切相关[6]395。在这一时期,西方社会的个体由于政治淡漠转而注重人际互动中的各种虚饰,在功利主义的解读者看来,《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是如何在现代科层制体系下生存并获得成功的指导手册。古尔德纳拒绝从社会批判的视角看待拟剧论,但他没有意料到的是,拟剧论以及后来的表演理论会被大量地运用于分析现代政治剧场。在戈夫曼展现的拟剧世界里,表演者为了维持印象而专注于印象管理的各种技术,他们并不关心如何实现标准的道德问题,戈夫曼讽刺地称这些表演者是“道德的贩卖者”[1]251。这实质上深刻揭示了现代性条件下的人性特征。
第三种是方法论误解,它将拟剧论视为戈夫曼社会学诠释生活世界的唯一工具和视角。事实上,戈夫曼很清楚拟剧论自身存在的局限性,这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的开头与结尾部分都有明确的表述。剧场是虚构的和预先精心设计的,并且可以重复排演;舞台上的演员通过扮演某个人物角色与其他演员发生互动,且舞台表演始终有作为第三者的观众在现场,而现实生活并不尽然如此。对戈夫曼而言,拟剧的隐喻仅是概念工具,是建构整个思想框架的“脚手架”。这些概念的脚手架终将被拆除,构成思想大厦的实质性材料是“社会交遇”(social encounter)的结构。
戈夫曼将社会机构视为相对封闭的系统,它们是制度整合在不同事实层面的构成部分。传统意义上将社会机构作为封闭系统的研究包含四种视角:第一,技术性的视角,强调以目的为导向的组织系统实现预定的目标;第二,政治性的视角,强调参与者彼此之间的行动要求和为了实现这些要求而产生的剥夺或赋予特权以及相应的社会控制类型;第三,结构性的视角,强调不同群体之间水平的和垂直的位置划分以及社会关系类型;第四,文化性的视角,强调影响机构活动的各种道德价值,如风尚、习俗、品位、礼仪、终极目标以及对手段的规范性限制等。而拟剧论则构成了这四种分析视角之外的第五种视角,戈夫曼并无意否定其他这些视角。
四、拟剧论的道德意涵
在拟剧论的批评者看来,戈夫曼展现了一个充满博弈的世界,表演背后是操控性的、愤世嫉俗的和谋取私利的自我。他们伪装成自己期望的形象,或躲在面具背后,避免暴露内心的自我。人人都在逢场作戏,人们见到的是虚伪的假象。通过拟剧论的思维方式,现实生活中的个体成为深谙变脸技巧的舞台演员,他们精通包装情绪和内心自我的各种化妆术。古尔德纳尤为批评拟剧论的实用主义逻辑,认为这种逻辑导致只关注外在表象,拒斥一切内在的道德价值。拟剧论将自我的本质表达为纯粹的商品,完全剥去了任何必要的使用价值,因而成为一门“贩卖灵魂的社会学”[6]383。总之,戈夫曼呈现的原子化世界不仅具有浓厚的商业主义色彩,而且还是去政治化的。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拟剧论模型展示了新功利主义的信条,戈夫曼则是“20世纪的边沁”[10]358。还有人认为,作为“模式生物”(model organism)的骗子是戈夫曼拟剧论中自我的方法论根基[11]138。此类批评都片面地将拟剧论视为关于互动的博弈论模型,将个体视为极端理性化和功利主义的有机体。
然而,戈夫曼的拟剧论并不乏道德的维度。很多批评者都忽略了戈夫曼在20世纪50年代初已经形成的关于博弈和仪式的观点,尤其是在《抚慰失败者》(1952年)、《论面子工夫》(1955年)、《论恭敬与风度的本质》(1956年)等论文中均有体现,而《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则是集大成者。在戈夫曼精心构筑的圆形剧场里,作为表演者的个体在他人面前保持体面的言行举止,他们专注于维持这样一种印象,即正在一丝不苟地履行诸多标准,并可以通过这些标准对他们进行评判。然而,作为表演者,个体“关注的不是实现这些标准的道德问题,而是从非道德的范畴出发来图谋正在实现这些标准的令人信服的印象”[1]251。戈夫曼这里说的“非道德”(amoral)是指“道德无涉”或“超道德”,而不是“不道德”(immoral),他是从纯粹技术的意义上来探讨面对面互动。
拟剧论的道德性至少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戈夫曼明确指出面对面互动系统是一个道德的世界。在戈夫曼看来,任何情境定义都具有特定的道德属性,而他关注的正是这种道德特征,“当个体投射出一种情境定义,并对作为特定类型的人作出含蓄或明确的宣称时,他自然而然地对他人施加了道德要求,责成他们重视他,并以像他这种类型的人有权期待的方式加以对待”[1]13。也就是说,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是任何个体有期望他人以适当的方式评价和对待他的道德权利,同时个体应表现得“名副其实”。在这种组织原则之下,个体的情境定义与自我宣称对自身和他人都提出了相似的道德性要求。在探讨维持前后台的区域秩序时,戈夫曼指出这种道德性要求不同于工具性要求,它通常以自身为目的,是“对他人不造成干预或妨害的规则”[1]107,如关于性别规范的原则、尊重神圣场所的规则等。个体倾向于以他人在当下呈现的关于过去和未来的印象之基础上来对待他们,正是在这里,沟通行为被转化成道德行为。他人给予的印象也倾向于以隐晦表达出来的宣称与许诺为基础,而这些宣称与许诺亦具有道德特征[1]249。
另一种道德性是行为导向的, 主要体现在互动过程中的合作、默契与认同等。戈夫曼强调的是行动过程中的表演, 而不是先在的原因或某个目的之实现[12]66。作为印象管理者, 个体不断地通过舞台表演制造合意的形象, 寻求在给予的和流露的信息表达之间保持一致, 从而给他人造成诚实正直的印象。表演行为包括剧班成员之间的合作、观众与演员的运作共识, 由此进一步引申到拟剧论的仪式性维度。如前所述, 剧班的重要特征是拟剧忠诚、拟剧自律和拟剧审慎。也就是说, 拟剧论更多地是表明互动的表意性特征, 而非工具性特征。互动参与者未必都是为了揭露对方行为中存在的不一致, 而是为了共同完成互动任务, 并为此不惜适时作出“临时妥协” (modus vivendi) [1]9。
在戈夫曼的互动剧场里,不管个体的社会地位或角色如何,若要产生正常的人际关系或互动秩序,他都需要遵守互动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关系。每一位表演者被迫“去安排一个(道德和其他)标准正在实现的令人信服的印象,要求它总是在一束固定的、被社会化了的个性的道德灯光中出现……这就是从舞台的各个角度都可以看到的那类人”[13]336。人际行为受施加在社会行动者身上的道德规范的管控,这些规范影响着互动者的自我评估和对他人的评估、情感展示以及仪式实践。因此,戈夫曼的世界不是茕茕孑立、梦魇般的世界,而是有规范、仪式和道德。更何况戈夫曼的行动者处心积虑的不是设法使利益最大化,而是使风险最小化[14]633。概而言之,戈夫曼的拟剧论既具有“尼采式道德冒险家”的特征,也具有“审慎的维多利亚式”风格[15]。
五、结语
本文论述了戈夫曼拟剧论的主要内容,认为拟剧论包含着两重性,它既有博弈、算计的一面,也有仪式、道德与秩序的一面。戈夫曼也因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具有独特的位置,对此,麦克德莫特(R.P.McDermott)和约翰·鲍格(John Baugh)曾如此形象地描述:“如果说社会世界是一场音乐会,那么在关于该世界的描述中,语言学家关注音符与琴弦,人类学家关注评价及其阐释,心理学家关注参与者的思维过程,社会学家关注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学家则关注票房。在这种场景里,戈夫曼关注的是参与者的印象管理和自我呈现”[16]833。通过详细论述日常生活的互动规则与沟通技术,戈夫曼关于互动参与者的一般模型从早期自我中心的论述转向更具普遍性的社会学思想。
拟剧论也可以被视为针对西方现代性文化的一种批判性视角, 诸多批评者事实上未能意识到拟剧论本身具有的这种批判立场。此外, 在当今高度媒体化的现代社会里, “展演性” (performativity) 已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构成。社会理论中关于展演性的探讨也成为重要主题, 从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 的性别展演理论到杰弗里·亚历山大 (Jeffrey Alexander) 的文化社会学等, 都致力于探讨展演性议题, 这也充分体现出戈夫曼社会思想的前瞻性。总之, 将戈夫曼的着作仅仅视为“愤世嫉俗”, 既是肤浅的, 也是不公正的[17]359。诚如兰德尔·柯林斯 (Randall Collins) 所言, 戈夫曼是深邃的, 倘若在知识储备上越是精深广博, 就越能感受到他的才华横溢, 否则可能无法真正进入戈夫曼的意义世界[18]41。
参考文献
[1] GOFFMAN E.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M].New York:Anchor, 1959.
[2] PERINBANAYAGAM R.The 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an Analysis of the Ethnomethodological and Dramaturgical View[J].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974, 15 (4) .
[3] MANNING P.Goffman’s Revisions[J].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989, 19 (3) .
[4] MANNING P.Erving Goffman and Modern Sociology[M].Cambridge:Polity, 1992.
[5] MANNING P.Drama as Life:The Significance of Goffman’s Changing Use of the Theatrical Metaphor[J].Sociological Theory, 1991, 9 (1) .
[6] GOULDNER A.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M].New York:Basic Books, 1970.
[7] HABERMAS J.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M].Translated by T.McCarthy.Boston:Beacon Press, 1984.
[8] GOFFMAN E.Frame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M].New York:Harper&Row, 1974.
[9]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
[10] WILLIAMS S.Appraising Goffman[J].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6, 37 (3) .
[11] PETTIT M.The Con Man as Model Organism:the Methodological Roots of Erving Goffman’s Dramaturgical Self[J].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2011, 24 (2) .
[12] ROBERTS B.Micro Social Theory[M].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 2006.
[13]珀杜.西方社会学[M].贾春增, 李强, 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2.
[14]SCHUDSON M.Embarrassment and Erving Goffman’s Idea of Human Nature[J].Theory and Society, 1984, 13 (5) .
[15] BERGER B.In Frame Analysis by Erving Goffman[C].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6.
[16] MCDERMOTT R, BAUGH J.A Review of“Erving Goffman: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J].Language, 1992, 68 (4) .
[17] FREIDSON E.Celebrating Erving Goffman[J].Contemporary Sociology, 1983, 12 (4) .
[18] COLLINS R.Theoretical Continuities in Goffman’s Work[C].In Erving Goffman: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 ed.P.Drew&A.Wootton, Cambridge:Polity, 1988.
注释
1 原文是“a harried fabricator of impressions”, “harried”有“受尽折磨、苦恼、痛苦”的意思, 而“fabricator”亦有“伪造者、杜撰者”的含义。戈夫曼认为舞台上的表演者身不由己、情非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