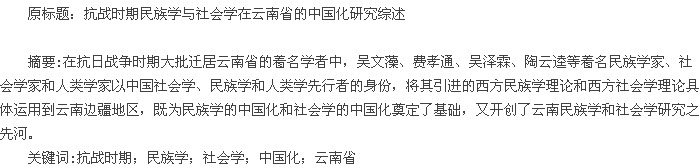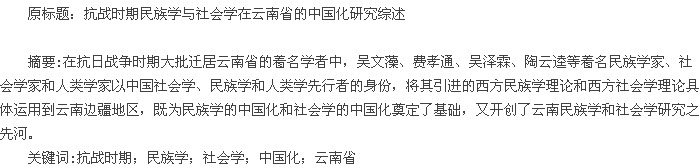
一、引言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就是慷慨激昂而又十分悲壮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满江红》。它是由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罗庸先生用《满江红》词牌所填写的歌词,由联大教师张清常谱曲。这是一曲20世纪中国大学校歌的千古绝唱。它凝聚了中国文人学者、莘莘学子在民族危难时刻最悲壮的呼喊,浓缩了联大文人在国家危亡之际的所有情感和意志。在中国历史上,岳飞的一曲《满江红》已成为历代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慷慨悲歌。罗庸先生感人肺腑的《满江红》则是20世纪文人学者的一曲新的救亡悲歌。联大校歌充满悲愤、激昂之情,历数三校迁移、联合的经历,痛陈国家急难、民族仇恨,表明联大学人坚持抗战的坚强意志,阐明为国发愤学习的意义和必胜的信念。歌词言简意深,曲调雄壮,催人奋进。它以古曲形式来唤醒学子们的民族自豪感,倡导民族的传统爱国文化精神,充分体现出了西南联大文化精神的民族文化特性,对振奋联大师生的精神,激励莘莘学子为国发愤学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当日寇汹汹扑来之时,为保护中华民族文化和教育之精华免遭灭顶之灾,华北和东南沿海的大批高等学府和一些科研院所纷纷西迁。一时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文教大迁徙运动。在这一波澜壮阔的文教大迁徙运动中,有七十多所高等院校迁到西南大后方,其中包括有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内的13所高校迁往云南,并大多集中在昆明。加上抗战前夕由省立改为国立的云南大学,于是,抗战大后方的云南成了当时的中国的文化和教育的中心之一。我国最负盛名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迁居云南省时间最长,长达八年之久,三校联合办校最成功,因此,它是迁滇高校中对云南乃至对整个西部地区影响最大和最具代表性的一所最着名的高校。
2014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对这一特定时期(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特定学者(当时迁居云南省的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特定社会(当时云南边陲社会)所进行的田野调查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课题截取的时段具有典型的意义。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国民政府迁都西南地区,着名高校和重要工矿企业的西迁,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对于整个中华民族都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但一批优秀的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云南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活动和相关的思考,却大大地加速了民族学和社会学两大学科的中国化进程,对于这两大学科来说,这一时期无疑是学科本土化重要的奠基阶段。
正是国难当头的特殊环境,使得许多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着名学者云集云南省,他们主要集中在昆明,推动他们去更深入地接触云南边陲的社会实际(云南农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比较、思索、整理出丰富的材料,提出许多有价值的科学成果和社会工作建议,并使民族学、社会学的“中国化”(即“本土化”)获得大步发展。在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发展史中,抗战时期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堪称民族学和社会学“中国化”的“黄金时期”。
抗战时期迁居云南的一批着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在调查经费短缺、资料匮乏和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迅速展开了对云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语言、民风民俗、社会结构、农业和农村经济、人口、地理等多方面的实地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人员不辞辛劳地在山高林密、人烟稀少的民族地区走访和实地调查。他们风餐露宿,沐风栉雨,跋山涉水,实地调查工作进行得十分艰苦,饥饿劳累自不待言,还经常要提防各种热带病的侵袭,有时还得和土匪交手。就是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学者们坚持不懈,取得了十分突出的调查成果,为人们认识和研究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和文化风貌展现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从而为民族学“中国化”和社会学“中国化”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研究是调查的深化和发展,没有调查就无从研究,没有研究调查便毫无意义。调查和研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对于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实地调查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在抗战时期大批迁居云南省的着名学者中,吴文藻、费孝通、吴泽霖、陶云逵等着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以中国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先行者的身份,将其引进的西方民族学理论和西方社会学理论具体运用到云南边疆地区,既为民族学和社会学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又开创了云南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之先河。
二、学术研究现状
笔者通过查阅国内外大量资料,目前未见国内外学术界有人选择与本课题相类似的题目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并撰写专着。只有有关中国民族学史、近代中国社会学、20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写西南联大、云南省志和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昆明的几本书里零散地、简明扼要地提到了这一问题,也就是说点到为止,由于着述旨趣、切入角度不同,并没有展开阐述,更没有进行全面而系统深入的论述。
1.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教授着的《中国民族学史》上卷第七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族学的发展》比较零散地提到了抗战时期对西南和华南的民族学田野调查,但遗憾的是只点到为止,写得很简单,只是调查成果的简单罗列,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的阐述。至于调查的准备、详细经过、调查方法和得出的结论等问题此书中根本没有涉及。这很可能主要是由于这方面的第一手原始材料很难搜集,再加上这些问题不是此书的重点所致。当然,这方面的第一手材料确实难找,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只发现了一部分这方面的材料,它们散见于众多资料中,查找出来困难确实很大。另外,这些第一手材料由于年代久远再加上当时长期战乱,保存下来的第一手材料很少。当年开展田野调查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绝大部分已仙逝,健在的也属高龄老人,所以要想获得这方面的第一手材料只能象“大海捞针”一样从众多资料中去寻找。但是,笔者对此充满信心。
2.杨雅彬先生写的《近代中国社会学》(上下册)、郑杭生教授,王万俊博士合着的《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此两书比较零散地提及抗战时期社会学家对云南省的社区调查和这一时期的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但也写得简明扼要,由于着述旨趣和切入角度不同,并没有进行全面而系统深入的论述。至于调查的准备、详细经过等问题此书根本没有涉及。笔者分析其原因同上,在此不再重复撰述。
3.赵新林和张国龙合着的《西南联大:战火的洗礼》一书的第三章《弦歌不辍 硕果累累》中的第三个小标题《成就斐然的学术研究》篇里提到了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对云南农业的调查(仅有300多字的简介)、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对云南的实地调查(仅有110多字的简介)和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语言、民俗、社会结构、经济、地理等多方面的调查研究(也只有750余字的简介)。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的论述。至于实地调查的详细准备、调查经过、调查方法和得出的结论一概没有涉及。
4.昆明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的《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昆明(一)(二)》,也只是记载抗战时期在昆明的名流大师发生的轶闻趣事和生活如何艰辛居多,很少涉及这批名流大师对西南地区的实地调查,即便零散地涉及一点点,也甚为简单。至于当时开展实地调查的详细计划、调查经过、调查方法和得出的调查结论基本上没有涉及。我分析除了如前所述的原因外,还由于此书回忆性的文章虽然很多出自这些名流大师的后代,但是他们仙逝的父母辈生前给他们讲述的可能大多是抗战时期在昆明的生活艰辛和轶闻趣事,至于高深莫测的学术上的事情则告知后辈的不是很详细所致。再加上长期战乱和举家搬迁,调查的第一手原始材料大多遗失(除了公开发表的调查成果,如论文和专着外)。另外,由北大、清华、南开和云南师大四校联合编写的六大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这方面的详细资料也不多。这六大本一千多万字史料主要来自现存的北京大学档案、清华大学档案、南开大学档案和云南师大档案。
(1)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邢公畹先生的儿子邢宁撰写了一篇文章《旧历亲闻———南开边疆人文研究室邢公畹先生在昆明》,收录于昆明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的《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昆明(二)》一书中。邢宁先生在此文中介绍了其父邢公畹先生在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工作概况,简单地记录了邢公畹先生在云南的罗平、新平、元江三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艰苦的语言学田野调查工作,介绍了一些轶闻和危险。但是,遗憾的是,此文对邢公畹先生开展实地调查的详细计划、调查方法和得出的结论没有涉及。
(2)梁吉生先生撰写的《英年一死献滇边———陶云逵在昆明的日子》,也收录于上书。梁吉生在此文中介绍了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的经过和陶云逵的学术生涯及其生平简介,还简单地介绍了陶云逵带领研究室同仁对石佛铁路沿线的综合调查研究经过。
(3)朱端强先生撰写的《浪迹学风镌滇海———记陈达教授在昆明》,也收录于上书。此文主要介绍了陈达教授寓居昆明期间的艰苦生活,而对于陈达主持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对云南环湖户籍示范区的人口普查的介绍太简略。
(4)杨立德先生撰写的《“把故国河山,重新整起”———曾昭抡先生在西南联大》,也收录于上书。此文详细地记述了曾昭抡先生在西南联大化学系严谨治学、教书育人的情况,此文简单地介绍了曾昭抡带领川康科学考察团步行考察大凉山的经过,而对于此次考察团的详细计划和准备、调查方法和内容、得出的重要结论这几个方面都没有提及。
(5)段家政先生撰写的《吴文藻昆明行》,也收录于上书。此文简要地提到了吴文藻和他的得意门生费孝通在云南大学创办了云大社会学系研究室(亦称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即“魁阁”研究室)的经过(仅240余字),至于此研究室的调查计划、调查方法等一概未涉及。
(6)陈康定先生撰写的《学苑清辉———记语言学大师罗常培》,收录于昆明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的《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昆明(一)》。此文简介了罗常培调查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情况(仅430余字),罗列了调查成果的名称,而对于调查计划、方法和得出的重要结论都未涉及。
5.由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云南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纂的《云南省志》卷七十五《社会科学志》,简单地概括和列举了抗战时期在昆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对云南省的调查研究成果,即他们发表的论文和撰写的专着的简单罗列,没有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我分析造成此种研究缺陷的主要原因,同前(1),在此不重复。
6.邢公畹先生撰写的《抗战时期的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兼忆关心边疆人文研究的几位师友》,选自《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此文介绍了边疆人文研究室创立的经过及其刊物《边疆人文》,介绍了他本人和黎国彬在1943年的红河之行调查中发生的轶闻趣事和遇险的简要经过,而对于此次调查的详细计划、调查方法和得出的重要结论没有涉及。
三、进一步深入地研究本课题的意义
1.对学科发展的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和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这种进展特别表现在当时迁居云南省的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西南地区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实地调查研究,在研究队伍、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等方面都有了可喜的变化。进一步深入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学与社会学在云南省的中国化研究”这一课题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民族学和中国社会学在抗战时期在云南边疆地区的发展历程与辉煌成就。抗战时期是民族学中国化和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阶段,进一步深入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学与社会学在云南省的中国化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民族学中国化和社会学中国化在抗战时期这一重要阶段的发展历程,可以填补专题深入研究这一重要课题的历史空白,从而为中国民族学史和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作出贡献,费孝通先生曾颇有感情地说过:“云南,是中国社会学的摇篮!”(见费孝通的《云南三村》)抗战时期的云南省是民族学中国化和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试验基地。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课题对于中国民族学和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现实的社会意义
抗战时期在迁居云南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克服了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对云南省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实地调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辉煌的成就,真可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他们给我们这些后世学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留下了一笔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源。在进行西部大开发和建设云南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西南边疆和谐社会的大手笔中,寻觅斯人久已失落之遗迹与学术遗事,以保护、充实和建设好昆明历史文化名城的底蕴,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而且,由于这些遗迹与学术遗事是与抗战历史相联系的印证,对于缅怀当年西迁高校名流学者可钦可敬的爱国事迹和敬业精神,激励青年一代勤奋攻读、奋发图强的精神,对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至于这一批名流学者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风餐露宿,沐风栉雨,跋山涉水,充分表现的严谨治学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更是我们当今学人应该大力继承和弘扬的。在遭受市场经济大潮严重冲击下的当今中国学术界,普遍存在着学术浮躁、急功近利、学风不正的现象。我们当今青年一代学人尤其是从事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青年学者更应该努力学习和大力弘扬老一辈学者一丝不苟的严谨治学精神。笔者认为,要想出传世的学术精品,首先必需要具备一丝不苟的“十年磨一剑”的严谨治学精神。从这个层面来看,系统深入地研究抗战时期迁居云南的名流学者对云南省的实地艰苦调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今中国正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毫无疑问,云南省是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在对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必须首先对云南省的民族文化资源、自然资源等进行调查研究。例如,我们要开发云南省的旅游资源,发展云南省的旅游业,我们首先要对云南省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进行实地调查,努力做到合理开发以保证云南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我们当今在云南进行实地调查会比抗战时期在云南的专家对云南省进行实地调查的各方面条件要好得多,尤其是交通方面表现最为突出。但是,老一辈学者一丝不苟的严谨治学的敬业精神是我们永远都应该大力继承和弘扬的,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调查方法在今天看来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抗战时期在迁居云南的专家对云南省的调查研究中得出许多精辟的观点和深邃的思想,即使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启迪意义与现实指导意义。在此仅举一例以示说明。陶云逵在边疆社会的研究中,并不是只把少数民族作为猎取资料的对象,而是着眼于边疆建设和民族团结,希望边疆各民族得到更快的进步。他在《云南摆夷族在历史上及现代与政府之关系》一文中指出:“为我全国民族之永久团结,似宜积极设计导此边胞社会,使其生活设备、文物制度和我国其他地区一样趋于现代化,以其地势之利,人事之优,好好建设。”为了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他认为必须正确地认识和分析边地汉人,正确估计他们在边疆建设中的作用。他在《论边地汉人及其与边疆建设之关系》一文中说,社会学认为,“两个人群,其文化物质彼此愈相近似,其份子间能了解的程度愈高。”边地汉人在生活样法上,一方面存了中原文化若干特质,另一方面又采纳了边胞文化若干方式,多少受到双重文化的陶熔,事实上成为人类学上所谓的“Marginal Man”(边缘人)。他主张发挥边地汉人的这一特殊作用,对促进边疆地区社会发展是很有利的。陶云逵教授上述这种深邃的思想和精辟的观点,即使在今天我们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过程中,对促进云南边疆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启迪意义与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