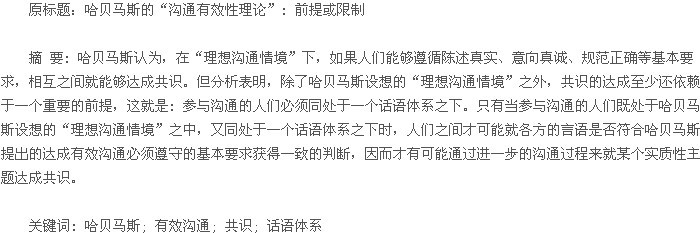
一、哈贝马斯的沟通有效性理论
哈贝马斯希望通过共识的形成来实现社会的合理整合。人们通常认为,在讨论共识的形成过程时,哈贝马斯提出了两个前提条件。一个被称为“理想沟通情境”,另一个被称为沟通有效性要求。
所谓“理想沟通情境”,其内涵主要如下:
( 一) 一种话语的所有潜在参与者均有同等参与话语论证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发表任何意见或对任何意见表示反对,可以提出疑问或反驳质疑。
( 二) 所有话语参与者都有同等权利作出解释、主张、建议和论证,并对话语的有效性规范提出质疑、提供理由或表示反对,任何方式的论证或批评都不应遭到压制。
( 三) 话语活动的参与者必须有同等的权利实施表达式话语行为,即表达他们的好恶、情感和愿望。因为,只有个人陈述空间的相互契合以及行为关联中的情感互补,才能保证行为者和话语参与者面对自身采取真诚的态度,坦露自己的内心。
( 四) 每一个话语参与者作为行为人都必须有同等的权利实施调节性话语行为,即发出命令和拒绝命令,作出允许和禁止,作出承诺和拒绝承诺,自我辩护或要求别人作出自我辩护。因为,只有行为期待的相互性才能排除某种片面要求的行为义务和规范判断,为平等的话语权利和这种权利的实际使用提供保证,解除现实强制,过渡到一个独立于经验和行动的话语交往领域。
①而在《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哈贝马斯则将人们之间为有效实现沟通过程所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表述如下:
任何处于交往活动中的人,在施行任何言语行为时,必须满足若干普遍的有效性要求并假定它们可以被验证。就他试图参与一个以理解为目标的过程而言,他不可避免要承担起满足下列———确切地讲,正好是这些———有效性要求的义务。这些要求包括:1. 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 2. 提供( 给听者)某种东西去理解; 3. 由此使他自己成为可理解的;以及,4. 达到与另一个人的默契。将上述四点展开就是: 言说者必须选择一个可领会的表达以便说者和听者能够相互理解; 言说者必须有提供一个真实陈述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 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 最后,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之,从而使言说者和听者能在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不但如此,一个交往行为要达到不受干扰地继续,只有在参与者全都假定他们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要求已得到验证的情形下,才是可能的。①由于可领会性( 按照交往参与者公认的语法规则说话) 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也可以将上述四个有效性要求简化为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言说者对事实的陈述必须是真实的; 第二,言说者对沟通的意向必须是真诚的; 第三,言说者所表述的话语从行为规范角度看必须是正确的。
在一次以达成相互理解为目标的交往行动中,上述三个有效性要求必须同时得到满足。只要其中有一个受到质疑,交往行动就会遭到困难。
在《交往行动理论》一书中,哈贝马斯举了一个例子来对此加以说明。
哈贝马斯写道: “我们现在来假定: 教授在课堂上向一位学生发出了要求: ‘请您给我拿一杯水。’”如果这个学生不认为教授的这项要求是一种命令,而只是从沟通的立场出发完成的一个言语行为,那么,“这个学生原则上可以从三个角度对教授的请求加以拒绝。他可以对表达的规范正确性提出质疑: ‘不,您不能把我当作是您的助手。’或者,他可以对表达的主观真诚性提出质疑: ‘不,您实际上是想让我在其他学生面前出丑。’或者,他可以对现实条件加以质疑: ‘不,最近的水管都很远,我根本无法在下课之前赶回来。’第一种情况质疑的是教授的行为在一定的规范语境中所具有的正确性; 第二种情况质疑的是教师是否言出心声,因为他想达致的是一定的以言取效的效果; 在第三种情况下,质疑的对象则是教授在一定的情境下必须设定其真实性的陈述。”哈贝马斯认为,“我们对上述例子的分析,适用于一切以沟通为取向的言语行为。在交往行为关系中,言语行为永远都可以根据三个角度中的一个加以否定: 言语者在规范语境中为他的行为( 乃至直接为规范本身) 所提出的正确性要求; 言语者为表达他所特有的主观经历所提出的真诚性要求; 最后还有,言语者在表达命题( 以及唯名化命题内涵的现实条件) 时所提出的真实性要求”②。
二、哈贝马斯沟通有效性理论的前提或限制
对于哈贝马斯“理想沟通情境”理论,福柯等人曾有过批评。福柯认为,哈贝马斯设想的“理想沟通情境”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模式顶多也就是一种无法兑现的乌托邦理想。福柯说: “关于存在着一种理想的交往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真理的游戏可以无障碍、无限制和无强制地循环往复地想象,在我看来纯属幻想的范畴……我相信,没有权利关系,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存在,只要人们把这种关系理解为个人用以控制和决定他人行为的手段。”③我不太同意福柯对哈贝马斯的批评。我不认为权力关系的不可摆脱性对沟通行动始终会构成一种障碍。正如福柯自己认识到的那样,权力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权力关系可能造成人们之间的不平等,因而阻碍人们之间的合理沟通; 但这并非意味着人们之间的权力关系永远都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尽管人们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一种权力关系,但却可以是一种平等的权力关系,或者,近似平等的权力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之间面临的沟通情境就可能近似于哈贝马斯设想的“理想沟通情境”。因此,如果以哈贝马斯设想的“理想沟通情境”不符合现实为由来否定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模式,我认为是理由不足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没有任何瑕疵。
如上所述,按照哈贝马斯的论述,“沟通行动”模式的实施至少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参与沟通的各方需要形成一种上面所说的理想“沟通情境”,二是参与沟通的各方必须遵守一些有效地进行理性沟通行动所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 参与沟通的行动主体对事实的陈述是真实的、沟通的意向是真诚的、所遵循的行为规范是正确的等等) 。然而,正是在这第二个条件方面人们之间可能存在着难以消弭的分歧。
以下我们试举几个例子来对此加以说明。
1. 如何判断“参与沟通的行动主体对事实的陈述是真实的”?
下面是几对内容相互矛盾的事实陈述:
( 1)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不是一个阶级社会”;( 2) “中国目前中产阶级占人口的比重只占5% 左右”/“中国目前中产阶级占人口的比重已占 20% -25%”;( 3) “1995 年中国居民总体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为 0. 35”/“1995 年中国居民总体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为 0. 45”;( 4) “1998 年中国现代化实现程度已达81% ”/“1998 年 中 国 现 代 化 实 现 程 度 只 有40. 4% ”;( 5) “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进入什么后现代社会,而是进入了新现代社会”。
深受传统“实在论”影响的人会认为,在上述每对两两相异的事实陈述中,各自只能有一个陈述是真实的。但其实,如果我们对上述每一对陈述的构成过程做过具体的考察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表面上看去相互矛盾的陈述其实都可能是真实的。它们之间的矛盾,不是源于它们对它们所欲“再现”的“客观现实”获得了不同的观察结果,而是源于它们是其陈述主体在不同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下所做出的。以第一对陈述为例,这是毛泽东和梁漱溟分别作出的两个陈述。
而毛、梁二人之所以会做出这样两个粗粗看去相互矛盾的陈述,其实并不在于它们对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现实获得了不同的观察结果,而完全是因为他们两人所使用的“阶级”一词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可以说,虽然他们都在使用“阶级”这个概念来描述和分析 19 世纪末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但他们所用的“阶级”概念属于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从他们各自所属的话语体系来看,他们各自所作的那一陈述都可能是“真实”的。①其他几对陈述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每对看上去相互矛盾的两个陈述之间的差异首先或主要也可能是来自于陈述主体对所用关键概念———如“中产阶级”“居民可支配收入”“现代化”“现代社会”等———含义界定上的区别所致,而非来自于陈述主体对客观现实观察结果方面的差别。换句话说,虽然每对陈述中的两个陈述主体都使用了从字面看相同的概念来描述现实,但他们使用的概念在含义上却有一定的或相当的差异,使得他们事实上不在一个话语体系之中。他们是在不同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下来作出自己的陈述的。就像毛泽东和梁漱溟的例子所展示的一样,从他们各自所属的话语体系来看,他们各自所作的那一陈述也可能是“真实”的。
因此,要想判断一个人有关某一“事实”的陈述是否具有“真实性”,一个首要的前提就是: 判断者必须要和被判断陈述的主体同处于一个话语体系之中。一个和被判断陈述的主体不处于同一话语体系之中、甚至对被判断陈述的主体所属话语体系毫无了解的人,是根本没有能力对该“事实陈述”的“真实性”做出恰当判断的。
2. 如何判断“参与沟通的行动主体所持有的沟通意向是真诚的”?
以下是罗纳德·斯考伦和苏珊·斯考伦夫妇在《跨文化交际》一书中使用的一个例子:“王先生和理查德森先生的会谈使理查德森先生很高兴,他在分手时表示要找个时间与王先生共进午餐。王先生欣然应允; 几周后他开始怀疑对方毫无诚意,因为理查德森先生在发出邀请后,再没有来约定午餐的具体时间和地点。”①但事实上,按照斯考伦夫妇的含蓄表述,理查德森先生并非是王先生设想的那样一个虚伪和缺乏诚意的人。王先生对理查德森先生交往诚意的怀疑纯属误会。
但为什么王先生会有这样的误会呢?
斯考伦夫妇分析说,中国人王先生之所以会认为西方人理查德森先生缺乏交往的诚意,完全是由于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说话时遵循了不同的话语模式所致。研究表明,“亚洲人使用的表达顺序是‘话题—说明’,而主旨( 即说明) 的出现是以关于话题的背景被充分交代为条件。这种结构最常见的形式如下: 因为 Y( 话题、背景或原因) ,( 所以) X( 说明、主旨或行动建议) 。与此迥然不同的是,西方人说英语时倾向于运用开门见山式的话语策略,一上来就交代主旨。这样,其他谈话者对此就能作出反馈,而他本人也能根据需要完善自己的论据。其结构形式如下: X( 说明、主旨或行动建议) ,因为 Y( 话题、背景或原因) ”②。
这样两个遵循不同话语模式来说话的人,很容易因为相互不了解对方用来组织话语的模式而使谈话陷入困境。斯考伦夫妇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一次商务会议上,一个来自中国香港的商人对其北美同行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因为现在我们大部分产品在中国生产,唔———现在还不能肯定 1997 年以前政府过渡时期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还有,从经费考虑,我认为对于电视广告问题我们得谨慎一些。因此,我建议我们在莱格高公司作出决定以后再做打算。”斯考伦夫妇指出,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这个中国香港商人的话语很费解。如果是由一个西方人来陈述,这段话将会变成以下这个样子: “我建议我们在莱格高公司作出决定以后再做打算。这是因为从经费考虑对于电视广告问题我们应该谨慎一些。
另外,现在我们大部分产品在中国生产,现在还不能肯定政府在 1997 年前的过渡时期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这样,这个西方人“一上来就提出了推迟决定的建议,然后再说明这样做的理由”。但对于习惯中国式表达的人来说,这个西方人的话语行为会显得有点粗鲁。“这种话语模式的不同导致了话语焦点的不同: 西方人认为话语的开头部分是最重要的,而亚洲人更倾向于从话语的后面部分寻找重要信息。”③斯考伦夫妇指出,正是由于中国人习惯于将最重要的话置于谈话的结尾,而西方人则习惯于将重要事项置于谈话的前面部分、将一些被认为无关紧要的客套话置于谈话结尾这样一种话语模式引发了前述王先生对理查德森先生交往诚意的怀疑: 正是王先生熟悉的话语模式“使王先生认为理查德森先生在会谈最后发出的午餐邀请是比较重要的。无论这次午餐对王先生来说重要与否,他都认为理查德森先生应该是郑重地发出邀请。相反,理查德森先生却觉得此事无关紧要,因此才在会谈结束时提出共进午餐的建议,对他而言,这仅仅意味着他的心情在会谈之后很愉快。换言之,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邀请,而只是一种告别时习惯性的客套话”④。
这个例子非常清楚地表明,对于参与沟通的行动主体双方是否持有真诚的沟通意向这一点,沟通双方其实也不容易达成一致的理解。和我们前面讨论“陈述的真实性”问题时所遭遇的情况一样,沟通双方在“双方沟通意向的真诚性”这一点上是否能够做出一致的判断,一个重要前提也是双方必须对“真诚的沟通意向”有一个共同的判断标准。而这就要求沟通双方必须要同处于一个话语体系( 或斯考伦夫妇所说的“话语模式”)之中。一个和沟通对方不处于同一话语体体系之中、甚至对对方所属话语体系毫无了解的人,在对对方“沟通意向的真诚性”作出判断时也是可能会遇到困难的。3. 如何判断“参与沟通的行动主体所遵循的行为规范是正确的”?
以下是大家熟知的鲁迅在《立论》一文中通过梦中“老师”之口讲述的故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 “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 “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 “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 ‘啊呀! 这孩子呵! 您瞧! 多么……。阿唷! 哈哈! hehe! he,hehehehe! ’”①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借“老师”之口,愤愤不平地说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这真是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
鲁迅为什么对故事中的第三位说话者遭到大家痛打这一现象感到如此愤怒? 其理由鲁迅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在他看来,前面两位说话者其实都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献媚者”: 他们正在试图借助于一些甜蜜的“谎言”来讨得故事主人的欢心;而第三位说话者才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正派人”:
他不屑于与前两位献媚者为伍,不愿意用谎言来取悦主人,坚持要说出反映事情之必然面目的“真理”。毫无疑问,在鲁迅以及第三位说话者的心目中,第三位说话者在说话时所遵循的行为规范才是“正确”的行为规范,前两位说话者说话时遵循的行为规范是“不正确”的,至少在道德规范的层面上看是如此( “说谎”“献媚”、没有人格等) 。
然而,绝大多数在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正常人”,却完全可能做出与鲁迅相反的判断。在绝大多数“正常”的中国人看来,违反了日常生活中大家公认之行为规范的显然应该是第三位说话者,而非前两位。无疑,在多数“正常”的中国人看来,假如上述故事情节不是发生在一个日常生活情境之中,而是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三位说话者也不是日常生活中相遇的普通人,而是正在讨论一个学术问题( “主人手中抱着的这个孩子未来会如何?”) ,那么,该受惩罚的的确就不是第三位说话者,而应该是前两位说话者,因为是他们违反了学术界公认的行为规范———“求真”( 假如我们当时就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两人说的是谎言) 。但问题在于,按照梦中“老师”的交代,上述故事情节恰恰发生在一个中国人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的情境———为满月的孩子贺喜———之中。而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关系亲近之人此时此刻应该说一些带有礼仪性质的祝福话语,以此来向孩子的父母表达“同喜”之心情,以巩固或加强与孩子父母之间的亲密关系。
这些带有礼仪性质的祝福话语并非一定要符合“真实”的标准,但一定要符合“吉利”“喜庆”“让主人高兴”等标准。因此,一个谙熟并愿意恪守中国传统习俗的人此时此刻一定会按照故事中前两位说话者的方式来说话。而不按这种方式说话的人则要么遭到第三位说话者的“礼遇”———被痛打一顿( 毫无疑问,其与主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也必将被终止) ,要么像“老师”指教的那样打“哈哈”———恐怕也免不了将来会受到主人的冷遇甚至报复。
无疑,故事中第三位说话者之所以无法与人正常沟通,正是由于双方在“何为正确的行为规范”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而双方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会出现分歧,又主要在于双方在沟通时处于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下: 故事中的主人和前两位说话者处于中国传统礼仪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之下,第三位说话者则处于以“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境下都应该求真务实、不说谎话”为原则的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之下。可见,和前面所讨论的两种情况一样,在判断沟通双方在沟通过程中是否遵循了正确的行为规范时,沟通双方是否处于同一个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之下,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只有处于同一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之下的沟通行动者,在“何为正确地行动规范”问题上才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的判断。
上述例子可以表明,无论是陈述的真实性也好,意向的真诚性也好,还是规范的正确性也好,都不具有一种不以人们的话语体系为转移的自然性质。相反,判断一个参与沟通过程的人在所有这些方面是否达到了所要求的标准,都是由人们所属的话语体系来决定,因而是随人们所属话语体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处于不同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之下的人们,会对陈述的真实性要求、意向的真诚性要求、规范的正确性要求做出不同( 甚至完全不同) 的理解,因而也就会对沟通参与者之陈述的真实性状况、意向的真诚性状况、规范的正确性状况做出不同( 甚至完全不同) 的判断。
可见,即使在双方的言语是否与理性沟通的有效性要求相符这一点上,人们之间尚且难以形成共识,更何谈在一些更为具体的讨论主题上达成共识?
三、结 语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上述的讨论并非是要完全否认人们之间通过理性沟通来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只是除了哈贝马斯设想的“理想沟通情境”之外,它还依赖于一个重要的前提,这就是: 参与沟通的人们必须同处于一个话语体系之下。只有当参与沟通的人们既处于哈贝马斯设想的“理想沟通情境”之中,又同处于一个话语体系之下时,人们之间才可能就各方的言语是否符合哈贝马斯提出的达成有效沟通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获得一致的判断,因而才有可能通过进一步的沟通过程来就某个实质性主题达成共识。这也就意味着,原本不处于一个话语体系之下的人们,如果要想通过沟通来就某个话题达成共识,那么他们就首先必须通过学习过程( 相互学习对方的话语系统,或者共同学习一种新的话语体系等) 来使双方能够同处于一个话语体系之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要想形成共识就是困难的,试图通过共识的形成来解决纠纷、实现社会整合也就只是一种空想。
哈贝马斯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了解上述道理的。在《交往行动理论》一书中,他就曾经指出,通过平等的沟通协商来达成共识的前提之一就是沟通过程的参与者必须处于同一“生活世界”之中。哈贝马斯说: “通过交往实践,交往行为的主体同时也明确了他们共同的生活语境,即主体间共同分享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界限是由所有的解释确立起来的。而这些解释被生活世界中的成员当作了背景知识。……符号表达的有效性前提涉及到的是交往共同体当中主体相互之间共同分享的背景知识。”①“交往行为的主体总是在生活世界的视野内达成共识。他们的生活世界是由诸多背景观念构成的,这些背景观念或多或少存在着不同,但永远不会存在什么疑难。这样一种生活世界背景是明确参与者设定其处境的源泉。”②可见,哈贝马斯是清醒地意识到有效沟通的前提之一就是沟通双方必须有“共同分享的背景知识”。这种“共同分享的知识背景”,在我们看来,主要就是沟通者们共享的话语系统( 虽然哈贝马斯并不一定同意这种说法) 。但遗憾的是,哈贝马斯将自己的注意力只放在或主要放在了具有“共同分享的背景知识”的主体之间的沟通行为上,而对于那些不具有“共同分享的背景知识”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却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和讨论。而事实上,后面这种情境却和前面那种情境一样,也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一种有关沟通的理论,如果有意无意地忽略或淡化了后面这一情境,显然应被视为一个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