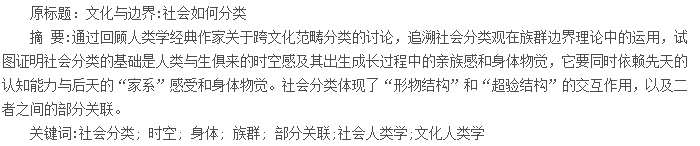
一、社会如何分类
法国社会人类学家爱弥尔·涂尔干和马塞尔·莫斯合著的《原始分类》认为:“人类心灵是从不加分别的状态中发展出来的”,分类观念是一部历史和史前史。他们举出澳洲祖尼人、苏人和中国人的例证,强调事物的分类“再现了人的分类”。
也就是说,人类最初的分类是根据自己的社会分类尤其是亲属分类,来对自然万物进行分类;分类也不是人类心智所固有和内生的能力,而是首先基于最熟悉的亲属关系而后天习得的:我们把同一属的各个种说成是由亲属关系联系起来的;我们把某种类别称之为“族”(family);另外,属(genre)这个词本身原本指的不就是一个亲属群体吗? 这些事实使我们得出这样的推断:分类图式不是抽象理解的自发产物,而是某一过程的结果,而这个过程是由各种各样的外来因素组成的。
如果从一个侧面来说,图腾制度是依据自然事物(相关的图腾物种)把人们分成氏族群体,那么,反过来讲,图腾制度也是按照社会群体对自然事物的分类。弗雷泽认为,人类依据事先已存在的食物分类来划分出氏族,涂尔干和莫斯反驳说,人类根据氏族分类来给自然界分类。此外,涂尔干和莫斯还把观念和分类的起源归因于情感,“纯粹知性的法则”不会给分类提供依据,分类的对象也不是概念;“事实上,对于那些所谓的原始人来说,一种食物并不是单纯的知识客体,而首先对应的是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
尼达姆在肯定涂尔干和莫斯在历史、方法和理论上的重大贡献的同时,也尖锐地批评他们关于社会分类决定符号分类的观点,并批评了他们关于分类的演化序列(如二分先于四分,四分先于八分,等等)。尼达姆在为《原始分类》写的导言中指出:首先,各地的民族志材料并不能支持符号分类源于社会分类的观点;恰恰相反,这些民族志材料都能证明这两种分类往往是不一致的。其次,尼达姆指出,涂尔干和莫斯把符号分类看作是概念的堆砌,属于认知的内容,不涉及认知的能力,换句话说,符号分类是后天习得的,不是内在的先天能力。但是,如果没有人类先天具有的对于空间和时间的认知能力,那么符号分类是不可想象的。尼达姆还认为,人类各种符号分类系统最终符合二元图式。
涂尔干和莫斯有专章提到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分类体系,如东青龙、南朱雀、西白虎、北玄武,罗盘八分,金木水火土五行,天干地支,二十四节气等等,时空万物、脾性色味共同构成“混杂”的符号系统。尼达姆用中国古代的这种“混杂”符号分类系统,以其矛攻其盾,反驳符号体系“循序渐进”的演化观,认为:一个社会并不一定非得使用单一的分类模式;而且,在采用两种或更多种分类模式的社会中,即使它们是可以相互还原的,这也并不意味着每一种分类就一定代表着社会范畴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
尼达姆和涂尔干、莫斯之间的分歧也反映了人文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内”“外”之争,即人类的认知从何而来,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是“内在的”,还是“社会的”。尽管尼达姆在《原始分类》导言中指出列维 - 斯特劳斯受到涂尔干和莫斯的影响,但列维 - 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和他们的核心观点即人对自然的分类起源于对社会的分类有所不同,认为人类的认知能力来自无意识的“深层结构”或心智“语法”,它潜在于心灵而非社会,与生俱来。涂尔干和莫斯认为社会认知先于个体认知,而列维 - 施特劳斯认为个体认知先于集体认知。持心智论观点的古迪纳夫和施耐德都认为意义来自人类心智而非外部世界,内在于人类心智。持社会论观点的格尔茨则认为意义来自公共领域,外在于人类心智。
从皮尔士指号三元论分析,这些争论可以得到合理解释。任何指号都有“质”的要素,即自然现实的特征,自然现实面前“人人平等”,人类的物觉和物感具有普适性、原生性和唯一性,拟声词和图像即是贴切的例子;任何标指都有“指”的要素,即指号从“自指”变成“他指”,即“一物指另一物”的特质,但这种指向关系是自然关联的或者是逻辑的,子弹和弹洞、兽迹和野兽是通常用的例子;任何指号也都具有“约”的要素,即基于任意性的象征性约定俗成,人类语言中充满了这样的例子,如汉语的“水”在英语里是 water,在蒙古语里是 os 等等。不过,“约定俗成”并非完全脱离物觉物感和指向关系,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外界对于心灵的触动是同一普世的,而用来表达这一触动的声音却多种多样。皮尔士始终强调“质”、“指”、“约”之间的关联一体、不可分割的性质,当我们认知到“质”的刹那间它已经指向“他”,与此同时,“质”和“指”又变成“约”,它们互相关联,在抽象度和具体性上有所差别。例如我们会看到红色的“质”,几乎同时,我们知道它是“红旗”之“指”,也几乎同时,我们知道它象征革命,与共产主义信仰有关等等。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很难将这个环环相扣的“红色现象”中的“质”、“指”、“约”一一明确区分开来,它们总是“一拥而上”,占据了我们的感官和认知,无意识和有意识地交织在一起,难分主次。因此,把内在和外在截然区别开来,争论哪一个更加重要恐怕是徒劳的,它们属于不同的抽象层面,具有互补共生的性质,没有必要“关羽战秦琼”。
人对于客观外界的分类既有对于人类自身的社会分类的根据,也有对于诸如“空间”、“时间”之类的先天认知的基础;既有对于群体的分类根据,也有对于个人身体的认知基础。社会、文化、自然、概念的分类是一个互动的综合过程,从普遍意义上说,很难有哪一个分类系统会占据优势。不过,从相对意义上说,在具体文化中确实存在基于某种“特质”或者“物象”的分类优势。谢莉·奥尔特纳(SherryOrtner)引戈弗雷·林哈特(Godfrey Lienhardt)在《神性与经验》一书中对于苏丹南部丁卡人以牛分类的讨论,指出牛为丁卡人对于自己经验的认知和分类提供了细致入微的概念范畴,牛的颜色分类被投射到周围世界,从亮度到浓淡都和“牛色”难以分割,离开“牛色”词汇,他们就无法描述自己的色觉经验。
二、投射式分类: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古人言:“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人类也通过自己的身体来认知“身外之物”,以身体比拟客体,以身体知识推演客观知识。同时,人类也能够以物喻物,物物相指,以亲知之物比喻欲知之物,举一反三。这种模拟有时候是明显的,有时候是暗含的,如“人潮涌动”、“心旌摇荡”、“川流不息”、“壮士断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等等,其中“人潮涌动”、“心旌摇荡”是明喻,“川流不息”、“壮士断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暗喻。
金特纳与金特纳(Gentner & Gentner)研究心理模型,发表了著名的《水流或人潮:电的心智模型》(Flowing Waters or Teeming Crowds: Mental Models ofElectricity)一文。金特纳与金特纳在文中引用的这段对答比较典型:
问:你插上电源,灯就亮了,为什么?
答:……大概来说,你插上就有电源了……电流进入设备的电线,就是灯的电线,流动上去了———流动———我想它是流动的,因为我脑子里有从负极流向正极的图像,也因为……电线是有负荷的细长东西,就像一条河。
在心理学认知领域有“表层术语假说”(SurfaceTerminology hypothesis ) 和 “生成模拟假说 ”(Generative Analogy hypothesis)之争。“表层术语假说”认为,认知者为了方便,用来自其他范围的词汇来描述认知对象,例如把电流比作水流,把电线比作水管,但是不会影响原有的思维方式。“生成模拟假说”则认为,这个过程是一个“结构映射”过程,能够把原属于甲范围的结构映射到乙范围之上,从而影响认知方式和认知结果;使用不同的模拟会产生不同的认知方式,也会影响对于事物的解释。金特纳与金特纳支持“生成模拟假说”,认为“人流模型”和“水流模型”导致对于电流的不同解释。
人流模型(the moving crowd model)把电流量和电压的变化,想象成密集的人群涌出大门时的流量和拥挤的程度:
人流 电路
通道 电线
人群 电池
人 电子
拥挤 电压
大门 电阻
人流量 电流
“水流模型”(the flowing water model)把电流量和电压的变化可以想象成水压系统中水流量和水压的变化:
水压系统 电路
管道 电线
泵 电池
细管 电阻器
水压 电压
管道的狭小阻塞 电阻
水流量 电流
金特纳与金特纳的研究证明,“水流模型”把并联电路中的电阻理解为“双重阻力”,因此通电量要比串联电路中小(不符合事实);“人流模型”把并联电路中的电阻理解为两扇门,人流先从一扇门蜂拥而出,然后从两扇门分流,当然流量就比一扇门要大(符合事实)。借用什么样的模拟显然对认知过程和结论有重要影响。
语言学家乔治·拉科夫(George Lakoff)等对美国英语中的“生气”隐喻进行了研究,涉及的仍然是“容器”: 身体是情绪的容器 (The body is acontainer for the emotions);情绪是容器里的液体(emotions are contained liquids ); 情绪是热的(Emotion is heat)。加热到沸点的水会变蒸汽,美国英语的蒸汽(steam)也表示“生气”;当容器里的压力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它就要爆炸:blow(爆炸)在美国英语里也表示“发脾气”。在英语里还有 pissoff(恼火)这样一个短语,原意为“解小便”:膀胱里憋的液体聚多了,压力大了,就要放出去。人类认识世界始于自我,以自我推知非我,以所知类比未知,并由此反观自我,循环往复。汉字偏旁是最好的说明:“提手旁”、“足字旁”、“目字旁”、“肉(月) 字旁”、“口字旁”、“言字旁”、“耳字旁”,由我及他,从具体入抽象,几千年的文明都是靠人体“写”出来的。
隐喻表现了典型的标指关系,以弹洞喻子弹,以烟喻火,以云喻雨等等。喻体和喻指之间有部分代替整体、结果代替原因、过程代替因果的关系,具有生动能产的特点,不仅和日常生活关联,也和抽象思维关联,是人类生活每天都不能离开的交流和思想工具。从抽象程度讲,隐喻 - 标指相对于象似和象征属于“中度”,而象征属于“高度”,象似属于“低度”。抽象的象征分类具有稳定性,例如宗教信仰,上帝的存在不容置疑,无需论证,要么信,要么不信,直截了当。
抽象度偏中偏低的象似分类和标指分类,则相对变化多端,它们直接属于“生活世界”,时时事事都要“协商”,各种人类主体在内的社会和非社会因素在反复互动中取得各种意义,每一阶段的互动都获得暂时的意义,接下来的互动又获得新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标指并不总是表达弹洞和子弹之类那般逻辑性很强的关系,它也表示社会习性,即法国人类学家布尔迪厄所说的“惯习”(habitus),指人们在特定文化中养成的习性或者行为举止,它是沉淀在身体及其活动中的历史遗产,社会成员不能加以完全摆脱,也不能加以完全认知。在民众生活中,在正统和闰统两极之间,存在一种客观秩序和主观组织原则之间的近乎完美的和谐一致,于是,自然和社会显现出“自明”的存在状态,布尔迪厄把这种体验称为“信习”(doxa)。“信习”不同于正统和闰统,它不会让人认识到信仰的差别或者对抗,而只能在无意识状态下让主客观互渗,让一切变得自然而然。倘若真要追究其中的因果关系,追究者就会陷入“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逻辑怪圈之中。
这种状态表现了象似、标指、象征之间的高度圆融,象似给予象征物感的支持,而象征又反过来对物感进行“指导”或者暗示,而标指是其中重要的“沟通者”,令象似和象征能够互相指涉,共成一体。
不过,这种主客观互融状态之下的主客观分类的和谐一致,在族际交流互动中会受到挑战,全球化时代的市场逻辑和经济理性,更加凸显了这样的挑战:传统时间节奏和空间格局被打破,各个非主流社会“哭着喊着被推向现代化”,城市化、市场化似乎成了不可摆脱的宿命,传统的分类系统忽然变得支离破碎,从主体分类范畴到群体分类规则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三、族群分类的边界
四十多年以前,1969 年,弗里德里克·巴特(Fredrick Barth)主编出版了《族群和边界》一书,他为该书撰写的序言成为族群边界论的代表作。他主要从现象学角度观察和解释族群现象,侧重族群的结构性对立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族群边界,避免用历史主义和原生论。在边界论的框架中,族群起源无足轻重,族群要素可有可无,均予以搁置,找不到把民族看成是“想象的社群”和“现代工业化产物”之类的宏大论述。族群研究者一般认为,文化是关于人类行为的知识和规则,每一个族群都有自己特有的相应文化。与此同时,族群研究者一直关注族群的历史边界和族群之间的关系,但并不重视族群的构成和族际边界的性质。仅仅用抽象的“社会”概念去描述和指称一个庞大的社会制度,分析其中的小群体和小单位,这不能解决和解释族群的实际特征和具体边界,不能上升到较高的理论层面。
巴特指出,过去有学者认为一个部落或者人们共同体故意忽视相邻部落或者人们共同体,以期由此保持自己的文化,这种幼稚的观点显然已经被人类学家放弃。但是,仍然有人坚持,文化差异取决于地理和社会隔离,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然而,巴特指出,尽管人们有可能已经在地理和社会意义上“越界”,但是原有的边界观念依然存在,也就是说,族群范畴不取决于人口的稳定和缺乏流动,不取决于互不接触和互不交流信息,即不取决于社会隔绝和社会封闭。但是,族群范畴却隐喻着排除与合并的社会过程,正是通过这样的社会过程,互不相关的范畴得到保持,不受制于社会身份的变化和参与社会方式的变化。同时,我们还可以注意到,持久、稳定和重要的社会关系,恰好跨越了这样的边界,并且建立在二分的族群地位之上。社会互动和社会接受并不一定导致民族特征的丧失;族群接触和互相依赖并不导致文化差别的消失。边界论认为,族群首先是族群成员的归属和认同范畴,它对于族群之间的互动具有组织和协调作用。边界论不强调族群和族群关系的类型和分类,而是关注和探讨族群得以产生和存在的不同过程,其重点在族群边界和族群边界的保持,而不是不同群体的内部构成和历史。许多民族志材料表明,族群之间的密切接触,并不意味着接触某一方或者双方的互化或消亡,相反,他们仍然会顽强地存在,有时甚至产生比过去更加强烈的族群意识。两个或者多个族群在接触中继续保持各自的独立存在,它们有各自的准则和标记,形成互动结构,保持文化差异。族群关系的的稳定取决于族群交往的规则和惯例,在一些方面允许甚至鼓励族际交往,在另一些方面加以禁止,避免外来文化的“腐蚀”,保持本族文化的“纯洁”。有的时候,交往禁忌不限于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还涉及“人身禁忌”或者“种的禁忌”,例如一些族群的习俗禁止本族女性与外族通婚,但男子可娶外族女性,也有完全禁止本族男女与外族通婚的严格禁忌。一方面,这种禁忌分类具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维基础,表现出对于外族的高度不信任,且拥有大量谚语、成语、故事、传说、神话之类的“话语”支持。另一方面,这些对立的族群之间在历史上可能发生过战争,形成随时付诸行动的“敌对语法”和仇视态度,其背后有强大的历史记忆和社会记忆的支持,日常生活中的族群成员之间的磕磕碰碰,被等同于族群之间的磕磕碰碰,从而也强化了这类敌对和仇视的历史记忆和社会记忆。
从文化生态角度观察,如果几个族群能够在某些文化特点上结成互补共存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根据巴特的分析,在族群接触的时候,他们互相依赖的生态关系具有几种不同形式。首先,它们可能在自然界各有自己的明确生存范围,不存在激烈的资源竞争,此时它们之间的互相依赖程度是有限的,贸易和仪式具有标志族群边界的作用。其次,各族群可能垄断各自居住的地域,它们之间存在资源竞争,沿边界的政治活动会划定族群边界。再次,各族群可能互相给对方提供重要的物品和服务,形成互相依赖的关系。最后,在群体杂居的地方,至少存在某种程度的竞争,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一个族群会取代另一个族群,或者它们包容共生,更加互相依赖,互相补充。
分类体系对于建构和保持族群边界至关重要。
分类范畴属于理想模式,相对独立于具体经验、具体行为和具体文化因素。例如在族群的亲属制度中,亲属地位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财产多少,也不取决于他的社会行为:一个没有尽到义务的父亲仍然是一个父亲。在族群接触和文化变迁的过程中,族群成员努力维护传统,信任对于当下形势的文化解释。
当然,这种文化解释有它自身的文化逻辑,是有选择的、临场的和约束性的,除此而外,要找到其他更合适的解释并不那么容易。里奇在描述缅甸克钦人时认为,他们的族群应当作为社会单位而不是文化单位看待,换句话说,稳定的族群边界是社会的或者是政治的边界,而文化边界则可能变化多端。族群的这种社会边界或者政治边界具有对立于其他族群的结构功能。族群之间的差别主要是结构上的差别,而不是文化上的差别。巴特认为,族群认同来源于族群成员的出身和背景,而他们所拥有的共同文化只不过是一种暗示或者结果,它们不是族群首要的和决定性的特征。但是,有的学者并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一个族群用不着非要拥有一系列文化特质才成其为族群,族群认同本身就为族群提供了确定的文化特质。根据巴特的族群认同来源于族群成员的出身和背景的说法,族群认同是遗传的或者是以某种神秘方式获得的,这显然不确切。族群认同产生于交流和表达,渗透在神话、宗教、信仰、仪式、民间历史、民间文学和艺术之中,族群认同及其相关文化交流和表达从不同角度保持和强化传统的符号分类体系,同时也为族群关系赋予社会意义。尽管文化特征是族群存在的必要条件,但它毕竟不是充分条件,应该同时保证族群边界存在的结构性对立。结构性对立不仅存在于族群之间对生产资源的争夺,而且也存在于对权力、知识以及合法权力等等的争夺。族群认同是人们对于某种特定社会经验的适应策略。如果族群的结构性对立消失,那么最明显的文化差异也会随之消失,族群和族群成员的同化也就会出现。一个族群成员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和需要采用不同的身份,而且不会造成认同危机。以泰国的克伦人 (Karen)为例,他们中有从事柚木贸易的极少数人,兼有泰人的身份,曾在泰语学校受教育,熟悉泰人的风俗习惯。同时,他们是泰国公民,忠于泰国国王,为国家履行应尽义务。由此可以看出,族群成员的认同边界也会随着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出于利益和价值的考虑而有所变化。
但是,族群成员的多样性认同并不影响族群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群体的存在,因为结构性对立一直是族群存在的基础,而不会因为个人或者部分人的认同多样性而发生动摇。
巴特在《族群与边界》的前言中再次总结了他的观点:族群是一种社会组织,与实际 的文化特征没有直接关系;族群身份是互动双方自识与他识的结果,即“我认为我自己是谁”和“别人认为我是谁”,不取决于研究者对族群文化的建构;文化特征的重要性和边界相关,即在“界内”的人会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会接受同样的文化表征。1994年,汉斯·韦尔默朗(Hans Vermeulen)和克拉·格沃斯(Cora Govers)主编了《族群人类学:超越 < 族群与边界 > 》(The Anthropology of Ethnicity)一书,再次肯定了巴特为《族群与边界》撰写的序言中提出的核心观点:族群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研究焦点是族群边界而非文化材料;自识与他识对于建构族群认同和族群身份具有同等重要性。不过,如尤金·卢森斯(Eugeen R oosens)和其他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把族群看作是社会载体而不是文化载体,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宗教群体、语言群体和其他类的群体,也都属于社会载体,也在自识和他识中维持自己的边界。那么,族群的特点到底是什么?卢森斯的回答是家系(genealogical dimension)。
家系总会和亲族及家庭的隐喻交织在一起,这类“家隐喻”和“边界”结合在一起,成为族群认同的主要根基。艾伯纳·科恩(Abner Cohen)认为,族群是政治经济的利益集团,家族、宗教、仪式等等文化要素不过是用来维持这个利益集团边界的符号工具,也就是说,从族群的组织原则出发,“利益”重于“血缘”,“血缘”为“利益”服务,族群是利益集团,不是血缘集团。
四、云南蒙古族个案
以上关于族群的争论同样是关于形物要素与象征要素在群体分类中扮演何种角色的争论,也是在族群分类体系中形物要素与象征要素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的争论。如果说涂尔干和莫斯在《原始分类》中提出的社会分类投射说主要属于约定俗成的象征维度,那么,卢森斯等学者的“家系原生说”②则相当执着地遵守了形物的维度。也许巴特在论说自己的族群边界论时对于“家系原生说”所持的暧昧态度,表达了他要超越这种形物与象征互不关联的一种努力:一方面,族群认同来源于族群成员的出身和背景,族群认同由遗传方式或者某种神秘方式获得;另一方面,族群是对于差异的社会分类,不一定和非得和族群成员的出身背景或者遗传方式挂钩,因为宗教、语言群体等等也可以培养和造就群体认同,也属于“对差异的社会分类”。巴特所说的“边界”就像“索绪尔棋法”,制作棋子的材料不重要,重要的是下棋的规则;同样,族群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等方面的外在要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族群边界,重要的是族群对于这些外在要素的社会分类,即“族群语法”。居住在中国云南通海县的蒙古族的民族认同比较符合巴特的解释,同时也肯定了卢森斯等学者关于族群认同源于家系隐喻的观点。家系隐喻为族群边界提供稳定的参照,也为社会分类提供主要的根据,物料、物象、物觉、利益、情感等等可以跨界流动,但界线和原则不会发生变化,我还是我,你还是你,只是换穿了不同的衣服,使用了不同语言,有了不同国籍,如此这般。
居住在云南通海县西部的兴蒙乡近 6000 蒙古族是元代入滇蒙古军的后裔,他们的祖先镇守河西曲陀关,落籍在那里,迄今已有 700 多年。1252 年,成吉思汗孙忽必烈统率 10 万大军进攻云南,由宁夏经甘肃入四川,然后兵分三路:兀良合台率西路军,途经今松潘、理塘、稻城、中甸一带;东路、中路经今茂州、鱼通、泸定、汉源,至西昌分兵,抄合也只烈率领东路军,经今德昌、会理,忽必烈率领中路军,经今盐源、宁蒗,抵金沙江后,灭云南大理国。1254 年,忽必烈还师,大将兀良合台镇守云南。1279 年,南宋灭亡。元朝统一中国的时间为 89 年(1279 -1368 年),但统治云南则长达 128 年 (1253 - 1381年)。1368 年,朱元璋建立明朝,云南的蒙古梁王拒守不降。1381 年,明将傅友德、沐英率 30 万大军进攻云南,梁王把匝拉瓦尔密兵败,在晋宁自杀。元末明初,建治在今通海县曲陀关的“宣慰司都元帅府”都元帅阿喇帖木耳与荫任都元帅的儿子旃檀“一十五翼”官兵镇守曲陀关,后迁居凤山脚下,形成现在的中村、白阁、下村、交椅湾、桃家嘴等蒙古族村庄,成为云南惟一的蒙古族聚居地。兴蒙乡蒙古族的先人们为了生存,学会了捕鱼、种田、建筑,从牧民和军人变成渔民、农民和工匠,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居住的地方曾被称为“中渔村”和“下渔村”,他们自己也被周边诸族称为“渔夫”。近现代以来,兴蒙之地以“建筑之乡”闻名,他们在清代和民国期间,曾参加昆明、通海、个旧、蒙自、开远等地的建筑工程,建造了聚奎阁、清真寺、兴文银行、震庄等中西建筑。兴蒙乡蒙古族使用的卡佐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语言,尤其在基本词汇和基本语法上存在较大的一致性,语音上也有严整的对应关系。
从使用无声调的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的牧民,到转用汉藏语系卡佐语的渔民、农民和工匠,兴蒙乡的蒙古族饱经沧桑。兴蒙乡蒙古族的丧葬随汉俗,行棺木土葬,墓前立碑。长子继承门户,能多分一些遗产;女子不能继承财产。居住样式亦与汉族同,过去殷实人家住三方一照壁或四合院,有的住洋式楼房,现在情况也是如此,只是房子的质量更好,盖的楼层数也更多。节日有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火把等,还有多种宗教仪式,如太平会、观音会等。兴蒙乡蒙古族的族性重建,首先离不开与“老家”内蒙古自治区的频繁来往,那里的同胞为他们提供重要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联想,在你来我往中交流感情,重建认同。
族性的重建要建立在“事件”和互动之上,它是一个活生生的过程。先是在 1956 年,有两个蒙古国的访客“发现”了这里的蒙古族,而在 1976 年内蒙古师范学院云南蒙古族调查组来此调查之后,北方的蒙古族来“探亲”的人越来越多,1984 年,从内蒙古来的客人达到 116 人。过去,白阁村的关圣宫里供的是关云长,后来在“文革”期间被毁掉。改革开放以后,经过村民们商议,1989 年,把关圣宫改成“三圣宫”,“三圣”指成吉思汗、蒙哥、忽必烈。每当有贵宾或北方的蒙古族兄弟来访,村里人总会带着他们去看看“三圣宫”。大殿里有“三圣”泥塑:成吉思汗居中,东侧是忽必烈,西侧是蒙哥。兴蒙乡和内蒙古频繁互动,推动本地的蒙古族文化重建。服装店里有鄂尔多斯蒙古袍,乡政府大楼有蒙古包样式的穹庐顶,新立的墓碑上也刻上了蒙古文和其他怀念北方族源的纪念文字。
兴蒙乡通过多族参加的庆典和仪式形成多族互构的民族格局,蒙古族也在多族共建中保持民族意识。这里的社会活动多族参与,生活方式反映多重文化,宗教儒释道三合一。桃家嘴的北海寺里面正中(庙座南朝北)供着观世音(面向北),其右侧是龙王,左侧是“三圣”(中间是成吉思汗,其右为蒙哥,左为忽必烈);东侧为财神菩萨;西侧为鲁班和啊吒哩神(驯龙神)。本地的蒙古族失去了北方的“物质文化”(语言文字、服装、住居形式等等)与生产和生活方式(游牧、祭敖包等等),但是,他们有北方的蒙古族万里来探亲,有周围各族一道“跳乐”,并且自认为也被承认为是蒙古族。通海蒙古人的身份是在各种各样的互动中维持和创新的,而这些互动的空间范围和样式,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兴蒙乡的个案告诉我们,历史可以传递“如何分类”,但不会涉及用什么样的“材料”去分类。历史上,包括蒙古人在内的内亚游牧诸族,尽管家庭生活和畜牧业生产上非常相似,但他们的政治组织、与外界的经济纽带以及集权的程度却千差万别。究其原因,这种差别出自不同的对外关系,即互动的对象不同,而非内部的发展。边界两侧居民对自己国家的忠诚,会由于经济利益而变化:他们在非法交易中利益共同体即“我群”;而其他本族人,尤其是统治者,成为“他群”。蒙古人自古就和周边诸族构成共生关系,通过边境贸易互通有无,形成“结构映射”关系。不同的民族在政治上也互相依存,中原的安定或动荡,会直接影响草原社会。兴蒙乡的蒙古族继承了前辈们“如何做”的历史,用彝语支的语言和舞蹈,借汉族的亲属称谓和居住方式,以多族相聚的“跳乐”,靠对太上老君、孔子、如来佛、鲁班、成吉思汗的崇拜,在远离故土的南方建构蒙古族的新形象。
兴蒙乡的蒙古族有建立在诸如旃氏族谱之类的家系书写传统之上的隐喻扩展的“民族语法”,他们借助与周边诸族共同参与的节庆及其他活动互构共建,文化要素的借入借出,民族成员的流出流进,不仅没有让民族边界和民族分类淡化或者消除,反而得以维持和强化。从语言宗教到农事庆典,形物维度的文化要素和象征维度的分类范畴,结成形气神的共生态,在狂欢中让各种族性得到彰显、复制、强化和延续。无可否认,人类生来具有空间和时间的认知能力,但这并不足以让他们产生族群认同,还需要借助出身和成长的培育过程并加以隐喻推衍,方能成就这样的认同。其实,人类的生长培育过程,是形气神共同“在场”的过程,触觉、味觉、嗅觉、听觉和视觉与时空逻辑的认知相结合,与比较概括的文化解释构成“三一”过程,使家系和家系隐喻具有真正的“质感”、“物觉”和“俗成”的坚实基础。社会分类的基础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时空感及其成长过程中的亲族感和身体物觉,它要同时依赖先天的认知能力和后天的家族感受和身体物觉,形成关键性的“社会语法”。
五、讨论
从上述关于社会分类的多角度讨论,可以得出下述结论。
第一,社会分类的基础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时空感及其出生成长过程中的亲族感和身体物觉。社会分类和符号分类共同属于兼有“形物”和“精神”的“指号分类”。
第二,兴蒙乡的例子充分说明了原有分类意识的沉积与复活,比较切合巴特的边界理论,即服装、习俗甚至语言等“物质材料”可以变,但其分类结构却保持稳定。需要指出的是,与内蒙古的密切联系和周边民族的分类和“被分类”都参与了兴蒙乡蒙古族民族认同的强化过程。
第三,社会分类体现了“形物结构”和“超验结构”的交互作用,以及二者之间的部分关联。一方面,如同“生成模拟假说”所证明的那样,原有事物分类会对后来的事物分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即便是原有的事物分类也是人类“客体化”的结果,因而离不开人的主体认知的潜质,离不开人类时空认知的先天能力,即确实存在“表层术语假说”支持的人类自主认知的“元能力”。总之,社会分类体现的维特根斯坦式的“家族相似性”结果,符合玛丽莲·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的“部分关联”理论。一种分类是另一种分类的延伸,一种分类是另一种类的条件,各种分类之间互为条件,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
参考文献:
[1] 爱弥尔·涂尔干,马塞尔·莫斯. 原始分类[M]. 汲喆,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 Ortner Sherry B. On Key Symbols[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73,75(5):1338 -1346.
[3] Dedre Gentner and Donald R Gentner. Flowing Waters or TeemingCrowds: Mental Models of Electricity[M]/ / Dedre Gentner andAlbert L Stevens. Mental Models. New York and London:Psychology Press,1983:129.
[4] Foley William A.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M]. Massachusett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1997:187 - 188.
[5] 纳日碧力戈. 语言中的身体隐喻[J]. 贵州大学学报,2012(1).
[6] Bourdieu Pierre.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159 - 197.
[7] Barth Fredrik.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M]. 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9.
[8]Leach E.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281.
[9]Keyes C. Ethnic Adaptation and Identity:The Karen on the ThaiFrontier with Burma[M]. Philadelphia:A Publication of the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1979:4.
[10]Hans Vermeulen and Cora Govers. Anthropology of Ethnicity: Beyon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M]. Amsterdam:HetSpinhuis,1994:1.
一、滕尼斯生平与《共同体与社会》(一)生平斐迪南滕尼斯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早期德国着名的社会学家。他于1855年7日26日出生于当时属于丹麦王国的施莱兹维希州的一个小城豪巴而格,他的父母均是农民世家,生活比较富裕,他们为七个子女请了一位...
长期以来,我党虽然十分重视社会建设,但明确提出社会建设的科学概念,则是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目前,社会建设理论正日益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在某些方面仍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本文主要对社会建设概念的提出、社会建设的内...
第三章弗洛姆健全社会思想评价前文已经详细分析过,弗洛姆是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健全社会构想的。弗洛姆认为,现存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并不能满足人类发展自我的需求,是落后的社会,于是他提出了一套新的社会模型,他将其称之为健全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强调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实现了快速发展。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由此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进程,迎来了社会学发展的春天。在这...
第一章弗洛姆健全社会思想的来源与形成背景1.1健全社会思想形成背景若论及弗洛姆健全社会理论的形成,笔者认为应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他的成长背景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另一则是他所受到的不同的思想理论的影响,可以说,任何伟大的哲学家都是站在前人的肩...
从学科角度讲,环境社会学大概有以下三种涵义:一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环境问题,尤其是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二是企图颠覆传统社会学甚至广义上包括社会科学的环境社会学,强调研究环境约束下的社会;三是强调研究环境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特别是社会...
在社会学中,社会变迁是一个表示一切社会现象,特别是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的范畴。它不仅是社会学中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而且也是最使人着迷、最难解答的问题之一。1920世纪最杰出的社会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尽力想解决社会变迁问题。本文以...
引言变迁、结构、话语是研究社会运动的三大视角,而变迁视角可追溯至涂尔干对于自杀的研究.涂尔干的理论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规范紊乱时,人就会变得难以控制.〔1〕涂尔干认为人与社会间有一个整合机制,自杀现象是由于这种整合机制的失调....
社会心理学家亨利泰弗尔于1978年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基于对这个概念核心的理解,泰弗尔区分出了个体认同与社会认同,影响区分的变量因素,并认为社会认同是群体间冲突和歧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