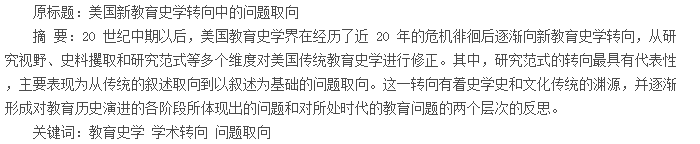
近代传统史学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面临诸多质疑,主要是因为传统叙述史学 ( Narrative Histo-ry) 将历史建构在关键事件和人物的枯燥叙述上,试图通过对埋藏的史料加以精细的考据研究,尽最大努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让史料本身 "说话",而史学家个人关于史料的思考被摒弃。依从传统叙述史学的美国传统教育史学亦带有比较浓厚的传统史学特征,虽然萌发了对教育实践意义的思考,但终究还是被传统史学理路羁绊。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是卡伯莱 ( Cubberley) 的 《美国公共教育》( The Public Schools in America) ,这本书几乎是一部美国公立学校教育制度史。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 "许多着名专业历史学家加入了教育史研究者的队伍,他们对于传统史学下成长起来的传统教育史学只关注学校和大教育家的做法感到不满,认为如果教育史领域不完成变革,新史学的变革也就无法完成"[1].美国教育史学面临学科地位危机,美国传统教育史学力图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找到一个突破口,实现向新教育史学转向。于是刚从美国社会大萧条中走出来的教育史学家开始考虑从传统的叙事史学转向问题取向的史学 ( Problem -oriented History) .
一、美国新教育史学转向中问题取向的来源
美国新教育史学中问题取向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向; 二是 20世纪初以来美国教育史学一直在学术与职业的功能取向之间徘徊。
新史学与传统兰克式的客观主义史学最大的冲突点在于历史的研究目的。年鉴学派是新史学的代表,认为对历史研究应该围绕一个中心--- "现实问题"进行,如果失去这个中心,历史学的价值才真正值得怀疑。马克·布洛赫 ( Marc LéopoldBenjamin Bloch) 直言不讳地说 "过去可以来理解现在,现在也可以来理解过去"[2].因此,新史学家主张将历史研究者的主体性价值和历史的因果关系写入历史之中,而这种现实价值最好的出发点便是 "问题".史学界关于历史书写范式的重新思考很快被美国教育史学家们敏锐地捕捉到。作为美国新教育史学转向的推动者---劳伦斯·克雷明( Lawrence Archur Cremin) ,美国教育史学在由传统叙述史学到问题史学取向的转向过程,恰好投射到了其对教育史书写的转变过程。在 1960 年以前,"无论是在对美国公立学校的历史概念的考察,还是对公共教育与美国未来的关系探究,克雷明都竭力 '让证据本身说话',并没有对教育家们就公共教育发表的言论推导出任何结论"[3].这一时期的克雷明秉持客观主义的传统,竭力让史料还原其本来面目。然而,仅过了一年,其在 《学校变革》(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 的研究中,迅速地抛弃了超然于一切的 "极度客观式历史学",明确提出 "我们必须正视学校变革的重要性,因为学校教育必须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否则就失去其力量的来源"[4].在 《美国教育史》( The History ofAmerica) 三部曲中,他借用 "大教育学" 的理论基础将自己的史学价值观和教育史的社会意义时明时暗地论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教育史学界经历的一场学术取向还是职业取向的争论,也是促使美国教育史学研究范式转向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教育史是为了适应教师职业化,从历史学科中分离出来的一门旨在为教师教育服务的专门史。由于历史学科的学术性和教师教育的职业性两者之间的张力,美国教育史在创立伊始,便面临学术取向还是职业取向的两难窘境。在大学历史教师看来,教师学院和教育系的教育史课程极其缺乏学术性,毫无研究意义,其本身就是一种纯粹的史料剪辑,缺少研究技术方法素养。然而,早在 1908 年,约翰逊( Henry Johnson) 和萨苏拉 ( Henry Suzzal) 就曾指出: "如果教育史想要在教师教育领域有所成就的话,就必须使其拥有更多的 '专业内容',最好是与我们的教师和教育管理者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内容,而不是狭隘的囿于历史学家荒谬的学术怪圈之中。"[5]
在 20 世纪 30 年代 "社会重建主义" ( So-cial Reconstructionism) 思潮的影响下,职业取向和社会问题取向一度成为教育史史料攫取的主要方向。例如,巴茨 ( R. Freeman Butts) 和安德森( Archibald Anderson) 在任 《教育史季刊》 (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编委的时候便主张教育应该成为一项社会改造的工具。他们认为,教育史学科地位的确立必须沿着社会问题取向进行。安德森在其论文 《教育史在教师培训中是否扮演着有用的角色?》( Is there a Functional Role for The Historyof Education in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中直白地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 "教育史的研究内容必须抛弃在传统的学术课程中所信赖的史料,而把攫取的眼光放在能对解决当今问题和教育政策问题起作用的材料上。"[6]
后来,美国教育史学界摩海尔曼 ( Arthur Hen-ry Moehlman ) 、 古 德 ( Harry Good ) 、 爱 德 华 兹( Newton Edwards) 和吴顿 ( Flaud Wooton) 等人在"问题取向"的理解层次上存在争议。例如,爱德华兹反对教育史单纯地依附于当今问题的解决,提出应该将 "问题"的概念赋予历史的纵深,他认为 "历史应该是一种对既定空间和时间的综合性理解"[7].但无论如何,他们并没有推翻 "问题取向",相反对这些问题的解剖和争论,让教育史学的 "问题取向"趋于成熟。美国 "历史基础委员会"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向美国教育史研究会 (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递交一份关于美国教育史研究状况的调查报告,明确提出"希望在教育史领域应当使其采纳问题取向法的专业计划中发生更为直接的联系" .
20 世纪 30 年代后,进步主义思潮将 "问题取向"的价值进一步凸显。杜威 ( John Dewey) 说:"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如果我们的教育要想对此发挥一点效用的话,那么也必然要经历一场相似的变革。"[9]正是在这些主要力量的作用下,美国教育史学在保留传统编纂范式的基础上,从传统的单纯叙事取向开始向以叙述为基础的问题取向的转变。
二、美国新教育史学转向中的问题取向
美国新教育史学家所探寻的 "问题取向"中的问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教育史学家所处的当下社会问题,这一取向主要是社会经济大萧条后期人们对教育与社会、学术与职业之间关系的历史现实价值的思考。20 世纪 30 年代,当时为数众多的进步主义历史学家诸如鲁宾逊 ( James Harvey Rob-inson) 、特纳 ( F. J. Turner) 等在社会经济大萧条后便开始寻找历史书写与社会价值的关系,并最终形成一股 "新重建主义"历史学思潮,他们主张建构一套 "有用的历史".这种有用的历史构架不但关注历史的社会效用,而且把目光放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价值上。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这主张便体现在巴茨的教育史研究上,他较早运用问题取向的方法进行教育史研究,在 《澳大利亚教育下的设想》 ( Assumption Underlying Australian Education)一文中提到: "我们如果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学术成就上,那么教师学院的教育就失去与社会现实性间的联系,从而丧失其本身存在的价值。"[10]
诺巴尔 ( Stuart G. Noble) 也强调: "教育史应该注重功能的研究而不是人文的研究。"[11]尽管这种取向性有 "狭隘的现时主义" ( Presentism)之嫌,但是其以现实问题为立足点,对史料进行特有角度的挖掘,架起了教育史与社会、教师教育等领域的桥梁,赋予了教育史研究新的社会价值。
历史形成中的教育问题也是 "问题"来源之一。克雷明在 《美国教育史》三部曲中一直试图将叙述史学与问题取向进行比较巧妙地融合。他首先从 "什么是教育"这个 "问题"出发,展开理论假设,然后将这种理论假设作为线索,以社会、家庭、学校等 "问题"为小主题,串联起书中庞杂的教育史料,以此叙述美国教育历史发展不同时期的教育结构、社会观念以及日常教育生活是如何变化的。克雷明正是从美国教育传统以及公共教育中提出并阐述的一系列问题来构建美国教育史框架的。[12]
凯茨在 《美国早期学校改革的讥讽》 ( TheIrony of the Early School Reform) 中以 "早期学校改革服务谁是利益获得者"这一问题为线索,在对马萨诸塞州立学校发展史的研究中发现中产阶级在改革中具有无比巨大的影响力,同时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后期这种问题取向在激进主义者那里表现得更加明显,斯普林 ( Jole Spring) 在 《美国教育》 ( The Education of America) 一书中始终贯穿着对多元文化、种族、学生在教育中的分层等问题的思考。需要注意的是,"问题取向"下的新教育史学并没有彻底抛弃对传统历史的叙述。事实上,从早期的克雷明到 20 世纪的里帕 ( W. Rippa) 和韦布 ( L. Dean Webb) ,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新教育史学家在传统历史叙述基础之上对历史问题进行系统性挖掘所做出的努力。
三、美国教育史转向过程中问题取向的意义
当教育史研究分析历史事件本身的价值时,史学家似乎必须担负着一种永恒的价值责任去思考历史的因果关系,并在这一逻辑中搜集教育史问题解决的经验,以期对当下乃至未来的教育生活和政策制定产生比较实际的效用。"问题取向"或许是教育历史研究与这种实际效用之间最好的桥梁,诚如劳凯声教授所言: "学科史就是问题史,人类就是在不断地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才不断地启迪思维、积累知识并推进学科的产生和发展的,因此是问题而不是学科才是学术研究的原初起点。"[13]
从实际效用来看,教育史的 "问题取向"使美国传统教育史学由单纯叙述为主的传统叙事史学转变为以分析为主的问题史学,并由此挣脱了正规教育、功利主义传统的束缚,摆脱了学科危机。
"问题取向"大大强化了教育史的实用价值。一直以来,教育史学科面临的最大观念挑战是 "由于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尤其是由于对应用、实用、功利、利益的普遍追求,因而,支持像教育史这样的基础学科研究的资源日益贫乏。" 因此,教育史研究者一直抱有对现实的埋怨,试图幻想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会在瞬间升华至某种可以理解基础学科理论价值的高度,这种想法既不现实也不科学。
"问题取向"并不是教育史对现实的妥协,因为教育史学科从诞生之始就担负着为当下教育问题寻求历史解释的 "功利化"使命,这一点并不需要避讳。因此,我们应从教育史本身研究范围出发,尝试在学术与实用之间寻找平衡点。正如美国新教育史学在转向中所表现出的 "问题取向",在教育史的研究和书写时以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将严谨的学术研究方法作为阐释这些问题的手段,这也不失为一条解决教育史学科危机的渠道。
一、美国新教育史学的转向20世纪后,曾风光一时、为历史学的专业化立下汗马功劳的传统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史学,正在不断地遭受着现代史学思考的质疑。这种从吉本(EdwardGibbon)-麦考来(MacaulayThomasBabington)-兰克(LeopoldvonRank)式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