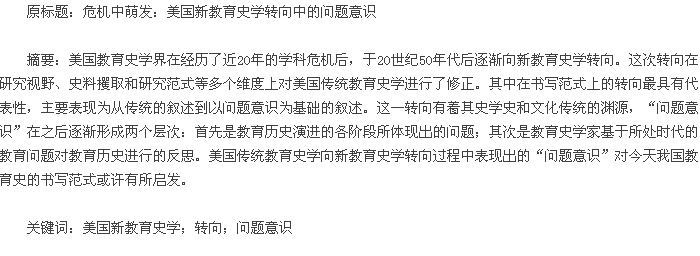
一、美国新教育史学的转向
20世纪后,曾风光一时、为历史学的专业化立下汗马功劳的传统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史学,正在不断地遭受着现代史学思考的质疑。这种从吉本(Edward Gibbon)- 麦 考 来(Macaulay Thomas Babington)- 兰 克(Leopold vonRank)式的传统叙述史学(narrative history),将历史建构在事件和人物的枯燥叙述上,试图尽最大努力追求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反对将因果逻辑强加于史实之中,因此它也将史学研究者的主体性彻底排斥在外。脱胎于传统叙述史学的美国传统教育史学也带着这种“苛刻的客观”色彩和比较狭隘的史料攫取视野,其基本特征是:注重上流社会的教育;关注区域性的教育史研究;基本上囿于以学校为主要形式的正规教育发展史,虽然萌发了对教育实践意义的思考,但是终究还是被传统史学观所羁绊。孟禄(Paul Monroe)的《教育史教科书》(A Text.Book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侧重教育思潮,卡伯莱(Ellwood Patterson Cubberley)的《美国公共教育》(The Public Schools in America)侧重公立学校教育制度史。这种以关键教育事件、人物和正规教育的叙述为基础的教育史学,充斥着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WASP)主流价值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这种直线进步史观、自上而下的史料发掘视角、教育思想和制度的严格二分法、学校教育史、叙述史学取向基本确立下来。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教育史学面临学科危机,不断地被质疑其价值。随着“许多着名专业历史学家加入了教育史研究者的队伍,他们对于传统史学下成长起来的传统教育史学只关注学校和大教育家的做法感到不满,认为如果教育史领域不完成变革,新史学的变革也就无法完成。”[1]
至50年代中期,美国在经历大萧条和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重建运动,加之受到当时社会科学史学的影响开始由传统教育史学向新教育史学转向。其在研究范式上最突出的特征便是在历史编纂方面从传统的叙事史学(narrative history)转向受到社会科学影响的问题意识史学(problem-oriented history)。20世纪70年代后,在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和新文化史学影响下,“劳工阶级教育史,少数民族教育史和多元文化教育史、城市教育史、儿童史、地方史成果不断涌现”[2],新教育史学又向新新教育史学转向,本文所要论述的就是美国教育史学的第二次转向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特征。
二、美国新教育史学转向中问题意识的渊源
对于美国新教育史学中问题意识的渊源探究主要可以追溯到三个方面:
首先,受法国年鉴学派历史研究观念转变的影响;其次,20世纪初以来美国教育史在学术与职业的功能意识上所面临的两难之争;最后,美国实用主义思潮和功利主义传统的桎梏。
年鉴学派与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最大的冲突点便是在历史的研究目的上。实证主义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客观主义的衣钵,主张研究应该如实客观地重现历史的真情实景。而年鉴学派则认为对历史研究应该立足于一个基础--“现实问题”.马克·布洛克(Marc Léopold Benjamin Bloch)对于历史研究的目的直言不讳到“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3].从这个立足点出发,年鉴学派将历史研究者的主体性价值和历史的因果关系重新植入了历史研究之中,通过对历史研究程序的修正来确立自己的主张,这一程序的具体化表现便是“问题史学”.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LucienFischer quot)则直接把这一修正程序解释为“问题的提出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初始点,没有问题也就没有了史学的意义。”在对历史“如何发生”的基础上继续追问历史“为什么”发生,这种追溯是将历史研究者投入到历史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结构中去,它并没有完全抛弃传统的叙述,而是认为历史研究靠单纯叙述是不够的,必须利用研究者的主体能动性去分析和补充。美国教育史学在这一由传统叙述史学到问题史学意识的转向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也是美国新教育史学转向的推动者--劳伦斯·克雷明(Lawrence Archur Cremin)。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无论是在对美国公立学校的历史概念的考察, 还是对公共教育与美国未来的关系探究, 克雷明都竭力“让证据本身说话”,并没有对教育家们就公共教育发表的言论推导出任何结论。[4]
这一时期的克雷明还秉持客观主义的精神信条,追求用一种自然科学的方式在官方史料的基础上实现对历史的还原,他生怕这样的叙述沾染意思臆想揣测的气息。但是到1961年,其在研究进步主义的专着《学校变革》(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的时候,似乎一夜之间也“沦陷”于实用主义的大潮之中,抛弃了那种超然于一切,述而不作的“科学历史学”的一贯做法,明确提出了“学校变革是必要的也是极具重要意义的; 学校教育必须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 否则就失去活力。”[5]
在此之后,克雷明借用“大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深入到某个时间的“内部”结构中去,或隐或明地陈述着对历史问题的探究和自己的思考。
另一个在美国教育史学研究范式转向中起发酵作用的因素,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教育史所经历的一场学术取向还是职业取向的争论。众所周知,教育史学科是伴随着近代教师教育而产生的,而其脱胎的母体是历史学。
换言之,教育史是应时代的要求从历史学科中分离出来的一门旨在为教师教育服务的专门史。由于历史学科的学术性和教师教育的职业性两者之间的张力,使得美国教育史在创立伊始,便面临着学术取向还是职业取向的两难窘境。在大学历史教师看来,教师学院和教育系的教育史课程极其缺乏学术性并且在研究意义上毫无价值可言,其本身就是一种内容空洞,缺少技术方法素养。另一方面,早在1908年,约翰逊(Henry. Johnson)和萨苏拉(Henry. Suzzal)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对那种学术主义者无不厌恶的警告道:“如果教育史想要在教师教育领域有所成就的话,就必须使其拥有更多的‘专业内容',那就是必须与我们的教师和教育管理者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内容,而不是狭隘的囿于历史学家荒谬的学术怪圈之中。”[6]
之后,在30年代“社会重建主义”(socialreconstructionism)思潮下,职业取向和社会问题意识一度占据主流,巴茨(R.Freeman. Butts)和安德森(Archibald Anderson)在任《教育史季刊》(History ofEducation Quarterly)编委的时候便主张教育应该成为一项社会改造的工具。
他们认为,教育史学科地位的确立必须沿着问题意识展开。安德森在其论文《教育史在教师培训中是否扮演有用的角色?》(Is there a Functional Role for The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中迫切地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教育史的研究内容必须抛弃在传统的学术课程中所信赖的史料,而把攫取的眼光放在能对解决当今问题和教育政策问题起作用的材料上。”[7]
虽然在之后的美国教育史学界摩尔曼(Arthur Henry Moehlman)、古德(Harry Good)、爱德华兹(Newton Edwards)和吴顿(Flaud Wooton)等人在“问题意识”的理解层次上存在着争议。例如,爱德华兹反对教育史单纯的从属于当今问题的解决,认为“历史应该是一种对既定空间和时间的综合性理解。”[8]
但是,他们并没有推翻“问题意识”,相反他们的质疑对问题的解剖更加深入,让“问题意识”法更加趋于成熟。美国“历史基础委员会”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为美国教育史研究会(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递交的一份关于美国教育史研究状况的调查报告,委员会明确“希望在教育史领域应当使其采纳问题意识法的专业计划中发生更为直接的联系。”[9]
最后,美国新教育史学中的问题意识还得益于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的桎梏,和在此传统下30年代的进步主义思潮。“美国文化中工具理性始终是压倒价值理性的,实用主义在美国成为一种传统,而史学深深浸润在这种传统之中,历来有着自觉为现实服务的倾向。”[10]
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特点首先是理论与实践即史学理论的构建与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紧密结合,其次是注重历史的现实效用。而这一“实际效用”按效用范围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历史研究在国内外政治中的工具作用,也就是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李德(JK.Reed)在1949年所说的“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之后新保守派(neo-conservative school)的“和谐论”(Harmony Theory)与“新左派”(New Left)的“冲突论”(Conflict Theory)无不从政治现实出发来研究历史;二是历史对于人们生活的实用价值。这一点从鲁滨逊(James H.Robinson)所说的历史知识对于普通人的现实功用,到比尔德(C. Beard)、贝克尔(Carl Lotus Becker)提出的’历史的用处是什么‘这一美国式的问题“都可以看出美国历史研究中所一以贯之的对解决现实问题的情怀。20世纪30年代后,伴随着大萧条后的”社会重建“而兴盛的进步主义思潮更是将”问题意识“的价值进一步凸显。借用杜威(John.Dewey)在当时的那句名言:”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如果我们的教育要想对此发挥一点点效用的话,那么也必然要经历一场相似的变革。是时,杜威的信徒如康茨(J. C. Kants)、克伯屈(William Heard Kilpatrick)和拉格(Harold Rugg)等人组建了“教师学院特别讨论团体”,企图让全社会意识到教育在社会改造和重建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还提出了“教育的社会基础”课程。他们把基础课程的目标定位于挖掘那些对于学校和社会基本问题的解决有作用的材料。
在上述三股主要力量的作用下,美国教育史学在保留传统编纂方法中关于学校教育发展的史料性陈述以及作为历史方法要素的编年史体例的基础上, 借鉴当代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材料,从传统的单纯叙事取向开始向以叙述为基础的问题意识转变。
三、美国新教育史学转向中的问题意识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新教育史学在历史编纂方面从传统的叙事史学转向新史学的问题史学的过程中,“问题”便是美国新教育史学家们解剖历史的“微创口”.他们力图在宏观背景的抽象铺叙上以微观化问题的研究进行切入。这些单数或复数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历史的沿革紧密结合的。当然,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必然会导致对“问题”这个词的内涵的多元化解释。
美国新教育史学家所探寻的问题意识主要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以教育史学家所处的当下社会问题为取向,这一取向主要来自上文已论述的大萧条后期对教育与社会、学术与职业的利益博弈和之后的年鉴学派关于历史现实价值的思考。早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为数众多的进步主义历史学家诸如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特纳(F. J. Turner)和贝克(C. Becker)在社会大萧条的社会反思下,以“新重建主义”(New Constructionism)为大旗,主张建构一套“有用的历史”.这种有用的历史构架不但关注历史的社会效用,还把目光放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价值上。卡伯莱在《美国公共教育》的前言中就批评传统的教育史一直“建立在迂腐陈旧的教育理论之上”,“缺乏对当前教育问题的敏感性”.巴茨较早运用问题意识的方法进行教育史研究,并直言道:“我们如果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学术成就上,那么教师学院的教育就面临着失去与社会现实性之间的联系。”[11]诺巴尔(Stuart G. Noble)也强调“教育史是一门功能研究而不是人文研究”.[12]
尽管这种取向性一直被冠以“狭隘的现时主义”(Presentism)和“辉格谬误”(Whig mistake)的帽子,但是作为实用主义者而言,以现实问题为立足点,对史料进行特有角度性挖掘在摆脱自身学科危机的同时,也架起了教育史与社会、教师教育等领域的桥梁。
其次是以历史形成中的教育问题为取向。克雷明在《美国教育史》中实际上将叙述史学与问题意识进行了比较巧妙的融合。在一开始,克雷明便试图提出并解决问题。他首先从什么是“教育”这个“问题”出发来展开他的理论假设, 然后将这种理论假设作为线索串联起书中庞杂的教育史料, 说明在美国教育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 教育结构、教育观念以及教育生活是如何变化的。随后克雷明还围绕着“什么是教育? 教育等于学校教育吗? 教育机构有哪些? 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教育结构由什么成分组成?它与社会的关系又如何? 克雷明正是从他在美国教育传统,以及公共教育中所提出并阐述的一系列问题来构建美国教育史框架的。”[13]
凯茨在《美国早期学校改革的讥讽》(The Irony of the Early School Reform)中就以“早期学校改革服务的阶层问题”为线索,最终发现中产阶级在改革中无比巨大的影响力,也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这种取向在激进主义者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斯普林在《美国教育》(The Education of America)一书中便始终贯穿着对多元文化、种族、学生在教育中的分层等问题的思考。这些问题存在于不同时期,或者在教育演进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样式。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哪一种问题意识,都没有彻底抛弃对传统历史叙述。事实上,从早期的克雷明,直到里帕和韦布(L. Dean Webb)的《美国教育史》(American History of Education)我们都可以发现美国新教育史学家在传统历史叙述基础之上对历史问题进行系统性挖掘所做出的努力。
四、美国新教育史转向中问题意识的意义
年鉴学派的史学大师马克·布洛克曾说:“只有一门关于事件中的人的科学,而这门科学的任务是把对死者的研究和对活人的研究结合在一起。”[14]
当教育史研究分析过去的不同事件本身的历史条件、尤其是用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的价值观念来考虑每一次事件时,我们必须担负着一种永恒的价值责任去思考历史的因果关系,并在这一逻辑中搜集教育史问题解决的经验,以期对当下乃至未来的教育生活和政策制定能有一丝丝的效用。
“问题意识”是教育历史研究和实际效用之间最好的媒介,诚如劳凯声教授所言,“学科史就是问题史,人类就是在不断地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才不断地启迪思维、积累知识并推进学科的产生和发展的,因此是问题而不是学科才是学术研究的原初起点。”美国教育史正是借助于这个媒介,并在如克雷明、巴茨和安德森等一批新教育史学家的努力下,实现了教育史研究范式的转向,从而逐渐摆脱了学科自身岌岌可危的境地。首先,从实际效用上来看,教育史的问题意识对于其书写范式而言,由单纯叙述为主的传统叙事史学转变为以分析为主的问题史学,可以很好地串联起因“教育”内涵扩大而涌进的庞杂史料,用史学家的主体性最大程度地置换出史料价值。其次,问题意识也大大强化了教育史的实用价值。一直以来,教育史学科面临的最大危机便是“由于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 尤其是由于对应用、实用、功利、利益的普遍追求,因而,支持像教育史这样的基础学科研究的资源日益贫乏。”[15]
因此,教育史研究者一直抱有对现实的埋怨,试图臆想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会在瞬间升华至某种可以理解基础学科理论价值高度,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教育史学科从诞生之始就担负着教师培训这一实用主义的使命,只不过后来随着学科地位的提高而与此目标渐行渐远,所以我们何不换一种思维,从教育史本身出发,以对教育实际问题的关注来指导教育史的书写范式,这种中观性理论也不失为一条解决教育史学科自身危机的途径。
参考文献:
[1] 周采。 美国教育史学:嬗变与超越[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2] 周采。 当代西方教育史学的发展[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3] 赵建群。 论“问题史学”[J]. 史学理论与研究1995(1):92;姚蒙。 法国当代史学流派--从年鉴学派到新史学。 香港三联书店,1998:47-48.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对研究下的定义,研究是多层面的活动,包括观察、提出问题、通过阅读书籍与其他信息资源查找结论,制定研究和学习计划,根据实验研究数据对已有结论作出评价、分析和解释,提出预测等。①研究性教学是以培养学生的研究性意识、研...
从西方世界教育学发展的路径来看,虽然其都源自于希腊的教育传统,但之后随着各国教育的发展总体上形成了以德国Pedagogue为典型的德国模式和以美国Education为典型的美国模式.从我国教育学发展的历程来看,20世纪初期我国从日本引入的教育学和新中国成...
近代传统史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临诸多质疑,主要是因为传统叙述史学(NarrativeHisto-ry)将历史建构在关键事件和人物的枯燥叙述上,试图通过对埋藏的史料加以精细的考据研究,尽最大努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让史料本身说话,而史学家个人关于史...
美国职业技能标准的设计和制定起步较晚,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受美国经济持续下滑影响,美国施政者开始认识到制定一套职业分类标准的重要性,通过借鉴其他工业化国家相关成功经验,于1977年引进职业分类标准(StandardOccupationalClassification,简称...
资助包(FinancialAidpackage)计划最早起源于美国,是美国混合资助模式的主要载体,也是其学生资助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其成功经验已被多个国家所采纳和借鉴。近年来,资助包计划也被引入我国,并在少数高校试行,今后还有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进一步助推我国教育...
数学作为实用性学科,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但数学作为一门理性化的学科,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实用性、严密的逻辑性和推理性,往往会导致教师用一种非情感的教学手段进行课堂教学,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很难得到应有的关注。这与当今...
本研究试图通过对美国学后托管项目实践与经验的介绍与分析,以期为国内的相关研究和政策实施提供参考和借鉴,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因“减负”而提早放学所引发的“三点半”难题。...
第三章美国社会机构及组织对中小学天才儿童教育的支持一、美国天才儿童教育的主要社会机构及组织。在美国,除了各州政府在政策方面给予天才儿童教育引导和支持之外,天才儿童教育研究机构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家及州级层面从事天才儿童的研究机构,为学校...
第一章美国中小学天才儿童教育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历史发展一、美国中小学天才儿童教育的社会文化背景。(一)美国注重天才儿童教育的背景。天才儿童与普通儿童相比,他们的生理和能力都有不同,存在特殊性,同时他们对教育也有着特殊需求。要根据天才儿童...
在幼小衔接教育中, 幼儿园和教师应将家长的参与作为改善教育、提高质量的一项重要策略, 保持幼儿园与家长的双向沟通与配合, 共同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 形成家园共育的教育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