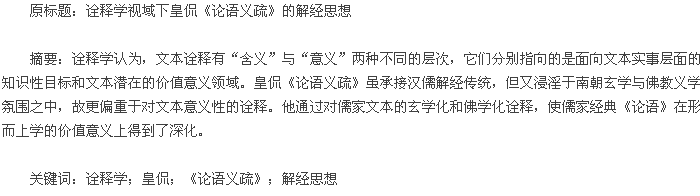
皇侃(488年~545年),吴郡人,师事贺玚,精力专门,尽通其业。《梁书·儒林传》云:“尤明三礼、孝经、论语起家,兼国子助教。”又云:“撰论语义十卷,与礼记义并见重於世。”[1]皇侃精通儒经并撰有《论语义疏》十卷见重於世,他又逢南朝玄学、佛教义学之风盛行之际,使得其对儒家经学之思想的诠释深具时代特征。本文拟对皇氏所撰《论语义疏》进行分析,以见其经学思想之诠释特色。
1 诠释学对文本“意义”问题的论述
诠释或诠释学的首要问题是意义问题。在西方诠释学的传统中,与“意义”相对应的英语词汇分别是“Meaning(含义)”和“Significance(意义)”.德国诠释学学者阿斯特说:“对于每一个需要解释的段落,我们必须首先问文字在陈述什么;其次,它如何在陈述,陈述句具有什么意义(Meaning),它在文本中具有什么意味性(Significance)。”可见,“Meaning”和“Significance”在文本诠释学中是有区别的。在阿斯特看来,“Meaning”指的是文字所构成的陈述句所陈述的具体内容;“Significance”指的是陈述句所陈述之具体内容在文本之中的价值性。
与“意义”相对应的德语词汇分别是“Bedeutung”和“Sinn”,弗雷格在《含义与指称》一文中对这两个语词进行了区分。“Sinn”是名称所表达的内涵,即阿斯特所说的“Significance(意味性)”;“Bedeutung”是指称,即指示的物或对象,倾向于实存之物或文句之实指层面,相当于阿斯特所说的“Meaning(意义)”.可见,二者对于文本意义的划分有两个层面:其一,文句指称的实指层面;其二,文本背后的价值性的潜在意涵。
文本诠释学的意义问题在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诠释学那里得到了更高和更深的超越,进入到了本体论的诠释。海德格尔说:“在领会着的展开活动中可以加以勾结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意义……先行具有、先行看见及先行把握构成了筹划的何所向。意义就是这个筹划的何所向,从筹划的何所向方面出发,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得到领会。”
意义是领会者在领会活动中进行的勾结、筹划,是对于先行具有、先行看见、先行把握的“此在”的理解和解释。伽达默尔说:“谁想理解某个本文,谁就总是在完成一种筹划。一当某个最初的意义在本文中出现了,那么解释者就为整个本文筹划了某种意义。一种这样的最初意义之所以又出现,只是因为我们带着对某种特殊意义的期待去读本文。”可见,对于文本的理解即是一种筹划、一种意义的筹划,是和解释者对于某种意义之期待密不可分的。
从阿斯特等人关于诠释学理论的意义问题的阐述中可知,文本的意义大致有两个层次:其一,由文本自身的语词系统所构成的最基本的和最稳定的内容,即“Meaning(含义)”;其二,文本在与不同时代的解释者或领会者的对话中生产出来的具有价值性和变化性的内容,即“Significance(意义)”.对于一个具体文本的诠释,要么诠释其含义,要么诠释其意义,亦或兼而有之。
这样就揭示了文本诠释的两种向度:知识和价值(意义)。美国诠释学学者赫施说:“含义和意义这两个概念与知识和价值这两个概念相似。一方面,含义是解释中稳定的、知识的目标,没有它,更广泛的人文主义的知识将不可能。另一方面,意义的主要意趣则在不稳定的价值领域。特定语境中的含义的意义决定了它在那个语境中的价值。因为意义命名了文本含义的关系,而价值是一种关系,不是实体。”含义是文本诠释之中的稳定性的知识体系;意义则指向文本的价值领域,是具体语境中的价值关系,它以文本之含义为基础,但又和具体之时代和解释者有关,并非是稳定之知识体系。
文本诠释的如上区分使我们对于皇侃《论语义疏》经学诠释的不同向度有了清晰的理解。皇侃所处之时代为南朝萧粱,其经学思想上承两汉解经训诂之学,又深受南朝老庄玄学和佛教义学的深刻影响。从诠释学的角度看,两汉解经偏重于文字、典故与旧制之训解,是弗雷格所说的“指称”,倾向于实物层面或文本之实指层面;亦是赫施所说的知识性的诠释,它关注的是文本中最基本的语词。所以,它所偏重的是训诂的方法---具有明显分析性的方法。在皇侃的《论语义疏》中,保存有汉儒马融、郑玄等人之注解,以及他本身拥有的深厚的经学训诂能力,使得他对于儒家经学中的名物制度等的训解深深扎根于经学传承之中,避免了南朝义学的蹈空之嫌。如《论语·乡党》“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一句,皇侃训解道:疾,谓孔子疾病时也……此君,是哀公也……东是生阳之气,故眠首东也……加,覆也。朝服,谓健时从君日视朝之服也。拖,犹牵也。绅,大带也……[6]
从皇侃的训解中可知,他是逐字对《论语》经文进行了疏解,这是汉学解经的特点,是知识性的诠释。他对于文本的内涵并没有实质性的增加,只是围绕着文本自身的语词进行的解释,它所指向的对象只是文本中具有确定性的含义。
皇侃身处玄学激荡的六朝时期,玄学和佛教义学对其经学诠释思想的影响亦是深远的。相对于汉儒解经传统而言,皇侃的经学诠释呈现出了价值性或意义性的文本诠释向度。这就是阿斯特、弗雷格所说的“意味性(Significance)、Sinn”,是文本背后的价值性的潜在意涵;亦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所说的领会者或解释者的筹划。它是不稳定的价值领域,是具体语境中的价值关系。皇侃援引玄学、佛教义学进行经学诠释,避免了汉儒泥于文字的狭隘性,更关注文本潜在的主旨和意涵;超越了汉儒注释中对于具体历史事件和知识的积累和关注,偏重于概念之间抽象性的思辨关系,使得这种诠释更具有哲学意蕴。出于这样的影响,皇侃《论语义疏》不再停留于文本确定性的含义方面的诠释,而是通过辨名析理而进入文本不稳定的价值领域,进行解释者的意义筹划活动。这种意义性诠释向度关注的是文本之言外之意或潜在内涵,往往忽略或较少留意语词的指称(Bedeutung),所以它能够超越文本,并增加文本的意义。
2 《论语义疏》的玄学化诠释
六朝经学反汉儒而动,超越了繁琐的经典训诂这种指向文本含义的诠释向度,在玄佛思潮影响下,更关注指向文本意味性的诠释向度。此一向度偏重的是文本语词的意向性层面,注重于文本潜在的关系结构(文本的意味性)和可能的生成境域(不稳定的价值领域),所以是不稳定的、多元化的和开放的,正是伽达默尔所说的“带着对某种特殊意义的期待去读本文”.皇侃借助时代思潮,利用玄学思想深化了对于《论语》经学的意义诠释,使得《论语》的意义呈现出了玄学空灵简洁之韵味。
首先,在对《论语》经文和注文进行疏解的过程中,皇侃运用老庄玄学化的语词,筹划了文本的言外之意,重新建构了文本的可能性的价值(意义)领域。如“筌蹄”、“鱼兔”,显然源于《庄子》,却被皇侃用于义解《论语·公冶长》“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一句,皇侃解道:子贡此叹,颜氏之钻仰也。但颜既庶几与圣道相邻,故云钻仰之。子贡既悬绝,不敢言其高贤,故自说闻於典籍而已。文章者,六籍也。六籍是圣人之筌蹄,亦无关于鱼兔矣。六籍者有文字章着焕然,可修耳目,故云“夫子文章可得而闻也”.“筌蹄”、“鱼兔”语出《庄子·外物》,其文曰:“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在庄子看来,筌和蹄只是捕捉鱼与兔的工具,正如语言只是表达玄理的载体。捕捉者的目的不是在于持有筌蹄,而是在于鱼兔;言者的目的在于由言而体悟玄理,并不在于作为工具的语言。所以,鱼兔得而筌蹄忘,玄理明而名言绝。何晏对于此句经文的注解为:“章,明也。文采形质着见,可得以耳目自修也。”何氏的注解重点在于“章”字,基本上是依文释义的字面解释;皇侃则着重于“文章”一词的诠释,他借用《庄子·外物》中“筌蹄”、“鱼兔”等词在原文中的语意,将“文章”解作“六籍”,将“六籍”比为“筌蹄”,并和作为玄理的圣人之道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六籍即儒家六经只是作为圣人表达玄理之工具,与譬喻为鱼兔的玄理是无关的,它们只能起到陶冶耳目的作用。正如得鱼兔而忘筌蹄,对于圣人之道的体悟也只能是超越于“六籍”言语之外的心领神会。何氏的名词的解释是知识性的,皇侃的名理的解释则是意义性的。
再如“方内圣人”、“方外圣人”,被用于义解《论语·宪问》“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逊悌,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一段经文。
皇侃解道:原壤者,方外之圣人也,不拘礼教,与孔子为朋友。夷,踞也。俟,待也。壤闻孔子来,而夷踞竖膝以待孔子之来也……孔子,方内圣人,恒以礼教为事。见壤之不敬,故历数之以训门徒也。言壤少而不以逊悌自居,至于年长犹自放恣,无所效述也……言壤年已老而未死,行不敬之事,所以贼害於德也。
皇疏中的“方内圣人”、“方外圣人”化用于《庄子·大宗师》中的“游方之内”、“游方之外”.其文曰:“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则陋矣。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彼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痪溃痈,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假于异物,托於同体;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复始终,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
庄子将孔子视作游方之内者,方内之人重视礼教对于自身之节制,言行均要中礼。他借孔子之口盛赞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等人为游方之外者,方外之人齐生死,与大道相耦合,忘乎内外,让生命遵循自然而变化,悠游于尘垢之外,逍遥于自然之境,又怎能据守世俗礼节呢!汉儒马融对经文“原壤夷俟”的注解为:“原壤,鲁人,孔子故旧也。夷,踞也。俟,待也。踞待孔子也。”
马融的注也是随文释义,和皇侃疏文基本一致,此即是文本诠释中“含义”或“知识”诠释的向度,正是赫施所说的“解释中稳定的、知识的目标,没有它,更广泛的人文主义的知识将不可能”.所不同的是,皇侃将“方内”、“方外”引入《论语》经文中,对于原壤和孔子,各冠以圣人之名,只是一为方内、一为方外,使方内不遵礼教的原壤玄学化,成为不拘礼教、率性自然的方外圣人。皇侃超越了经文文辞层面的知识性诠释,进行了深具玄学化的意义性诠释,使原有经文的意境更具有形而上的哲学意蕴。由此可见,何晏以及前引汉儒马融的知识性注释,是在文本整体关系之内做出的整理疏解,两者虽然引入了新的语词,但是就文本的意义层面而言,这种诠释基本没有产生出新的 “意义”.相反,皇侃的意义性向度的诠释,则总是要比原有文本多出一些东西,这些多出的东西不能在文本之中找到依据,但正是这些多出的“意义”才丰富了文本的生命力。
所谓读经,即为读“经典”。说文曰:“经,织也。”经的本意是织布的纵线,后被引申为恒常不变之准则的意思,如《中庸》说:“凡天下国家有九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