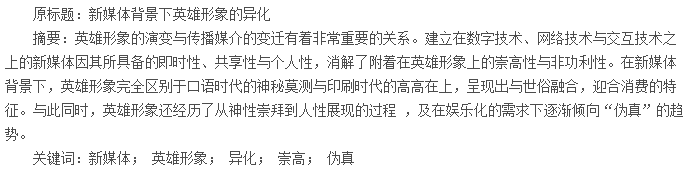
在我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中,“英雄者,乃人群中之豪杰,为天下先者”(扬雄《法言》),是有胆识、有谋略、有正气,真正立于天地之间的人。英雄作为一种民族精神,是实现“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榜样,是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标杆。
不论哪个时代,社会总需要有一些英雄人物来支撑,人类生存状态的改进也需要一种英雄气概去突围,个人的生存境遇同样离不开英雄主义精神的维系。
英雄作为一种理想的人格外显,崇高是其形象塑造中最重要的特征。在欧洲,第一次提出“崇高”概念的是公元1世纪古罗马时代的希腊文艺理论家朗吉努斯,他在其名着《论崇高》中认为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并概括了崇高所包含的五个方面,即庄严伟大的思想、慷慨激昂的感情、辞格的藻饰、高雅的措辞和尊严的结构。
在中国,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提出的善、信、美、大、圣、神六个等级,“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是我国传统美学中对崇高认识的代表思想之一。东西方对崇高的定义虽然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崇高是一种能够带给欣赏主体强烈的心灵撞击,进而获得强烈的激昂情绪,引起人们产生敬仰和赞叹的感受,从而提升和拓宽人的精神境界的形象特征和审美对象。
然而,在新媒体的条件下,不管是英雄还是英雄形象都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新媒体下的定义:“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两种定义,各有千秋,互为补充。就目前而言,较为通行且相对全面的新媒体概念是:一种相对于传统媒体,诸如报纸、广播、杂志等,依靠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交互技术,通过互联网链接手机、电脑等终端设备,进行信息的传递与接收的媒体形态。新媒体具有即时性、共享性、个人性等诸多特点,这些特点正深刻影响着英雄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它逐渐消解原本附着在英雄形象之上的崇高感、敬畏感和仪式感,使之逐渐呈现出一种单一化、娱乐化和庸俗化的特征。
一、失语的英雄——崇高被撕裂
英雄形象所具有的崇高性是与特定的媒体方式紧密联系的。马歇尔·麦克卢汉曾说:媒介即讯息。媒体及媒体方式的更替深刻影响着它所传递的内容。在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口头文学是信息保存和传播的主要方式。到了农业文明时期,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推广,拓宽了信息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使得信息交流的频率和内容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在我国传统文化体系中英雄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主要是依靠口头文学和书面阅读的方式进行,尤以后者为重。然而,阅读一直是一种以精英主导、参与、扩散的文化传播方式,因为学习、理解、运用文字所需要的时间远远超过观看图画理解含义的时间。“生命体接受光信号的功能至少进化了5亿年,人类接受影像信息的功能至少进化了300万年,而读的能力人类只练习了几千年,作为个体则不过学了几十年,儿童才学了几年,所以图能吸引任何眼球就不奇怪了,而儿童喜欢图更是天经地义”
。美国传播学者梅罗维茨也说过这样的话:“即使对有文化的人来说,阅读也是一项辛苦的工作,例如页面上的墨字必须一个词一个词,一行一行,一段一段地扫过。为了获取讯息你必须认真阅读。为了阅读这些词,你的眼睛必须经过训练,就像打字机的滚筒移动纸一样沿着印刷的行移动。”
因此,英雄形象在以纸为载体、文字阅读为主的传播方式下所具有的内在意义与精神指向必然会凝结成为崇高二字。文字自身的严谨与冷峻使得英雄形象所具有的崇高性得到更大程度的展现,带给人们庄严、敬畏和强烈的震撼感。“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荆轲,“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的项羽,“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李广,“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岳飞,“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等,无不体现了这种闪耀在英雄身上的崇高感,文艺作品的创作者们在表现这些英雄的时候也都是带着一颗尊敬、赞扬的心,真诚地歌颂英雄身上所闪耀着的精神光辉。
与此同时,口语和文字塑造的英雄形象往往是模糊且具有神秘性的。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口头传播和书籍传播的抽象性使得受众因无法对文本中出现的英雄人物有一个具象的认识,因此会运用自己的想象力不断丰满文艺作品中的英雄形象,不自觉地参与到英雄形象的塑造中去。譬如司马迁在《项羽本纪》的开篇写到: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人们在阅读这样的文字时,虽然没有看到一个具体的人物容貌,但是蕴含在文字当中的气势是非常明显的,短短数语,寥寥几句就将项羽少年时的英雄气概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来。文字描写的精炼性、多义性让读者能有更为宽旷的想象空间,这就是中国文学艺术讲究留白的精妙之处,它充分激发了受众对某一个艺术形象的创造热情。因为横看成岭侧成峰,人们看不见具体的画面,如此便从对那些故事、文章以及传说的抽象印象中,绘制出一个源于文艺作品但同时又属于自己的英雄人物,加之个体的生命体验各有不同,因而英雄形象最终是众多愿望性想象的集合体,它集结了人们对于伟大、崇高、无私等诸多美好的期望。黑格尔说,“美是理念的感性的显现形式”,美是与心灵相通的,运用传统媒体进行传播的文艺作品所体现出的抽象性、象征性、概念性,给读者提供了仔细回味、反复咀嚼乃至思接千载的文化空间。正如伟大的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所说的:“书面文字远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提醒物:它在现实中重新创造了过去,并且给了我们震撼人心的浓缩的想像,而不是什么寻常的记忆。”
数字技术的发展促使社会主流传播方式由口头文学和书面阅读变更为以移动电视、网络、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希利斯·米勒说,尽管印刷的书还会在长时期内维持其文化力量,但它统治的时代显然正在结束,新媒体正在日益取代它。与此同时,米勒又补充道:这不是世界末日,而只是一个由新媒体统治的新世界的开始。新媒体改变了艺术审美的方法,用视听结合的形式去除了传统文艺作品中的模糊性、距离感和神圣性。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完全迎合了大众文化为主体的当代文化体系以读图为主要交流、分享、传播的信息交换方式。在新媒体背景下,图像成为英雄形象传播的最主要的方式,传播终端不再是书籍、文字,而是电子计算机、数字电视、移动手机,英雄形象不再是阅读和思考之后的结果,而是直白干脆的画面,它抽离了传统口头文化或纸质文学中的想象力。尼尔·波兹曼说,电子和图像革命所产生的最令人不安的后果是“电视呈现出来的世界在我们眼里已经不再是奇怪的,而是自然的。”
想象中的英雄开始以一个个具体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是,除了最开始的一点点惊喜之外,越来越多的是失望和厌恶。因为,书籍作为最主要的传播媒体,它所具有的稳定性和严肃性能把英雄形象作为一个固定的符号长久地保存。人们在阅读过程中是安静的、专心的,英雄形象是在行云流水的文字中慢慢塑造而来的,英雄情结则是在字里行间的蕴藉中逐渐传承的。但是新媒体不同,讲究刺激、暴烈、具有瞬间吸引力,画面是第一位的,人们打开网络一下子就被眼球主宰,受媒体限制,影视作品变得越来越通俗、简单、幼稚,因此即便是抗日剧也是飞车爆炸、帅哥美女、大场面样样不少。有学者指出:“大致言之,读小说是工业时代(甚至是农业时代)的发明,因此,慢、重、深就成为文学阅读的基本特征;看电视、网上冲浪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于是,快、轻、浅就成为读图时代的重要表征。”
现在人们一天接受的信息量比古代人一年信息量还要多,尼葛洛·庞蒂在《数字化生存》中把“比特”称之为“信息DNA”,这种“信息DNA”能以光速进行传播,而这正是新媒体得以致胜其他媒体的关键之一,即便捷的复制能力。
当今时代,每天都有上万亿条信息被创造、交流与传播,人们现在每天了解的信息与以往任何历史时代相比都多得多。技术缩短了世界的距离,地球村成为事实。新媒体高效便捷的复制手段,使得传播的范围和速度都得到了巨大提升。然而,单纯的机械复制导致新媒体在传播过程中缺失了英雄形象本身的韵味。如同文字一般,旧时写有文字的纸不能随意丢弃,“敬惜字纸”是一种守则。但是现在伴随着机械印刷而来的是对文字的毫不在意。英雄形象亦是如此。在不断成为随处可见、随时可得的商品之后,英雄形象本身所具有的那种崇高性、神秘性就荡然无存了。在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曾提到膜拜价值与展示价值的问题。他指出,艺术品由于复制方式的多样化与便捷的技术手段,使得复制品唾手可得,艺术品越来越成为一种可被展示与被消费的对象而不是顶礼膜拜的对象。对于英雄形象而言,一旦脱离舞台、神龛、名着等特定的语境之后,就很容易成为大众的消遣对象。因为英雄形象的欣赏需要特定的场合和情境,仪式感是其能否传递崇高和敬畏的重要条件。在人类学范围内,仪式是一种能够准确传达和强化某种观念,并且引起相应的特定情绪的人类行为。被引发的情绪反过来又可以强化这种仪式所要表达的意义和观念以及社会关系。对于英雄形象而言,新媒体的互动性、共享性打破了仪式进行的封闭和严肃,从而使得它想要传达的庄重和崇高的感觉被冲散直至消失。回想一下,在电脑上看电影与在电影院看电影两种不同的欣赏就会发现其中的奥秘,英雄形象所需要的庄严肃穆的舞台在新媒体的条件下是无法满足的,它的便捷性消解了这种由于距离感而产生的特殊的审美感受,因为在马桶看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再激动也不会涕泗横流。
二、“超级英雄”的狂欢——“伪真”的娱乐需求
同样的黄飞鸿,在关德兴的时代稳扎稳打、细致真实是塑造其英雄形象的必然,而到了徐克时代,飞檐走壁、特效炫技就成为稀松平常的事情,英雄形象的崇高性在不断被撕裂之后,越来越被娱乐化的“伪真”裹挟。发达的技术手段使得合成、特效成为大众造梦的机器。人们热烈地参与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图像运动中去,在一个又一个视觉奇观中满足自身的需求。因为英雄情结是人的主体性的心理情结,在安全需要、生理需要等获得满足之后,有追求“尊重”和寻求“自我实现”的需要,每个人都有做英雄的欲望。于是,动不动就拯救世界、拯救地球的英雄越来越多,俨然狂欢舞台上的演员。新媒体的低门槛、重参与、易制作使得普通大众也生出了英雄梦,故事的新奇性、画面的刺激性成为是否能够流行、获得赞同的主要标准。在这种狂欢化的、全民娱乐的氛围下,凭借着新媒体的强大支持,英雄形象的塑造开始无所不用其极,各种手段蜂拥而上,各种畸形英雄“应运而生”。原本试图通过英雄形象的传播达到社会教化的功能在不断削弱,英雄越来越成为某一个人英雄,纯粹为满足个人的私欲,英雄原本的社会公共属性已经丧失殆尽,“个性”夸张成为新的标签。
诚然,艺术创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有时为了使人物更加丰满、更加具有艺术表现力,难免会融入一些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做一定的虚构和夸张。例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作家为了凸显出诸葛亮神机妙算、足智多谋的特点就把曹操的空城计、孙权的草船借箭都安放在了他身上。有限度的艺术夸张和嫁接有利于人物塑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合逻辑的胡乱编造、东拼西凑就会使英雄变成一个笑话,英雄形象也变成鬼画符一样的东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抗日剧就陷·第一总百九十一期入到了这种追求伪“真”制造伪“神”的运动当中去:《抗日奇侠》的铁柱、《向着炮火前进》的雷子枫、《铁道游击队》的彭亮,一个一拳打穿鬼子身体,徒手撕裂鬼子;一个戴着黑墨镜,骑着哈雷机车,随身携带沙发;一个骑自行车表演飞车绝技,一辆单车竟然飞上火车车顶。如此雷人剧情,不靠谱的情节竟也堂而皇之地进入主流电视平台。在这些影视剧里,原本的普通人被渲染到了近乎“神”的地步,完全失去了真的本质。编创者将各种元素诸如爱情、暴力、悬疑、时尚、性感等统统塞进一部影视剧里,在完全卸下宣传教育的包袱之后,纯粹为利益将历史曲解,原本在抗日英雄身上体现的大义凛然、坚强不屈的精神逐渐被游戏化、娱乐化。我方革命军人像开了外挂的外星人一样,以鹰爪功、绣花针就轻松制服了敌人,完全丧失了基本的求真精神。英雄形象逐渐沦为一个个游戏角色,斩断了他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剥离了他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成为一个单纯过关打怪的“英雄”。
当然,文革时期因为坚持三突出原则,塑造了很多高大全式的英雄,缺少了人性温情和社会性体现,英雄形象显得单一、脸谱化。因此,王蒙在《读书》1993年第1期上发表《躲避崇高》一文之后,1994年就掀起了消费英雄主义,躲避崇高、拒绝高雅、放逐理想的思想文化潮流。这股文化潮流在新媒体时代走向高潮,其内涵的实质就是大众消费主义向精英教化主义的公开挑战。“逃避崇高、回避伟大、躲闪庄严、拒绝高雅,不期然成了一股自发的群体趋势,反英雄时代粉墨登场。”
但是,此“英雄”非彼英雄,无人性、无生命的高大全英雄是该反,但英雄情怀不能反,英雄主义精神不能反。以消费、娱乐为主导的现代市场体系直接导致了众多艺术创作倒向惟利是图的道路。崇高不仅被完全抛弃,丧失基本的求真精神,还越来越往低俗、浅薄、恶搞的道路上走。据横店影视城公布的数据,从2013年1月30日到3月2日这可查的17天的时间里,一共打死鬼子是10846个人,如果敌人可以这么轻而易举就消灭的话,那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抗日“神”剧这种抱着戏说的心态,完全不尊重史实的行为使得原本要塑造成英雄的人物变得荒诞搞笑。齐美尔悲哀感叹道,一个“文化悲剧”的时代正在到来。传统艺术中,审丑是为了通过审视生活丑获得艺术上的美从而让生活更美,然而当今时代的审丑却是单纯的迷恋丑所带来的排解压力的愉悦感。人们遵循着弗洛依德的“本我原则”,通过看芙蓉姐姐、小月月等的扭捏做作、丑态百出来缓解现实生活的紧张感。但是,这种审丑行为已经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主流行为,整个艺术审美事业走向低潮,人们沉溺在这种表层次的哈哈大笑的快感中,失去了追寻内心和灵魂深刻的欲求。
三、从神性到人性——世俗生产的现状
在对英雄的传统认知里,英雄往往是“神”,神往往也是英雄。由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和频繁的社会战乱,英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被当做神一样来崇拜和尊敬的。英雄形象作为一个精神图腾,作为一个行为典范,作为一种内心渴望,他集中体现了人民的愿望和理想,他集合了许多常人无法拥有的才能和品质,概括而言就是圣、德、贤的完美统一。因此,英雄形象的塑造也遵循着这个规律,即把英雄塑造成为智力超群、无所不知、完美无缺的神人形象。纵观中国的英雄形象都具有非常突出的神性特征。首先是外貌特征的奇特性,譬如伏羲女娲就是人首蛇身,神农更是生来长了一个水晶肚,项羽则是“重瞳子”,刘邦是“隆准而龙颜,美髯须,左古有七十二黑子”,刘备则是“双耳垂肩,目能自视其耳,双手过膝”,异于常人的外在形貌特征为神化英雄提供了第一个条件。对于中国人来说,异象通常有两种解释,一种指向祸端,一种指向福寿。在农业文明社会时期,英雄的异象自然是后者,奇异的外貌特征使得英雄一出场就获得了先天的关注和好奇,“奇”是中国英雄形象的一个普遍特征。张飞是“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关羽更是“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
试想一下,身高2.24米的姚明在人群中已经是鹤立鸡群,2.6米的张飞,3.1米的关羽怎么能不引人注目。其次是性格品质的完美性。远古创世英雄,如伏羲女娲、盘古、精卫、神农、禹舜等,都集中体现了奉献牺牲精神。从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来看都是完全的利他行为,个人私欲是根本没有的,也无所谓个人需要。从一开始,先民们对于英雄的塑造就立下这样一个标准,即英雄是没有私欲的。尔后,随着宗法礼乐制度的建立,附着在英雄身上的社会愿景越来越多。这其中,尤其是以关羽的形象塑造最为显着。关羽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刮骨疗毒、千里走单骑、华容道释曹、义解黄忠,作为一个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人物,关羽的行为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求义的心理需求。然后通过文学作品的再创造、民间传说的丰富和增添、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佛教的嫁接借用,关羽就从一个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变成了关帝爷、珈蓝菩萨,设龛祭拜,香火供奉。其他英雄也大多经过类似的过程,在其人其事不断传播的过程中经过加工、改造、增添,逐步去掉其常人特性,加强神性特质,最终变成一个可供供奉的神和一套公认的社会价值体系。
现代社会讲求个性独立,个人价值的彰显,传统英雄形象的神性特征阻碍了英雄和受众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两者是二元对立的。英雄和受众是不可同日而言、等量齐观的,二者之间保持着绝对的距离,以凸显英雄的绝对权威。普通人无法超越英雄所享有的至高地位,所有人在英雄面前都只能谦卑低头。但是依赖于网络技术、移动技术与数字技术的新的媒体条件的改变和人类内心需求的变化,使得二者之间仿若天堑的差距逐渐缩小,英雄和受众开始走向一元融合的方向,英雄身上的神性特征逐渐被人性特征所替代。萨特认为,普通人、平凡人都有可能选择“自己成为自己的英雄”。英雄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偶像,也可能是身边的人,或者你自己。《亮剑》《士兵突击》的热播充分显示出了英雄形象在当今时代不再是遥不可及而是平易近人。李云龙是抗战英雄,他骁勇善战,不仅有气魄和胆量,还有计策和谋略。他带领的军队屡屡获胜,在战场威风凛凛。他用事实证明了他是一个英雄,但是这个英雄又不是传统的具有神性的英雄,而是充满人性特点的英雄。譬如,他经常满嘴脏话,还鼓动士兵和人打架,为了救媳妇,他把整个晋西北搅得天翻地覆,为了死去的警卫员,他就血洗匪穴,更别说平常动不动就和政委打嘴仗,经常先斩后奏了。李云龙既有英雄的不一般,又有常人的小毛病,神性就在这种个人化的特征表现中被去除了。观众看到这样的英雄,非但不觉得遥远,还会觉得亲切。因为这样的英雄是有血有肉、真实感人的,他不再是神人、圣人,而是活生生的人,能做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为人民谋幸福,也会有自己的欲望,他高兴就喝酒,生气就骂人,看到喜欢的姑娘也会大胆真诚地去追。相较于李云龙,许三多更是体现出了英雄和个人的融合统一。梁启超曾提出“无名英雄”说,他认为英雄不再是少数有“胆识、勇气、智慧超群的杰出人物”,而是广大的平民百姓,是“隐于世界中之农夫、职工、役人、商贾、兵卒、小学教师、老翁、寡妇、孤儿等恒河沙数之无名英雄也”。
许三多从一个农村出身的普通士兵,不抛弃不放弃,最终成为一名出色的侦察兵,直接就是一个平民英雄的样本。这样的英雄形象,观众会有强烈的共鸣感而且更加容易代入自身感情。对于普通大众而言,许三多就是自己,出身卑微,资质愚钝,前途仿佛一片晦暗。所以当他们看到许三多一点点成长、壮大,一步步变成英雄,内心的激动是无以复加的,因为在许三多身上他们也经历了一次成为英雄的洗礼。
然而如同李云龙、许三多式的人物是英雄形象在新媒体的条件下做的一种调整,同时也是一种妥协。因为传统的英雄形象是作为一种崇拜对象而存在,他不仅作为一个伟大的英雄受到敬仰,同时还作为一种精神实体供人信仰。受制于生产力的束缚,人们面对自然灾害和朝代更迭都显示出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无奈感。这时英雄作为一个信仰的图腾就会不断发挥作用,为人们提供一种心灵安抚和精神慰藉。备受中国人尊敬的关帝爷就直接是“义”的化身。关羽作为一个已经固化的英雄形象的同时,也是作为一种信仰存在于民众的精神内在之中。人们开店做生意、建房搬家都要请一尊关帝爷,逢年过节也是一定要去烧香叩拜。人们崇尚关羽对待朋友兄弟的义薄云天,并用他的行为作为标尺去衡量一切与义有关的事件和人物。英雄成为信仰就更加具有神性特征,神性的加强又促使这种信仰更加坚定。
现代商业社会消费欲望的合法化,使得物欲、权欲、隐私、性欲等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各种各样的传播终端上,不再有观众、读者、受众,只有消费者。英雄在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语境里受人尊敬,被人供奉的崇高地位到了现代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消费文化主导的社会里遭到了巨大的落差。英雄不再是被信仰的对象,而是被娱乐的对象。当颠覆经典、解构经典、消费经典成为一种社会时尚之后,英雄形象也无法躲避。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英雄形象也不断被开发成各种各样的商业产品供人挑选、购买、使用。人们不再需要深刻体会英雄形象所具有的精神内核和灵魂诉求,只需要单纯地以一种悠闲消遣的心态打开电视懒洋洋地观看。“消费大众感到的快乐不再是全身心的沉浸式体验,他们感受到的是文化工业再生产中可以重复制造的价廉物美的艺术品备份。”
英雄形象在这场商业化的浪潮中逐渐从一个信仰的对象变成一个消费的元素。综艺舞台上关公耍大刀屡见不鲜,《三国演义》《西游记》被恶搞的段子实在不少,人们只图一乐,再无其他。日益兴起的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潮流消解了意义、精神和崇高,更多地讲求直接的感官感受。英雄形象的信仰、救赎内涵被消费、娱乐所取代。人们不再需要一脸严肃、不怒自威的关羽,而是迷恋抱着电视看着一个穿着跑偏了的苏格兰裤子的小沈阳插科打诨,哈哈大笑。百万张选票选出一个李宇春,整个社会与一个女孩子的梦想共同紧张。她是娱乐时代到来的直接例证,全民偶像的另外一个名称就是娱乐偶像。偶像取代英雄,娱乐取代崇高。表现在影视剧中就是各种戏说、改编接踵而至,譬如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抗日剧就把恶搞、暴力、武侠、美女、时尚等娱乐元素通通堆到一起,胡搅一气,满足部分观众低俗的观看欲望。人们追求的不再是形而上的精神探索,转而迷恋形而下的官能享受。英雄形象也就在这样的追求中变成普通大众的一个简单娱乐选项。
任何事物都是随着新的历史条件不断变化,英雄形象也是如此。新的媒体方式,改变了英雄形象的外在表现形式,也迫使其从崇高、严肃转变为世俗、娱乐,但其作为一种长久以来确立的精神品质还是必须葆有基本的向上、朝前的特点。新媒体作为一种传播工具虽然没有直接的宣传教化的作用,但是作为一种能够深刻影响人类的媒介还是必须要审慎对待。创作者必须明白塑造于新媒体背景下的英雄形象其异化背后的社会成因,力争在艺术和市场中找到平衡。
参考文献:
[1]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16.
[2]陈海燕.从“读时代”走进“阅时代”[J].出版人,2012(10):28-30.
[3]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体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78.
[4]黑格尔.美学:第1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42.
[5]诺思洛普·弗莱.伟大的符号:圣经和文学[M].多伦多:学术出版社,1981:227.
[6]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M].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7.
[7]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05.
[8]赵勇.媒介文化语境中的文学阅读[J].中国社会科学,2008(5):131-148.
[9]周泽雄.英雄与反英雄[J].读书,1998(9):75-81.
[10]梁启超.无名英雄[M]//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281.
[11]欧阳友权.网络传媒艺术的文化消费性[J].湖南社会科学,2009(5):134-135.
随着行业发展逐渐走向成熟,微电影的商业价值开始显现,并逐渐发展成为推动媒体传播的重要工具。本文从微电影发展背景出发,基于微电影的概念分析其传播模式与传播效果,以探究我国微电影行业的发展现状与前景。...
1998年初,蔡智恒在国立成功大学修读水利工程时,在BBS连载成名作《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这部新时代的网络作品深受网友喜爱,并在网上不断转载流传,痞子蔡这个名字也步入了人们的视野。《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被人们视为第一部网络文学作品。从网络文学发...
由互联网引发的现象尹鸿(以下简称尹):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对信息的传播方式、社会的组织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产业的运营方式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当然,也对整个电影的创作、生产、营销带来了越来越明显的改变,甚至对未...
对微电影在新媒体语境下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从播放平台的合理选择、故事内容的精心打造、品牌影响力建设、受众参与度及互动性提升四个方面,提出新媒体语境下微电影的发展策略,希望能为微电影行业的创新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在当今社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人们已经进入到新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为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同时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获取到自身想要的信息。...
2015年2月28日的新媒体,微博、微信朋友圈都被一部叫《穹顶之下》的视频刷了屏:多个污染现场寻找雾霾根源,多国实地拍摄治污经验---在沉寂一年之后,柴静归来,推出公益作品《穹顶之下》。本次的作品联合人民网、优酷同步播出,视频推出的24小时内...
就现代美学而言,视觉艺术是由点、线、面、色彩、材质等多种要素构成,而形态各异的文字则是由笔画、结构、字形等要素构成。本文研究的动态影视字幕基础要素是以文字为主体的视觉元素,包含笔画、结构、字形,再加上色彩、材质、空间、声音。...
以新媒体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在科技发展的带动下与时俱进。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已不用赘述。铺天盖地的信息洪流对人们的生活习性、生活作风乃至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在进行悄无声息的潜移默化。在大众媒介建构的拟态环境中,仍然保...
网络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越来越紧密,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如何认识网络?如何正确的利用网络,使之为人类服务?是网民乃至普通大众迫切需要理解和掌握的知识问题.可以说,提升人们网络媒介素养的紧迫性前所未有.因为只有提高人们的网络素养,才能冲破...
近些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进步,我国新媒体影视也随之开始迅猛发展,但是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影视制作与传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