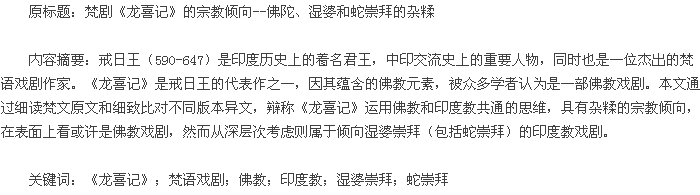
印度戒日王有三部梵剧传世,分别是宫廷喜剧(nā?ikā)《妙容传》(Priyadar?ikā)、《璎珞传》(Ratnāvalī)和传说剧(nā?aka)《龙喜记》(Nāgānanda)。《龙喜记》是戒日王的代表作之一,被众多学者认为属于佛教戏剧。本文旨在探讨《龙喜记》杂糅的宗教倾向。
一、《龙喜记》中的佛教元素
《龙喜记》①中有不少看上去与佛教相关的元素。首先是开篇的两首赞佛颂诗:
愿胜者佛陀庇佑你们!菩提树下,摩罗女满怀嫉恨对他百般勾引:“你假装冥想,却在念着哪个姑娘?
请睁睁眼,看看这个被爱神花箭射伤的人!你是保护者,却不肯保护我们!你假意慈悲,谁能比你更残忍?”(1.1)拉满花弓的爱神,敲打着刺耳的战鼓、跳来跳去的魔军,蹙额、摇曳、频申、微笑、嬉戏的天女,躬身施礼的悉陀们,以及惊讶得身毛直竖的婆薮之主都亲眼目睹他纹丝不动,悉心禅定,证得菩提。愿牟尼之王保护你们!(1.2)胜者(jina)和牟尼之王(munīndra)都是佛陀的称号。
其次,《龙喜记》序幕中宣称剧情取材于已散佚的佛本生故事《持明本生》(Vidyādharajātaka);剧中有关于青春无常、身体可憎、王位可舍、归隐山林等论述;苦行者和云幢王用相好庄严形容云乘;金翅鸟将云乘比作菩萨;云乘最后决定抛弃生命、保护蛇族,并劝请金翅鸟戒杀生。这些都可以作为《龙喜记》是佛教戏剧的证据。其中最关键的部分是云乘舍身救蛇,以两首“身体可憎”诗作为铺垫:“这身体注定毁灭,又忘恩负义,是一切 / 不洁的处所,愚痴者却为它犯下种种罪恶”(4.7)。“所谓身体,不过是脂肪、骨头、肌肉、脊髓、血液的会聚,/ 再包裹上一层皮,总是面目可憎,如何谈得上英俊美丽?”(5.23)进而在先后两次出现的“舍身颂”中推向高潮:“布施我身,保护蛇族,此刻功德我成就;/ 轮回中获得身体,是为了向他人伸出援手”(4.26)。
佛教的最终目的是“抛弃身体,获得涅盘”.对身体的憎恶和摒弃是涅盘的前提。凭据云乘之前种种自我牺牲的誓愿以及最后这个美妙“舍身”,很多学者将《龙喜记》界定为佛教戏剧。博伊德(Boyd)在英译本中直接加入了副标题:“佛教五幕剧”.考威尔(Cowell)认为《龙喜记》的情节是佛教传说(Har?avardhana, Nāgānada, or, the Joy of the Snake-Worldxii)。吴晓玲在汉译前言中说,《龙喜记》题材选自民间流传的佛教故事,杂糅了印度教的气氛,主要体现佛教的利他主义,与投火、饲虎等佛教舍身故事一致(吴晓玲 1,12-13)。提婆胡蒂认为《龙喜记》撰写时间最晚,具有佛教主题;而戏剧中对高利女神的描述,也表明了戒日王印度教和佛教混合的信仰和当时宗教自由的思潮(Devahuti 180-81)。段晴教授认为,《龙喜记》因其笔法最为娴熟,应该是戒日王最后创作的戏剧。这部戏剧以佛教故事为题材,主要受请的神是佛陀。这证明了戒日王佛教信仰的加强(段晴 55)。
二、《龙喜记》中的印度教元素
上述例证是否真的具有佛教倾向呢?
(一)关于赞佛颂诗《龙喜记》开篇的两首颂诗确定无疑是赞颂佛陀的。
梵语戏剧颂诗中歌颂的神,通常是毗湿奴、湿婆或因陀罗,也有高利女神和辩才天女等,赞颂佛陀的颂诗非常罕见。然而并不是说颂诗中歌颂哪个神,整部戏剧的基调就是赞颂这个神。尤其不能因罕见的赞佛颂诗,就将整部戏剧定义为佛教戏剧。颂诗和戏剧内容往往是脱节的,更多的是体现戏剧表演的场合,如考威尔猜测的“在佛教的节日看《龙喜记》,在印度教的节日看《璎珞传》”(Har?avardhana. Nāgānada, or, the Joy of the Snake-World xi)。换句话说,颂诗是针对观赏戏剧的观众而言,而非影射剧情。结合玄奘对曲女城的描述,这一情形就更容易理解:“僧徒万余人”、“异道数千余人”(季羡林等 424-425)。在戒日王朝的政治中心,佛教徒数量远超过印度教徒。《龙喜记》上演的时候,面对更多的佛教徒,就更可能吟唱赞颂佛陀的颂诗。还有些时候颂诗是随机的。很多戏剧开头并没有颂诗,例如跋娑十三剧中,只写上一句“颂诗结束”(nāndyante),就直接进入剧情。这更体现了颂诗因时因地而异的性质。
因此,开篇的赞佛颂诗,仅体现出当时观赏《龙喜记》的观众中可能以佛教徒居多。《龙喜记》本身的宗教倾向则要看颂诗之后的部分。
(二)关于《持明本生》
在《龙喜记》序幕中称戏剧取材自《持明本生》。《持明本生》已失传。《故事广记》(Bhatkathā,又译《伟大的故事》,6 世纪之前)中有“云乘故事”,也已失传。现存云乘故事的版本见于《僵尸鬼故事二十五则》(Vetālapa?cavi??ati,成书年代不详,约为10-14 世纪)以及根据《故事广记》编辑的《广故事花鬘》(B?hatkathāma?jarī,11 世纪)和《故事海》(Kathāsaritsāgara,11 世纪)。《僵尸鬼故事二十五则》第十五个故事几乎包含了《龙喜记》的全部情节,但并没有佛本生故事的痕迹。故事中称云乘是湿婆的信徒(Barker 252),而舍身救蛇只是为了履行刹帝利的职责(Barker 270)。《故事海》中的云乘故事补入了云乘的前生和金翅鸟与蛇的宿怨,虽在结构上与佛本生故事相似,但这种框架结构的叙事模式在印度传统故事文学中也比较常见。
汉译佛典中有大量金翅鸟以龙(蛇)为食的叙述,但没有云乘故事,也未出现云乘的名字,仅在三国支谦译出的《菩萨本缘经》第八品《龙品》中有菩萨前世因“恚”因缘堕入龙身,为救龙族只身涉险,用佛法劝说金翅鸟“生慈心”不再杀生的故事。这个故事当中,菩萨本身属于龙族,舍身为救他和自救,并没有替龙赴死的关键情节。云乘故事除了《龙喜记》序幕中提到的仅存标题的《持明本生》之外,既没有收录在现存的本生故事中,也未见于当时的佛教艺术,也没有任何版本的云乘故事具有本生故事的标志。并且,佛教对于龙蛇的态度是居高临下甚至包含谴责的。正如沃格尔所说,云乘故事最初与佛教并无关联,无论它看起来与佛教思维多么相似。将其看待为本生,应该是比较晚的情况(Vogel170)。
而且,《龙喜记》中印度教诸神恣意横行。摩罗耶公主觐拜高利女神(gaurī,喜马拉雅山神之女,大神湿婆之妻)的神庙(第一幕 11)。花冠儿信奉力天(baladeva,黑天的哥哥,由毗湿奴的一根白发产生,属于蛇族)和爱神(第三幕 34)。云幢王向太阳神苏利耶(sūrya,又译日天)祷告(第五幕 68)。螺髻礼拜牛耳天(gokar?a,湿婆的称号)(第四幕 61,第五幕 70)。云乘持明(vidyādhara)太子的身份就表明他是湿婆的侍从,他最后也跪拜在高利女神脚下(第五幕 88-89)。云乘对蛇的宗教感情也可纳入印度教范畴。即便真的将云乘故事归入本生,其浓重的印度教色彩及内在情节和逻辑与佛本生的貌合神离,也将拼接凑搭的痕迹暴露无疑。因此,将《龙喜记》的取材说成是佛本生故事并不恰当。
(三)关于归隐山林
序幕中戏班主人(舞台监督)说要效法云乘太子“归隐山林”:“决意侍奉双亲,/抛弃权力承袭,/ 我也前往森林,/ 正如云乘太子”(1.5)。
对于云乘心向往之的山林有如下描述:
树皮被剥落,用来做衣裳,不是大块树皮,仿佛慈悲心肠;古老的水罐破碎了,依稀可见;瀑布泉水明澈澈好似青天;莎草编成的腰带,磨损断裂,被婆罗门少年随意丢弃;由于常响耳畔,连那鹦鹉也能诵念《娑摩吠陀》的诗篇。(1.11)快活的牟尼们讨论着深奥难解的吠陀章句;年轻的婆罗门一边吟诵经典一边砍斫湿漉漉的柴薪;苦行女在小树坑浇满了水;真是个宁静而美好的净修林!
树皮衣、水罐、莎草腰带都是婆罗门苦行者的标志。《娑摩吠陀》更是印度教的典籍。
每一个细节都指引向印度教式的苦行,其为云乘所渴望,也是佛陀在证得菩提之前尝试过并且摒弃了的。
可见,云乘的归隐山林不是佛教意义上的出家,而是印度教式的苦行。与之相连,青春无常、王位可舍的论述虽然与佛教思想相似,却也是源自印度教的传统:当国王完成了俗世的义务,他们把王位传给儿子,然后携王后居住山林。这些描述不能证明云乘的佛教情怀,反而增加了戏剧的印度教倾向。
(四)关于舍生和大团圆结局“慈悲”和“利益众生”并非佛教专属。印度教徒在形容他们的天神时也会用到类似的字眼。湿婆为拯救众生吞下搅乳海时产生的剧毒,从而有了“青颈”(nīlaka??ha)的称号。
在戒日王铭文中,“同情一切众生”就是用来修饰大自在天(湿婆)。
同样,“布施”和“舍生”(即布施生命)亦非佛教独有。佛教和印度教同样讲布施。
佛教信徒布施给僧侣,印度教徒布施给婆罗门。佛教借用普世的“牺牲奉献”来宣扬自己的教义,佛教中也确实包含各种各样的舍生故事,然而这并不能带来佛教对舍生的垄断。
印度教中同样不乏舍生的例证。例如,莎维德利为救丈夫至诚,以血肉之躯跟随阎摩到达冥界,事实上就是一种舍生,而这种舍生作为苦行的特殊表现最终感动阎摩,使她的丈夫复生。又例,尸毗王割肉养鹰救鸽的故事,见于《摩诃婆罗多》、《五卷书》(季羡林290)等,又同时被佛教利用收入本生故事,从而尸毗王变成了佛陀的前生。
印度民间故事宝库中的舍生情节本身没有宗教倾向,可以被佛教和印度教(甚至任何宗教)各自利用。二者的不同在于,佛教的舍生是真正的舍生,指向最终解脱(涅盘);而印度教的舍生从属于苦行,结局是天神被取悦,舍生者死而复生,获得种种俗世的恩惠。
那么,《龙喜记》中舍生(或者说全剧)的结局是什么呢?
摩罗耶公主向高利女神祷告。高利女神现身,让云乘复活:“云乘!你救助众生,不惜牺牲自己生命!/我对你非常满意,孩子啊!快快复生!”(5.33)云乘站起来,毫发无损,礼敬高利女神的双足。高利女神宣布:我满怀喜悦,用心愿铸造的宝瓶亲自为你灌顶,即刻册封你为持明转轮王!宝瓶盛满最胜清净水,产生自我的思想;混合着天鹅翅膀击打金莲花时掉落的花粉,却没有泥浆。(5.36)赐你面前金轮常转!再赐四牙白象!三赐黑骏马!四赐公主摩罗耶!转轮王啊!
请你看这些珍宝琳琅!(5.37)女神描述了摩腾迦等持明国王的臣服(第五幕 90),又询问云乘是否还祈求其他恩惠,云乘双膝跪地答道:
……还能有什么恩惠比得上这些?
从鸟王(金翅鸟)口中救出螺髻;毗那达之子(金翅鸟)改邪归正;被金翅鸟吃掉的所有蛇王复生;我重获生命;因此,我的双亲不再轻生;我正式成为转轮王;女神啊!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恩惠我心向往?(5.38)云乘曾说身体污浊如肉皮囊,最终却不是抛弃肉皮囊,而是让它起死回生。不仅如此,云乘得到了王权(转轮王,以金轮为代表)、财富(同样以金轮为代表)、军队(象、马)、女人(摩罗耶公主),以及当初作乱的摩腾迦等国王的臣服。对于这些赏赐,云乘的回答是,没有什么恩惠可以比得上这些 -- 这些正是他所渴望的。再回头看云乘之前所说的舍弃王权、舍弃生命,虽客观上达到拯救众生(蛇族)的目的,实际上确为一种取悦天神的苦行,也是一种间接的对权力的追逐 -- 通过苦行取悦天神,得到天神赏赐,然后最终获得世俗权力而不是获得宗教上的报偿。所有这些都将戏剧指向典型的印度教式(入世)的结局。
如果是佛教式(出世)的结局,那应该不是复活、恢复形体、确立王权,而是转生成佛。
虽然舍生是佛教与印度教共有的情节,然而起死回生却更具有印度教特色。天神的威力之一就是起死回生。为救摩罗根底耶(mārka??eya),湿婆曾一度击败死神。而佛教中,生死轮回,原本就是需要摆脱的。这一生与那一生本无差别,也就没有了起死回生的必要。
综上所述,云乘的舍生,不是佛教式为获解脱的舍生,而是印度教式的舍生,是苦行的极端表现和最高境界。《龙喜记》的结局是典型的印度教式大团圆的结局,以取悦天神、获得种种俗世权力告终。
有趣的是,云乘并不是《龙喜记》中唯一发誓舍生的人。螺髻听说云乘被金翅鸟抓走,立刻赶去营救,对金翅鸟说:“他不是蛇族!放开他!吃了我!我才是婆苏吉蛇王送给你的食物!”{ 把胸膛敞开给金翅鸟 }(第五幕 76)螺髻敬拜湿婆。他的举动很可能源自湿婆信仰。可以说,螺髻的舍生 -- 同样是印度教式的舍生 -- 追求的是比云乘更为纯粹的宗教报偿。
三、《龙喜记》与蛇崇拜
(一)Nāga 释义汉译佛典中常常将 Nāga 译为龙,也有译为蛇或龙蛇。Nāga 在英文中通常的译法是“serpent”或“snake”,几乎从未译成“dragon”.在印度雕塑和壁画中,Nāga 是蛇的形象,或是人身蛇尾,或是幻化成人形。剧中螺髻将幻化成人的 Nāga 的特点概括为:有蛇皮蜕化的痕迹,舌头分叉,有蛇冠(5.18)。因此,将 Nāga 翻译成“龙”是不恰当的。佛典中之所以将 Nāga 译为龙,大概是因为蛇在中国文化中是极其负面的形象。虽然蛇王木真林陀曾庇护佛陀,如是等等,如果在佛典中频频出现蛇,则很可能让信众将佛法与西域及西南少数民族的巫术联系起来。而龙是九五至尊皇权的象征。佛陀得到龙的庇护,才更能体现佛陀在汉文化中的尊贵地位。抛开宗教考虑,从学术角度应该将 Nāga 还原为“蛇”,这样才更容易理解 Nāga 所传递的文化信息。
《龙喜记》标题,恰当的译法应为《蛇喜》。从标题来看,蛇被施恩或取悦;从内容来看,戏剧与印度传统的蛇崇拜紧密相关。
(二)舍身救蛇之蛇崇拜《摩诃婆罗多》中记载了关于蛇族的两个几近灭族的巨大灾难。其一是仙人迦叶波(ka?yapa)的妻子迦德卢(kadru)和毗娜达(vinatā)之间的矛盾转嫁给了她们的后代,蛇族和金翅鸟,结局是金翅鸟以蛇为食;其二是迦德卢诅咒蛇族遭遇镇群王蛇祭的灭顶之灾,结局是阿斯谛迦中途阻止了蛇祭(毗耶娑 53-131)。第二个灾难可以说化险为夷,而第一个灾祸却依然悬而未决。云乘故事,即是通过云乘“舍身救蛇”彻底解决蛇与金翅鸟之间的宿怨,与蛇崇拜密切相连。
蛇崇拜来自古老的太阳世系图腾崇拜(Oldham 7-8),又见于吠陀典籍,源自对自然力(蛇毒)的敬畏和对蛇这个生灵的神话想象,并没有过多理论或教义的支撑。蛇崇拜的原因有很多种,如蛇族象征王国稳定(Sinha 45-46),蛇王掌控雨水(Oldham 9),或作为毗湿奴崇拜和湿婆崇拜的分支;其主要表现就是不能伤害或杀死蛇,而且主要指有蛇冠的蛇(Oldham 12)。
蛇崇拜是印度教的延伸,为印度教独有。在佛教文献中,蛇出现的频率并不逊于印度教。
然而“佛教传统中,有一个明显倾向,即将印度诸神,甚至梵天、帝释天等,都置于佛陀的仆从地位。蛇自然也不例外”(Vogel 93)。蛇的法力越是无边,蛇对佛陀的臣服才越发凸显出佛陀的伟大。例如佛陀施展法力降服喷火毒蛇优楼频螺(uruvilvā)。并且,佛陀对蛇族的胜利,是具有绝对优势的歧视性的征服。在《巴利律》中记载,一条蛇想摆脱蛇身,于是幻化成人形,混入僧团修炼佛法。然而在他熟睡后现出原形。佛陀将他逐出僧团,并定下戒律:蛇族不得修行佛法(Davids 217-219)。蛇族被佛教视为恶业堆积的孽缘产物,比人类更低劣,并且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印度诸神的范畴之外。因此,即使蛇族在佛教典籍中获得了驯良的形象,例如在佛陀降生之时二龙王降下冷热甘霖,目真邻陀龙王为佛陀遮风避雨,佛教也很难与蛇崇拜相连。蛇族在佛典中的形象是被驯服和依靠佛法自救。真正救助过蛇的,只有印度教传统中的阿斯谛迦、湿婆等。
如果仔细考察佛教对于蛇的态度就可以发现,云乘的“舍身救蛇”与佛教的观念有不小出入 --《龙喜记》虽未说明救蛇的原因,却在字里行间透露着“不能伤害蛇”的信念。
对于蛇族的遭遇,云乘认为婆苏吉与金翅鸟的约定是怯懦的表现 -- 蛇王婆苏吉并没有保护蛇族,而是牺牲蛇族,苟且了自己:“哎呀!蛇王是这样‘保护’蛇族啊! / 难道他那两千条蛇信子中,竟然没有一条说:/‘今天我把身体献给蛇敌,为了保护一条蛇'?”(4.5)然后云乘自忖道:“难道我不能通过布施自己的身体,救出哪怕是一条蛇的性命吗?”
(第四幕 52-53)再看云乘的“舍身颂”(布施我身,保护蛇族)以及高利女神现身救活云乘时说的话:“云乘!你救助众生,不惜牺牲自己生命! / 我对你非常满意,孩子啊!
快快复生!”(5.33)和云乘的回答:“从鸟王(金翅鸟)口中救出螺髻;毗那达之子(金翅鸟)改邪归正;/被金翅鸟吃掉的所有蛇王复生;我重获生命;/因此,我的双亲不再轻生;我正式成为转轮王;/ 女神啊!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恩惠我心向往?”(5.38)首先,云乘的舍身,是将身体布施给蛇族,是比佛陀舍身饲虎还要高尚的一命抵一命,而且是“人命抵蛇命”.如果说布施给僧众是佛教徒,布施给婆罗门是印度教徒,那么布施给蛇,不能不说包含了蛇崇拜的成分。按照佛陀舍身饲虎的逻辑(一人抵三虎),蛇的性命与人的性命不止是平等,还要更高。尤其从云乘回答高利女神恩赐时所说的话“我重获生命;因此,我的双亲不再轻生”(5.38),以及摩罗耶公主发誓殉夫来看,云乘一人舍生,连带着三个人的性命;而螺髻罹难,加上他的母亲伤心而死,总共是两条蛇。由此可见,云乘把蛇族的生命看得远高过自己,把拯救蛇族置于侍奉自己双亲之上。
其次,高利女神被取悦,是由于云乘“舍生”和“救蛇”.二者同等重要。对于高利女神的世俗赏赐,云乘十分欣喜。然而在他的回答中最先强调的三点,与“裨益众蛇”紧密相连:救出螺髻,金翅鸟不再杀蛇,被杀死的蛇获得重生。
至此,云乘的意图更为明显。他固然以印度教式的舍生苦行取悦了天神,然而其直接动机包含了对于蛇的宗教情怀。
(三)蛇崇拜与湿婆崇拜在《龙喜记》中,与金翅鸟达成协议“日送一蛇”的是蛇王婆苏吉 -- 湿婆的装饰。
螺髻在准备赴死之前敬拜了湿婆(牛耳天)的神庙。(5.7)螺髻将月光般洁白的蛇骨比喻为湿婆,暗含着向湿婆献身(湿婆身披蛇饰,头顶有新月):“这坟冢每天以蛇为食满足金翅鸟,从不落空;/ 月亮般洁白的骨骼堆积,如同楼陀罗(湿婆)的身形”(4.19)。
因此,《龙喜记》中的蛇崇拜,以自己特有的形态从属于湿婆崇拜。蛇由于自身的灵性和膜拜湿婆大神,在某种程度上分享了湿婆的威严和信众,因而不能被伤害。舍身救蛇的行为,与虔信湿婆相关,得到高利女神的赞许,获得俗世报偿的恩惠。
四、《龙喜记》是具有佛教和印度教共通思维的戏剧
佛教和印度教有很多共通的思维(慈悲、舍生等)。因此,从现象上看很容易对《龙喜记》产生不同的解读。
例一:
戏班主人(舞台监督)开场便说“今天是祭祀帝释天的盛大节日”(序幕 2)。
因陀罗(帝释天),虽然被后来崛起的印度教诸神击败退居二线,却也是名副其实的老牌印度教天神,依然受到不少印度教徒的信仰膜拜。祭祀因陀罗属于印度教的节庆。然而在众多佛经中,因陀罗俨然已成为佛陀的护法天神,所以将因陀罗的节日理解为佛教节日也不为过。
例二:序幕接下来的偈颂出现了有趣的现象:
喜增诗人技艺炉火纯青,在场观众个个妙解德行;世间悉陀王传 / 菩萨传引人入胜,我们的表演功力精深。
单独一桩都能带来成功,如同每个细节指向结局圆满;更何况由于我积福颇甚,所有的美德汇聚相连?(0.3)这 一 颂 与《 妙 容 传》(Har?avardhana, Priyadar?ikā of ?rīhar?adeva 0.3) 和《 璎 珞传》(Har?avardhana, The Ratnavali of Sri Harsha-Deva 0.5)几乎完全相同,除去第二行的“vatsarāja-carita?”(犊子王传)。《龙喜记》中这一颂梵文,Karmarkar 本、德里本、吴晓玲译本、Ramachandra 本、Kale 本注释异文为“bodhisattva-carita?”(菩萨传);Kale 本、Gho?a 本、Karmarkar 本注释异文、Boyd 译本为“siddharāja-carita?”(悉陀王传)。
由此可见,不同的抄录者对于《龙喜记》戏文有了不同的理解。佛教信徒更倾向于认为这是讲菩萨的故事,而印度教徒觉得这是悉陀王的故事。
例三:
苦行者用相好庄严形容云乘:
沙滩上有一串转轮王的辐轮脚印儿!这是谁的?(看着前面的云乘)一定是这位大贵人的!因为他头顶乌瑟腻沙高耸;眉间白毫放光;眼眸好似青莲;胸膛堪比雄狮;手足有轮相;我看他一定会成为持明转轮王!(1.13)这些特征代表吉祥,既可以修饰佛陀,也可以形容印度俗世的王。形容沙滩上的脚印时,Kale 本、德里本、Gho?a 本作“prakā?a-cakra-cihnā”(清晰的辐轮印记);Karmarkar本、Ramachandra 本为“prakā?ita-cakravarti-cihnā”(清晰的转轮王印记)。德里本称云乘为“mahānubhāvasya”(光辉者);Gho?a 本、Karmarkar 本、Ramachandra 本、Kale 本注释异文称云乘为“mahāpuru?asya”(大人物,与佛陀的“大人相”同语);Kale 本、Karmarkar 本注释异文为“mahānubhāvasya padavī”(光辉者的足迹)。这些差异也很可能代表了誊抄者不同的宗教倾向。
另例:“舍身救蛇”,既可以理解成佛教式的“众生平等”(略显牵强),也可以理解成印度教系统下的“蛇崇拜”.
综上所述,《龙喜记》运用了一些佛教与印度教共通的思维,产生了混合杂糅的效果:在表面上看或许是佛教戏剧;从深层次考虑则属于倾向湿婆崇拜(包括蛇崇拜)的印度教戏剧。
一、导言中韩两国的文学往来渊源已久。新罗时期,中国文学便已传入朝鲜半岛。高丽和朝鲜时代,在中国文学的影响下,韩国的古典文学逐渐发展、成熟和繁荣。进入十九世纪后,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朝鲜半岛开始接受美国及欧洲文学的影响,韩中文学呈...
《源氏物语》以日本平安王朝为背景,描写了主人公源氏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小说刻画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她们坎坷、悲惨的命运,无不让人惋惜。当时长期存在的访妻婚,也导致了这一悲剧的发生。...
一、引言《野菊之墓》是描写少男少女恋爱的小说,其中的女主人公民子对爱情的渴望、对纯爱的追求的形象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纵览中日至今对伊藤左千夫小说的研究,大多数为叙事策略的研究,而对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女性的研究甚少。基于此,笔者选取这一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