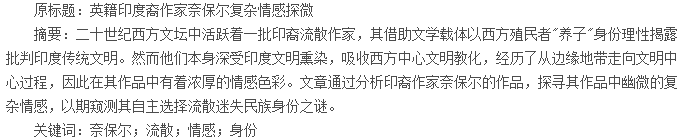
一、引言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英国文坛上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地方,即获得本国文坛最高成绩甚至是世界文坛最高成就的往往是印裔英籍作家,诸如V.S.奈保尔、阿·克·纳拉扬、拉伽·拉奥,以及萨尔曼·拉什迪等。奈保尔获得过英国文坛的布克奖,并凭借《河湾》荣获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其获奖作品有《米古埃尔街》(1959年获毛姆奖),《斯通先生与骑士伴侣》(1963年获霍桑登奖)、《效颦者》(1967年W.H.史密斯奖)、《在一个自由国家里》(1971年获布克奖)。萨尔曼·拉什迪也曾于1981年因小说《午夜的孩子》获得英国布克奖。这些印度裔英籍作家文学成就斐然,然而其代表后殖民时代的文学作品内容也颇受争议,拉什迪曾因讽刺穆斯林的《撒旦诗篇》而被伊朗穆斯林最高领袖霍梅尼判处死刑,他们在这些融杂东西方元素的作品中更多的倾注了私人情感,并对其原籍国家进行全面深入的评判式思考。本文试图探究其文学作品中的多股复杂情愫。
二、英籍印裔作家奈保尔的复杂情感
(一)对母国印度的情感
从奈保尔的生平经历来看,其幼年时期曾在印度家庭环境中生活过,即便没有在印度这个国境里成长,也是深受印度式家庭氛围熏陶而成长,其身上带有浓重的印度气息,这也是后来他的作品皆以印度的社会、文化、习俗等内容作为永恒主题的缘故。据陆建德在《河湾》译序中写道奈保尔的成长环境:"特立尼达的印度移民后裔有自己的社区,他们保存了印度的风俗习惯与文化传统。奈保尔曾对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改编的罗摩戏难忘,以至于其在作品《黑暗地带》说道'印度对他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个有形的世界,因而从来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它远离特立尼达,是个存在于虚空之中,没有具体历史的国度'"(奈保尔,2002a:2)。后来奈保尔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三次访问印度,出版了三部关于印度的游记,即《黑暗地带》(1964)、《印度:受伤的文明》(1977)和《印度:现今的无数叛乱》(1990)。在这历经近三十年的对印度现代文明的考察过程中,奈保尔对印度国父甘地标榜的传统农业文明毫无好感,对尼赫鲁信誓旦旦的国家社会大变革,建立强大的工业文明失望至极,对英吉拉·甘地的"紧急状态"阻碍民主进程,操控国大党,玩弄民众大肆鞭挞,而这些仅仅是反应在政治上的。在社会生活中,奈保尔对印度延续几千年的"种姓"制度在新的国家仍旧延续悲愤痛心,对"种姓"制度造就的社会结构板结,民众严重分层对立,国家民主自由社会迟迟不能建立焦躁不安。这些内在的情绪凝结在作品中传达出来的即是奈保尔对印度这个原殖民地的复杂感情。
与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产生的本土作家的文学作品类似的是,这些英籍印裔作家对其母国的情感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与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反映出来的中国国民劣根性有着本质上的一致。
印度民众在历经甘地时代、尼赫鲁时代之后,其数千年的陋习依旧存在,恰似于中国民众历经辛亥革命之后的奴性依然。在《自由国度》中桑托什叫普利亚"老爷"一样,这个词本身即具奴性,在《河湾》中那些政府公务员绝对不会为普通服务生甚至一般民众倒杯开水,这即是印度传统的"种姓"、"贱民"制度的遗留结果。
奈保尔对印度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文化考察后发现印度社会的种种弊端,社会动乱不安,民众生活未能改善,民主政治进程受阻,以至于奈保尔对印度失望至极,对印度文明悲观绝望。在《后殖民:印英文学之间》一书中有关奈保尔文学作品关于"黑暗地带"意象解析,即是奈保尔本身记忆中关于印度本来就无多少亮色,在其对印度真真切切的"旅行"之后,他心目中的印度在现实之中变得更加"黑暗",他无法摆脱"黑暗"的感觉,"黑暗"不仅成为其观察的对象,而且变成了他"观察和思考印度的方式".正如奈保尔所说:"这是生活于偏僻地带的感觉,它生发于要被偏僻本身吞没掉的恐惧,是偏僻地带生活着的人们的恐惧,这种恐惧一直伴随着我"(石海军,2008:58)。
(二)对移入国英国的情感
奈保尔在把印度文明阐述为世界文明中心的偏僻地带的同时,其所认为的文明中心地带应当在欧洲、在北美,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英国。事实上奈保尔在其小说中对英国的赞美向往有着过于繁多的笔墨,以至于令读者生发出对作者献媚于英国而产生不屑之态。如《河湾》中主人公萨林姆对欧洲的评价:"……如果没有了欧洲人,我们的过去就会被冲刷掉,就好像镇外那片沙滩上渔人的印记一样"(奈保尔,2002a:12)。奈保尔甚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次演讲中将英国的文明等同于普世的文明,他说,从特立尼达到英格兰意味着从边缘到中心,这旅程是在同一种普世的文明中完成的(奈保尔,2002a:3)。
这一话语毫不掩盖一个印裔作家对英国文明的欣喜和赞赏。结合奈保尔的人生经历,我们亦可以窥见其对英国文明的歆羡,少年留学英国,后与英国本土姑娘组建家庭,再后来以英语进行文学创作,等等,可见奈保尔的英国文明中心论的根深蒂固。
奈保尔作为一个印裔作家,其经历从偏僻地带走向中心文明必定有着诸多的坎坷,从一个边缘地带的亚裔人走向中心文明的欧洲必然有着艰难的融合之苦。他渴望融入新的社会文化之中,但母国文化在他们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以至于这个磨合过程异常艰难(石海军,2008:96)。在其作品《自由国度》中桑托什跟随其恩主到达美国后即被一个哈布舍胖女人引诱,以至于其在浴缸里泡了又泡,洗了再洗,甚至于想用柠檬祛除身上的气味,赤身裸体地在浴室和起居室地上翻滚,嚎叫,泪水夺眶而出(奈保尔,2008b:41)。事情发展到最后,桑托什"逃避"恩主,来到一个印度同乡处专心做起了大厨。在"告诉我,杀了谁"一章中,主人公"我"在伦敦开了一家烤肉店即遇到各种麻烦,先是昂贵的租金、水电、装修和原料,然后又遇到偏见和制度的麻烦。这儿他们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那些穿花呢和法兰绒的年轻人带着各种表格来到店里,这些人生性多疑,严格审查小店的方方面面,不给我片刻安宁(奈保尔,2008b:102)。其实作品中主人翁的遭遇也正是奈保尔这类外来移民入居英国所遭受的困境。
但在英国落定之后,奈保尔察觉所谓的西方文明中心于他而言并没有想象的那般美好,英国的中心文明是建立在对全球各个殖民地的奴役和掠夺之上的。以至于奈保尔在其作品中多次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的破坏效应:不相信自我的文化,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异化(陌生)感,同时对"自由"的西方文化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石海军,2008:59)。在奈保尔看来,如今的世界,旧有的国际社会制度依旧存在,传统的道德价值崩溃了,金钱至上、利益至上的信条即是西方文明的核心本质,其不再相信西方殖民者,更对西方文明的梦想破灭了。
对母国的悲观失望,对宗主国文明的深度怀疑造成了奈保尔的孤独行者身份,其无法再对自己身份进行新的定义,也无法对其身份作最终的认同,他把自己称之为流散的"世界公民".他与拉什迪等流散作家一道构建出一个"第三空间",充当西方文明中心与印度边缘文明沟通的桥梁,且试图以西方中心文明改造传统粗陋的印度文明。奈保尔的文学创作含沙射影式的摧毁着封闭的、线性的文化"身份"说,打破殖民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的界限,实现着开放的"文化"认同的流散政治理想,借以试图化解其失却了民族身份的困惑和悲哀。
以奈保尔为代表的英籍印裔流散作家的情感历程可大致梳理为:对母国悲切、失望,对宗主国文明中心向往走向对英国中心文明的深深怀疑,对欧洲文明幻灭走向流亡,以中心文明传播者身份改造母国的边缘文明,迷失民族的身份。
三、复杂情感在奈保尔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在奈保尔代表作品《河湾》中主人公萨林姆这个角色本身即带有很强烈的个人色彩,萨林姆从小就接受了海岸那块英国殖民地的英式教育,并且持有英国护照,他对欧洲文化和本地文化差异性极其敏感,并且坚定的站在西方中心文明的角度来批判伊斯兰文明。
诸如"……看着这个虔诚的女人掩在自己的墙后,我突然发现她对铜瓶的关注是多么的琐屑。粉刷成白色的墙是多么单薄,比沙滩上奴隶围场的墙还要单薄,能给她提供的保护实在是少的可怜。她太脆弱---她的为人,她的宗教,她的风俗,她的生活方式,全是脆弱的。"(奈保尔,2002a:19)这段话语虽然否定的是萨林姆的婶婶,然则深层之意是奈保尔对整个印度文明的否定。
在《河湾》中,奈保尔借萨林姆之口表达其对西方文明的崇拜之情。在萨林姆与菲尔迪南讨论新的科技产品时,其对西方人有这样一段叙述:"他们是公正的,高高在上,端坐云端,如同造福的神明。我们盼着得到他们的赐福,有了他们的赐福就四处炫耀---比如我向菲尔迪南炫耀廉价的双筒望远镜和高级相机---仿佛这些东西的设计发明也有我们一份功劳。"(奈保尔,2002a:44)以西方技术上的优势即对整个西方文明的赞赏和歆羡,着实有些以偏概全,然而这是奈保尔年轻时期对以英国为中心的欧洲文明最为本性的认识。
作品中还有以总统为代表的民族运动之后新兴的国家建设情节。在起初的革命胜利初期,以本土部落总统为代表的上层人士极力建设一个新兴的非洲国家,为此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社区,并努力向欧洲文明看齐,"非洲人也可以成为现代化的人了,也可以造出水泥和玻璃组成的大厦,也可以坐到有仿天鹅绒椅套的椅子。惠斯曼斯神父说过:非洲式的非洲将要退让,欧洲的移植将取得成功。
这语言仿佛歪打正着地应验了。"(奈保尔,2002a:104)这段话语中,奈保尔借非洲之名叙述印度之事,1947年印度独立后,以尼赫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确实努力尝试带领民众走向繁荣、富强、民主、文明的新社会,然而这一切很快即因旧有的国际关系格局而失败。在作品中奈保尔借总统这个形象,来阐述其移植西方文明未果之事。总统的头像越来越大,且覆盖了其他政府官员全身照;非洲丛林中建有圣母像,且让整个国民前去祭拜;再到后来军队和警察又横行肆虐,各种反叛势力重新崛起……,这些都是印度独立后几十年间发生的事件,奈保尔把其移植到非洲丛林,且对这混乱的局势失望痛恨。
萨林姆很快乘机去了欧洲,并且和凯瑞莎订婚了,且见识到了伦敦街头各种形形色色的欧洲人,然则所见所闻渐渐颠覆了其对欧洲文明的美好憧憬。其在初抵欧洲时道:"在我年幼时,欧洲统治着我的世界。它打败了非洲的阿拉伯人,控制了非洲内陆……是这个欧洲给了我们那些丰富多彩的邮票,让我们从中了解到自己多姿多彩的一面。是这个欧洲给了我们新的语言。"(奈保尔,2002a:243)然则在伦敦待了六个星期,萨林姆即产生了"用伦敦来比照非洲,或是用非洲来比照伦敦,结果二者都是虚幻化了","回家、离开、别的地方---多少年来,这些想法何尝不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只是形势有所不同罢了……在伦敦,在旅馆的房间里,这些想法让我彻夜难眠。它是幻觉,我现在才发现,这些想法表面上能给人以慰藉,实际上让人疲软,让人毁灭"(奈保尔,2002a:255,259)。萨林姆在文明中心的欧洲感到无所适从,然而回到非洲回到出生地的欲望虽然强烈又让人毁灭,这注定其只能选择流散之路,而这亦是奈保尔所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