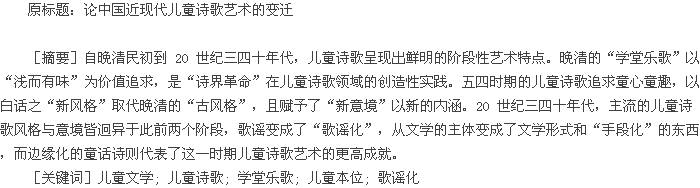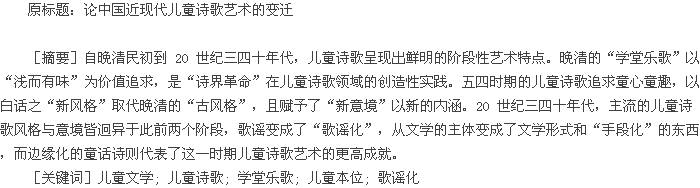
晚清民初的“学堂乐歌”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儿童诗歌的创作之门,从晚清到五四再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儿童诗歌显示出较鲜明的阶段性艺术特点。选取以“老鸦”为内容的几首儿歌作为线索,能够以点带面勾勒出 20 世纪上半叶儿童诗歌从“风格”到“意境”的流变轨迹,揭示出各阶段儿童诗歌的典型特征,亦可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中国近现代儿童文学的整体样貌。
一、晚清民初的“学堂乐歌”: “浅而有味”
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在童话、寓言及儿童小说领域皆以翻译改编为主,唯独以“学堂乐歌”的歌词形式存在的儿童诗歌多为创作而绝少译介,时称“唱歌”、“乐歌”、“歌词”、“童谣”、“学生歌”等。梁启超、林纾、黄遵宪、曾志忞、沈心工等人均涉足过理论的探讨与歌词编创。现以曾志忞编创《教育唱歌集》中的一首《老鸦》( 幼稚园用) 为例分析晚清民初儿童诗歌的特点。
老鸦老鸦对我叫,小鸦真正孝。
老鸦老了不能飞,对着小鸦啼。
小鸦朝朝打食归,打食归来先喂母,自己不吃犹是可,母亲从前喂过我。
首先在语言形式上,不同于古奥的文言句式,《老鸦》是浅近的文言,格律上也不特别严格,一二句与七八句均押脚韵,但所押之韵并不一致,中间四句则完全不押韵,读起来却仍流利上口,有种内在的韵律感。儿歌通过小鸦打食喂老鸦的形象比喻,意在传递“孝”的传统美德观念,正体现了编者“以最浅之文字,存以深意”的主张,或谓之曰“浅而有味”。这也正是晚清民初儿童诗歌的美学追求。学堂乐歌恰处在倡导“以古风格含新意境”的晚清“诗界革命”背景之下,后者要求既吸纳西方诗歌的新思想和新内容,同时又保留传统诗歌的格律和韵味。初期还曾主张“新语句”,但因与“古风格”常相背驰会破坏诗歌句法与格律,后来删削了“新语句”的要求,折中为允许“间杂一二新名词”。在此基础上,儿童诗歌的创作因为有了对儿童年龄特征的顾及,从而在语言的通俗化、音韵节律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要求,如梁启超所言: “盖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使合儿童讽诵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
再如,黄炎培在为沈心工《重编学校唱歌一集》所作的序言中亦肯定其歌词符合儿童心理,取材与文字程度皆“通俗而能不俚,其味隽而其言浅”。这意味着儿童诗歌既要不失传统文学之精粹———“味隽”、“不俚”,又要合儿童讽诵之程度———“通俗”、“言浅”。或者说既要保留“诗”所特有的诗味———音韵与内涵,又要有儿童容易接受的浅显流利,避免僵硬的“高古”、“填砌”。这似乎可看作晚清民初儿童诗歌对“诗界革命”之“古风格”观念的创造性实践。
然而,这首《老鸦》对“新意境”的体现并不典型,它所赞颂的“孝”仍是传统道德。晚清民初学堂乐歌更多是以表现“爱国”、“民主”、“尚武”、“科学”、“冒险”、“进取”等思想为其“新意境”的,体现了当时“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的新民教育主题。而当时被视为“小国民”的儿童,被赋予了跟成人同样的历史使命,成为借文学以新民的对象之一。大量的学校唱歌集和报刊在其编辑大意或发刊词中皆强调了学堂乐歌的此等功用,具有浓厚的启蒙色彩。这些时常间杂“新名词”的“新意境”,因无法完全放弃“古风格”的音韵格律,又要兼顾儿童的年龄特点,所以创作起来殊非易事。黄遵宪曾把所作《幼稚园上学歌》、《军歌二十四章》等新体诗寄给梁启超,在附函中大叹其“择韵难,造声难,着色难”,想必这也是当时儿童诗作者普遍遭遇的“三难”。但即便如此,晚清民初还是产生了一批颇具感染力的学堂乐歌,其中的《幼稚园上学歌》就被周作人赞为“百年内难得见的佳作”,“不愧为儿童诗之一大名篇”。
晚清民初以学堂乐歌为代表的儿童诗歌创作,是那个时代儿童文学的重要收获。它在“诗界革命”的感召之下,艰难地恪守着传统诗歌的格律与韵味,同时将时代的重大命题融入其中,旨在发挥对于儿童的激励与启蒙之用,事实证明它确实做到了。同时,与成人文学界所关注的“诗界革命”不完全一样的追求在于,儿童诗歌加入了对于儿童特征维度的考量。这不但在当时的理论文字中有明确论述,而且体现在诸多作品的有意尝试中。这对于草创时期的儿童文学意义重大,它意味着人们开始结合儿童自身的特点为儿童提供文学作品,这是儿童文学从一般文学中独立出来的必要前提。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确立,就是基于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一种“二分”,尽管“二分”的具体标准时常在变。进而言之,当时提出的所谓“浅而有味”、“通俗而不俚”、“味隽而言浅”等艺术标准虽然尚显笼统,似乎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区别仅仅在于深浅难易的程度,而非性质上有所不同,但它毕竟预示了一个重要的区分。当然,具体到诗歌这种体裁,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儿童诗歌与成人诗歌的区别比其他体裁的二者间之区别更难确定。因此,对于儿童诗歌的艺术特征的探讨从晚清开始就是一个有难度的问题,直到今天也尚未泾渭分明。
自晚清以降的半个世纪里,儿童诗歌伴随着社会运动与文化变迁也不断变换其价值坐标,从这些变化中不但可以追索诗歌自身的艺术规约,也可以透视其所处时代与社会所理解的儿童是什么样子。正是对于儿童的不同想象与期待,从根本上影响儿童诗歌的精神面貌和美学追求,无论晚清的“小国民”、五四的“小野蛮”还是三四十年代的“小战士”和“小英雄”,都概莫能外,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儿童文学史就是一部以契合儿童艺术审美的形式表达,表征着儿童观也受制于儿童观发展演变的、在过程与联系中行进的文学之历史”。
二、五四时期: 对童心童趣的自由歌吟
五四时期确立了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观。随着对儿歌展开的民俗学研究,辅之以儿童学的视角,“歌吟”被视为儿童的天然需要,儿歌与童话一起成为这一时期最典型的儿童文学体裁。五四时期儿童诗歌的创作与儿歌( 亦称歌谣、童谣) 的征集出版及理论研究密不可分。早在民初,周作人就开始从民俗学、儿童学角度研究儿歌,主张“儿歌之用,贵在自然”,批评当时的学堂乐歌“率意造作,明着教训,斯失其旨”,显然是反对利用儿歌( “乐歌”) 进行“新意境”所标榜的爱国勉学等启蒙教育。同期他还利用儿童学知识指出半岁小儿听觉已很发达,“闻有韵或有律之音,甚感愉快”,而且是“先音节而后词意”,因此儿歌的作用在于“满足其喜音多语之性而已”。他对儿歌的研究、搜集整理及倡导在当时虽无人应和,但作为“潜文本”却为五四时期的儿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定下了“基调”。五四时期儿童诗歌的翻译比晚清民初明显增多,同时大量收集、整理、出版古代民间歌谣,这反过来为儿歌童谣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材料,推动了儿歌的理论探讨。周作人不但是儿歌理论的领航者,而且尝试写下了数篇儿童诗歌,我们可借其中一首《儿歌》来反观五四时期儿童诗歌的艺术追求:
小孩儿,你为什么哭?
你要泥人么?你要布老虎么?
也不要泥人儿,
也不要布老虎;
对面杨柳树上的三只黑老鸹,
哇儿哇儿的飞去了。
显然,这首儿歌已经是很通俗的现代白话,堪称典型的五四时期的“白话诗”。口语化的语言就像成人在哄孩子时的日常对话,晚清时执着的“古风格”已不见踪影,格律和韵味被自由的诗体形式和童真趣味所取代。两个“你要”,两个“也不要”,造成一种回环往复的节调,这种节调并非古典诗词里刻意的韵律,而是更接近俗歌的自然音节。起始的三个问句,则满蕴着成人对孩子的关切,成人猜测孩子为什么哭,结果都没有猜对,真正的原因竟是三只黑老鸹的飞走,想必这种趣味也非古典之韵味。最妙的是老鸹飞走时的“哇儿哇儿”,这一拟声词的运用更是凸显了“小儿语”的特色。周作人在诗后附言中称,这篇诗是他仿儿歌而作,想借用儿歌和民歌这类“俗歌”的调子来写新诗,“我这一篇只想模拟儿歌的纯朴这一点,也还未能做到。”作为一首儿歌,它的艺术成就暂且不论,这里要关注的是其相对于晚清时风格的变化。从这首儿歌不难看出,与前面那首《老鸦》相对照,五四时期的“诗体大解放”已将晚清时的“古风格”变成了“新风格”。但考察这一时期的其他儿童诗歌创作,这种对“古风格”的颠覆,不同程度存在过犹不及问题,有些儿童诗歌的语言过于直白,没有外在的格律,也没有内在的音韵,既无诗的味道也无歌的节奏,势必会影响小读者的接受。
除了风格上的变化,诗歌内容上的“新意境”也有了不同的内涵。诗后附言中作者还交代说,写三只黑老鸹并无神秘的思想,只是因为乌鸦很多比较常见,其写作动机仅在于“儿童性爱天物,他的拜物教的思想,融入诗中,可以造成一种汛神思想的意境”。由此可见,作者创作这首儿歌,是以儿童的“性爱天物”为出发点,是适应儿童的“拜物教”———即儿童的泛灵论思想,是为满足儿童自身的需要。因为依据当时认同的进化论,作为系统发生上的“小野蛮”,儿童在精神上都是“拜物教”的,他们相信草木能思想、猫狗能说话。而只有完全按照儿童自身的需要,以适当的语言提供合乎其情感与想象的文学,这才是五四时期倡导的儿童本位的文学。倘若以此“儿童本位”的文学标准去衡量,晚清时那些借儿童诗歌以鼓吹爱国、民主、科学、尚武、进取等的学堂乐歌,恐怕多半是既非“儿童”也非“文学”的。因为宣扬的那些“大道理”都是基于现实的功利需要,年幼的儿童难以明白也不一定感兴趣,所以能否称得上是“儿童的文学”都很可疑。秉持着这样的儿童文学观念,五四时期的儿童诗歌自然要告别晚清民初构成其“新意境”的那些主题内容,代之以猫狗说话的“鸟言兽语”,追求的是富有儿童趣味的“新意境”,甚至对有没有“主题”也不介意: “至于有没有作意,倒是次要的,有作意而有趣味,固然很好,就是没有作意,而音节铿锵,儿童喜欢唱的也很好。”可见,唯一的标准就是“儿童喜欢唱”。无独有偶,俞平伯的《儿歌》( 二首) 中也有一只“老鸹”,读来有异曲同工之妙: “老鸹,/老鸹飞。/怎么不在屋子里! /这个! 这个唷! ”这首短儿歌模拟“小儿语”的腔调,句式与节调更是没有“章法”,孩童式的指点动作与天真好奇却呼之欲出,洋溢着一股“无意思之意思”的童趣。
这两首《儿歌》只是五四儿童诗歌之一种。当时搜集整理及翻译的大量儿童诗歌暂且不论,诗人创作的适合儿童诵读的诗歌也有很大一部分并非“专门”为儿童所做。实际上,童诗与成人诗本来就没有绝对的界限,好诗未必都适合儿童诵读欣赏,但一首好的儿童诗必须首先是一首好诗。笔者曾对五四时期的儿童诗歌进行爬梳整理,大体将其分为四个类别,其中只有一类是对象意识比较明确的,无论语言、立意等都较适合儿童,极富童趣,如严既澄的《早晨》、《地球》,胡怀琛的《大人国》、《小人国》,郑振铎的《两只小鼠》、《春之消息》等。还有一类是模仿传统儿歌民谣所作,节奏鲜明,音韵和谐,趣味盎然,儿童往往也喜唱能诵,例如顾颉刚的《吃果果》、《老鸦哑哑叫》,刘半农的《拟儿歌》,刘大白的《两个老鼠抬了一个梦》,陶行知的《为何只杀我———民歌改作》等。此外如汪静之的《我们想( 拟儿歌) 》、郭沫若的《天上的市街》、朱自清的《小草》、应修人的《温静的绿情》以及较优秀的散文诗如刘半农的《雨》、徐玉诺的《冲动》等,虽然不是有意为儿童所作,但因以纯真童心抒写出稚拙的诗意,仍然称得上优秀的童诗。倒是一些“童年忆往”的诗作,堪称好诗甚至经典,却因写法与所抒发的情怀志趣不太近于儿童,所以对当时的小读者影响有限,比如俞平伯的新诗集《忆》等。后三类诗歌都并非专门为儿童而作,但这并不妨碍其拥有儿童读者,正如英国当代对童诗卓有贡献的 Charles Causley 所言: “为儿童写诗如果有最好的方式,我想可能是先想办法努力写一首好‘诗’,然后再决定这首诗适合哪些读者。一首好‘童’诗的测试,必然是它对儿童和成人而言都一样成功。”五四时期儿童诗歌的许多“无心插柳”或许正因此成就了“柳成荫”的丰硕实绩。
五四时期的儿歌讲究自然的音韵节调,不在意其有没有主题意旨,目的在于满足低幼儿童“喜音多语”的天然需求,除了搜集整理的古代儿歌民谣,仿作的歌谣也具有这一特点。适合年龄稍长儿童的诗依然满蕴着童真童趣,却更讲究诗情诗意,或者以童心写景状物,或以欣赏的眼光描写孩子的生活情态乃至游戏与淘气。这一时期的儿童诗歌丝毫不顾及诗歌本身的现实功用,完全从孩子的生理心理特点出发,迎合其对于文学审美的独特需要。这种功利色彩几近于无的儿童诗歌,不但与晚清民初学堂乐歌的风格、意境迥然有别,而且在五四之后的几十年中亦不多见,由此它对于诞生期的现代儿童文学而言便显得弥足珍贵。
三、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从“歌谣”到“歌谣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以后,儿童诗歌的“天籁”之音被继之而起的革命战争“号角”所淹没,一度被歌赞的童心童趣成为奢侈品,强烈的现实功用性延续了晚清儿童诗歌的精神特质。然而,无论形式上的“风格”
还是内容上的“意境”,三四十年代主流的儿童诗歌都呈现出不同于此前两个时期的新质,从下面的短诗《乌鸦》可见一斑。
我有嘴巴,就要说话。
“呀,呀,呀! ”
我看了不顺眼,我可不能装哑。
“呀,呀,呀! ”
人家恨我要害我,我也全不怕。
“呀,呀,呀! ”
这是作家鲁兵作于 40 年代后期的一首诗歌,以物拟人,讽喻现实,“乌鸦”俨然被塑造成了一位勇士和战士,敢于直面现实,揭露黑暗针砭时弊,不怕牺牲。全诗大体可分为三小节,每节以“呀,呀,呀”为重复,且从头至尾一韵到底,语言近乎口语白话,节奏鲜明,诗中传达的意思也一览无余。三四十年代的儿童诗歌大都具有这种特点,从其“意境”来看,不但异于五四时吟唱童心之美的“无意思”之作,也区别于晚清民初“爱国”、“尚武”、“勉学”等思想道德启蒙主题,而是融入了鲜明的阶级观念和抗日救国的时代理想,体现出更为具体明确的政治指向性。强调诗歌以直接描摹现实或直抒胸臆的方式,及时反映工农大众的斗争,对现实的革命与抗战运动发挥鼓动效用。从诗歌艺术本身来讲,其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姚雪垠评价陶行知此期诗歌时所指出的: “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得到教育,但不能得到较多的美学享受,也不能令人感到回味无穷,并愿意反复吟咏。”其“风格”之新在于,进一步摆脱了晚清刻意保留的古典诗词的音韵格律,语言追求通俗化、口语化。如果说晚清民初崇尚的是儿童诗歌的“浅而有味”、“通俗而不俚”,那么三四十年代则是“通俗而不避俚”,“浅显”未必要有诗“味”。同时,三四十年代在“文艺大众化”及“通俗文艺运动”的大背景中,主张“诗歌大众化”、“新诗歌谣化”,鼓励采用民谣、小调、鼓词、儿歌的旧形式等进行创作,倡导“诗歌应当与音乐结合在一起,而成为民众歌唱的东西”,让诗歌成为“群体的听觉艺术”,从而易于普及到工农大众中去。
儿童诗歌也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加入了时代的大合唱。三四十年代儿童诗歌的“大众化”、“歌谣化”可看作是“以旧形式装新内容”,这与晚清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相似,但前者的“旧形式”主要是对民间文艺形式的借鉴,后者却是对古典诗歌格律韵味的保留。这种民歌体的诗及儿歌在五四时期亦有不少,然而两者在提倡的出发点、趣味的旨归方面皆有本质不同。五四时期歌谣作为“原人之文学”,本来就是典型的“儿童之文学”,是为满足儿童情感的、想象的、韵律节调的诸种需要; 然而到了三四十年代,歌谣却变成了“歌谣化”,从文学的主体部分变成了文学形式方面的东西,它不再是适应儿童吟唱需要而供给儿童读者的诗歌作品,而是把要告诉儿童的教育性、革命性、政治性内容以歌谣的外套包装起来,使读者对这些新内容的灌输更容易接受。五四时期对歌谣的征集采编,主要出于民俗学、文化学研究以及供给儿童文学的目的,强调歌谣的原汁原味,民歌体新诗的创作也是为了“能用最自然的言词,最自然的声调,把最自然的情感发抒出来”。三四十年代对歌谣的提倡,却不是因为学术兴趣或抒发个人感情的需要,也不是要满足儿童的吟唱需求,而是借助歌谣这一民间艺术形式的节奏性、音乐性、朴素性,去实现新诗歌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的价值追求。当时中国诗歌会的发起人之一蒲风,曾指出“儿童文艺在抗战中不能被忽视”,儿童诗歌应该“适应于大时代的进化”,形式上要“简短”,“可歌唱也不碍于大众合唱”,而且应“活泼天真,音韵多变换,连接灵活,伸缩自如,不刻板”。 他还在《儿童亲卫队·后记》中写过一段话: “童谣,童歌应当多写。惟其是童子话,童子的意趣,因之成为最有力的武器。除了童谣,在大众化方面,没有第二样适当的形态。”显然,在革命与抗战的年代,儿童诗歌首先是作为一种“武器”,而不完全为了“称孩子们的心”。当时很多诗人为儿童写作过歌谣化诗歌,这类堪称“战歌”的儿童诗歌,具有强烈的时代性、鼓动性、写实性,也别具一种粗犷刚健的力量之美。虽然对宣传鼓动作用的片面强调不同程度影响了诗歌的艺术水准,有些急就章近于标语口号,诗味不足,但它毕竟扩大了儿童诗歌的表现领域,赋予了歌谣形式以新的内容,凭借对政治与历史的自主性介入,儿童诗歌也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获得了一种力量与尊严。同时,创作中也不同程度体现出对儿童兴趣、欣赏特点等的顾及,只不过这些儿童兴趣、爱好、欣赏特点等在五四时期曾属于儿童文学的“价值单元”,这一时期却在很大程度上被“手段化”了,成为实现儿童文学宣传、鼓动,教育功能的手段。这一点也反映在三四十年代的儿童科学文艺、儿童小说、童话和儿童戏剧中,“革命”与“抗战”成为整个时代儿童文学的核心话语。
本时期“非歌谣化”的儿童诗也取得了丰硕成就,产生了不少散文化的自由体诗,这些诗作虽也是以“革命”与“抗战”为主题,语言通俗,但不讲究朗朗上口的音韵,句式上也相当自由,更注重构思的巧妙、内在的节奏、诗情的渲染与诗境的营构。例如孙犁的《儿童团长》、方明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贺敬之的《牛》等儿童叙事( 长) 诗的创作,表现出比那些歌谣化“战歌”更为深沉厚重的诗情,诗味浓郁且颇具儿童性,避免了歌谣化诗作的概念化、标语化、口号式,从而将此期的儿童诗歌推向更为成熟深化的境地。此外,在时代的边缘与夹缝中还产生了部分抒写童心童趣、不涉及“革命”与“抗战”等现实主题的诗作。比如 30 年代前期叶圣陶创作的《萤火虫》、《蜗牛看花》、《蜘蛛和蜻蜓》、《北边冷地方》等儿童诗,40 年代后期圣野和郭风的童话诗,亦追求一种“无意思之意思”的诗歌情趣,是“用无邪的童心在歌唱”,其风格意境直追五四时期儿童本位之诗歌。圣野的《欢迎小雨点》、《小河骑过小平原》、《小妹妹醒来》、《鸡冠花与公鸡》等,沉浸在童心的世界里,用儿童的眼睛去观察体味自然界的美妙诗意,不含政治讽刺意味与教育性主题,多用拟人化手法塑造形象,趣味盎然。郭风的《我的叔叔———稻草人》、《油菜花的童话》、《菌的旅行》、《小野菊的童话》、《豌豆的三姐妹》、《小野花的茶会》、《木偶戏》、《林中》等,则以一颗纤尘不染的童心、质朴优美的语言、自由匀称的结构和音乐般的旋律赋予一草一木纯真的生命,在炮火硝烟中为孩子们开辟出一片温馨静谧的天地,具有田园交响诗的抒情风格。这些诗作以其内容和风格的新颖在当时就引起文坛注目,“标志着中国儿童诗走向成熟、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一个新起点”。
综上所述,从晚清民初时体现儿歌“浅而有味”价值理想的“老鸦”,到五四时期表现儿童“拜物教”思想、体现儿童本位观念的“老鸹”,再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寄寓着社会政治意义的“乌鸦”,三只“老鸦”以各自的形貌与内涵勾勒出中国近现代儿童诗歌艺术的演变轨迹,显示了迥然相异的诗歌风格与意境,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中国近现代儿童文学的三次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