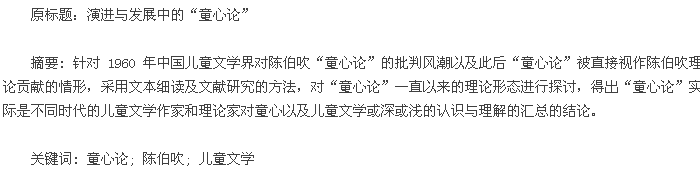
就如同茅盾在《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一文中所提到的那样: “1960 年是少年儿童文学理论斗争最热烈的一年。”
[1]在这一年,我国儿童文学领域里发生了批判陈伯吹“童心论”的运动。这场批判运动缘起于陈伯吹在 1956 年和 1958 年先后发表的《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和《漫谈当前儿童文学问题》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后来又都被收录在陈伯吹 1959 年出版的《儿童文学简论》一书当中。
在《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中,陈伯吹认为存在着年龄差异的儿童会有不同的阅读需求: “即使在儿童文学自身中,也由于儿童年龄特征的关系,各个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各有他们不同的心理状态和社会环境,从而产生不同的特殊的需要。”他进而提出: “一个有成就的作家,能够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所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
[2]在《漫谈当前儿童文学问题》一文中,陈伯吹有感于自己在编辑审稿工作中的体会而格外强调编辑在审读儿童文学作品时要拥有一颗“童心”,否则就会出现成人读者叫好而儿童读者并不感兴趣的成人化儿童文学作品:
如果审读儿童文学作品不从“儿童观点”出发,不在“儿童情趣”上体会,不怀着一颗“童心”去欣赏鉴别,一定会有“沧海遗珠”的遗憾; 那些被发表和被出版的作品,很可能得到成年人的同声赞美,而真正的小读者未必感到有兴趣。这在目前小学校里的老师们,颇多有这样的体会。这没什么奇怪,因为它们是“成人的”儿童文学作品啊![3]293无疑,上述这些看法均显现着作为儿童文学作家和理论家的陈伯吹对如何创作出令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儿童文学作品的精准而清醒的认知。但在高度强调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的政治年代里,陈伯吹的上述观点很容易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在儿童文学领域中的反映”,是在“鼓吹‘儿童文学特殊性’,它抹煞儿童文学的阶级性,促使儿童文学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并游离了思想性而只着眼于艺术性,会陷入‘艺术至上论’的泥坑中去……”[3]300“企图在儿童文学领域内,以资产阶级的‘童心论’,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以资产阶级庸俗的、低级的儿童趣味,来代替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无产阶级政治思想教育”[4]。因此,像《人民文学》《上海文学》《文汇报》《文艺报》《儿童文学研究》等权威报刊在 1960 年较为集中地刊登了诸如左林《坚持儿童文学的共产主义方向》、杨如能《驳陈伯吹的童心论》、徐景贤《儿童文学同样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批判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特殊论》等文章,对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理论主张乃至创作进行了火力集中的清算与批判。这场旨在大破儿童文学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运动令正常的也是可贵的儿童文学的艺术探索与理论研究遭遇了重创,也长时间地造成了一种理论错觉,很容易让人们简单地将陈伯吹与“童心论”直接画上了等号。就是到了今天,研究界在历数陈伯吹的儿童文学贡献时,还会特意提到是其“提出了着名的‘童心论’”[5]的。
而如果稍加体察就会看到,仅在文学领域而言,“童心论”绝不会是某一个人的理论贡献,而一定是不同时代的儿童文学作家和理论家们对童心或深或浅的认识与理解的汇总,陈伯吹个人对“童心”的阐述只是“童心论”中比较有代表性、比较有影响的一种观点而已。对于这一切,有必要清醒地体认到。
如果贴标签似地把它归结于某一个人的理论发现或发明,那就有可能一叶障目,造成理论认识上的误区与盲点。在中国,“童心论”向上可追溯到明代李贽《焚书》中的大量相关论说,诸如: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 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6]自然,李贽的“童心说”还并不在于唤醒人们认识儿童,而是在借机呼唤和赞美人的真心真情,其“童心说”的文学主张旨在将文学创作从代圣人立言而拉回到对现实人生和真性至情的热切观照上来。
在中国,真正发现儿童和认识儿童,是要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这之前,中国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7]。儿童的独立人格和社会地位尚且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也就不可能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的儿童文学创作。
而“五四”以后随着西方理论家诸如杜威“儿童中心主义论”等先进儿童观被引进和广为接受,国人逐渐树立起现代的新型的儿童本位观。一个人、一个时代、一个国度具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就决定了这个人、这个时代、这个国度具有什么样的儿童文学观,并因此会有与之相应的儿童文学实践活动。所以,中国儿童文学真正形成一个独立的、自觉的文学门类,只能是在“五四”时期儿童被发现之后。像鲁迅、周作人兄弟相继在 1919 年和 1920 年撰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儿童的文学》两篇文章不但有对陈腐的传统儿童观的无情批判与质疑,也有对西方“儿童本位论”的倡导: “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 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8],更对儿童文学创作应顾及儿童“内外两面的生活的需要”而有着积极的思考: “在诗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倡爱国,专为将来设想,不顾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的办法,也不免浪费了儿童的时间,缺损了儿童的生活。”[7]只有当成人们真正意识到儿童的特殊性,与儿童心理接轨的儿童文学的产生才是可能的。
因此,“五四”时期对儿童的发现,令中国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而与“发现儿童”相伴而生的“认识儿童”,则令儿童文学的发展变得规范、细致,也更加科学可行。只是人们对儿童生理和心理特征的认识与理解不可能一朝一夕之间就完成,因此“童心论”的沿革演变也必然要有很长一条道路要走,必然会在不同时代被注入新的内容或代以新的名称。早在《儿童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就已经借助自己掌握的儿童心理学知识,依据有关儿童的不同生长阶段———婴儿期( 1 至 3 岁) 、幼儿期( 3至 10 岁) 、少年期( 10 至 15 岁) 和青年期( 15 至 20岁) ,而着重探讨了儿童文学的幼儿前期( 3 至 6岁) 、幼儿后期( 6 至 10 岁) 和少年期( 10 至 15 岁)的不同心理特征,并对此间儿童对诗歌、童话、寓言、故事和戏剧等不同文体的喜好与接受进行了较为细1应该遵从儿童的心理特征。这种认知虽未必就能说明周作人一定是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童心论”的始作俑者,但足以说明他的儿童本位主义主张者的身份,其据此对儿童文学的认知殊为宝贵; 只是他这有价值的见解在其后因为种种复杂原因而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如 20 世纪 30 年代为配合阶级革命乃至民族救亡等时代需要而令儿童本位观遭到了搁置与冷落,那种全力展现儿童情趣的儿童文学创作也因此搁浅。
到了和平建设的 20 世纪 50 年代,对儿童内在经验世界与想象世界的重视不免会被提到日程上来。类似陈伯吹“童心论”的相关理论认识得以抬头也属于必然。其实,在陈伯吹“提出”“童心论”的前后,许多作家就都已经对童心以及儿童文学特殊性有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认识了。比如作家冰心在 1957 年 2 月 15 日写就的《〈1956 儿童文学选〉序言》中表示:所谓“童心”,就是儿童的心理特征。“童心”不只是天真活泼而已,这里还包括有: 强烈的正义感———因此儿童不能容忍原谅人们说谎作伪; 深厚的同情心———因此儿童看到被压迫损害的人和物,都会发出不平的呼声,落下伤心的眼泪; 以及他们对于比自己能力高、年纪大、经验多的人的羡慕和钦佩———因此他们崇拜名人英雄,模仿父母师长兄姐的言行。他们热爱生活; 喜欢集体活动; 喜爱一切美丽、新奇、活动的东西,也爱看灿烂的颜色,爱听谐美的声音。他们对于新事物充满着好奇心,勇于尝试,不怕危险……针对着这些心理特点,我们就要学会用他们所熟悉,能接受、能欣赏的语言,给他们写出能激发他们的正义感和同情心的散文和小说; 写出有生活趣味,能引起他们钦慕仿效的伟大人物的传记; 以及美丽动人的童话,琅琅上口的诗歌,和使他们增加知识活泼心灵的游记,惊险故事,和科学文艺作品。
[9]冰心不但看到“童心”与生俱来的天真活泼的自然本性,更看到“童心”后天成长中的社会属性,其对“童心”的认知带有那个时代对儿童社会道德规范的明显烙印,也因此对理想的儿童文学创作有她的期冀。甚至就是陈伯吹“童心论”的批评者们,事实上也对童心和儿童文学有着与陈伯吹近乎一致的认识,虽然可能是浅尝辄止或者蜻蜓点水。如杨如能就认为: “创作和研究儿童文学,应该研究儿童的年龄特征,看不到或者否认这一点是不对的。”
[4]左林认为: “儿童文学作品既然是写给少年儿童看的,那末,它要达到教育少年儿童的目的,它就必须切合少年儿童的水平,为他们所喜闻乐见。为此目的,作者就应当努力了解儿童的心理、儿童的思想感情,了解他们的生活,熟悉他们的语言。”
[10]再如同样是陈伯吹“童心论”批判者的贺宜,早在《火花》1959 年 6 月号上撰文《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关键问题———儿童化》时,就举出自己看到的一些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种种怪现象: “对低年级的孩子,用高年级才能懂得,才能感到兴趣的话( 包括着语法和思想内容) ; 对高年级的孩子,用低年级孩子感到兴趣的话”,并对其中原因进行剖析,认为那是因为写作者“忘记了在给谁写。忘记了: 孩子们并不是一样大,并不是不懂得一样多”。因此他主张: “对于一个儿童文学作者重要的是善于了解不同年龄的儿童的阅读兴趣。只有这样,才可以使作品更儿童化,更吸引小读者。”
[11]其对童心以及儿童文学所持有的观点与陈伯吹如出一辙。又如对“童心论”这场论争予以重视并进行评述的茅盾在《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中一面肯定“童心论”是从资产阶级儿童文学理论“童心论”或“儿童本位论”引起来的,“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一面认为对“童心论”中的合理成分要认真分析对待,“从 4 岁到 14 岁这 10 年中,即由童年而进入少年时代这 10 年中,小朋友们的理解、联想、推论、判断的能力,是年复一年都不相同的,而且同年龄的儿童或少年也不具有完全相同的理解、联想、推论、判断的能力。这种又由年龄关系而产生的智力上的差别,是自然的法则,为儿童或少年服务的作家们如果无视这种自然法则,主观地硬要把 8 岁儿童才能理解、消化的东西塞给五六岁的儿童,那就不仅事倍功半而已,而且不利儿童智力的健全发展”。在茅盾看来,儿童文学作家“了解不同年龄的儿童、少年心理活动的特点,却是必要的; 而所以要了解他们的特点,就为的是要找出最适合于不同年龄儿童、少年的不同的表现方式。在这里,题材不成问题,主要是看你用的是怎样的表现方式。
你心目中的小读者是学龄前儿童呢,还是低年级儿童,还是十三四岁的少年,你就得考虑,怎样的表现方式最有效、最有吸引力; 同时,而且当然,你就得在你的作品中尽量使用你的小读者们会感到亲切、生动、富于形象性的语言,而努力避免那些干巴巴的、有点像某些报告中所用的语言”[1]。
至于作为“童心论”批判运动中众矢之的的陈伯吹本人,在《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中引用了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每一个进入儿童文学的作者都应当考虑读者年龄的一切特点。否则他的书就成为没有用的书,儿童不需要,成人也不需要”的经典阐述为自己的“理论”开路,借此呼吁要“正确地、深刻地理解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他还看到了儿童年龄层次的差异性和因此产生的不同阅读需求:“学龄前的幼童,小学校的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生,以及中学校的初中生,因为他们的年龄不同,也就是他们的心理、生理的成长和发展不同,形成思想观念和掌握科技知识也是在不同的阶段上,儿童文学作品必须在客观上和它的读者对象的主观条件相适应,这才算是真正的儿童的文学作品。”
[2]即令在1960 年遭遇了铺天盖地的批判,陈伯吹在稍后发表的《幼儿文学必须繁荣发展起来》一文中还是对自己先前的观点有所保留,并小心翼翼地提出来儿童文学创作与阅读分层次的必要性问题: “在儿童文学中,是否也还存在着幼童文学( 或者叫做低幼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少年文学的分野? 从特定的教育对象的儿童年龄阶段上来看,是否有这样划分的必要?
更从教育的任务上来看,这样划分了是否更利于教育效果的丰收? 这,当然是个人意见,有待于深入讨论。”[12]其本人的“童心论”无非是根据自己的创作心得呼唤儿童文学创作者们能深切地了解儿童的心理状态,并能有针对性地艺术而技巧地创作出为不同年龄段儿童所喜闻乐见的作品来。
在进入新时期以后,现代的、进步的、文明的儿童观重新得到了确认,现代儿童文学观也因之得到了大力张扬。儿童文学作家鲁兵 1981 年发表长文《教育儿童的文学》,其中就有对“童心论”老调的重弹: “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和时代,出身于不同的阶级、阶层和家庭,接受不同的教育,那么同一年龄的儿童,其心理特征也会有所差别。我们说的儿童,包括三四岁的幼儿到十三四岁的少年,人在这十年中变化很大,幼儿刚刚离开妈妈的怀抱,可以说是乳臭未干,而少年再往前迈一步,就是青年了。幼儿还不识字,给他们阅读的书是以图画为主的,而少年已经能啃大部头的小说了。因此,我们很难笼统地列出一些儿童文学特点。因为幼儿还只能接受主题单一、人物较少、情节简单的故事。少年就不同了,他们热衷于曲折离奇的故事。这种差别,不仅仅表现在作品的篇幅之大小、容量之多少、程序之深浅,同时表现在题材、形式、构思、语言等各方面。将供少年阅读的作品,篇幅缩短一点,文字改浅一点,就当作供幼儿阅读的作品,这是不行的。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意见,将我们现在所说的儿童文学一分为三,幼儿文学,儿童文学,少年文学,再来探讨它们的特点。
这个意见是可取的,如果要将儿童文学特点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就得这么办。”
[13]虽然此文对儿童文学按照儿童年龄层次划分的思考还不够细致,还只是一种设想,并没有作出更明确的理论阐析,但无疑是对从前包括周作人、陈伯吹、茅盾等诸位大家有关儿童文学见解的承继与发扬,更直接启发了后来的儿童文学理论者们。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王泉根那篇对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论少年儿童年龄特征的差异性与多层次的儿童文学分类》文章就明显得益于前人的理论探索,其中有提到: “正如儿童心理学只注重研究幼年———童年———少年的不同心理特征而从来不研究三到十五岁这一整个年龄阶段的少年儿童有什么共通的心理特征一样,我们的儿童文学也完全没有必要探讨为三到十五岁的少年儿童服务的文学有什么统一的本质特征,而应当集中精力去探讨为幼年———童年———少年这三个层次的孩子们服务的文学各有什么本质特征,及其思想、艺术上的要求。用不着再把它们生拉活扯捆绑在一起,试图提出一个统一的而结果又往往是混沌一团、各说各有理的标准。换言之,我们应当做的是: 第一,把‘儿童文学’分一为三,明确提出并肯定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的概念。把它们从‘儿童文学’这个单一概念中独立出来,自成一系。第二,然后再去探讨这三种文学各自的本质特征与思想、艺术应有怎样的要求。”
[14]在其后 20 年间,他相继在《儿童文学的三个层次与两大门类》《论儿童文学审美创造中的艺术形象、艺术视角》《论新时期儿童文学》《论少年小说与少年心理》等诸多文章中进一步对此论断进行了更为细致的阐发和合理的深化,产生的巨大影响有目共睹。
而此间真正在儿童文学创作中践行“童心论”并获得小读者衷心拥戴的儿童文学作家更是数不胜数,如张之路、曹文轩、秦文君、杨红樱、薛涛等均取得了文学成功,像有着“中国童书皇后”之美誉的杨红樱,其作品总销量至今早已经远远超过了 6000 万册,而这就得益于其对童心深刻而独到的理解与表现,得益于其对自己作品目标读者的成功定位。
另外,还要提到的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在我国推广和实践的分级阅读观念及相关的推广活动,看上去既像是一个新生事物———属于新理念、新方法,同时也更像是一个地道的舶来品,因为以“分级阅读”这一术语本身来看,可以追根溯源到西方英美国家在 20 世纪 20 年代出现的分级阅读体系,甚至还可以上溯到 18 世纪 70 年代美国成立之初的阅读教学。但事实上,分级阅读不过是人们按照儿童不同年龄段的心智发展特点而为其量体裁衣设置和提供的较为科学、合理的阅读计划而已。归根结底,分级阅读仍然不过是“童心论”的理论变种与另类表现模式,是人们在对童心有了充分、深入的理解与认识之后,基于儿童本位立场而对包括儿童文学作品在内的儿童读物所做的自觉有序的区分与认定。它并没有超出前面文中引用的诸如陈伯吹、茅盾、贺宜、王泉根等对童心的理解和对儿童文学分层次、分年龄段的见解,只不过是换了理论“马甲”,并更具有可操作性而已。
回眸“童心论”,不难发现,其绝不是某一个人的理论发明与贡献,而一定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从事着与儿童有关工作的人们———儿童心理学家、儿童教育学家,自然也包括诸多儿童文学作家与理论家们———的智慧的凝结。一切正如歌德所说: “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 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15]随着人们对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成功“破译”与尊重程度的加深,“童心论”这一理论体系还会不断得到完善,而其对儿童文学健康发展的引领作用仍然值得人们期待。
参考文献:
[1]茅盾. 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J]. 上海文学,1961( 8) : 3 -14.
[2]陈伯吹. 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M]/ /王泉根. 中国儿童文学 60 年( 1949—2009) . 武汉: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 23.
[3]陈伯吹.“童心”与“童心论”[M]/ /王泉根. 中国儿童文学 60 年( 1949—2009) . 武汉: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
[4]杨如能. 驳陈伯吹的童心论[J]. 上海文学,1960( 7) : 66- 68.
[5]刘颋. 陈伯吹先生诞辰 100 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京召开[N]. 文艺报,2006 -07 -20( 1) .
一、现代性概念的界定现代性被学界引入文学领域后,即被作为一种文学理论范畴,发挥着对文本进行讨论和批判的作用。关于文学理论现代性的定义学界一直是众说纷纭,要对文学理论现代性下一个明确定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笔者在对有关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含义...
一切理论的探索,归根到底都是方法的探索。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是密切相关的,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会有不同的研究方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将方法划分为三大层次,认为,方法论在不同层次上有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之分。作为一门新...
王泉根教授三十余年来一直坚持在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勤奋而默默地耕耘着,不但奠定了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坚实基石,也有效推进和深化了人们对儿童文学的认识。《担当与建构:王泉根文论集》所收录的三十多篇文章集中呈现了王泉根近些年来对儿童文学理论关键问题...
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蒙古族的迁徙生活直接推动了文化的流动,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汉化,或者西征途中对于西方文明的裹挟,以及宗教信仰的发展、变化,都直接推动了蒙古民族文化多元共生局面的出现。而蒙古民族世代相传的开放心态,进一步加速和强化了这种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