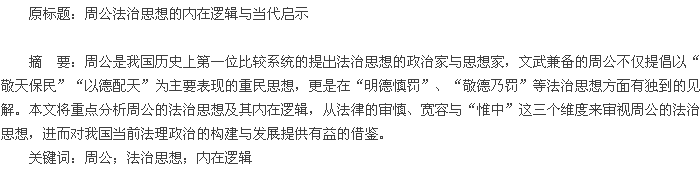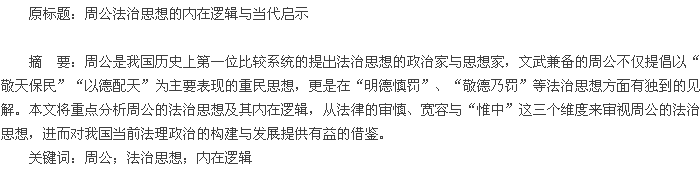
一、“惟命不于常”的政治现实催生了法律的公正与审慎
周公的法治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康诰》中,而《康诰》是周公封康叔时作的文告。周公在平定三监(管叔、蔡叔、霍叔)武庚所发动的叛乱后,便封康叔于殷地。这个文告就是康叔上任之前,周公对他所作的训辞。也就是说,周公的这篇《康诰》是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的,至少有两件大事影响了周公《康诰》的思想。
一是周公辅佐武王伐纣。这场革命的胜利让周公深刻感受到:牧野之战中商兵的阵前倒戈让武王顺利进入朝歌,殷商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商纣王的暴虐无德失了人心,进而失了天下。这使得周公认识到“惟命不于常”(《尚书 · 康诰》)的政治现实,没有万年不易的朝代,周取代殷在当时看来是顺应天命,那么将来周又会被谁同样以顺应天命来取代呢?或者说周要如何做,才能让这一天来得更晚些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虽然不仅仅体现在《康诰》里,但的确《康诰》的思想比较集中反映了周公对现实的应对与思考。
二是三监叛乱。据《史记 · 周公世家》记载,周武王伐纣后两年生了一场大病,虽然周公在祈祷中甘当人质、代发受命,但武王还是死了,而这场叛乱便是在武王新死、成王年幼的状态下发动的,这场集合了商纣之子武庚和周公的两个兄弟管叔与蔡叔的叛乱终于被镇压了,但这次叛乱让周公认识到,叛乱的发生是周朝的政权不稳,为了让周朝的政权具备长久且稳固的统治根基,周公对即将赴任管理殷朝余民的康叔写下了这篇训辞,意在告诫康叔如果不看到“惟命不于常”这一政治现实,不采用切实有效的办法来笼络当地民心,政权是不会稳固的。在这一背景下,周公给康叔开出了快速有效地收拢民心的一剂药方:坚守法律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 确保刑罚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刑罚本身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更是将国家意志向下层民众传递的重要载体,而刑罚不当必然会损及国家的权威、危害国家的统治。为此,周公认为必须要确保刑罚本身的权威性。“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不畏死,罔弗憝。”(《尚书 · 康诰》)意即,“凡是民众自己犯下了罪行,作贼抢劫,内外作乱,杀人越货,为人强梁不怕死,就不能不诛杀掉。”对于那些作奸犯科之人,只有施以刑罚才能让老百姓养成遵守法律的习惯。“有叙时,乃大明服,惟民其敕懋和。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无或劓刵人。”(《尚书 ·康诰》)其意为:“如果你能照这样去做,就会使臣民顺服,臣民就会互相劝勉,和顺相处。要像医治病人一样,尽力让臣民抛弃自己的过错。要像护理孩子一样保护臣民,使他们健康安宁。除了你封可以惩处人、杀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权惩罚人、杀人。除了你封可以下令割罪人的鼻子和耳朵外,任何人都不能施行割鼻断耳的刑罚。”此部分强调法律本身的权威性。作为治理一方的君主,决不能将生杀予夺的大权假借于人,不仅是为了防止刑罚大权被他人滥用,更是确保君主大权独揽的必要手段。否则,刑杀权旁落,遭到怨恨的不仅仅是施刑者,还有将权力交给施刑者的主政者,这对治国安民是极为不利的。因此,由君主一人掌管和实施刑罚,可以确保刑罚本身的权威性。
2. 明德慎罚,即对待法律要谨慎严明
所谓谨慎严明,不仅要赏罚有类,还要考察犯罪者的动机,重罚故意犯罪且不思悔改者,适当处罚过失犯罪且愿意悔改者。“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尚书 · 康诰》)大意为:“对刑罚要谨慎严明。如果一个人犯了小罪,而不是过失,还经常干一些违法的事;这样,虽然他的罪过小,却不能不杀。
如果一个人犯了大罪,但不是一贯如此,而只是由过失造成的灾祸;这是偶然犯罪,可以按法律给予适当处罚,不应把他杀掉。”可见,对于那些犯了大错,但是只是偶然一次的过失,和那些虽然犯了小错,却屡教不改一再以身试法的人,在用刑上要区别对待。前者可以宽恕,但后者必须严惩。可以说,犯罪者的主观态度在量刑定罪方面起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二、“明德配天”思想指导下的法律中的伦理与宽容
《召诰》有言:“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也就是说,夏代和殷代的国运之所以没有继续延长下去,是因为彼时的君主都不重视行德,才过早失去了他们的福命。我们只有吸取教训,认真推行德政,发扬美德,才能让我们的国家更长久。由此可见,周公将敬德看作是掌权者长久保有统治的不二法门,而刑罚作为与德相对的统治方式,刑罚亦应为德服务,由此推导出刑罚的主要目的不是惩戒,而是教化民众,使他们行德扬德,以此延续国家的长久统治。正所谓“勿庸杀之,姑惟教之”(《尚书 · 酒诰》)。“殄戮多罪,亦克用劝,开释无辜,亦克用劝”,“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尚书·多士》)可见,先教而后杀是周公法律思维中的首要原则,只有先对民众进行教化,对于屡教不改者再行刑罚才能让对方心服口服,不经过教化就直接实行刑罚只会激起百姓的怨怒。因此,将道德教化融入法律之中,用宽容的精神来实施刑罚才能真正发挥法律的功能。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周公提出了将道德教化融入法律的相关举措。
1. 重罚不孝不友者
人情伦理能否融合到实际的法律判决之中,这个问题历来就没有定论。因为秉公执法,在很多时候就不能将人情伦理掺杂进来,这往往会损害法律本身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但是如果离开了人情的参照,白纸黑字的法律是否就一定能彰显社会公正,还是会变成僵硬死板的教条?我国被誉为“法律文化论开创者”的梁治平曾专门着书《法意与人情》来探讨这一问题,足见对该问题的解答不是简单为之的事情。不过在周公那里,他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即他承认人情的重要性,并将反映人情是非的伦理纲常融入到实际的刑罚当中,使刑罚与伦理相结合,进而确保刑罚的双重功能的实现,即刑罚不仅要“杀人”,还要“救人。”
“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其意为,“遭人怨恨的大罪恶,就是不孝敬不友爱。
儿子不恭敬地从事他父亲的事业,就很伤他父亲的心;身为父亲不疼爱他的儿子,还厌恶他的儿子。当弟弟的不顾念天理,就不能尊敬他的兄长;兄长不惦念幼子的可怜,就是对弟弟不友爱。到了这种田地,如不由我们的官员治罪,上天将使我们民众所遵守的法律混乱。那就迅速使用文王制定的刑罚,惩罚他们,不要赦免。”
2. 引养引恬的宽容之政
周公虽然讲到对于杀人越货者、不孝不友者要重罚,绝不姑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刑罚思想是以重罚为主,相反,在《梓材》篇中,周公强调刑罚只是一种手段,还是以道德教化为主,劝民向善,整饬民风。《周礼·秋官》中有“三赦之法”的规定:“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西周法律规定,年幼无知的孩童、年老体衰的耄耋老人和精神障碍的痴呆愚蠢者违法犯罪,除亲手故意杀人外,一般均可赦免,免予追究刑事责任。“肆往,奸宄、杀人、历人;肆亦见厥君事、戕败人,宥。王启监,厥乱为民。曰:‘无胥戕,无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养引恬。’
自古王若兹监,罔攸辟。”(《尚书·梓材》)大意为:“往日,内外作乱的罪犯、杀人的罪犯、虏人的罪犯,要宽恕;往日,泄露国君大事的罪犯、残坏人体的罪犯,也要宽恕。王者建立诸侯,大率在于教化人民。他说:‘不要互相残害,不要互相暴虐,至于鳏夫寡妇,至于孕妇,要同样教导和宽容。’王者教导诸侯和诸侯国的官员,他的诰命是用什么呢?就是‘长养百姓,长安百姓’。自古君王都象这样监督,也就没有什么偏差!”以及“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已!若兹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意即:“上天既已把中国的臣民和疆土都付给先王,今王也只有施行德政,来和悦、教导殷商那些迷惑的人民,用来完成先王所受的使命。唉!像这样治理殷民,我想你将传到万年,同王的子子孙孙永远保有殷民。”
三、“敬天保民”思想衍生出的法律“惟中”之道
“天”在古人眼中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如同西方人眼中的“上帝”一样,但是必须指出,此处的“天”与西方的“上帝”并不是一个概念,只能说在功能上起着类似的作用。“天”在古人那里因神秘而获得了无上的权威,但凡有重大事件,都需要通过占卜来传递上天的旨意,蔡元培先生曾说:“五千年前,吾族由西方来,居黄河之滨,筑室力田,与冷酷之气候相竞,日不暇给。沐雨露之惠,懔水旱之灾,则求其源于苍苍之天。而以为是即至高无上之神灵,监吾民而赏罚之者也。”可以说,在经济、科技发展水平都相对落后的古代社会,大自然界、社会中发生的一些奇怪的事件无法得到人为的科学的解释,于是将这些无法解释的现象都诉诸于天,天又因为本身的这种神秘莫测更加重了自身的权威,最终演变为古人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支柱。
周公把“天”与“德”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君主敬天就必须要明德,君主明德也就是在敬天,“天”与“德”的一致性也就自然引申出君主的无上权威,君主是代表了上天的意志来治理百姓,百姓是不能违背的,因为违背君主的意志也就等于是违背了上天的意志。如果说德是君主借上天旨意教化小民,在君与民之间确立良性沟通的精神中介的话,那么罚则是君主为维护社会稳定与规范社会秩序而对民采取的普遍性的制度约束。而这种约束的指导原则便是“惟中”,即“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尚书·立政》)强调刑罚应宽严适当,刑当其罪,以适中的态度使用刑罚,避免出现过重或过轻的现象。周公之所以采用“惟中”之道来施行法律,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主要源于殷商末年的严刑酷法带来的民怨的积聚,而最终导致人心涣散、政权瓦解,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法律适用的主观随意性。夏商周时期,由于没有公布成文法,统治者往往“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左传 ·昭公六年》)而墨、劓、刖、宫、大辟等五种酷刑在适用过程中往往会因为施刑者的主观随意而给民众带来巨大的伤害,商代甲骨文则记录了大量通过占卜来定罪量刑的内容,如“贞,王闻不惟辟,王闻惟辟。”(《殷墟文字乙编》,4604)刑罚的使用主要根据天意或者说占卜的随机结果来进行裁定,必然会在现实中积累民怨。
其次,法律的严苛与重罚。商朝的法律规定,“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韩非子 · 内储说上》)到了商朝末年,纣王的荒淫无度更加剧了法律的严苛程度,导致“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史记·殷本纪》)“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痛四海”(《尚书·泰誓》),这种“折民惟刑”(《尚书·汤誓》)的统治方式只会造成法律的过度滥用而引起百姓的叛离。
最后,法律中酷刑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一人犯罪,株连甚广,刑罚的酷烈程度让殷民心生恐惧,民心涣散,法律的过度使用和过重的惩罚最终将商朝推向了灭亡的深渊。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周公坚决反对不加甄别的“罪人以族”和“妻子无辜,并为鲸鲵”的族诛连坐刑罚,主张“罪止一身”,消除滥施族刑牵连众多无辜的弊端。周公强调“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要求只惩罚犯罪者本人。周公这种“罚不及嗣”的法律态度便源于殷纣王使用株连酷刑而导致的恐怖社会氛围与沸腾的民怨。为此,周公吸取殷鉴不远的历史教训,认识到如果继续奉行严刑峻法,民心自然不会归附,要想笼络人心,就必须让法律的使用处于“适中”的状态,不会过度地使用和滥用,百姓只有在宽和的法律环境中才能感受周朝的仁政与美好,进而才会真心拥护周朝的统治,因为周公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天”与“民”存在着某种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要求法律的适用必须要在“民”与“天”认可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法律的“惟中”之道既体现了上天的意志,又符合民意的要求,是二者共同要求下的现实结果。因此,周公倡导的“惟中”之道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其“敬天保民”的政治策略了。
四、周公法治思想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1. 法律的审慎精神
法律本身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情,一旦被适用就意味着被实施者必然会因此而受到人身或财产上的约束或剥夺,这种伤害往往是直接的,一旦用刑不当就会给被实施者带来严重的利益伤害,更为重要的是法律的权威和公正会因此受到破坏。可见,在适用法律的时候必须保持审慎的态度去认真对待,尤其遇到一些重大且复杂的案件时,非常需要施刑者具备强烈的审慎态度来做出公正的判决,一旦判决有误,其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个人的,更重要的是给社会带来的深远的危害。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言,“一次错误的判决,有甚于十次犯罪, 因为犯罪污染的是水流,而错误的判决污染的却是水源。” 由此可见,适用何种法律并且适用到何种程度不仅仅会对当事人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给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一旦法律适用错误,其影响便带有根源性而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危害。因此,法律的适用必须用审慎的态度考虑到其产生的社会后果,以确保法律的权威与威信。
2. 法律的宽容精神
周公一再告诫我们,惩罚并不是法律的主要功能,只是法律的一种表现方式,法律的主要功能是寓教于中的宣导与劝引。也就是说,教化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事情,法律也可以起到教化的作用,关键在于如何将道德有效合理地嵌入到法律体系当中,虽然周公将不孝不友者看作是最重大的罪行需要加以法律的惩戒,这在今天看来也许有些极端和过度,但是不容忽视的是,道德的某些层面是不是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来加以引导,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尤其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带来的人们对利益的追求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如何应对冷漠带来的见死不救、见义不为等现象,是否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来得到缓解,确实值得我们思考。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记住,法律的宗旨并不是“杀人”和“惩戒”,而应该是“治病和救人”,用法律的宽容来引导社会风气,用道德来感化不法之徒与不法之举。
3. 法律的“惟中”精神
我们知道,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那么法律也就必然地与道德关联在一起。中国历史上曾经上演过不止一次的“恶法”现象,从商纣王到秦始皇,他们都把严刑峻法作为治国的主要手段,结局自然是注定的失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抛弃了严苛的法律,就可以径直走向它的另一个极端,将人情、个人意志过多地掺杂进来,审案、断案都以人情、关系为基础,“近爱有过不诛、疏贱有功不赏”,法律被一层厚厚的关系网包裹起来,法律条文则成为了装饰品,这样的法律无疑既不会维护当事人的正当合法权益,也不会将国家与百姓的利益联结在一起,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因此,坚守法律的“惟中”之道要求我们,既要依据清晰明确的法律制度,又要参照法律事实背后的人情道德,同时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只有带着这种法律意识去处理法律事务,才能真正有效地彰显法律的精神,并为构筑强大的法治文明的国家提供依托。
参考文献:
[1] 梁治平 . 法意与人情 [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2] 蔡元培 . 中国伦理学史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 李文娟 . 周公的“明德慎罚”法律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J].淮海工学院学报,2011(13):4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