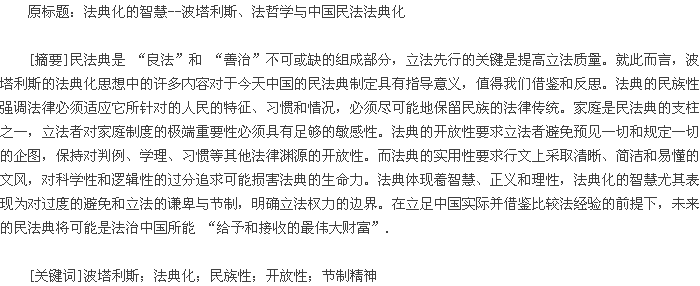
中国民事领域的法典化工程如今进入到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在法典化进程启动近二十年后,立法机关成功地制定了 《担保法》、 《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一大批民事法律;但人格权、民法总则等重要法律仍然付之阙如。
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未来的民事立法工作注入了新的动力,并指明了其方向与出路:“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
2015年5月和7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组织起草了 “民法典总则”和 “民法典人格权编”的专家建议稿。这些都标志着中国民法典编纂工作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为了编纂一部高质量的民法典,我们有必要充分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尽管我国立法和法学研究历来注重对比较法的借鉴,然而,这些借鉴主要是教义学意义上的,侧重于对国外具体制度的比较;而从法哲学层面在整体上对国外法典化思想的参考,是比较稀少的。随着我国法典化进程的加快,对比较法的借鉴参考显得尤其必要。
就此而言,法国民法典的核心起草人波塔利斯关于民法典的法哲学思想,就是我们当下推进法典化事业十分宝贵的思想财富。波塔利斯关于民法法典化的法哲学思想,集中体现于其在民法典草案审议过程中的数篇演讲中,尤其是其于1801年所发表的 《关于民法典草案的说明》。在立法史上,“这一声誉卓着的文本无论是在风格还是在内容上,都可以作为法典起草者对法典的主要原则导向、对其启示源泉的选择以及对民法在社会 中 的 角 色 的 概 念 等 在 理 论 上 的 正 当 性依据。”[1](P455)在中国民法法典化事业进入到一个关键时刻的今天,重温波塔利斯两个世纪前的法典化思想的意义在于:其一,法国民法典被公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民法典,波塔利斯的演讲则集中宣告和阐述了现代民法最为基础的一般性原则。其二,尽管民法史上曾出现了多部伟大的民法典 (如德国民法典)可以与法国民法典媲美,但是,“关于民法典草案的说明”在法律史上的地位却可谓空前绝后和独一无二,因为在法律史上不曾再有另一部对民法典精神进行系统的法哲学阐释的类似文献。其三,波塔利斯关于民法典的许多思想,是对孟德斯鸠等思想家学说的总结和提炼,具有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意义,在今天看来,其中的许多内容仍然具有浓郁的现代气息,因为它 “包含了民事立法的一般性公理……在立法大量膨胀的今天,其中的许多思想仍然值得我们深思,许多建议值得认真去倾听和采纳。”
一、民法典与法律传统。
立法必须顺应社会的演进,预测社会的需求,并适度超前于社会的发展:立法既不是革命性的颠覆,也不是一成不变,但立法必须尊重传统。孟德斯鸠曾生动地这样形容: “有些时候我们确有必要修改某些法律,但这种情形很少。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只能以颤抖的手去触碰它。”[3](P129)这就是说,法律当然可以修改,但其修改应当经过深思熟虑,绝不可轻率地修正或者废除已有的法律。在 《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的着名论断是:人受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先例、习俗、风尚等多种因素的支配,其结果是由此而形成了普遍精神。只要民族精神与整体原则不相违背,立法者就应该尊重这种民族精神;民族的习俗和风尚与他们的法律关系密切。所以,法律应当量身定做,适合于它所要适用的民族,只有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一个民族的法律才可能适合于另一个民族。只要民族精神与政体原则不相违背,立法者就应当尊重这种民族精神,因为 “只有当我们自由自在地依照天赋秉性行事时,才能做得最好”.[4](P15、357、373)这就是说,不可将人置于某种抽象的环境之中,不要去追求法律形而上学的完美,要从整体角度看待人性,尤其要注意到每个民族的独特性,注意气候、地理环境和种族等的影响,尊重本民族的特性。这与今天所说的法的 “地方性”特征是一致的。孟德斯鸠的研究也被视为政治人类学和法律人类学的肇端,具有浓厚的启蒙思想的特质。从这样的视角出发,立法者必须了解民法典所要服 务 的 “民 族 的 风 俗、特 征、政 治 与 宗 教 形势”,应当 “评估在每一种情形下,在每一个地区中,决定公理应当多元地适用于每一个民族、由此应制定不同法律的特殊的物质上和道德上的原因”.由此,好的法典起草者 “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主 义者,而是一个民族学家或者人类学家”.[5](P87)受这样的思想影响,波塔利斯富有哲理地告诫说: “切不可忘记的是,法为人而立,而非人为法而生;法律必须适应它所针对的人民的特征、习惯和情况……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最好的法律是最适合于该民族的法律。由此,不可能为不同的民族制定同一部法律,也不可能将所有的人民改造为同一个民族。”[6](P23)因此,法典化必须基于 “民族的风俗、人情和条件”而进行,以使法典在未来成为 “理性的典章”.显然,我们从波塔利斯身上可以看见孟德斯鸠 “历史相对主义”的痕迹。所以,他认为: “有必要保留一切没有必要废除的东西,法律应当珍惜习俗,如果这些习俗不是陋习的话……只有在不革新是最糟糕的时候,才必须要变革。”[7](P17、20)此点与历史法学派有共通之处,二者均强调法律形成的历史维度。但是,与萨维尼不同的是,波塔利斯强调立法者的介入,在有必要进行改革的时候,他仍然认为立法必须进行必要的变革,这种意志主义哲学显然比历史法学派更为积极。正是由于对传统的尊重和对立法连续性的考虑,民法典的起草人在民法典中广泛保留了以前的习惯法的内容。
作为对传统的尊重的表现,法国民法典 “实现了成文法与习惯法的折中,在所有可能的场合去协调它们的规则”.[8](P42)这种折中和协调具体表现为,法国民法典中的合同、债法制度、所有权与物权制度几乎都是源于罗马法,而家庭法、继承法则主要沿袭了原来的本土习惯法。做出此种选择的原因在于,起草人认为本土的习惯法与外来的罗马法之间更多的是补充关系而非竞争关系,前者适用于那些与各民族独特的风俗和习惯有密切关联的领域,而后者则适用于应由普适性原则和永恒的理性来调整的部门。正因为如此,有法律史学者形象地指出, “尽管按照起草者关于民法典结构的思路,民法典被分为三编;实际上,民法典只应该被分为两编,反映出自然法和实定法的并立”[9](P18),以分别对应于成文法和习惯法两个部分。
对自身传统的尊重及强调立法的民族性,这对于我国当前的民法典制定工作同样具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国的立法和学理界一致认为,我们应起草一部具有中国特色、可以与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等伟大法典相媲美的中国民法典。
“民法典必须体现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因为只有最民 族 化 的 民 法 典 才 是 最 有 生 命 力 的 民 法典”.[10](P49)也就是说,中国的民法典应反映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继承优良的中国法律传统,而决不能是外国民法典的简单翻版。根据法律社会学和法律人类学的研究,法律传统是 “深刻植根于历史且由历史所决定的社会主体行为的整体,包括法律的性质,法律在社会以政治性方式组织的过程中的作用,组织法律体系的最好手段,或者法律制定、适用、学习、完善和思考的方式。法律传统的概念与法律体系和法律文化密切相关;它将法律体系置于文化的视野中”.(P47)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必然要求对中国民法传统进行总结、提炼和传承。
遗憾的是,我国很多民法学者存在着这样一种误解 甚 至 偏 见:中 国 不 存 在 自 身 的 民 法 传统[12](P1138),对于今天的民法典编纂来说,在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中没有可资借鉴的资源。理由在于:根据韦伯的法律理性理论,礼法合一的传统中国法律显然不是形式理性的法律。然而,作为法典化工程最终目标的民法典,无疑是形式理性的最高成就,法典法体系具有高度的恒常性和可预见性。因此,民法法典化的使命与性质,决定了其不可能取法于中国法律传统。这些误解和偏见的错误之处在于:一方面,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中存在着大量的民法资源,如物权制度、契约制度、家庭和继承法等,其中的部分制度甚至具有很强的现代性气息;另一方面,传统中国法律其实是超越了形式理性、实质理性的区分,而且同样具有很明显的形式主义理性,是恒常和可以预期的。(P181-183)正是由于上述误解和偏见的存在,使得尊重和发扬传统的原则在我国立法中很难得到真正贯彻。以典权为例,它被公认为是中国传统民法“土生土长”的一项他物权制度,是传统中国为数不多的不动产物权之一。典权构造精妙,曾被国外学者类比为不动产质权或附买回权之买卖,或者被形容为 “向作为一种担保制度的近代质权发展中的一种过渡形态”.(P294-295)但是,典权的内涵比这些西方制度更为丰富和精巧:出典人以出典不动产的租金来充抵典权人借款的利息的安排、回赎、绝卖、找贴等制度的设计,充分体现出务实、公平与智慧,并具有济弱等促进社会正义的功能;民间还发展出 “值十当五”等规则;典权在精神上被认为更接近传统中国的 “圣王之道” 而 非 “霸 王 之 道”, 有 利 于 实 现 社 会 正义。[15](P217)总之,从各个方面看,它完全符合上述关于法律传统 的定义和特征。正因为如此,1911年 《大清民律草案》中没有规定典权,被后来的学者批评为 “不明我国习惯,贸然起草,自难免闭户造车之讥也”.这一疏漏后来在1929-1931年 《“中华民国”民法》 (第911-927条)中被弥补。这说明立法者 “在参酌外国法律趋附民法潮 流 的 同 时,并 没 有 忽 略 中 国 的 民 法 传统”.[16](P226)新中国成立后,最高人民法院也曾就典权问题颁发了数个司法解释。
然而,这一在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物权制度,在2007年 《物权法》的文本中并没有出现。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学者从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出发,认为典权在现代社会中没有实际效用,已然 “没落”.[17](P113)这一看法的错误在于,台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与大陆差异巨大,“典权没落”这一论断如果有些许道理,也只能适用于大陆地区某些一线城市,因为这些城市中由于近年来房价的高涨,不动产的租金远高于借款利息,以房屋出典来借款的情形在城市中自然很少出现;而且城市私有房屋可以有抵押等融资渠道,自无出典之必要。而反观农村,农民的宅基地不允许自由转让,地上所建房屋也无法向银行进行抵押融资,且农村的房租低廉,因此,以房屋出典来借款融资,自然有存在的合理性。尤其需要看到的是,随着农村承包经营土地流转制度的发展,典权未来所适用的对象将从房屋重新回归为土地,出典完全可以成为农地流转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典权制度在农村将大有作为。 《物权法》最终将典权排斥在外, “并不代表典制从此 将 在 我 国 的 社 会 经 济 的 舞 台 上 销 声 匿迹”.[18](P101)成文法对脱胎于长期习惯法中的制度的排斥,也折射出立法者对于传统和历史的价值缺乏必要的敏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