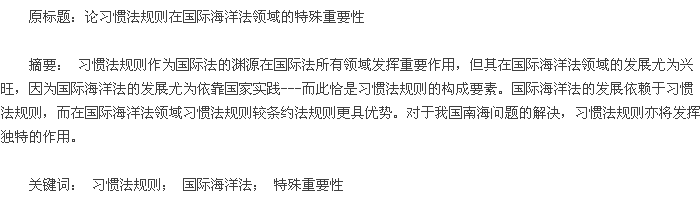
无论是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还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海洋对于人类而言,都至关重要。人类开发和利用海洋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然而在 1492 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导致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所订立的《托底西纳斯条约》之前,应当认为,国际海洋法的发展都存在于各国的国内立法( 如古印度的《摩奴法典》、罗马帝国的《罗得海上法》、拜占庭帝国的《巴西里卡法典》) 、各法学家的学说( 例如,公元 2 世纪,罗马法学家马西纳斯宣称海洋为全人类所共有)以及各国的主张( 例如,随着罗马帝国势力的发展,开始出现一些论证君主的权力应扩展及于海洋的主张)之中,尽管也有诸如“公元前 406 年( 一说是公元前508 年) 罗马与迦太基签订条约……”等条约实践,但相对于前者而言,后者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处于弱势。许多学者主张,国际海洋法的发展源于前者。
一、习惯法规则是国际海洋法领域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法源
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案”中认为,“习惯国际法的要素主要应在国家的实践行为和法律确信中寻找,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①从而确立了判断习惯国际法规则是否存在的两个经典标准,即国家实践( usus) 和法律确信( opinio juris sive necessitatis) .
关于国家实践,“无论是国家的实际行动还是其言辞行为都能构成有助于创制习惯国际法的实践”.只要其内部之间不存在冲突,“一国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的实践均可能有助于习惯国际法的形成”.
国际法院认为,“事实上并没有仅仅因为有人认为习惯法具有不同的要素而明确地说同一个行为不能同时表现两个要素。实际上,通常很难、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将这两种要素分解开来”②,因为常常会出现某个行为既反映了国家实践,又反映了法律确信。
例如,国家立法一方面是国家的立法实践行为,另一方面却又反映出了该国在该立法领域内的法律确信。因此,如果要说国际海洋法源于古代各国的立法、法学家的学说以及各国主张的话,那么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国际海洋法渊源中的习惯法规则源于古代各国的立法、法学家的学说以及各国主张,并且,作为国际海洋法发展的先驱,习惯法规则历史更为悠久。
国际法学作为一门“势利”的学科,紧紧跟随于国家实践的脚步。“格老秀斯( Grotius) 和其他国际公法的创始人主张,国际法应为主权国家间协商一致的产物,并应以国家实践与国家同意为基础”.
因而,应当认为包含了国家实践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尽管在《国际法院规约》第 38 条第 1 款的规定中并未处于优先地位,但其在国际法的发展进程中仍处于重要地位。居于国际法发展重要地位的习惯法规则在国际海洋法中也处于重要地位。因为,在现代国际法中,涉及到习惯国际法规则的案例大多出自国际海洋法领域,在研究习惯国际法规则时,许多国际海洋法领域的案例也不得不提,如常设国际法院“荷花号案”及国际法院“北海大陆架案”、“渔业管辖权案”等。尤其是在国际法院的“北海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更是得出了判断习惯法规则存在与否的经典标准。因此,可以说,习惯国际法规则在国际海洋法的所有渊源中,就其影响力而言,居于近乎“中流砥柱”的重要地位。
二、习惯法规则在国际海洋法领域特殊重要性的体现
( 一) 国际海洋法的发展依赖习惯法规则
认真分析习惯法规则存在的领域,便会发现它在商人法和海洋法两个领域尤为发达,而究其原因,是因为无论是商人法还是海洋法,其最初乃至现在发展的推动力都是人们的实践。而“实践”在习惯法中恰好处于“基础构成性”的重要地位,国际习惯法规则的两个判断标准( 即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足以说明问题---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国家实践,就没有现今的国际海洋法律制度。如现今国际海洋法律制度中的领海法律制度的发展就伴随着沿海国和海洋大国之间利益的相互角逐,并在其中不断发展成熟。“领海”这一概念于 1930 年由国际联盟框架下的国际法编纂会议提出,从而取代了之前作为领海制度雏形的“领水”概念。而人类“最早对沿海海域的政治关切,涉及的是统治者的特许权的分配,而这些特许权包括: 对浅海渔场及湖沼盐床的专属权利、港税的豁免、狭窄海域的无碍通过以及礁脉等海岸地形作为地产疆界的标志”.
然而,尽管最初各个主权国家意识到了沿海海域的权力和利益,但由于科技尚欠发达,海洋的巨大利益尚未被发掘,主权国家对于领海制度的国家实践仅限于沿海资源的极小一部分,而并没有经济利益的驱动力来对领海制度进行基于国家实践的进一步探索。而此时的领海法律制度的主张所透露出来的利益主要体现在领土主权和国防安全方面,先是一些沿海国为了主张其对于沿海海域的管辖权而认为其主权权力及于从海岸算起的 100 海里( 或是当时的船舶两天的航程) ,这些国家实践透过意大利法学家巴托鲁斯、荷兰法学家真提利斯等国际海洋法先贤们的学说主张体现出来。而一些国家则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主张所谓“视野说”,即“以目力所及的地平线作为领海的界限”,其认为一般的领海宽度为 14 海里,当时的西班牙、丹麦、英格兰和苏格兰采取此主张。
接着便是 1610 年由荷兰和英国之间的渔业争端中所确立的所谓“射程说”,即当时一国的武器威力所能达到的地方,便是该国的领土主权权力所及的地方,其目的是为了增加沿海国对于沿海海域的控制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该说由荷兰法学家宾客舒克提出,并为荷兰、法国等国家所采纳。尽管以上各个主张之间并不一致,但其各自在一定的时间、区域内被相关国家默认一致地遵守,至少是在一定时间或区域内形成习惯法规则,使国际海洋法律制度有了不小的发展。工业革命之后,科技的发展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沿海国对于沿岸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从而促进了沿海国以及海洋强国相继作出国家实践表明自己对于领海法律制度的主张。到了 18 世纪,一些海洋强国为了最大化地获取海洋利益而主张缩小领海宽度,最早由瑞典于 1756年提出,并被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海洋强国坚定地执行,而其他各国则为了各自不同的利益主张不同的领海宽度,诸如 4 海里主张( 挪威、冰岛等国) 、6 海里主张( 葡萄牙等) 等。至此,各国基于各自不同利益的驱动进行了各种不同的关于领海的国家实践,国际海洋法中的领海法律制度也由此有了蓬勃的发展,但由于各国之间利益的不一致,进而国家实践亦不一致,因此领海法律制度并未统一。之后的1930 年国际联盟框架下的国际法编纂会议、1958 年和 1960 年联合国框架下的第一次海洋法会议和第二次海洋法会议也由于各国之间主张的不一致,使得领海法律制度的内容尽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丰富,但总的来说进展不大。到了 1973 年至 1982 年的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由于殖民地国家的纷纷独立,联合国内部发展中国家成员国的剧增,对“陷入少数”的发达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尽管各国仍有不同的领海宽度的主张( 例如,美国为保持其在公海上的利益而主张 3 海里、前苏联主张 12 海里、英国主张不大于 12 海里内由沿海国自己决定,以厄瓜多尔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为维护自己的沿海利益而主张 200 海里) ,但在各个阵营之间相互妥协之后,最终达成了不大于 12 海里的、这个具有一定伸缩性的领海宽度的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这个海洋大国并未加入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使得这个被寄予厚望的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的成果的作用大打折扣,然而幸好美国之后发表声明认为该公约除第 11 部分以外已经形成了习惯法规则,它也将遵守该公约第 11 部分以外的内容,从而使领海法律制度的发展在不幸中的万幸中得到了质的飞越。另一依赖于习惯法规则而发展的例子是专属经济区法律制度。专属经济区的完整概念于1972 年 8 月由非洲国家肯尼亚正式提出,而其雏形则源于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拉丁美洲国家所发表的主张 200 海里海洋权的声明。19 世纪开始,由于科技的迅速发展使得人类对于沿海广阔海域的渔业资源的开采成为可能,各主权国家开始相继作出以沿海海域的渔业资源为内容的国家实践。1945 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大陆架宣言》和《渔业资源宣言》,主张对其大陆架的海床和底土内的自然资源以及其沿海海域的渔业资源拥有管辖权。在美国国家实践的驱动下,智利于 1947 年首先提出 200 海里海洋权的主张( 即主张对于海岸起至 200 海里的海域享有专属的主权和管辖权) ,同年 8 月,秘鲁亦提出同样主张,之后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相继通过单边立法或联合声明( 如《圣地亚哥宣言》) 的形式提出200 海里海洋权的主张显然如此宽泛的沿海海域权利主张势必会遭到美国等海洋强国的强烈反对,在进行了一系列相互斗争与妥协之后,1971 年智利又提出承袭海的主张( 即主张对 200 海里内水域、海床和底土的自然资源享有主权) ,而之后拉丁美洲各国之间的 1972 年《圣多明各宣言》则正式声明了承袭海的五项内容。与此同时,1972 年 6 月,17 个非洲国家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举行国际海洋法区域讨论大会,并提出了在沿海海域设立“经济区”的建议,而之后 1972 年 8 月肯尼亚则正式向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提出“专属经济区”的概念及具体内容的草案,并在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作为一项新的国际海洋法律制度规定下来。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专属经济区的发展正是建立在各个国家的各种国家实践的基础之上的,而尽管专属经济区及其相关法律制度规定在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但在其生效之前,公约中关于专属经济区的内容已经成为了习惯法规则。“1984 年国际法院的一个分庭指出,关于专属经济区的某些条款‘可……在当前被视作与一般国际法相符',此后在1985 年,国际法院以更为肯定的语言称: ’在法院看来……各国实践表明……专属经济区制度已经成为习惯法的一部分这是无可置疑的‘”,[3]而“对于以国际公约中的一个条款---该条款本身并非法律的渊源,因为该公约尚未生效---作为一项国际习惯法规则产生的起点这一工程,专属经济区概念在国际法中的创设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 二) 习惯法规则在国际海洋法领域较条约法规则具有优势
有人提出: 国际海洋法渊源中的习惯法规则之所以研究得不多,是因为已经有了 1982 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其他众多的相关条约,条约法如此发达,便几乎不再需要习惯法。但笔者认为,这不仅是错误地理解了条约法和习惯法的关系,而且也是错误地理解了条约的本质。一方面,条约的确在许多时候会反映习惯法,进而被称之为是对习惯法进行了编纂,甚至有些缔结条约的活动成为构成习惯法规则的国家实践,从而促进习惯法的产生,但并不是所有的条约都会反映乃至编纂习惯法规则,甚至对于同一主题,两个乃至多个条约的规定并不相同甚至相反。也并不是所有缔结条约的活动都会促进习惯国际法规则的产生,这不仅仅取决于缔约国的数量,更取决于缔约国的质量( 例如,有重大利益的国家是否加入了某项条约) .因此,我们应当认为: “条约的广泛批准仅仅是一种现象,还必须根据实践中的其他因素( 尤其是那些未加入该条约之国家的实践) 来加以判断”.
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某些条约具有重要作用,而以偏概全地认为所有的条约都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许多条约有时并未生效,有时即便生效,其所产生的作用也没有达到缔约之初的想象。亦因此,应当认为: 条约法和习惯法虽然偶有重合,但该重合并不具有必然性,它们各自以其不同的调整方式、效力范围发挥着调整国际社会的作用,并常常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国际海洋法的发展依赖于习惯法规则,而在国际海洋法领域习惯法规则较条约法规则更具优势。对于我国南海问题的解决,习惯法规则亦将发挥独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