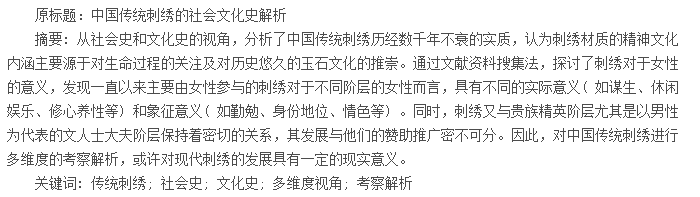
近些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热的带动下,传统手工艺的研究又成为了热门。作为传统手工艺中的重要门类———刺绣也不例外。检索相关研究信息,文章、专著等研究数量的确不少,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其中也存在着诸多不足。
首先,过度强调地域观念和地方特色。为强调自身刺绣的悠久历史而急于追根溯源,但是因为缺乏客观、冷静的态度使得这种溯源显得颇为牵强。
正如徐坚在一篇研究湘绣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1]244:由于以湖南民间刺绣为湘绣的前身过度追溯湘绣的起源,导致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长沙本地出土的战国到西汉刺绣的误读。它们能否与“民间刺绣”有联系尚存疑问,也无法与19世纪晚期崛起的湘绣联系在一起,反倒是和湖北江陵、马山出土的战国刺绣有着更紧密的关联。从空间上讲,不同区域的刺绣在题材内容、风格样式、材质技法上确有差异之处;从时间上讲,不同历史时期在对刺绣的认识与解读也会有所不同,但是这种差异与不同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总的说来还是“大同而小异”的。其次,从研究的视角来看,研究者大都是孤立地把刺绣看作一门手艺来研究。从事刺绣行业的人员多从技法的总结和创作的体会入手,总体上缺少深度。而学术界的研究又多从工艺美术史的角度着力,从而失去了研究的广度。在研究中一直以来都缺乏对刺绣与人的关系及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讨论。
鉴于此,本文尝试打破刺绣研究的地域界限,主要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角切入,利用出土文物、文献记载和图像资料,从刺绣材质的精神文化内涵、与女性的关系、与社会精英的关系特别是文人士大夫的关系,以及刺绣对于不同阶层不同人群所具有的不同意义等几个方面入手,来探讨历经数千年不衰的刺绣发展的“大同”。
1、刺绣材质的精神文化内涵
刺绣材质的精神文化内涵中首先包涵了对生命过程的关注。虽然目前尚无考古证据表明最早的刺绣材质是丝线,考古发掘也确实显示有其他材质的刺绣,例如羊毛、头发等。但是丝线材质至始至终占据着刺绣制品的主流,几乎也成了后世刺绣的代名词。与其他的纤维如植物纤维麻和后来的棉相比,丝的特别之处在于丝是由有生命的动物产生的纤维。与同样是取自于动物的纤维如羊毛相比较,蚕丝的取得就意味着蚕的死亡。而羊毛的取得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它是可以再生的。当然,现在已无法确知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社会先民对蚕和丝是如何认识的,但是从不同地区的考古发掘中都发现了许多与蚕相关的纹样和器物,或许能说明一定的问题。比如: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有陶蚕形饰[2]7,这些发现至少可以说明史前先民对蚕有了相当的关注。赵丰[3]认为:史前先民对于蚕丝的追求起先并不是源于实际生活的需求,而是把吐丝的蚕当神灵来崇拜的。因为他们观察到了蚕一生的四种状态,并把它与人的生死与死后灵魂的去向相联系,而且把这种联想引入到丧葬和巫术。他指出,瓮棺葬和用丝绸包裹孩童尸体及用丝绸做尸衣都是与蚕茧有关联。这似乎也印证了古代人的联想是按相似性原则进行的[4]17。虽然对于无文字记载的史前先民的思想观念大都只能属于推测,但是他的观点确实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而对有文字记载的殷周思想观念的研究,似乎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正如葛兆光所言:由天地四方的神秘感觉和思想出发的运思与想象,是中国古代思想的原初起点,换句话说,是古代中国人推理和联想中不证自明的基础和依据。它通过一系列的隐喻,在思维中由此推彼……人类应该按照这种宇宙、社会、人类的一体同构来理解、分析、判断及处理现象世界,因为现象世界中,拥有同一结构、同一特性的不同事物是有神秘感应关系的[4]19,53。或许正是这种感应促使古代先民把丝作为刺绣的首选材质。
但是,对于生命来源的好奇、对于死后世界的敬畏并不是中国思想的特色而是世界普遍思想的共性[4]16。也就是说,对于生命的关注还不足以完全说明刺绣材质的精神内涵和长盛不衰的内在动因。笔者认为对玉石的崇拜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中国人对玉石的崇拜和喜爱无需多说,史前文化中无论是北方的红山文化还是东南的良渚文化都发现了大量的玉器。中国人把玉看作“神物”,喜爱其温润、含蓄的感觉。董波通过不同民族对不同材质的选择和加工方法的对比发现,西域各民族选择金属与玻璃是因为他们看重光,而中国人选择玉石是因为更看重光在玉石所体现的含蓄和暧昧[5]。可能就是这种温润、含蓄正是中国人的内在精神需要。
这种需要还深刻影响了其他工艺门类。瓷器和漆器的兴盛都是源于对玉的模仿,董波甚至认为青铜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仿玉[5]。其实,使用丝作为刺绣的主流材质也是源于对玉石的崇拜,因为丝制品所散发的光泽与玉石有相似之处。张晓霞等[6]总结丝的基本性质时就谈到:蚕丝之白如邢窑釉色,类银类雪、温润文静,毫不炫耀闪烁;蚕丝之光,古人曰通灵辟邪,赋予其神灵的意义。此外,从古人与丝有关的文学作品中也能看出丝与玉的密切关系。汉代的王逸在《机赋》
中写到:“蚕人告讫,舍罢献丝;或白或黄,蜜腊凝脂[7]674。”他将丝的质感形容为脂,与之相同的是古人在文学作品中也经常会把美玉形容为脂。
2、刺绣对于女性的意义
2.1刺绣的实际意义
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说刺绣具有许多实际的意义。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性它是谋生的技能,是贴补家用、寡居后养育后代的谋生手段,也是农闲时的休闲娱乐。明代宋濂的《元史》卷103《刑法志二·户婚》规定:“诸匠户子女,使男习工事,女习黹绣,其辄敢拘刷者,禁之。”从中可以看出刺绣对于这些匠户的女儿来说就是她们无法回避的工作。清代冯桂芬的《同治苏州府志》中记载:寡居的杨氏昼夜刺绣积钱六千银十两,对于她来说刺绣可能意味着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清代玉魫生的《海陬冶游余录》中记有:秦淮人杨绣芸贫家女,母女二人工于刺绣,赖十指以度日;出自良家的金秀卿家贫乞灵于十指,刺绣精巧绝伦。
从一些图像中也可以看出刺绣对于一个普通家庭的实际意义。绘于晚清时期的《点石斋画报》中绘有金孝女一图。从文字说明可知孝女姓金名而英,母亲早亡,父亲有病且没有再娶,弟弟又年幼,金而英一人担起家庭重任。如图1所示窗前的那副绣架,可能就是金而英赖以维持一家生计的主要工具。在小说《金瓶梅》
中同样可以看到刺绣对于出生于社会底层女性来说的实际用途。潘金莲14岁就能描鸾绣凤,但是那并不是在家里向她从事裁缝行业的父亲学的,而是在她8岁卖于一大户人家为婢在那里学会的[8]13。显然,让她学习刺绣的实用目的是很明显的,就是借此提高她的身价将来可以卖个更好的价钱。对于在乡间劳作的普通农妇,刺绣也同样不太可能意味着高雅的品德、富足的生活,更多的时候可能还是农闲时的一种休闲活动,或者为丈夫孩子绣上一些吉祥图案以达到趋利避害的实际目的。
此外,还有一个同样处于社会底层的青楼女子群体。她们或许不需要通过刺绣来直接谋生,但是刺绣对于她们也是谋生的间接工具。这就像很多高级的妓女擅长绘画、诗词、音乐一样,刺绣也是她们吸引文人士子的手段之一。她们有的还在文人的记载中留下了名字。例如朱启钤的《女红传征略》中就有对于妓女董小宛和薛素素擅绣的记载[9]2390-2391。
刺绣对于信教的女性来说也同样具有特殊的意义。一针一线的绣就如同不断重复的诵经抄经,代表着内心的虔诚和日复一日的修炼,也是一种积福[10]。正如曼索思指出的那样:有些女性追求一种佛家或道家的需要全神贯注和打坐静修的精神生活,这种追求就包括刺绣佛经或观音菩萨像,甚至一些虔诚的信徒还能用头发作为绣线[11]83。柯律格在其专著中曾指出:制作的难度及制作器物需要耗费的劳动量可能决定了它的虔诚度[12]83。从这个角度上讲刺绣也是符合这个标准的。这种情况还可以从大量的诗词笔记中找到。例如:清代孙学勤的《薄命曲》中就有“妆奁已典囊无物,斗室长斋惟绣佛”的词句;清代西溪山人的《吴门画舫录》中记有:陈佛奴误落风尘怨恨三生,长斋绣佛,故更名佛奴;清代玉魫生的《花国剧谈》中记有:小莲,名静仙,蒲团默坐,绣佛长斋。月珍,绣佛长斋,每晨静诵金经。绣蓉,绣佛长斋,焚香顶祝。除了绣佛像还有绣经书的。唐代苏鹗的《杜阳杂编》记载有南海的卢眉娘可在一尺绢上绣佛经法华经七卷。值得注意的是,道教的文献(宋代陈葆光的《三洞群仙录》卷十九)里也借用了卢眉娘这个人,只是把绣佛教的法华经七卷改成了绣道教的灵宝经八卷。
宋元以来受理学的影响,妇女的生活被严格限制在家庭以内,特别明清两代大力提倡为夫守节,这又使刺绣延伸出了新的意义。卢苇菁认为刺绣有助于守节女性的精神健康。她举了纪昀记录的一则轶闻:彭元瑞看过一件16岁就守寡的黄夫人的刺绣作品,绣的内容恰好就是《女诫》的作者班昭的《东征赋》,他将其带回家给他为夫守节的女儿看,让女儿也刺绣。女儿也遵从了父亲的安排绣出来了精美的作品[13]254-255。类似的例子在很多地方志中也有不少记载,编纂者往往都是把这些女性都放在列女卷中。
例如《同治苏州府志》中就有沈氏寡居每日刺绣或临夫的画册;文氏以发代线绣佛兼绣山水的记载。巧合的是徐坚在其文章中所举的早期湘绣绣工胡莲仙、李仪微也都是寡居后从事刺绣行业的[1]264-265。看来妇女由寡居而从事刺绣这或许不完全是巧合。卢苇菁在其研究中就提到了清代妇女为了控制性欲在夜晚往地下抛撒铜钱或者绣花针,然后在黑暗中一一拾起,以此来耗过漫长的夜晚[13]206-207。清代顾震涛所撰《吴门表隐》中就记载有:许氏三十岁守寡虔诚地绣金刚舍利宝塔石佛像等,以此守节三十一年。
由此可以看出,寡居妇女通过刺绣来控制性欲从而度过漫漫长夜这是完全可能的。
2.2刺绣的象征意义
2.2.1勤勉的意义
在中国“男耕女织”的观念古已有之,甚至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14]281。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桑蚕业基本都是由女性来从事的,而与蚕桑业相关联的包括纺织、印染、缝纫、刺绣在内的女红更是与女性的生活密切相关。这种分工又逐渐演变为女性道德品行的象征。而且它延续了数千年之久,时至今日也没有完全消失。曼索思在一项关于18世纪及前后中国妇女的研究中也指出:对于男人来说远避体力劳动是地位上升的第一标志,而对于妇女来说正相反,从事生产劳动尤其是纺织还有对于上层妇女来说的刺绣都是妇德的体现。她甚至指出懒惰的女人给人以放荡印象,这有损于她在婚姻市场和家庭中的地位[11]15。
2.2.2身份地位的象征
胡平按技术类型将女红分为:染、纺织、缝纫、绣和编结[15]126。印染、纺织与刺绣相比除了需要一定的场地还需要比较专门的技术,而且劳动强度也比较大;刺绣与缝纫、编结相比除实用价值外,好的刺绣还具有艺术价值。从事刺绣的人除了要有一定的技术还需要一定的文化艺术修养。而且从一份1930年代关于农户与非农户的调查中即可看出,从事刺绣行业还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16]300-301。同时,从事刺绣还需要耐心、平和、细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刺绣又与绘画最为接近(刺绣与绘画的关系在下文中还要进一步谈到),而绘画又是身份教养的标志之一。由此,笔者可以认为,刺绣在女红中的地位最高,所以它自然成为上层女性身份、地位、教养的象征。曼索思将缠足称为是蕴涵着富有、闲适、美丽、较弱、肉感、依赖性和身份等各种意味的人生记号,成了强有力的性别标志;刺绣具有一种性别的意义,正在刺绣的女性看上去很富性感,她的针线遂成为性别魅力的象征[11]72-199。其实,刺绣和缠足一样似乎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清代的徐震在《美人谱》中就把刺绣与弹琴、吟诗、围棋、写画等一同列为美人必备的技能。这样的形象也常常成为绘画的题材。唐代周昉的《挥扇仕女图》(图2),明代仇英的《汉宫春晓图》(图3),康熙时期的宫廷画家焦秉贞的《仕女图册》(图4)中都有妇女刺绣的形象。画中的女性都身处优雅的环境,各个衣着华丽,神态安祥、平静,气质优雅。从朱启钤的《女红传征略》所辑录的擅绣的女性中也可以发现,她们大都家境殷实地位较高。
例如:吴主赵夫人、管道升、韩希孟等。对于她们这些人来说刺绣大都脱离了实际的用途而更具有象征的意义。刺绣所具有的这种象征意义使得富裕家庭纷纷让自家的女儿学习刺绣。明代张景在《疑狱集》中就记载宋咸淳年间,浙江有户人家专门请尼姑来教女儿刺绣。日本的中川忠英编著的记录清乾隆年间风俗的《清俗纪闻》中“女子工作”一条记载:“大户人家中,妻女不缝制衣裳,只依爱好剪切纸、绣花、挑花等。”而“女子教育”条记载:“十岁以后以绣花、针工、纺织之道。大户因衣服多交给缝匠制作,故只教以缝纫荷包、烟包等缝纫之事。但依据情形,有时也教以衣服之做法。如母亲不善于绣花之道,则请邻近妇女或雇佣绣娘等类之人在家传授[17]153-340。”
《清俗纪闻》仅是一本反映社会中下层民俗的调查记录,不过它从侧面也反映出对于刺绣的地位和所具有的象征意义的认识向社会底层的传导。刺绣及绣品不仅成为身份的象征也成为代表闺秀优雅生活方式的一种符号。清代卫泳在《悦容编》中就将绣具和笔砚、琴箫、禅椅、妆盒等一同列在雅供的条目下。
此外还可以从许多女性的名字和她们给自己的集子起的名字中看出刺绣在女性心目中的位置。清代的许夔在《香咳集选存》中就有不少这样的记载,例如:浦映渌著有《绣香小草》;卞梦珏著有《绣阁遗草》;张瑶瑛著有《绣墨斋偶吟》;叶宏湘著有《绣余草》。张绣佛,字抱珠;孙廷桢,字绣墨;陈淑旂,字绣庄。
2.2.3情色的意味
据高罗佩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一文中的研究,明中期的春宫画中就有一女子正在刺绣,旁边坐着她的情人的图像。并指出“绣”字具有双重含义,含有女子性交的意思,所以这类画也同样具有挑逗性。他还指出,在清代的色情诗文中,“爱绣”一类的说法或指淫妇。而清代的一首词(《闺中十二曲》)也确实印证了高罗佩的说法:“闺阁女郎年幼,十五心头春斗。怕的见丝鞭,躲向窗前佯绣。休骤,休骤,侬要任他消受。”除了刺绣,绣品也同样具有情色的意味。《闺律》中就有规定:闺人给予物件,荷囊绣带是不许私自送人的。后面还做了说明,刺就百花之带,中有同心之缕,暗藏比翼之思。只宜密系郎腰,岂可轻抛人手。而曼索思也同样指出:出嫁年龄的女子一般都要用丝织品裹脚并亲手在弓鞋上绣花[11]199。
3、刺绣与社会精英阶层的关系
3.1刺绣与贵族的关系
由于对丝的喜爱,丝及与丝相关的刺绣历来被社会精英阶层作为等级地位的象征。丝的地位也奠定了刺绣的地位,从祭祀、丧葬到皇室贵族文武百官的日常服饰、鞋帽等也常见刺绣的身影。例如:1982年江陵马山砖厂一号战国楚墓出土了多达21件绣品。早期的文学作品《诗经》中也有诸如:素衣朱绣、黻衣绣裳、衮衣绣裳的记载。汉代的贾谊在《新书》中有“匈奴之来者,家长已上,固必衣绣;家少者必衣锦”的记载,这说明绣的衣服要比锦更尊贵。对比丝与棉的发明者也可以看出来。
传说中丝绸发明者嫘祖是一位皇后,而纺棉术的发明者黄道婆却是出身于低贱的平民家庭。此外,刺绣还被广泛使用于宗教场所成为宗教用品,考古发掘就有不少刺绣的佛像出土。由此可以看出刺绣似乎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与尊贵划上了等号,非一般平民可以使用的,不仅如此,皇族与政府官员还热衷于对刺绣的推广。清代沈寿的《雪宦绣谱》中有记载:光绪三十年十月,慈禧七十寿辰,沈寿绣寿屏作为进贡礼品。慈禧见后大加赞赏并亲笔写下“福、寿”二字赐予沈寿,沈云芝从此才更名为沈寿。
清廷同时任命沈寿的丈夫余觉为农工商部绣工科总理,同年夫妻俩就赴日考察美术学校教学情况。
无论慈禧赐字出于何种原因,她的赐字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为刺绣的推广做了一个大大的广告,也为沈寿日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刺绣对于摄影术出现后的应对也能说明其与社会精英的关系。摄影术诞生的初期,由于其技术的复杂和成本的高昂也非一般民众所能承受得起的,能拍得起照片除了青楼女子就是富裕家庭出生。正如曾佩琳指出的那样[19]402-403:由外国人所引介的肖像照至少在中国的上层阶级当中造成风潮。在上海其主要顾客是文人及其家人、政治人物、国家的杰出人士和城市的寻欢者。刺绣对此也做出了反应,由先前对文人士大夫绘画的模仿又拓展出了对摄影的模仿。沈寿发明的仿真绣写实人物肖像就是以照片为蓝本进行创作的。而且仿真的写实人物肖像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以社会名人精英为主要的对象,这种密切的关系至今还保持着。除了这些人是主要的消费群体外,刺绣可能也是通过这种手段保持与贵族精英阶层的紧密联系,强化其高贵的品质。
3.2刺绣与文人士大夫的关系
3.2.1文人士大夫对刺绣的态度
除受到皇室贵族的青睐,刺绣还与精英阶层中文人士大夫的关系密切。例如:明代顾绣的扬名应该与董其昌、陈子龙等画坛文坛大家的青睐不无关系。董其昌、陈子龙甚至亲自为韩希孟的顾绣题跋(图5),而韩希孟的丈夫顾寿潜自身也是精于书画且还是董其昌的学生[20]50-51;再如:沈秀的代表人物沈寿其丈夫余觉本身就是出身书香世家的浙江举人,她的许多绣稿都是余觉悉心挑选的。此外,更重要的是沈秀还得到了时任北洋政府实业部长晚清状元张謇的提携,请她担任女红传习所的教员,沈寿的《雪宦绣谱》也是张謇帮助整理出版的。同样,近代湘绣的发展也离不开赵尔巽和端方的大力支持。
许多文人士大夫在各种著作笔记中也发表了对刺绣的看法,表达了对刺绣的关注。苏绣“精细雅洁”特点也是明代的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王鏊在其主编的《姑苏志》中提出的;董其昌的题跋称赞顾绣“有过黄筌父子之写生”;陈子龙的题跋“生气回动,五色烂发”;明代的高濂在《遵生八笺》中就比较了宋人绣画与元人之绣的不同;而李渔在《闲情偶寄》中甚至抱怨他那个时期的贵妇们正放弃刺绣转而搞学问,连绣鞋都要雇人来绣。有的文人士大夫更是直接参与苏绣创作的。明代万历丙辰进士出身的布政使来到苏州后特地慕名去学习苏绣,而且比一般妇女还绣得好[21]59。
当然,对于刺绣的态度也不是所有的文人士大夫都是喜爱和赞美的。明代的张瀚在《松窗梦语》中就认为“刺绣组锦,伤蚕事者也”,他指出,农桑是本业而工作淫巧是末业。清代的张履祥也在《农书卷》中发表了“刺绣淫巧在所当戒”的相似看法,他鼓励织布、养蚕,反对从事刺绣。他们可能都觉得刺绣费事费工,占用了大量的农时,从国家的层面上讲不利于农业的发展。陈宏谋和吕坤则从另一个角度认为,刺绣对于妇女来说只是次要的学习,是不充分的道德和实践教育,应该首先教她们读书。无论他们从哪个角度对刺绣发表看法,都说明文人士大夫阶层对刺绣的关注,他们甚至把它上升到国家经济建设和妇女教育的层面。这似乎也从侧面反映出刺绣的社会地位和影响。
3.2.2刺绣受到文人士大夫关注的原因
如前文所言基于对玉石的崇拜和喜爱,君子以玉比德,而绣品所呈现的光泽与玉石所呈现的光泽相似。这方面前文已有论述,在这里不再重复。
此外刺绣与绘画具有相似性。这种观念出现较早。《说文解字》中绘与绣都从“糸”部,出土文物也有体现。如:1974年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发现的绣品,刺绣绣轮廓,内部填色。这说明在早期绘与绣是一回事,都是用于装饰。例如汉代的刺绣与漆绘从形式与题材内容看没有太大的区别,基本上只能称为图案或纹样,是实用的装饰艺术,只是材质不同。隋唐科举考试以来至宋代形成文人士大夫阶层,使绘画地位大为提高,这也带动了刺绣的地位提高。大致也是从那时起,刺绣的风格题材与绘画越来越接近,开始了刺绣对文人士大夫绘画的模仿。
在苏绣中民间总结的“平、齐、细、密、和、顺、匀、光”的八字特点中至少“平、匀、顺”都是与绘画的模仿有关,这种传统甚至一直延续至今。此外,在纺织工艺中,刺绣与纺纱织布不同,它同绘画一样需要一个基底,而且是唯一直接用针而不借助于其他机械的手艺,与纺相比更具创造力、灵活性和艺术性。纺织品过于刻板匠气,这也与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要求不符。
从这一点上说,刺绣也是和绘画在气质上最为接近的,只是以针来代笔而已。丁佩在《绣谱》中就说:以针为笔,以缣素为纸,以丝绒为朱墨铅黄,刺绣就是闺阁中的翰墨。而且从刺绣的过程来看,要先有粉本,先绘后绣。对刺绣艺术特点的总结也可看出刺绣与绘画的亲近关系。文人士大夫无非把刺绣作为绘画的延伸,高濂在《遵生八笺》中对宋绣和元绣的比较是放在“赏鉴收藏画幅”条目下的,从某种程度上说,高濂把画和绣看成是一回事。
从以男性为主的文人士大夫的角度看,女性从事刺绣可能更符合他们心目中理想女性形象的设定:高贵、优雅甚至带点性感,女性刺绣的形象成为一种符号被组织进画面被消费被观看。这一点从当时的绘画中也可以看出来。文人士大夫喜爱描绘和观看女性刺绣的形象。例如:仇英的《汉宫春晓图》《千秋绝艳图》《百美图》《女红图》,佚名的《竹林仕女图》,清陈枚的《月曼清游图册之十月文窗刺绣》(图6),还有前文提到的焦秉贞的《仕女图册》都有女性刺绣的形象。这些作品虽然无法一一去考证它最终是为谁而画,最终目的是单纯的欣赏、装饰还是起教化作用亦或是几者兼而有之,但是这其中对女性刺绣形象的关注是可以确知的。仇英的《汉宫春晓图》就是为项元汴而作,而他的《女红图》据称也是为项元汴而作[24]258。此外,西方人眼中妇女绣花也是中国女性的典型的形象,19世纪广州外销的通草纸水彩画(图7)中就表现了这一形象。
4、结语
通过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视角对传统刺绣的考察,可以发现另外一条不同于以往工艺美术视角下的发展脉络。刺绣历经数千年不衰折射出的是中国人对生命的关注和玉石文化的影子。而社会阶层和角色的不同又赋予刺绣不同的内涵和象征意义。对于上层妇女来说它是地位、教养甚至是性感的标志,对于底层妇女则更为实际,它是农忙时的休闲或者谋生和贴补家用。同时,对于所有妇女来说,刺绣是妇德的象征符号;对于信教的妇女来说具有宗教积福的意味。在以男性为主的精英阶层,刺绣始终与绘画关系密切并得到他们的推崇。皇室贵族也一直是刺绣的直接消费者和发展的推动者。对古代刺绣的多维度的考察同时或许对现代刺绣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徐坚.早期湘绣的物质文化观察:民艺、工艺和艺术[G]//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艺术史研究·第12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
[2]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平谷县文物管理所,上宅考古队.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1989(8):7-8.
[3]赵丰.丝绸起源的文化契机[J].东南文化,1996(1):67-74.
装饰设计的表现力为我们开拓了一个新的视感领域, 丰富了我们的情感与想象力, 改善了我们的观念意识, 审视着世间万物的无限变化, 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并描绘出美的形式, 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0引言粉彩花鸟瓷画自康熙晚期诞生以来,其艺术风格的发展演变除了依存于其本身的艺术规律以外,更多地表现为在社会自然环境影响下而形成的时代风貌,是自然、社会人文以及工艺技术变迁等各种因素形成的整体环境融合的产物,反映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1图形的符号化是导识系统的构成基础图形的符号化是导识系统的构成基础,用图形符号来记录生活的历史早于文字,图形和符号被用来表达特殊含义,后来出现的象形文字,也是由具体的图形和象形符号所构成,图形担当了信息传达的主要载体。其中有许多图形传递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