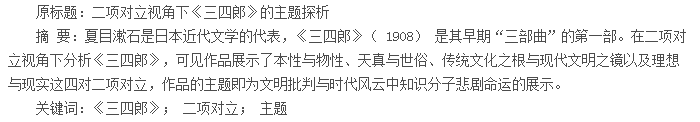
《三四郎》是日本近代大作家夏目漱石的一部经典作品。学术界对《三四郎》的研究一般是将《三四郎》视为“教养小说”,表现了“文明开化”问题。随着20世纪西方文论的层出不穷,为我们阐释经典文学作品提供了新的方法,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有的研究者就从女性主义和空间理论的角度重新解读《三四郎》,得出了比较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如陈静的硕士学位论文《性别(gender)视角的〈三四郎〉解读》,郑礼琼的《从空间符号解读〈三四郎〉的自我认同主题》。本文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切入,会对《三四郎》有新的理解。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上承俄国形式派和布拉格结构主义,以索绪尔语言学模式为理论支柱,流行于1985-1986年的法国,而二项对立是结构主义批评的重要概念。二项对立本是索绪尔语言学一种重要的分析方法,音位学关于“对立区分”原则,“在语言学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各项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1]
这对结构主义思维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着名的“二项对立”思维方式即由此而来,成为结构主义重要的思维方式。正如卡勒在总结索绪尔这一观点的重要性时说“其实,结构主义分析中最重要的关系又极其最简单:两项对立。语言学的模式也许还有其他的作用,然而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鼓励结构主义者采取二项式的思维,在研究的各种素材中,寻求功能性的对立形式。”[2]
能指与所指、共时与历时、语言与言语等语言学的研究方式都给结构主义在具体方法上以很大的启发借鉴。普罗普、格雷马斯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已就从这一思维方式出发进行了探索研究,以二项对立的思维方式来对文本进行结构分析和意义探寻。二项对立的解读能够进一步丰富文学意义的建构。因此,我们也将借助这种思维方式来分析《三四郎》的二项相对立并进行主题意义的探寻。
一本性与物性
爱情是人的天性,追求爱情是人的一种本能,异性相吸是自然规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将人类生活中的两性关系提升到至高的地位,特别重视力比多,即性欲。美满的爱情会给人们带来希望与快乐。但是人的欲望会受到现实、经济的制约与压迫,这就是爱情的社会性。在对爱情对象的选择中,会考虑到多种因素,亦即所谓的爱情选择的标准。“爱情的社会成分自然也存在于选择性的欲求对象的过程中。选择和中意的标准不单单是生物的,而且也是社会的、社会-心理的。”[3]44《三四郎》中的重要女性里见美弥子为了地位与金钱放弃了爱情,体现了本性与物性的二项对立。
美弥子放弃爱情。小说中说“大凡女子,总不愿嫁给一个连自己都瞧不上的男人。”[4]231美弥子最后既没有选择野野宫宗八也没有选择三四郎。其根本原因是美弥子的等级观念以及拜金主义。美弥子违背本性的行为,不仅给自己,也同样给三四郎、野野宫宗八带来不可愈合的伤害,导致惨痛的爱情悲剧。美弥子绝不是稚拙的,她非常的现实。
美弥子嫁的男子是一个绅士,出身高贵,生活富足。因为“在她内心深处还是摆脱不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无法跨越世俗伦理的鸿沟,最终因经济上无法独立也不知道如何独立,选择了抛弃三四郎,嫁给自己哥哥的朋友,和一个她根本不爱的人在一起。”[5]
“我知我罪,我罪常在我前。”[4]238是美弥子的忏悔。美弥子没有选择三四郎,是出于等级观念。
三四郎只是一介书生,经济上未能独立,出身平民阶层,自然不能步入上流社会。不管三四郎个人品质如何高尚,求学精神如何可贵,也敌不过自身的出身。在美弥子眼中,三四郎可以说是一无是处。美弥子没有选择野野宗八宫是因为她的拜金主义,尽管野野宗八宫是卓越的物理学家,但是他在经济上的清贫却是不争的事实。
美弥子是“新式女子”,她生于上流社会,接受过教育,英语会话很流利,生活在西式的房子里,享有一般女子所没有的自由,万事都可以为所欲为,不拘流俗。然而骨子里却带有旧式的特征,依然摆脱不了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所以她不会选择出身平民的三四郎。“日本人十分强调等级观念,”[6]167“毫无疑问,强调等级观念的部分原因,是日本的权利世袭和贵族统治具有很悠久的历史。社会划分为阶级、权力世袭以及贵族享有特权是日本进入现代社会以前整个历史时期的特征。”[6]168纵使文明开化,然封建时代的等级制依然大行其道,仍然被看做是可行的社会结构,并以此作为解决各种问题的出发点,他们的各项活动仍然以此为准则。“这说明当时的社会是一个肤浅、虚伪的社会,人们醉心于西方文明而出现了道德上的混乱,所谓现代女性只不过外表上学点西方文明的皮毛来装点自己的门面,而西方女性那种自立、自强的风格一点儿也没有吸纳。”[7]
她受到文明开化的影响,接受的不是西方文化民主、平等的先进观念,而是习得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糟粕---拜金主义。非但没有学到西方文化的优秀之处,却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糟粕,这就是文明开化中的弊病。
那么小说中的情爱悲剧就超越了三四郎的个人悲剧,从而具有了深刻的社会意义。“爱情的悲剧是情感冲突与社会冲突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个人的高尚追求与同反对这种追求的外部力量,某种重大的客观障碍之间深刻冲突的一种特殊形式。”[3]438三四郎的爱情无果而终,就是遇到了克服不了的障碍,遭到社会的否决,这样就进入到社会问题的深处,触及到最痛苦的悲剧,这种悲剧深深地被织入社会之网中,从而达到对明治维新后文明开化弊端的批判。
二天真与世俗
三四郎还没有正式进入社会,他将社会想象成玫瑰色的。不知人世间的坎坷与艰辛。“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个女人,她是现实世界的一道闪电。”[4]17火车上的女子让三四郎感到愕然,她和自己认识的阿光姑娘是如此的不同,让三四郎觉得无所适从,这也预示了后来在东京接触形形色色的人之后更加的惶惑。现实对单纯的三四郎来说是多么的复杂。这便是天真与世俗的二项对立。做学问是三四郎对事业的追求,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手段,然而,三四郎将学问想得过于简单。
而且,三四郎有许多不利于做学问的因素。
第一,他缺乏深厚的学术素养。三四郎没有学问,作为东京大学文科部的学生,并未博览群书,许多作为一个文科生本该涉猎的书籍他都不了解,更谈不上进一步的研究式的学习了。
第二,他的性格存在缺陷。从野野宫宗八身上我们可见一个做学问的人应该具备的品质:勤奋、耐心、内心纯粹,安于清贫、安于清苦、安于寂寞,这才是真正的励志学术。半年多来,物理学家野野宫宗八在地窖里进行光压试验,“欣然以地窖为根据地,孜孜不倦地埋头于研究工作。”[4]21若三四郎志在学问,那么他面临的环境极有可能与野野宫是一样的,即条件异常艰苦,生活清贫,不为人知,不被人理解,生活单调,但是三四郎却是一个自由派,喜欢悠闲自如。三四郎还有随波逐流的弱点,“细心一观察,与次郎等人也是如此,三四郎觉得这样也许就行了。”[4]55-56由此看出,他未必能做到野野宫宗八所做的,而况,志在学问之人,一般无心恋爱,但三四郎显然有着青年人的激情。
第三,做学术的种种艰辛。首先是学海无涯,“他从图书馆里的”羊皮纸、牛皮纸等两百年前的纸张上的“”高贵的灰尘“中看到了学问世界无边的深渊,他本能地拒绝了这个世界。”[8]
其次是学校治理之散漫、漫不经心,课程讲授之索然无味,纵然三四郎认真地上课,也很难提升三四郎的学术素养。明治政府“强调教育乃立国之本,强国之路。”[9]
事实上,我们从野野宫宗八做科研的条件上得以知道,政府对教育并没有这么重视。
第四,他自身的生存环境存在不足。三四郎来自闭塞的乡间,信息封闭,经济落后,见识少,没有东京那种大都市的丰富的资源与开阔的视野,可谓先天不足。这就是现实的无奈。而做学术的艰苦条件是因为明治政府并不像西方那样重视知识,重视学术。野野宫宗八在西方大名鼎鼎,在日本国内却无人问津。这说明明治维新并未学习西方的精髓,从而达到对明治维新后文明开化弊端的批判。
也就是说,三四郎从主观到客观都不利于从事研究工作,这就是他的天真之处了。
三传统文化之根与现代文明之镜
在小说中,与次郎与三四郎形成鲜明的对照,如果说与次郎是新时代的沐浴着现代文明的青年人的话,那么三四郎就是依然具有传统文化之基的大学生。文中对与次郎的批评与讽刺是显而易见的,对三四郎的同情与偏爱也是有目共睹的。三四郎与与次郎构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二项对立。
与次郎是一个在金钱上不受人信任的人。与次郎向人告贷为家常便饭,其中一次的借主居然是美弥子。美弥子生活尚未独立,他根本不考虑会给女孩带来许多麻烦。与次郎借钱不还还若无其事,信用关乎一个人的名誉,特别是在日本,“借款者如果无力还债,就会用自杀来洗刷污名。”[10]
然而与次郎显然满不在乎,近乎厚颜无耻。
与次郎不是一个真正的好朋友。日本人其实是不随便结交朋友的,但是一旦成为对方的朋友,便是真正的朋友,同甘共苦。还不熟悉时,与次郎拉着三四郎到本乡街淀见轩吃咖喱饭,一起乘电车,听说书。看上去与次郎带三四郎是去体验浮华世界,但是实际上,他对三四郎做的这些事他也对其他许多人都做过。特别是幕后活动结果使广田先生的人格受辱,而承担后果的却是三四郎。
三四郎成为与次郎的替罪羊。这不啻是对他们友谊的讽刺。与次郎是一个不懂报恩之人。作为广田老师的食客,本应该报恩于先生,但是却使老师的名声因为自己的缘故受损。日本的传统美德是报恩于万一,然而与次郎非但不报恩,反而使先生名誉受辱,在日本,个人视名誉为生命。与次郎不能说是一个全然的坏人,他身上也有可爱之处,但这个人的确做了几件极为恶劣之事。与次郎想通过自己的运动让广田先生当上大学老师,似乎是有独自运筹天下大事的本领,但是实际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而三四郎却是一个厚道、单纯而老实的人。与次郎不管是在金钱上不守信用,对朋友不忠诚,对老师不懂回报恩情,都说明与次郎是受时代影响的青年,身上流淌着的是自私自利的血液,极为卑劣。同时,故乡熊本与东京又是一对鲜明的对比。如果说熊本是温情脉脉、人情融融的话,那么大都市东京则是漠然与冷漠。这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二项对立。故乡是淳朴的。在东京求学的三四郎会经常收到来自故乡母亲的家书,母亲对他的体贴与关怀无时不在,尤其是当他在东京感到失望之时,故乡母亲的信件就弥足珍贵,是他的安慰与心灵的栖息地。
然而与故乡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都市的冷漠。面对乞丐、面对迷路的孩子,都市的人们都是漠然的。都市还是危险的,稍微不慎,几乎连生命都不保,比如那个被列车轧死的年轻女子。乡间与都市不同的成长环境,接受西方文明的不同程度也是造就与次郎与三四郎性格的主要原因。“当晚,三四郎在思索与次郎的性格,他想,也许是久居东京才变得这样的。”[4]153东京,作为大都市,不仅有着东京味,而且沐浴着欧风,发生着巨大变化,但东京人的刁钻狡猾,也体现着现实世界的危险。三四郎在熊本长大,熊本意味着闭塞与落伍,同样意味着三四郎是在单纯的环境里长大的。
传统文化之根与现代文明之镜就是通过三四郎与与次郎这两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以及故乡的书信与东京的截然不同呈现出来,其中的反差一目了然。
四理想与现实
理想是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想象、向往与追求。然而现实却决定着理想的命运,理想与现实也就构成了一对二项对立。“世界如此动荡,自己看到了这种变动,然而却不能投身于这种动荡之中。”这很形象地说明了三四郎在理想与现实之中的徘徊不定。“总之,最好是把母亲从乡间接出来,娶个漂亮的妻子,一门心思搞学问。”[4]69这是三四郎的理想,很平凡,实际上也代表了三四郎对爱情婚姻、对事业的追求,是对个人幸福的一种追求。但是三四郎的理想注定无法实现,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平凡的理想,一一失败。首先是事业上的失望,接着是爱情的挫折,最后只能是“迷羊”,终至以失败告终。三四郎的理想注定惨遭失败是因为当时的时代,时代导致世风日下,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物质文明在日本迅速发展的同时,物化意识在人们的生活中到处弥漫,人的自由本质被取代。”[11]49众所周知,文明的进步往往伴随着人性的堕落和道德的沦丧,“人类每向文明迈进一步,都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背离了旧道德。”[11]42因此,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三四郎的悲剧不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三四郎的悲剧固然有其自身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时代的风云变化,事态的变迁。接受了西方文明熏陶的夏目漱石,既对文明开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又对在开化中带来的急功近利、丧失自我的现象表示深切地担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日本的明治维新必然是历史的进步,然而在当时的近代化进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夏目漱石作为一位入世的作家,他能深刻地看到这种现象中的弊端,“日本的文明开化,在引进文明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混入一些糟粕,一方面是全盘加以吸收;另一方面外国好的东西引进来后,由于一些人为的原因,往往在传播中走形变样;还有的人干脆就是打着外国文明的幌子,达到自己自私自利的目的。
而真正的文明,又因为它背离了原来的道德标准,将人异化为非人,成为金钱的奴隶、权势的仆人。这一切,都令有着东西方文化高度教养的夏目漱石忧心忡忡,对现代文明的批评,也成为其前期小说的主要内容。”[11]42从而达到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另外夏目漱石还揭示了知识分子步入现实世界的惶惑与迷惘。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让人面对美丽梦想破灭的深创剧痛。面对现实的残忍与不如意,个人莫可名状的伤感,这是人类普遍的悲剧。“不幸的童年时代使夏目漱石过早地品尝了世态炎凉,天生敏锐的感悟力和心灵的创伤使其自幼就体验到人生的无奈,他带着淡淡的忧伤,对”人“的思索,以其横溢的才华,细腻的笔调,写下了一首首凄凉的人生之歌,剖析了现实人生的虚无与绝望,揭示了悲凉人性中的自私与残酷。”[11]90-91对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关心、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对人性的关注“使夏目漱石将探讨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文明开化的本质结果、关注社会人类的未来、对人性的深刻揭示作为自己终身之奋斗目标,这些都直接和深刻地在他的文学活动中体现出来。”[11]41
夏目漱石的《三四郎》正是展现了本性与物性、天真与世俗、传统文化之根与现代文明之镜以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尖锐对立,揭示了它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通过对小说中的二项对立的具体分析,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了《三四郎》对明治维新实质效果中的诸多弊端的揭露与抨击,达到了文明批判的高度,同时也书写了知识分子即将进入现实社会时的迷惘与痛苦,对个人命运的悲苦与个人价值难以实现的无能为力,这是永恒的悲剧。总之,《三四郎》以其深刻的社会批判与对人生命运的描写而不朽。
参考文献:
[1]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28.
[2]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M].盛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37.
[3]基·瓦西列夫。情爱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4]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小说选:上[M].陈德文,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5]吴二林。探析明治文学作品中“新”女性的精神世界:以夏目漱石早期三部曲中女性形象为例[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2,21(10):10-13.
[6]埃德温·赖肖尔。日本人[M].孟胜德,刘文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茶花女》(1847)是法国小说家亚历山大·小仲马的代表作,小说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虽是一名妓女,但其形象却如其名字Marguerite一样盛开在世界经典名着的花园里,引得人们去研究、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