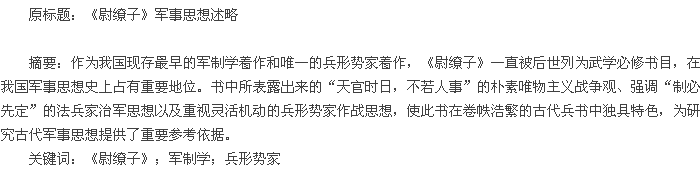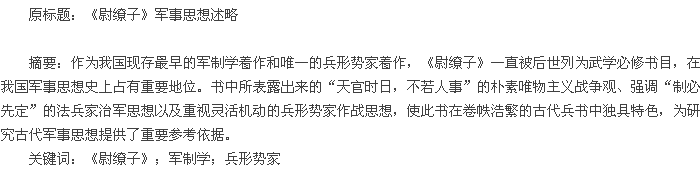
《尉缭子》乃战国中期尉缭所着兵书。北宋神宗时,此书与《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六韬》《三略》和《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一起被编为《武经七书》。清朱墉在《武经七书汇解》中说:“七子谈兵,人人 挟 有 识 见。而 引 古 谈 今,学 问 博 洽,首 推尉缭。”
现存《尉缭子》共五卷,二十四篇约九千余字,这在先秦古籍中已经算是篇幅很长的典籍了。全书论述范围极广,从大战略到小战术无所不包。现存的《尉缭子》二十四篇,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前十二篇从“天官第一”至“战权第十二”为第一部分,主要内容是战争观与战略战术;后十二篇从“重刑令第十三”至“兵令下第二十四”为第二部分,主要内容是军制和军令。
与《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全书由唐太宗李卫公一系列问答组成不同,《尉缭子》全篇仅有一例一问一答,即全书第一句“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全书似为尉缭对梁惠王一个问题的回答。所以,弄清梁惠王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想要什么,无疑对认识《尉缭子》一书的中心思想极为重要。
梁惠王本为魏惠王,乃三家分晋后魏国第三代国君。魏惠王所在之时,是魏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魏国通过李悝变法,在战国初期最先强大起来,领导三晋多次打败秦、齐,所以惠王曾不无自豪地对孟子说:“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
(《孟子·梁惠王上》)然而魏国到了惠王手中,先是在桂陵、马陵之战中两败于齐,两年之后又败于秦,不得已将国都由安邑迁到大梁。魏惠王曾经苦闷地对孟子倾诉:“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孟子·梁惠王上》)此时的魏惠王已经把魏国历经文侯、武侯建立起的霸业红利消耗殆尽,而魏国本身身处四战之地的弊端开始显露,魏惠王迫切需要能快速制胜的法宝重建国威,一句“吾闻《黄帝刑德》可以百胜,有之乎?”透露出惠王想要富国强军,重振魏国雄风的急切心理。而尉缭也以诚恳的态度对此进行了认真解答。
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换的时期,各诸侯国纷纷采取富国强兵的革新政策,以巩固和发展新兴地主阶级政权。诸侯国之间战争频繁,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迫切需要适应时代要求的军事理论作指导。尉缭明确反对当时流行的“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来定战争胜负的兵阴阳家的做法,提出了“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进步思想。他认识到了“武植文种”,政治才是军事背后本质的东西。他依托法家思想,主张重赏重罚,强调纪律的重要性,力主通过完善的制度建设来管理军队,确保军队的战斗力。他主张集中兵力,奇正结合,避实击虚。综合尉缭上述思想为核心而成的《尉缭子》一书,成为先秦一部颇具特色的兵书。
一、“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朴素唯物主义战争观
《尉缭子》一书中反天命、重“人事”、反不义之战、提倡农战的思想在战国时期阴阳思想盛行、战乱不断的时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一)强调战争中“人事”的重要性
我国古代用阴阳来解释宇宙间万物对立、消长的规律,战国时邹衍等把五行说与阴阳说合并,独树“阴阳家”一派,后来阴阳的概念也被引入兵学研究领域,发展出兵阴阳家。兵阴阳家的特点为“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强调通过观星象、占卜来判断战争胜负。《黄帝刑德》正是传说中的兵阴阳家的不传秘籍。魏惠王开口便问尉缭《黄帝刑德》,可见战国时兵阴阳学说之盛。
尉缭围绕“刑德可以百胜”说,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兵阴阳家的思想。他首先解释了黄帝所说的“刑德”,是指以武力征伐敌人,用仁德治理国家(“刑以伐之,德以守之”),并非兵阴阳家所谓的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然后又用四面攻城、武王伐纣背水列阵、公子心伐齐三个生动的案例说明“天官时日,不若人事”(《尉缭子·天官》,以下《尉缭子》引文只着篇名),战争中最为关键的仍是“人事而已”。尉缭明确提出“今世将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欲以成胜立功,臣以为难”(《武议》),认为“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治本》)这种破除封建迷信,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战争观在春秋战国时期求神问占流行于世之时无疑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二)朴素地认清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
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是古今中外历代军事家所关注并试图回答的问题。尉缭鲜明地提出“武植文种”的观点,认为“武为表,文为里”(《兵令上》),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中,政治是内在本质,军事是外在表象,政治比军事更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在西方两千多年后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才在《战争论》中明确提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与尉缭认识相类似的着名论断。
此外,尉缭还对政治与军事各自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兵令上》)二者只能相辅相成,不能偏废。《尉缭子》非常重视政治制度建设,认为国家的政治制度搞好了,才能富足安定,才能“威制天下”,所以“兵胜于朝廷”(《兵谈》)。
(三)认识到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提倡义战
尉缭发展了老子“兵者,不祥之器”的认识,明确提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兵令上》),主张慎战。同时他也认识到战争既有“挟义而战”,也有为“争私结怨”(《攻权》)而战。他明确支持“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武议第八》)、“伐暴乱而定仁义”(《兵令上》)的正义战争,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武议》)的不义战争。
(四)认识到经济与战争的关系,提倡农战
尉缭认为,治国的根本在于经济,“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治本》)。只有不废耕织二事,国家才有储备。而这一储备正是战争的基础。所以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尉缭提出把发展农业作为治国之本,提倡农战,“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民众就会“扬臂争出农战”(《制谈》)。这与商鞅“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农战》)的思想是一致的。商鞅认为“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入使民尽力则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商君书·算地》)只要人民耕种能富足,就会尽力耕种;打仗能得功名,就会卖命打仗。这样内可以提升粮食储备,外可以战胜强敌。
尉缭痛恨腐败浪费,他看到了“百里之海,不能饮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军渴”的现象,认为“欲生于无度,邪生于无禁”,私欲的产生在于没有节制,邪恶的产生是由于禁止不力,提出“夫禁必以武而成,赏必以文而成”(《治本》),主张通过严格的制度建设,以强有力的惩罚措施来杜绝腐败浪费。
二、“制必先定”的法兵家治军思想
《尉缭子》全书二十四篇,《重刑令》之后十二篇几乎全部是条令条例,涉及军队管理、士兵训练、部队推进、部队驻扎等军队建设所包含的诸多内容,保存了战国时期许多重要军事条令,并提出了一套极富时代特色的军中赏罚条令,从这个意义上讲,《尉缭子》一书可谓我国现存最早的军制学着作。
(一)强调“制必先定”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儒、墨、道、法、兵并行于世,其思想也相互影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兵家思想中也蕴含着儒、墨、道、法诸家思想。吴如嵩先生就认为“先秦的兵家可以分为法兵家、道兵家、儒兵家、墨兵家、杂兵家、纵横兵家等”,并明确指出,“尉缭子就是法兵家”。
汉代刘向《别录》中也曾言:“缭为商君学。”《尉缭子》一书的军事思想中明显带有浓厚的法家色彩。尉缭十分重视制度建设,明确提出“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制谈》),强调治军必须先定制度,只有制度明确,才能依法治军。尉缭对于军事制度的重视、强调从体制和制度上加强军队管理,是先秦其他军事思想家所不及的,即使在今天看来,尉缭“制必先定”的思想仍然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更难得的是《尉缭子》后半部以十二篇的篇幅记载了当时建军、治军的十部条令,大到将帅任命、军队编成,小到军需粮用、着装徽标等都作了详细的描述,这无疑为研究先秦军事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主张“重赏重罚”
有了良好的制度,还需要严格的刑罚来保障制度的权威,所以尉缭主张“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重刑令》)。尉缭主张将战败、投降、临阵逃脱的将士宣布为“国贼”“军贼”,不仅处以“身戮家残”之刑,还要削户籍、发祖坟、变卖家属做奴隶。他在《束伍令》中提出了严酷的战场惩罚条令:战斗中本伍伤亡与敌相当则功过相抵;如果自己伍内有伤亡而没有斩获敌人,全伍的其他人都要处死;如果己方伤亡了一个军官又同时消灭敌人一个军官,则功罪相抵;如果己方伤亡了一个军官而不能消灭敌人一个军官,所部其他人全部处死并惩办他们的家庭。这些规定都体现了重罚的原则。尉缭认为人民只有“内畏重刑,则外轻敌”。所以前代圣明的君主都会首先申明法令制度,然后注重刑罚威慑督促,“刑重则内畏,内畏则外坚矣”(《重刑令》)。
尉缭汲取了法家“刑不辟大夫,赏不遗匹夫”的进步思想,明确主张为了严明军纪,赏罚要遵循“刑上究、赏下流”的原则。上至将吏,下至士卒,“有功必赏,犯令必死”(《兵令上》),真正做到“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武议》)。
(三)提倡精兵强军
《制谈》中,尉缭举齐桓公、吴起和孙武各带“十万”“七万”“三万”之兵即能纵横天下,说明“兵贵精,不贵多”的道理。他强烈鄙视“所率无不及二十万之众者,然不能济功名”的“今天下诸国士”,他认为“百万之众而不战,不如万人之尸;万人而不死,不如百人之鬼”(《兵令下》)。尉缭在全书最后总结道:“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其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其十一者,令行士卒。”(《兵令下》)这段话中“杀”字曾令不少学者动容,认为其片面鼓吹严刑峻法。如果把这个“杀”字理解成今天的意思,尉缭主张自残军队的作法确实令人费解。但如果把这个“杀”解释为“裁减”,则与全文提倡精兵强军的思想一脉相承。尉缭主张通过精减兵员来保证部队战斗力的做法在战国中期具有进步性。
三、灵活机动的兵形势家作战思想
作战思想是先秦兵书的一个重要内容,以孙、吴为代表的兵权谋家都长于此道。《尉缭子》作为先秦有影响力的兵书,在作战思想上也有其独特的特点———强调形势。班固《汉书·艺文志》把兵学流派分为四类: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兵形势家,特点为“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注重战术研究。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记录的十一篇“兵形势家”着作中,《尉缭子》是至今唯一存世的兵法着作。《尉缭子》的兵形势特色主要体现在强调兵力集中、先发制人、兵贵神速、避实击虚和奇正相辅上。
关于兵力集中,《孙子兵法·虚实篇》曾专门论述过“我专而敌分”“我众而敌寡”。尉缭进一步提出“兵以静固,以专胜。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兵权》),强调军队靠兵力集中取胜,兵力分散就会导致力量削弱。尉缭还以水为喻,“胜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触,丘陵必为之崩,无异也,性专而触诚也”(《武议》),说明兵力集中的强大力量。
关于先发制人,尉缭认为:“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战权》)用权谋先施加于敌人,敌人就没法依靠实力来交锋;用军事实力先行打击敌人,敌人就没有威势来抵抗。然后得出结论:“故兵贵先,胜于此,则胜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战权》)。自古以来,无论施谋用计还是武力打击,先机制敌、先发制人,以达成战略上的突然性,总是能取得最大效益。
关于兵贵神速,《尉缭子》中写道:“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敌境。卒聚将至,深入其地,错绝其道,栖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攻权》)。这里不仅明确规定了部队进攻时的行进速度———相距千里到达期限为十日,相距百里到达期限为一日,而且指出了部队快速机动的具体战法———部队集结后,应深入敌境,切断它的交通要道。关于避实击虚,《尉缭子》强调:“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战威》),“我因其虚而攻之”(《攻权》)。战争中选取敌防守薄弱而又是要害之地,才能事半功倍,奠定胜基。这与同样贵“势”的孙膑所提倡的“批亢捣虚”的思想是一致的。
关于奇正相辅。奇正是中国古典兵学中一对重要的概念,自孙武提出这对概念以来,历代兵家一直在研究,尉缭认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这与孙武所说的“以正合,以奇胜”,先用正兵当敌,后用奇兵出奇制胜,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不能固守教条,是先用正兵还是先用奇兵完全要依战场形势而定,要以克敌制胜为目的。所以说“或先或后,制敌者也”(《勒卒令》)。奇正是重要的谋略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奇正已经成为谋略的代名词,尉缭说:“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坚,三军之众,有所奇正,则天下莫当其战矣”(《武议》)。这说明一定数量的部队,配上好的装备,再辅以谋略,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尉缭子》一书十分重视军事行动的运动性和战术运用的灵活性,在战术上确实做到了“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强调“以轻疾制敌”———以速度和灵巧压制敌人,与重视战略谋划的兵权谋类孙、吴兵书有所不同,在卷帙浩繁的先秦兵书中自成“兵形势”一派。
作为先秦成书较晚的一部兵书,《尉缭子》全书以法家思想为渊源,以“法制”为主线,以“形势”为特色,其中既可见孙、吴的谋略思想,又不乏“仁”“义”的儒家思想,可谓先秦兵学的集大成之作。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军制学着作和唯一的“兵形势家”着作,《尉缭子》一书在我国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研究古代军事思想和军制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徐勇.尉缭子浅说[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0.
[2]华陆综.尉缭子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吴如嵩,张秦洞.白话尉缭子[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