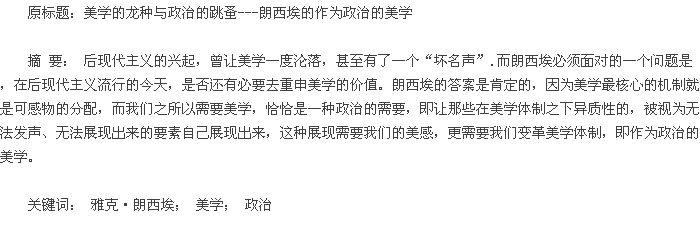
海涅的名言“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如今用在美学身上再适合不过了。曾几何时,尤其在启蒙时期,美学如同一颗明星,照耀着人类艺术和思想前进的方向。在那个时期,一个很正常不过的看法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就是将最合乎理性,最崇高的美学思想,贯穿始终,当温克尔曼静观古希腊的雕塑时,不由得发出感叹: “这便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正如海水表面波涛汹涌,但深处总是静止一样。”[1]( P.17) 但如今,美学成为了一门诘屈聱牙的话题,似乎只有在酸腐气十足的老学究的课堂上,才能一本正经地谈美学。自从鲍姆嘉通以降的那种带有宏大倾向的美学似乎已经逐渐堕落,它不仅离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远,同时也与当代艺术家的创作越来越远。或许正因为如此,朗西埃在《美学中的不安》一书中不由地感叹说: “美学有个坏名声。”[2]( P.9) 实际上,朗西埃如此感叹,并不是为美学唱诵挽歌。相反,朗西埃的一个信念是,那个曾经志向宏远,试图在人间播下龙种的美学还在,它矢志不渝,并一直致力于在用它独特的方式面对着我们的世界。
一
我们可以这样进入朗西埃的美学思考之中。在一次讲座中,一个学生向笔者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有一次他问一位搞艺术的朋友什么是艺术,那个朋友将刚刚抽完的烟头径直扔到还没有喝完水的一次性水杯里,说这就是艺术。但这个学生反过来问道,如果他自己也将烟头丢入水杯,是否算艺术呢? 那个搞艺术的朋友明确回答不是。这个学生的困惑是,为什么同一个行为,一些人做出来是艺术,而另一些人做出来就不是艺术?
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其中最着名的案例是杜尚( Duchamp) 的小便池。那是在1917 年的纽约独立艺术家协会的展览上,身为评委之一的杜尚,从商店里购买了一个在男厕所里随处可见的小便池,并以化名 R. Mutt 签名在了这个所谓的“艺术品”上,并提出要在展览中展出。当然,对一个不知名的 Mutt先生送来的特殊展品,展览的主办方一开始认为这是对展览的侮辱,并严词对这个“作品”加以拒绝。
然而当知道了这件作品是出自大名鼎鼎的杜尚之手时,世人对待这个作品的态度瞬间发生了大逆转。
在今天,这个名为《泉》的作品不再像独立艺术家协会的评价那样是对艺术的侮辱,而成为对当代艺术史发展产生最重大影响的作品之一。尽管纽约的展览拒绝了这部作品,但后来这个着名的小便池游历全世界最知名的博物馆和美术馆,最终留在了法国巴黎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 即蓬皮杜中心) 里。这里的问题并不是作品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内涵,任何试图从作品的内容和对象的意义角度来找寻《泉》这个作品的艺术地位都必然会走入死胡同。问题在于,一个署名 R. Mutt 的匿名作者,和大师杜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或者更严格地说,即便在收录该作品的蓬皮杜中心,杜尚的小便池和一个普通水管工人拎进蓬皮杜中心的小便池的区别何在?
实际上,这个问题涉及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艺术与非艺术的分界线在什么地方? 更简洁的问法是,什么是艺术? 对这个问题,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就不停地追问其答案,不论他们如何界定艺术是什么,都在重复一项工作,即在艺术与非艺术之间划定界线,以十分清晰的态度来区分两者。可惜的是,无论将艺术归结为模仿,还是表现,抑或创造,乃至游戏,各种定义都无法圆满地解释这个问题。因此,在进入现代之后,尤其经过分析哲学的洗礼之后,大家公认的一个态度是艺术界定具有不可能性,因为各个艺术作品间尽管有维特根斯坦所言的家族相似性,但不可能找到可以贯穿一切艺术作品的准绳,将所有作品一个不落,也无一多余地纳入到一个定义之中。尽管如此,一些分析美学家试图以一种更为模糊的方式来界定艺术。其中最为着名的是美国当代美学家迪基( Dickie) 的定义: “一件艺术作品在描述意义上是( 1) 一件人工制品( 2) 一些社会团体或社会团体的亚组织已经认可了这个人工制品具有被欣赏的资格。”[3]( P.254) 事实上,迪基对艺术的界定已经非常接近朗西埃的思路了。首先,我们需要理解,迪基对艺术界定的优势所在,其实,条目( 1) ,作为人工制品的东西已经在最近的艺术实践中被打破,而且不能体现迪基定义的独特之处。迪基定义的最大优势在于,在条目( 2) 中,不是从艺术的对象,艺术的内涵,而是从艺术的运作方式( operation) 上,来理解什么是艺术。简言之,就是有一堆人,迪基称之为团体( society) ,这是个相对较封闭的圈子,而正是这个圈子,可以承认,可以授权,什么样的人工制品才能算得上是艺术品,什么样的东西才值得我们欣赏。据说,迪基对他提出的这个定义颇为自得,至少他认为,只有他的定义才较好地解决了杜尚的“现成品”艺术对艺术定义的挑战。正如他在文章的末尾所说“现在我已经说到就像说‘艺术作品就是某人会说: 我将这个东西称之为艺术作品'.我想就是这个样子”.[3]( P.256)不过,迪基真的完成任务了吗? 没有,远远没有! 其实,对朗西埃而言,指出有一个这样的团体,来认可某个东西是艺术品,仅仅解开了冰山一角。
迪基的定义仅仅开了一个头,就迅速得意洋洋地沉浸在自己打开的这扇门之前,根本没有把脚迈入门内。实际上,与迪基同时,作为迪基的辩论对手的丹托( Danto) 也提出了着名的“艺术界”理论,与迪基对社会团体的描述是极其类似的。不过丹托也没有将这个问题深入下去,而是将艺术圈或艺术的社会团体的评价和承认机制当作一个固有的状态加以肯定,而不是对之进行更深入的反思。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团体,一个圈子来承认?
他们承认某个制品为艺术品的资格和品质何在?
实际上,无论是迪基还是丹托,都无法在这样一些问题上继续阐发下去。其中最根本的困境在于,他们在坚持这个定义的时候,同时必须坚持艺术本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就是说,当我们谈到有一批人,或有个圈子可以承认和确定什么东西可以称得上是艺术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不是在纯粹艺术的范畴内谈问题了。说得更严重些,这个定义实际上是以非艺术的方式来定义艺术,或用一个外在于艺术的标准来框定艺术。如果过多地托付于一种外在于艺术的标准,势必会让旨在坚持艺术独立性或审美自主性的美学家们感到难堪。因此,避免进一步弱化艺术本身的价值,他们选择了点到为止,将艺术变成一个纯粹艺术圈自己玩的事情。
但对于朗西埃来说,这样做不过是掩盖了问题,而不是真正解决了问题。实际上,离真正解决问题还差得远呢! 也正因为如此,朗西埃坚持认为,审美、艺术和政治具有高度的一体性,更为准确地说,所有审美的问题和艺术的问题,在朗西埃看来都是政治问题。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朗西埃格外强调,不能把这里的政治问题理解为一种日丹诺夫主义的现代翻版。在《政治的边缘》一书中,朗西埃就格外小心地处理了法语中的阳性政治( le politique)和阴性政治( la politique) 的区别。也就是说,所谓的审美的政治或艺术的政治,并不意味着艺术和审美要为某个体制、政治集团、党派和宗派服务,相反“政治( la politique) 不是治理共同体的艺术,它是人类行为的一种异议( dissident) 形式,对于集合与领导人类群体所依据的那些规则来说,它是个例外”.[4]( P.4)也就是说,审美或艺术之所以是政治的,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不同于体制和治理秩序的异议模式,它是一种在正常体制下无法被感受到的东西的在场,是一种直接将原本被体制或治理秩序所压抑的东西表达出来的症候( symptme) .让我们回到艺术领域。迪基的定义实际上解释的就是一种艺术领域中的政治。有一个圈子,一个团体,他们以制度和体制方式,决定了在艺术维度上,什么可以被感知为艺术,什么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在场。艺术家将烟头投入到水杯中以及杜尚将小便池置于博物馆中可以被感受为艺术行为,而大众同样的行为不过是一种日常生活经历或者是拙劣的模仿。这里的中心词是感受,有一个关键性的划分( lepartage) ,它将未分化( indifférence) 的状态的存在物区分 为 可 感 之 物 ( le sensible) 和 不 可 感 之 物( l'insensible) ,唯有前者,通过这种划分的区隔,才能变成一个真正的艺术品,成为审美的对象。而后者被这种划分的区隔排斥在成为艺术作品,成为审美对象的可能性之外。
正是在这里,我们邂逅了朗西埃美学的第一个重要概念,可感物的分配格局( le partage du sensi-ble) .正是这个分配格局,将可感之物和不可感之物区分开来,也正是这个格局,让艺术成为了艺术。
朗西埃自己的说法是: “我所谓的可感物的分配格局,即是一个自明的意义感知事实的体系,它在显示了某物在公共场合中的存在的同时,也划清了其中各个部分和各个位置的界限。”[5]( P.12) 也就是说,通过可感物的分配格局,原先悬而未分状态的世界,被这个格局分配为多个不同的区域,而在这些区域中,最典型的区分就是可感与不可感,我们的创造、观看、扮演、甚至市场性的交易都取决于可感物的分配区域,而不可感之物的区域视为被压制的、被排斥的、甚至被湮没的区域。它们尽管实存着,但是它们没有能力以自己的方式来呈现自身。同样是潦草的绘画,出自大画家之手的叫抽象艺术或先锋艺术,带有开创性的冲击和感受,如若出自一个 4 岁小孩之手的图案,只能叫做涂鸦,很快就被抹除和忘却。前者居于我们视觉可感性的中心,而后者,在这个分配格局之下,我们甚至察觉不到它的存在。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朗西埃坚持认为艺术就是政治。决定艺术的不是艺术本身,而是外在于艺术的一种区分的体制,朗西埃称之为艺术的审美体制( le régime esthétique de l'art) .这个体制,在迪基的定义中,被作为一种实证性( positivité) 的事实接受下来。实际上,朗西埃认为,这种实证性的体制构成了对艺术本身的压抑和束缚。真正的艺术,与真正的政治一样,是异议性的,它要表达出异质性,一种不能同当下体制的连贯一致性同流合污的政治。简言之,让原先在可感物的分配格局下不能被感觉到的那些存在物以异质性的方式出场。这样,问题被转换回来,怎样让不可感之物在可感物的分配中出场呢? 朗西埃或许会会心一笑并给出答案说: 美学。
二
倘若艺术是可感物分配格局的产物,那么美学呢? 在理解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理解另一个问题,即朗西埃对当今艺术发展的趋势的评价。对朗西埃而言,艺术的发展呈现出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趋势: 首先,一些艺术批评家会指出,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构成上不可避免地留下社会、经济、文化的印记,所有的艺术的创作,难免沾染上现实生活的痕迹,也即是说,各种生活方式( les formes de la vie) 构成了艺术的基本要素。这样,一些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需要的是一种积极与现实生活相连的,并致力于面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形式。与此同时,他们所认定的艺术,不是独立于生活之外,其创作的目的也是为了让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更为美好。尽管这种态度不一定需要艺术创作沦为商业化和资本运作的附庸,同时为这个消费色彩已经过于浓厚的社会再增添一个仅仅作为一种粉饰太平的装潢的作品,但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的确呈现出让艺术尽可能贴近生活的倾向。比如像彼得·贝伦斯( Peter Beh-rens) 这样的“德国工艺同盟”( Werkbund) 的设计师,他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种在艺术国度里孤芳自赏的艺术形态,而是将艺术的形式积极转变为工业时代的产品,小到电水壶、灯泡,大到现代建筑,都成为这种艺术的象征。这是工艺美术的“新哥特”运动,而后包豪斯( Bauhaus) 将这一理念发扬光大。对于他们来说,艺术原则与生活的原则不断切近,而艺术存在的本身就在于对生活世界的改在,并重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方式。也即是说,这种艺术形式致力于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通过独特的异质性的感受,我们被艺术的感染力吸纳到这种力量之中,最终通过感受和感觉中枢上的革命实现对整个世界的革命。
这是一幅现代主义的景象,它带着对美好未来社会的许诺而存在着。艺术的存在就是为了一个更辉煌灿烂的明天。这种影响力不仅存在于贝斯特的“德国工艺同盟”和包豪斯那里,也存在于那些仅仅用来对抗资本主义堕落的左翼激进运动那里,如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提出的城市漂移( dérive) 运动。这种“政治的美学化”运动已经对一个固定格局下处于一定范围的艺术表现产生不满,比如说,长期以来,艺术被等同于挂在墙上的某个画框里的东西,那个东西被强制性地缩微在一个局部空间,它与观众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反距离的态度也在戏剧中得以表达。朗西埃指出:剧场涉及观看行为,而观看行为,是个坏东西。我们需要一个新剧场,一个没有观看行为的剧场。我们需要一个剧场,在那里视觉关系---它隐含在观众区中---隶属于另一种关系,而它隐含在戏剧之中。戏剧意味着行动。剧场是行动的的确确通过一些生命体在另一些生命体面前被表演出来的地方。后者也许放弃了他们的权力。但是他们的权力在前者的表演中,在开发它的智慧中,在它传递的能量中被重新激活。真正意义上的剧场一定是以表演的动能为前提的。剧场不得不被拉回到它的本质,它与我们平常所知的剧场相反。我们 所要寻求的是一个没有观众的剧场,在那里观众将不再是观众,他们学习东西而不是被图像所虏获,他们将变成一场集体表演中的活跃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观者。[6]( PP. 3 -4)这样,剧作家、导演和演员与观众的界限被消除了,观众也变成了演员,这里没有看与被看的关系。
而戏剧本身就是在观众的共同参与中建构的。在最近的一些潮流中,剧场的空间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这些戏剧的狂欢者的节奏。显然,他们已经摒弃了剧场本身,而进一步以更广阔的活动舞台来表演自己。
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在伦敦街头和巴黎郊区的抗议中,都有这样的艺术家们的身影,他们的艺术理念就是要通过艺术性的创造,去面对生活的节奏,从而许诺一个更为美好的明天。
其次,沿着这个逻辑推演下去,我们会得出一个悖论。要让艺术尽可能地去接触生活世界; 而去改造现实的生活世界; 而去许诺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前提是,艺术必须与现实生活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将艺术放置在生活世界的大染缸里,否则艺术与生活世界一旦不能彼此区分,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艺术的终结”.因此,艺术面对生活世界的唯一的方式是与现实生活的经验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悬搁掉现实生活的经验。朗西埃以悖谬的方式说道: “将艺术实践与普罗大众衔接起来的,正是在物质上和象征上构造出一个专门独立的艺术的时空,去悬搁掉日常生活的感觉经验形式。”
[2]( P.36) 艺术不是向日常生活的沉溺,而是保持自己相对的自主性( autonomie) .在这里,朗西埃借用了席勒《审美教育书简》中对古罗马的女神朱诺的雕像的分析,从而提出,在雕刻师雕刻这座石像的时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自由表象”( libre apparence) 的态度。由于不是对现实的物体的临摹,对雕刻师而言,塑造女神的外形的时候有一定的自由程度,在整个成型的过程中,雕刻师考虑的不是某个凡间女子的形象,而是他心目中最美好的女神形象与最优质的石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席勒将这个雕塑的活动称为“自由的游戏”.在这个“自由的游戏”中,人的创造性的潜力被激发出来,雕刻师不再是被动的摹仿,而是主动的赋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席勒才明确地说: “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7]( P.124) 正如朗西埃所说,在这个“自由表象”或“自由游戏”中,体现的是一种“无所顾忌”( gratuite) 的游戏行为,而正是这种“无所顾忌”的“自由游戏”,才构成了艺术的自主性。事实上,在《韩非子》中,也曾提到画师面对齐王的提问时回答说“画鬼最易”的问题,画师曰: “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其中由于鬼魅从未被人所见过,因而画师可以逍遥游戏于笔端画纸之间,成为一种真正的自由创造。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运动更喜欢这种游戏的方式,它们将这种戏耍和反讽的方式推到极致,在利奥塔那里,已经没有宏大的严肃的艺术原则,有的只是在破碎的艺术的废墟中自由建立马赛克式的拼贴的艺术。无论如何,这种思潮致力于一种与当下生活经验的直接隔绝,也就是说,建构出一种专属于艺术创造的国度,无论这个独立的、悬置了一切日常生活经验的艺术国度所倾向的是古典主义的艺术,还是抽象的先锋派艺术,抑或后现代式的杂拼式艺术。总而言之,这种艺术的意义在于与使艺术日常生活划清界线,在艺术与非艺术之间建立起严格的壁垒,这是一种严格的政治性的区分。
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艺术路径,前者要求艺术努力地接近生活世界,努力地创造一个新的生活世界来。前者追求的是与生活世界的兼容性和一致性,让生活的原则和血液同时流淌在艺术的血管之中。后者是一种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悬搁,即保持艺术的相对独立性,实际上要求的是艺术与生活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一道在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裂缝,而且是一道无法弥合的裂缝,艺术坚持了这种“崇高”的分配格局,同时要求自己与非艺术保持一定的感觉上的分别。
也就是说,艺术不能与日常生活有共通感。这两个思潮同时在我们的世界里发生,正如马拉美的诗歌与包豪斯的设计是同时发生的一样。整个艺术潮流,在当代,正是呈现出这种悖谬式的格局,一方面,要求趋向于生活世界,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悬搁掉日常生活经验,保持自己领域中的高雅而不受凡尘的玷污。
朗西埃用了两个古希腊词语来表达这两个过程。前一个过程被称为 mimesis,但是对这个mimesis 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自然万物以及生活世界的摹仿。尽管奥尔巴赫的名着《摹仿论》使用的就是这个古希腊语的标题。对于朗西埃来说,“mimesis 意味着意义与意义之间的对应的体制”.[6]( P.60) 也就是说,mimesis 奠定了艺术创作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创作要求与生活世界之间保持一种和谐和连贯的关系。相反,后一个过程表现为一种创造与创生,即 poiesis,这是作为诗的词根的古希腊词语,正是要求艺术去悬搁日常生活的世界,去“自由地游戏”,去打造一个属于艺术自己的国度。
事实上,朗西埃最为关注的既不是让艺术与生活形式走近 mimesis,也不是让艺术悬搁了日常生活经验的 poiesis,而是将两者真正衔接起来的第三个希腊语单词 aisthesis.2011 年,朗西埃曾将自己的一批文章结集出版,他为这部集子命名的书名就是 Aisthesis,而这个书的副标题则为“艺术审 美 体 制 的 诸 场 景 ”( Scènes du régimeesthétique de l'art) .在书的序言中,朗西埃解释说: “Aisthesis 一词确立的是一种经验的模式,两个世纪以来,按照这种模式,我们将各种事物,无论在其生产的技艺上,还是在其最终目的上,都视为归属于艺术。它并不是对艺术作品的’接受‘问题,相反,它所涉及的是生产出艺术作品的经验上的感性的框架。”[8]( P.X) 这就是朗西埃意义上的美学,一种感受和感觉的机制问题。它将艺术所呈现的两种不同且保持一定张力的趋势以悖谬的形式拼贴( collage) 起来,正如朗西埃强调的那样,“拼贴将隐藏在幕后的两个有着明显差别的世界之间的联系昭然于天下”.[2]( P.88) 而Aisthesis,及其产生的艺术的审美体制,都是在两个有着明显差别的世界的张力之间存在着,两个悖谬方向的张力,使得审美感成为了必要,因此,Aisthesis 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感受,而是一种悖谬式的拼贴,一种强制性将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之下,规定了哪些东西是可感的,哪些东西是不可感的,某些东西以某种形式不可感,但以另一种形式就变得可感。Aisthesis改变的是我们感觉的神经中枢,这种分类,决定了艺术的 mimesis 和 poiesis 之间张力关系的分配格局。也正是在这种审美体制之下,美学才成为必要。
三
由是观之,美学并不像巴迪欧和利奥塔所说的那样毫无用处,成为艺术创作中拙劣的先知。
在朗西埃这里,美学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美学,或 Aisthesis,就是艺术的审美体制,而这个体制又进一步决定了可感物的分配。由于艺术这个独特而专门的领域是由于可感物的分配而产生的,那么,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美学,没有艺术的审美体制,根本没有什么独特的艺术领域存在。这样在巴迪欧那里,艺术成为哲学的前提变成了一纸空谈,更不可能存在巴迪欧所谓的非美学。因为,在哲学之前,根本没有一个领域可以独立出来被称之为艺术。在美学之前,艺术淹没在与宗教、法律等领域悬而未分的状态之中。如果没有专门的艺术的审美体制出现,我们根本无法认识一个被称之为艺术的领域。甚至利奥塔也错了,利奥塔准备“在崇高的美学面前,艺术的关键在于让自己成为证人,证明存在着不确定之物”.[9]( P.171) 利奥塔似乎要期待某种不可确定之物的“突然降临”,但在没有可感物的分配格局的时候,我们如何感受到某种东西的降临?
而朗西埃给出的一个关于美学最清晰的表达是“美学不是关于艺术或者美的哲学或科学,美学是可感性经验的重构”.[10]( P.196) 这里,朗西埃将美学还原为这个词在词源学上的意义,即古希腊所指的一种起到布局和分配意义上感觉结构,即 Aisthesis,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美学是可感物与不可感物之间的分布,即可感物的分配格局。因此,对于当前艺术的局面而言,我们并不是简单地靠近生活或远离生活的问题,因为对于朗西埃而言,这两种选择不过都是遵循同一个可感物的分配格局,也同时遵循同一个艺术的审美体制。在根本上,无论是主张独立艺术和高雅艺术的艺术家,还是力图在街头巷尾喧哗的关系艺术家,都没有真正突破这个局限。而真正的艺术创造,需要的是对既定的艺术的审美格局的打破,改变既有的可感物的分配的状况,让原先不可感的东西最终在艺术可感的方式下呈现出来。
然而,当下的艺术潮流,却没有矢志不渝地坚持这个方向。相反,他们往往会固守既定的审美体制边界。于是,我们在今天,看到的状况仍然是,一堆玩艺术的人去欣赏另一堆玩艺术的人的创造,那些在专业美术馆里经过策展人的环境设定,仍然迎来的是少数高冷的观众和顾客,芸芸众生仍然过着芸芸众生的生活。一个更为讽刺的画面是,一个住在美术馆旁边的居民都不知道这个美术馆在干什么。这种艺术领域与普罗大众的分离状态,这种艺术的审美体制的区隔,并没有真正被触动,而且由于艺术家们越来越激进,从而离大众的理解能力和范畴越来越远。
的确,按照朗西埃的看法,美学有一个承诺,它不仅是艺术的引领者,也是政治上的生活方式的引领者。美学,不仅仅决定了艺术是什么,怎么玩艺术,更重要的是,怎么跟大众一起玩艺术,最终创造一个未来的审美共同体,当然,也是感觉的共同体。但是,当代的批判性艺术和激进艺术都没有很好地承担这个责任,并不是艺术不够反叛,也不是艺术不够高深莫测; 相反,正是艺术的反叛和高深莫测拉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与普罗大众的鸿沟。相反,市场化的逻辑和资本的产物比艺术品更能捕捉到大众的心灵。在许多艺术家看来,大众简直是政权统治和商业化资本主义的行尸走肉。其实,做出这样批判的艺术家恰恰忘记了美学的使命,当他们越是执着于自己的独特与叛逆时,恰恰是强化了他们的分立关系,进一步巩固了朗西埃意义上的艺术的审美体制。
这种做法,显然与朗西埃意义上的审美革命相去甚远。或许,对于那些旨在兑现美学的许诺的艺术家们来说,他们深切地感觉到,播下了龙种,却在政治上收获的是跳蚤。当他们越是使劲去创造一个作品的时候,试图以最叛逆和最深刻的方式创作的时候,艺术可感性的分配格局恰恰发挥了最大的功效。换句话说,艺术家自己的孤芳自赏,带来的仅仅是政治上可怜的收获。正如朗西埃说道: “批判艺术是这样一种艺术,它要引起对统治机制的关注,并将观众变成有意识改变世界的行为人。我们也非常清楚,这条道路如履薄冰。一方面,就其自身而言,理解无助于改变知识态度和情境。被剥削的人很少会要求对剥削的法律作出解释。被统治者也不会因为他们误解了天下大势,就不会继续受奴役,他们受奴役是因为他们没有转变当下局势的信心。”[2]( P.87)这样,如何兑现美学的“龙种”,如何缔造一个未来没有分割,没有彼此可感物的差异,消除了各种不必要的分野之后,实现真正平等的未来共同体,成为摆在朗西埃面前的最大问题。实际上,朗西埃给出的答案以及他最终追求的就是一种美学上的共同体。这个美学共同体也是一种感觉和意义的共同体,它建立在共同而平等的审美形式之上,朗西埃将之分成了三个层次: 首先,这个共同体是“诸多不同形式的感觉数据的结合: 形式、词语、空间、韵律等等。这也涉及不同的’意义 ' 的感觉的结合”.[6]( P.57) 比如说,巴黎郊区的一个区域的全部市民将自己的需求印制在统一的黑 T 恤上,他们构成了一个共同的姿态,并在摄像头面前表现出来,这就是一个共同体,各种元素杂合而成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其得以构成的不是统一要素,而是各种歧异链接,他们共同在政治上表达出“异议”( dis-sensus) ,它们为我们的感觉系统增加了另一套感觉系统,两种感觉体制相遇了,成为异质性的“歧异”型组合。而这正是朗西埃所强调的共同体的第二个层面,哲学家为歧异的感觉体制提供一种概念性框架。可以在这个概念性框架下,将异议和歧异的表达统一起来。不过哲学概念的框架并不是将异议和异质性的因素化解在一个一致性的整体之下,这样我们进入到第三个层次,一种各种矛盾交织的现实的社会整体的共同体。
在这个共同体中,异议的声音可以直接而不是通过再现表达出来,我们需要的不是由艺术家再现出底层人的苦难,让我们成为底层穷人的苦难的见证人; 相反,我们不需要这种伪善的仁慈。朗西埃的目标是,摧毁一切替所谓的异议代言和再现的状况。一旦如此,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就会按照自己的概念框架对异议的异质性进行了不恰当的切割。
因此,无论是艺术也好,政治也好,美学也好,它们的目的都不是去再现那些不可再现之物,我们并不需要让有异议的异质性元素以某种方式再现,因为这种再现必定意味着按照既定的审美体制进行切割,最终根本没有触动应该加以革命的艺术的审美体制以及其可感物的分配格局。相反,我们要让这些发不出声音的声音自己发出声音,让他们自己显现( présence) 出来,而不是通过某些人的代替而再现( représentation) .因为再现机制仍然意味着,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有资格发声,更有资格表达,而美学革命要取缔的就是这种逻辑。正如朗西埃所说: “美学革命所描绘的场景,就是提出将美学对统治的支配性关系的悬搁,转变为没有统治的世界里的生成性原则。”[2]( P.54) 唯有如此,激进的艺术创作才不至于是对艺术的审美体制的强化,相反,艺术有可能直接面对公众,并真正将公众纳入到未来共同体的共同创建之中。也唯有如此,“龙种和跳蚤”的悖论才能真正得到解决,美学的政治许诺才能转化为一个更为灿烂的明天。
参考文献:
[1]温克尔曼。 希腊人的艺术[M]. 邵大箴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Jacques Rancière. Malaise dans l'esthétique[M]. Paris: Galiée,2004.
[3]Gorge Dickie. Defining Art[J].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1969,6( 3) .
[4]雅克·朗西埃。 政治的边缘[M]. 姜宇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5]Jacques Rancière. The Distriubution of the sensible: Politics andAesthetics[C]/ / Gabriel Rockhill trans.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London: Continuum,2004.
工笔人物画是以人物活动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中国画传统画科,是中国画里直接反映现实的画科,在中国画各科中最富认识价值与教育意义。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其仍能流传至今而不被时代所淘汰,是由于其不断的进行创新,将时代中的特色元素融入绘画之中,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