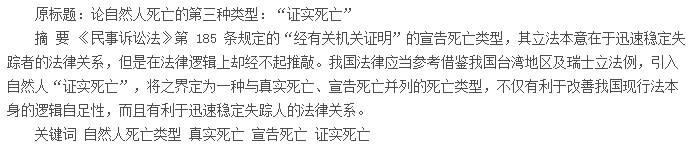
一、问题的提出。
2008 年汶川地震造成失踪人员达 17923 人,时任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要求震区保险机构:“对于被保险人失踪的,按照当地政府提供的失踪人员名单,保险公司先行赔付保险金额的一半,一旦确认死亡即全额赔付。” 中国保监会这一高擎社会责任立场的临时性应急举措固然值得激赏,但是亦折射出我国现行法律制度难以因应现实需求的窘境。虽然无从探知吴定富主席所称“确认死亡”这个非法律术语的确切含义,但是遵循《民法通则》关于自然人死亡的规定,所谓“确认死亡”应当既包括嗣后发现被保险人尸体从而确定其死亡的情形,亦包括被保险人因地震失踪而被法院宣告死亡的情形。
据学者考证,宣告死亡制度萌芽于中世纪日耳曼法,成型于1763 年制定之《普鲁士失踪法令》,后为大陆法系各国普遍采行。
郑玉波教授曾就宣告死亡制度的立法意旨做出精辟阐释:“盖人既失踪,则其有关之权利义务,必无法确定,此种状态,若任其长久继续,则不利于社会者甚大,例如财产之荒废,及配偶、继承人之不利等问题,均有善后处置之必要,因此法律上遂设有死亡宣告之制度,以济其穷。”《民法通则》第 23 条规定,因意外事故而失踪者,失踪满两年方可申请宣告死亡;《民事诉讼法》第184 条、第 185 条除重申《民法通则》第 23 条的规定之外,增加两项规定:一是明确宣告死亡的公告期为一年;二是规定“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的,无须失踪满两年即可申请宣告死亡,公告期亦缩短至三个月。《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的“经有关机关证明”条款,以“有关机关证明”取代失踪期限要件并大幅度缩短公告期,旨在迅速结束失踪者法律关系的不确定状态。考诸宣告死亡制度的发展史,大陆法各国立法例从未规定过“经有关机关证明”的宣告死亡类型。在此我们不禁要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5 条的这一“创新”究竟是理论基础与实践价值兼备的结晶,抑或是立法者全凭臆断的产物,究竟有无实益?为全面考察实务现状,笔者通过“北大法宝”,搜集到 50 个法院根据“有关机关证明”做出宣告死亡判决的案例作为分析样本。
二、“有关机关证明”的实证考察
“有关机关证明”取代失踪期限要件并缩短公告期,实际上体现出立法者赋予此种“证明”以高度的可信性期待,这种期待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通过限定“有关机关”范围以及“证明”记载内容的可信性两项要素实现的,因此,实证考察即从这两个方面展开。
(一)“有关机关”的范围
无论《民事诉讼法》抑或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均从未明确界定“有关机关”的范围。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做出《关于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受理宣告失踪、死亡案件应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法研[2008]73 号,以下简称《答复》),其中第二条指出:“…有关机关,主要是指公安机关,也可以包括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但不包括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或者下落不明公民的工作单位。”尽管《答复》的规范效力无法企及法律、司法解释,甚或根本不能称之为法源,但是其毕竟是最高人民法院就“有关机关”范围的首次表态,参考价值不容小觑。《答复》以列举与排除两种方式界定“有关机关”范围,其中,对于公安机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采取完全列举方式,意即只有这两类机关才有出具“证明”的资格;基层自治组织及失踪者的工作单位被排除在外,看似不过是对前述完全列举的再次肯定,但亦体现出最高人民法院避免出具“证明”随意性的考量。
50 个样本案例中的意外事故均发生于《答复》出台之后,但是《答复》的精神显然未获各地法院足够的重视,样本案例对“有关机关”范围的界定仍显混乱,虽然不能据此认为这些案例属违法裁判,但是部分案例显然缺乏妥当性。样本案例中“有关机关”范围主要区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判决书未载明“有关机关”名称,仅指出“经有关机关证明已不可能生存”的有 14 件。
二是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作出宣告死亡判决的有26件,其中,被申请人户籍地与意外事故发生地重合的有 7 件;被申请人户籍地与意外事故发生地不是同一地域的有 19 件,该 19 件中,由被申请人户籍地公安机关出具证明的有14 件,由意外事故发生地公安机关出具证明的有 4 件,由其他公安机关出具证明的有 1 件。
三是根据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调查报告等作出宣告死亡判决的有 9 件,该 9 个样本案例均系被申请人因海难事故下落不明,海事部门综合事故发生及搜救情况出具证明。四是根据外国机构出具证明并经我国驻当地大使馆认证而作出宣告死亡判决的有 1 件,被申请人丁某在毛里塔尼亚海域遭遇风浪坠海失踪,毛里塔尼亚努瓦迪布宪兵大队海事支队出具证明文件,并经我国驻毛大使馆公证认证。
(二)“证明”质量现状
考诸 50 个样本案例,“有关机关”所出具证明的质量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
1.不知所云型。因宣告死亡判决书既未提及“有关机关”的名称,亦未提及意外事故的发生经过,从而无从判断出具证明的机关是否适格及其出具证明的准确性如何。以此而论,法院以不知名的“有关机关”出具的证明作为基础事实,据此而推导出的推定事实——宣告死亡判决,究竟有多少可信度与公信力呢?应当指出,《民事诉讼法》采纳的“有关机关”并非准确的法律术语,过于模糊而缺乏明确的指向性,极易造成适用困难。然而,法院在判决书中照搬不误则明显不够严谨,我们有理由追问:“有关机关”究竟意所何云?如果任何国家机关出具的证明都能够成为定案依据,则势必损害宣告死亡制度的严肃性,亦与法律设计初衷不符。
2.公安机关出具型。如果失踪人系因在其户籍地发生意外事故而下落不明,即户籍地与意外事故发生地重合,则失踪人户籍地公安机关具备调查了解意外事故发生情况以及失踪者失踪情况的便捷条件,由其出具的证明显然具备较高的准确性。但是,如果失踪人户籍地并非意外事故发生地,甚至两地相距非常遥远,那么只有当失踪人户籍地公安机关前往事故发生地进行调查,或者目击证人就事故发生、失踪者失踪情况做出详尽证明的情况下,失踪人户籍地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才能作为事实推定的基础事实而加以采用。《答复》第二条限定的“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当地”二字应当是指“意外事故发生地”,之所以做此限定,应当就是出于此项考虑。在上海海事法院(2008)沪海法特字第 4 号案件中,“晓阳”号轮船从香港航行至越南胡志明市的途中,船员殷索杰意外落水,经搜救仍下落不明,上海海事法院根据上海港公安局出具的证明做出宣告殷索杰死亡的判决。事实上,上海港既不是殷索杰的户籍地亦不是意外事故发生地,我们不禁要质疑上海港公安局是否为适格的证明出具机关以及其出具的证明是否能够采信。当然,适格的出具证明的公安机关并非仅限于失踪者户籍地、意外事故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特殊情形下亦应当将其他公安机关涵盖其中,如前述案例中,假设上海港系“晓阳”号轮船的登记地,那么即便上海港公安局未能前往事故发生海域进行调查,只要其对有关证人就事故的发生、殷索杰落水失踪情况进行调查、询问,其据此出具的证明就应当具有高度的可信性,足以作为宣告失踪者业已死亡的依据。
3.其他机关出具型。《答复》将出具证明的机关的范围限定于公安机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似不全面,因为某些行业主管机关或者具有搜救职能的机关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达到现场,对事故及失踪情况最为了解,由其出具的证明可能更加符合“高度盖然性”的证明要求。如在广州海事法院(2010)广海法特字第 4号案件中,判决书援引东海渔港监督出具的《关于“粤湛江00306”船员失踪情况的调查报告》,详细叙述了船员叶朝科落水失踪情况以及搜救经过:“2010 年 3 月 24 日,‘粤湛江 00306’渔船在湛江市硇洲岛东南方向海域渔场作业,当时航速 6.3 节,四名船员没有穿救生衣在甲板上下笼。约 15 时,放笼至 100 多只时,船员叶朝科不小心被笼绳扣住手部后被拖下海。‘粤湛江 00306’渔船转向返回施救,因船的惯性较大,船舶调头返航后叶朝科已游离渔船 80 多米,人在海上挣扎,当渔船向叶朝科方向驶去 2 分多钟,叶朝科已沉下海。‘粤湛江 00306’渔船立即起机收笼搜寻,并电话呼叫在附近作业的‘粤湛江 8054’和‘粤湛江 04039’渔船参加搜救,搜救过程约2至3个小时,没有再发现叶朝科的踪影。”
法院根据该《调查报告》并经三个月公告,做出宣告叶朝科死亡的判决。在海口海事法院(2012)琼海法宣字第 1 号案件中,2011 年11 月 20 日,“招洋”号轮船从广东省顺德市驶往海南省洋浦港途中,在琼州海峡中水道发生机舱爆炸,造成该轮水手长肖正祥落水失踪,经多方搜救无果。2011 年 11 月 28 日,海南海事局出具证明,证明经过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评估,认为肖正祥在该海事事故中生存的可能性已经很小,海口海事法院依据该证明并经三个月公告,做出宣告肖正祥死亡的判决。在上海海事法院(2009)沪海法特字第 4 号案件中,法院系根据连云港海上搜救中心出具的证明,做出宣告“鲁荣渔 1615”号渔船船员曹春鹤死亡的判决。
以上三个样本案例中,出具证明的机关分别是作为渔业主管部门的东海渔港监督、海南海事局、连云港海上搜救中心,虽然与《答复》限定的“有关机关范围”不符,但是这些机关出具的证明显然具备很高的可靠性,特别是广州海事法院(2010)广海法特字第 4号案件中,东海渔港监督出具详尽叙述事故发生及搜救经过,完全符合“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其证明效力不容否定。
综上,“有关机关”出具的“证明”在我国实务中明显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状态,既有出具“证明”机关明确、适格,且“证明”详载事故发生经过,凭借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失踪者确无生还可能者,亦有不知“证明”机关为何,且“证明”对意外事故的发生经过语焉不详,令人怀疑“证明”质量者。在此,我们不禁要问:《民事诉讼法》
第185 条无视“证明”质量高下之别,均采取相同的处理方式——公告三个月后做出宣告死亡判决的规定是否妥当?在“证明”质量很高的情形下,仍然要求公告三个月是否属多此一举?
三、域外立法例的启示
“太阳底下无新事”,意外事故致人失踪并非我国独有,因此,在对我国法律规定存疑之余,有必要考察域外立法例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一)我国台湾地区
2009 年 8 月 8 日,“莫拉克”台风重创我国台湾南部地区,据台湾当局统计,截至 2010 年1 月 21 日,共造成703 人死亡,23 人失踪。 根据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因特别灾难而失踪者,须待失踪满一年后始得申请宣告死亡。 鉴于该规定难以满足失踪人家属亟待抚恤的迫切需要,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于 2009 年 8 月 27 日制定的“莫拉克台风灾后重建特别条例”(下称“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对于因台风失踪之人,检察机关得依应为继承之人之声请,经详细调查后,有事实足认其确已因灾死亡而未发现其尸体者,核发死亡证明书”。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又于 2010 年 1 月 5 日增订“灾害防救法”第四十七条之一,其中第一款规定:“人民因灾害而失踪时,检察机关得依职权或应为继承之人之声请,经详细调查后,有事实足认其确已因灾死亡而未发现其尸体者,核发死亡证明书”。据此,作为暂行性规定的“莫拉克台风灾后重建特别条例”第二十八条经“灾害防救法”第四十七条之一的增订,遂成为常态性规定。
依传统大陆法,自然人死亡涵盖真实死亡、宣告死亡两种基本类型。真实死亡无论系因何种原因所导致,死者遗体尚在,且有医院或者侦查机关出具相关证明予以确认;宣告死亡则系针对长期生死不明之失踪者而专设的制度,因“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故须经由司法程序予以推定。前述我国台湾地区“条例”第二十八条、“灾害防救法”第四十七条之一所规定之死亡类型虽以失踪人为规范对象,却无需经由宣告死亡程序加以推定,而是由检察机关进行详细调查,只要“有事实足认其确已因灾死亡”即可核发死亡证明,从而具有与宣告死亡相同的法律效果。易言之,尽管自然人因灾失踪,然而检察机关虽经调查而不足以认定该失踪人确已死亡的,则不能适用前述规定,仍须适用“民法”关于宣告死亡的规定。以此论之,我国台湾地区“条例”第二十八条、“灾害防救法”第四十七条之一实际上是在真实死亡、宣告死亡之外规定了自然人死亡的第三种类型,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将之称为“推定真实死亡”。
(二)瑞士民法典
《瑞士民法典》第三十四条规定:“失踪的人,只要在使他人对其死亡确信无疑的情况下失踪,即使未发现其尸体,亦视其死亡已得证实。”该条文规定于《瑞士民法典》第一编“人法”之第一章“自然人”之第一节“自然人的权利义务”中,在其之前,第三十一条的标题是“自然人权利能力的开始与终止”,第三十二条的标题是“生存、出生及死亡的证据”,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一起被置于“提供证据的方法”标题下,第三十五条至第三十八条则系关于宣告死亡的相关规定。由此可见,关于自然人权利能力终止事由,《瑞士民法典》区分为三种类型:真实死亡、宣告死亡及“证实死亡”。考诸第三十四条与第三十五条以下关于宣告死亡的规定,可以发现“证实死亡”与宣告死亡虽然都适用于失踪者“生不见人、活不见尸”的情形,但是二者的区分界线亦“泾渭分明”:既然宣告死亡是一种推定事实,那么失踪人死亡就是一种“高度盖然性”的死亡,连接失踪之基础事实与宣告死亡之间的“桥梁”是经验法则,即根据生活经验、一般常识,失踪人在此情境下死亡的概率非常高。“证实死亡”则并非是一项推定事实,《瑞士民法典》第三十四条要求其必须是“确信无疑”的死亡,即虽然未能发现失踪人的尸体,但是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认定其已经死亡,几乎可以完全排除失踪人生存的可能性。
瑞士联邦法院对适用“证实死亡”条款限定了非常严苛的条件,一是失踪的方式,只有在因为失踪人失踪的方式将使其生命遭受重大危险,而且失踪人已经证据确凿地遭受到这个必然使其丧生的事件。二是亲眼目击或有具体依据可证该具体状况发生,例如失踪人在目击证人眼前坠入冰河裂缝中,在第三人亲眼目睹的坠机事件中,或者在其他旅客目击之下,沉入海中。可以说,失踪方式的危险性是适用“证实死亡”条款的前提性要件,遭遇该危险的确定性是适用“证实死亡”条款的关键性要件,如果失踪人非因致命性事故而失踪或者欠缺亲眼目睹其遭遇该致命性事故的目击者,均不能适用“证实死亡”条款,而应适用宣告死亡制度。
例如,对于全体乘客因船舶在公海上沉没、飞机在寂无人烟处坠毁而失踪的情形,由于没有目击者亲眼目睹事故发生经过,所以尽管失踪方式足以致命,但是却因直接证据的缺失而无法适用“证实死亡”条款,而应适用宣告死亡程序。
概括我国台湾地区以及瑞士立法例可以发现,自然人死亡除真实死亡、宣告死亡之外,尚存在第三种死亡类型——“证实死亡”。“证实死亡”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85 条规定之凭“有关机关证明”而判决宣告死亡既有一定的相似度,亦有定性上的巨大差异:相同者,均须法院之外的相应机关就意外事故发生情况进行调查并出具证明性文件;不同者,主要在于此类“证明”的效力如何,在我国现行法中,其不具有直接认定自然人死亡的效力,仅仅是一种法院做出宣告死亡判决的前置程序。在我国台湾及瑞士法中,符合特定要求的“证明”则可以取代宣告死亡判决,具有直接认定自然人死亡的法律效力。显然,我国台湾及瑞士法的处理模式具有便捷性特征,有利于迅速结束失踪人法律关系的不确定状态,从而成为破解前述我国现行法窘境可资借鉴的立法模式。
四、“证实死亡”检讨与立法建议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85 条的规定虽然未尽科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完全照搬我国台湾地区及瑞士的法律规定,而应本着扬弃的态度吸收合理内核,摒弃不合法理及我国法制实际的内容。
(一)“证实死亡”定性再审视
我国台湾“条例”第 28 条、“灾害防救法”第 47 条之一是以“未发现尸体”之“证实死亡”为规范对象,从而与宣告死亡程序分庭抗礼,互不统属。基于此,上列条文中均未规定失踪期间、公示催告程序等宣告死亡的要件。然而,尽管“证实死亡”是一种趋近真实死亡的状态,但是由于尚未发现失踪者尸体,从而终究与真实死亡有别,难免出现“真实死亡”时间与“证实死亡”时间不同或者出现已经被“证实死亡”的失踪者生还的情形,因而有撤销该不正确的死亡证明书之必要,进而须准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640 条撤销宣告死亡判决程序。尽管如此,但“证实死亡”与宣告死亡在法律体系中的定位毕竟有别,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台湾地区“灾害防救法”第47 条中“经详细调查后,有事实足认其确已因灾死亡”之规定参考《瑞士民法典》第 34 条进行从严解释:一是“失踪之方式”足以致命;二是“有人亲眼目击或有具体依据可证该足以致使失踪人死亡之状况发生”。如此,方有减少“民法”第640 条之适用几率,从而在降低失踪人法律关系变动可能性的同时,维护法律的安定性与稳定性,亦使得能够在法律技术层面区分“证实死亡”、宣告死亡成为可能。据此,我国法律如规定“证实死亡”类型,也应充分借鉴瑞士司法实务经验,以提高失踪人死亡的确定性为导向,对相关要件进行目的限缩性解释。
(二)调查失踪事实的机关
适用“证实死亡”程序,我国台湾地区及瑞士均由检察机关根据失踪人家属的申请调查失踪事实,然后依据是否符合“证实死亡”的要件进行处理:符合要件者,核发死亡证明书;不符合要件者,失踪人家属须依照宣告死亡程序向法院申请宣告失踪人死亡。根据我国《检察院组织法》第 5 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对于由其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这些案件主要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的刑事犯罪案件。以此观之,由检察机关负责调查失踪人因意外事故导致的失踪在现行法律体系中缺乏法律依据。根据我国《警察法》第6 条的规定,公安机关的职权范围包括侦查犯罪、治安管理、户籍管理等,因此,自然人因意外事故失踪的,由公安机关负责调查失踪事实既有较为充分的法律依据,而且公安机关亦有能力、有经验实施相关调查。此外,意外事故发生后,灾害救助部门往往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实施救助,此类机关对于灾害事故的发生、自然人失踪情况掌握有第一手资料,因此,特定情形下,救助机关亦可作为调查失踪事实的机关。正如前文所引用广州海事法院(2010)广海法特字第 4 号案件中,由东海渔港监督出具的详尽载明事故发生及失踪、搜救经过的证明材料即是此类证明的典范。除公安机关、灾害救助机关之外,《答复》第二条所规定的“县级人民政府”亦可考虑予以保留,据以应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情况。
(三)认定“证实死亡”的机关
根据我国台湾地区“灾害防救法”第 47 条之一第一项之规定,检察机关负责调查失踪事实并核发、撤销死亡证明书。根据台湾地区“法院组织法”第 58 条规定:“各级法院及分院各配置检察署。”第 60 条规定检察官职权:“一、实施侦查、提起公诉、实行公诉、协助自诉、担当自诉及指挥刑事裁判之执行。”我国《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所规定之检察机关职权与台湾地区检察署大体相当,但是二者的法律地位存在显着差异:我国大陆地区的检察机关是与法院、政府并列的法律监督机关;台湾地区的检察机关配置于各级法院,但隶属于“行政院”序列的“法务部”。尽管两岸检察机关均有司法职能,但是该职能主要体现为行使侦查权、公诉权以惩治犯罪、保护人民,而并非人民权利的最终决定者,因此,由检察机关核发、撤销死亡证明书并不妥当。再者,既然“证实死亡”与宣告死亡的规范对象均指向因意外事故而失踪者,那么如果宣告死亡由法院决定,“证实死亡”由检察机关决定显然亦于理不合,甚至有可能因“政出多门”造成法律适用上的相互抵触,损害司法公信。基于此,“证实死亡”也应当由法院做出判决较为适当。
五、结语
《民事诉讼法》第 185 条规定的“经有关机关证明”的宣告死亡类型,其立法本意在于迅速稳定失踪者的法律关系,但是在法律逻辑上却经不起推敲:毫不考虑“有关机关证明”是否足证失踪者确实已经无生存可能,均要求公告三个月,立法技术稍嫌粗糙。
而且,诚如前文所做之实证考察,部分案例中的“有关机关证明”含混不清,以其取代两年的失踪期间要件并将公告期从一年缩短至三个月,难免导致《民事诉讼法》第 184 条存在内在逻辑上的冲突。鉴于此,我国法律应当参考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及瑞士立法例,引入自然人“证实死亡”,将之界定为一种与真实死亡、宣告死亡并列的死亡类型,不仅有利于改善我国现行法本身的逻辑自足性,而且有利于迅速稳定失踪人的法律关系,从而避免前述汶川地震发生之际,保险机构在面对失踪者迫切需要之际所面临的的法律适用上的尴尬局面。
第四章我国民事证据契约制度的现状考察我国实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所以法院在诉讼中无论是对证据的调查收集还是审查判断都拥有绝对的权力。法院可以根据庭审进程决定是否调取某项证据、是否要求某位证人出庭作证、是否认定某项证据的证明力、是否采信当事...
第三章我国司法拍卖方式的实证分析针对司法拍卖领域呈现出的种种问题,各地法院开始了一系列创新和改革。在这场改革浪潮中,形成了最有代表性的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最为保守的上海公共资源拍卖中心模式,依旧采用委托拍卖的方式,将司法拍卖放置于公共资源...
第二节自行拍卖方式的实证分析。一、浙江网络司法拍卖模式:法院-淘宝网。(一)网络自行拍卖模式概况。面对传统司法拍卖的弊端,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启动了新的改革部署,将司法拍卖推向互联网平台。2012年1月,浙江省高院和淘宝网联合推出了网络司法...
一、知识产权诉前证据保全概述知识产权领域所讲的诉前临时措施是指知识产权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知识产权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或者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