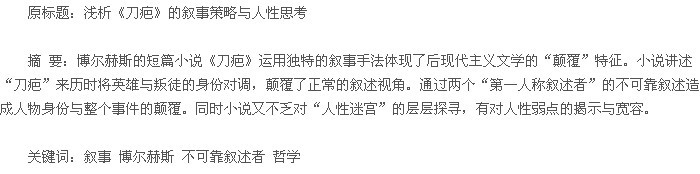
一、叙事角色的颠倒
《刀疤》收录于 1944 出版的博尔赫斯小说集 《虚构录》集中,它不是博氏创作中“玄之又玄”的“迷宫建筑”。 小说篇幅短小,情节简单,故事本身也并不惊心动魄,但“颠覆”性的叙事方式却令读者耳目一新。
小说出现了两个第一人称叙述者。 先由“我”(博尔赫斯)叙述了神秘“英国人”的一些事情,文中用了“我听说”、“据说”、不少人说”这样的字眼 ,点明叙述者“我”之前关于“英国人”的了解来自道听途说,而“我”其实是不可靠的叙述者。 随后,这个“英国人”又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他在早期革命生涯里被人出卖、愤恨之下用军刀在那个叛徒脸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刀疤的故事,先前的叙述者“我”变成叙述接受者。而“英国人”同样进行着不可靠叙述,在“英国人”的讲述中,他是作为被同伴出卖的英雄身份出现的,而最终揭示的谜底却是———其实他才是那个为人所不齿、被人留下刀疤的懦夫。 从叙事修辞角度来看,文本完成了两个不同层次的叙述, 讲述就包含了叙事者的讲述,通过这两个不可靠叙述者的叙述,小说最终达到了修辞目的。 由于叙述进行了身份对调,颠覆了正常的叙述视角, 叙述接受者和读者不清楚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当读者正要为英雄惨遭叛徒出卖而惋惜时,他公开自己的身份,并坦言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你能从头听到尾”。正揭示了叙述者的叙述意图,而叙述接受者的直接引述也进一步揭示了作者的叙述意图。 这样,两个不可靠的叙述者的叙述使小说的结局出乎意料。
叙述接受者(the narratee)一词由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普兰斯提出。 叙述接受者是指与叙述者对话的人。叙述接受者与读者不同,他是叙述者的听众,同时也是叙事的参与者,有时也作为人物出现。 虽然作为文本一部分,叙述接受者的能力、活动范围甚至对叙述者话语的理解都是有限的,但在故事中,他是叙述者与读者的中介,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左右读者的认知。故事中的叙述接受者在听刀疤来历时已经领教了叙述者的叙述策略,而在引述时也采用了同样的叙述策略。“英国人”讲述刀疤来历时担心听者先知道真相会产生抵触情绪,从而影响讲述的预期效果,因此,他把叛徒的身份置换成被自己出卖的英雄。叙述者一直以“我”的第一人称进行叙述,使人毫不怀疑“英国人”就是那个被穆恩出卖的勇士。叙述接受者完全接受了他的叙述意图,他的叙述也自然不会引起读者对其身份和所述故事真实性的怀疑。但当他叙述到“我”用军刀在穆恩脸上划了一个弧时, 读者隐约觉得有点不妙,意会到已经进入博尔赫斯叙述圈套。 但作为叙述接受者来说,虽然看到叙述者的情绪很激动,可他仍坚信眼前这个叙述者就是那个被叛徒出卖的英雄,所以不停追问叛徒穆恩的下落。 当真相大白时,读者才放心地相信背叛组织、出卖同志的胆小鬼就是“英国人”的事实。
反观作为叛徒本人在叙述自己这段罪孽时的陈述,我们不难发现叙述者对穆恩的描写处处存在着不屑,他借用因他告密而死去的同伴的口吻,深刻地描绘了出卖灵魂者内心的忏悔与不安。比如:“他年纪不到二十岁,又瘦小又窝囊,像无脊椎动物(invertebrado)似的叫人看了不舒服。 ” 一个卖友偷生的人当然是没有骨气的(invertebrado adj.没有骨气的)。 “穆恩的右肩给一颗子弹擦过,我们逃进小松林时,他竟然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我明白他已经怯懦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我那位十分理智的朋友正在十分理智地出卖我”。这些描写都体现出了农场主悔恨至极的心情。
叙述者的那种对自己所犯罪行的厌倦和悔恨以一种自我否定的极端形式表现得淋漓尽致。
也有人认为这种调换身份的叙述恰恰更加说明穆斯的怯懦和不敢担当。通过让叙述接受者直接引述的叙述策略,作者成功将叛徒穆斯的丑恶嘴脸展露无遗。证据也是他那些对自己怯懦本性的表现进行了细腻的描写,在叙述中为穆恩因胆小怕死而选择投敌叛变的行为开罪,其实是在为自己狡辩,这再一次暴露了他卑劣的人性。 当然,我认为博尔赫斯并不是简单地教我们去憎恨或是同情穆恩这个人,对于这个开放性的文本,任何人都可以有他合理的见解,这就是大师之作。
二、作品中隐含的哲学思辨色彩
博尔赫斯说过,他写的故事“旨在给人以消遣和感动,不在醒世劝化”(《布罗迪报告》序言),但他的作品几乎都完成了探讨命运的使命。《刀疤》的叙事策略无疑是小说的最大亮点,然而并不乏“人性”叙事。
这里所说的人性,并不是简单的善恶美丑或是人的各种感情, 更包括了隐藏在人的行为中的种种动机。 穆恩脸上的那道刀疤不仅引起了读者的注意,更引起了故事里的人物的兴趣。 在故事开头,他竟用讲述刀疤的来由作为附加条件,顺利地向卡多索买下了他本不想出售的那片农场———好奇心实在是人性中的一个大弱点。卡多索的好奇心让他心甘情愿地将农场卖给“英国人”,“博尔赫斯”的好奇心使得农场主向他讲述了刀疤的秘密。
博尔赫斯的作品中处处体现了他对时间循环往复的无限性、自我与他人(镜子)等哲学问题的探讨。
叔本华可以算是对博尔赫斯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在“英国人”的叙述中,当怯懦的穆恩令其产生了 “好像胆小鬼是我,不是穆恩”的感觉时,他对这种现象和心理的产生进行了一次哲学上的思索。作者借主人公约翰·文森特之口提到了叔本华的一句话:“我即他人,人皆众生。 ” 博尔赫斯认为这句话很有道理,并作了引申:“从某种意义上说,莎士比亚就是那个可悲的约翰·文森特·穆恩。 ”虽然他们并不具有可比性,但在向他人讲故事的这段时间里,他们是一样的,是可以互换的。于是,批判的境界顿时得到升华。既然人性的弱点是普遍的和共通的, 既然犯错是人类共同的可能,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说,不可以承担的呢? 这也许就是忏悔者愿意向“我”讲述往事,并勇于接受听者蔑视的原因。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穆恩的忏悔是代表人类在向上帝忏悔。 多少年来,这个当年的犹大带着横贯脸上的伤疤,走过了多么艰难曲折的心路历程,是可想而知的。 毫无疑问,他已经严厉地惩罚了自己,拯救了自己,也超越了自己;而采用叙述圈套叙述不光彩往事的做法,让当年的胆小鬼变成了一个勇者,同时也让人理解了这个与雇工一起改造世界的农场主的今天:“严厉到了残忍的地步,不过办事十分公道。”
尽管这种哲学思辨受文章篇幅所限而不能够继续深入,但是类似这些思辨色彩的闪耀使博尔赫斯的作品充满了灵性,它提醒我们所面对着的是一个“作家的作家”。
正如博尔赫斯在一篇小说中写道:“我们在此地睡觉的时候,我们在彼地醒着,因此,每一个人都是两个人。”这一点,在博尔赫斯的众多作品中都以“镜子”这种意向来体现。
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两个博尔赫斯。 他曾经有这样的话:“ 在幸福和不幸的极端, 我能感受到———仅仅在一瞬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也发生在和我无关系的另一个人身上。”在《刀疤》这篇作品里,博尔赫斯既是他想成为的坚定的革命者,同时又是带有严重人性缺憾、一生陷入黑洞不能自拔的叛徒。 在革命者和叛徒之间, 他对后者有着更为熟悉的一份贴近,因为胆怯是人性自身的弱点,它是一种恍惚间难以把握的情绪。 承认它的恍惚,即意味着承认人性的完整和真实。 只要生命没有结束,人性就永远处于不确定的时刻。
小说《刀疤》中匠心独运的叙事策略是其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不可靠的叙述在给人“新奇”感的同时也促使读者深刻体会人物身份对调后的叙述所产生的独特艺术效果, 进一步理解小说中关于人性的主题,通过塑造两个不可靠的叙述者,“叛徒”的复杂人性特质得以充分体现。 至于对穆恩是憎恶、同情或者原谅,读者心中自有承载。
参考文献
[1] 博尔赫斯小说集[M].王永年,陈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
[2]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谈话录[M].王永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3] 叔本华论说文集[M].范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作为戏剧史上最着名的荒诞派剧作,《等待戈多》自1953年首演以来,被人们多次搬上荧幕。荧幕上的《等待戈多》大多数都是忠实于原剧作,无删减的。...
关于《坟墓里的旗帜》①,至少有两件事广为人知。其一,这是一部年轻的艺术家非常想籍此扬名立万却到处碰壁投之无门的长篇。他于1927年9月29日完成该小说的创作,并信心十足地将书稿交给他前两部小说的出版商利弗赖特(Liverright)。在给后者的信中,...
叙事学家申丹在其论着《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中指出:任何一位作家创作小说并出版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听众并传递其意识以至建立影响,每一位发表小说的作家都想使自己的作品对读者具有权威性,都想在一定范围内对那些被作品所争取来的读者群体产生权...
探讨夏洛蒂·勃朗特“为何要”使用月亮意象的心理价值原因,以及“为何能”使用月亮意象的文化传统因素。...
一、引言安吉拉卡特(19401992)以独特的写作风格驰名英语文坛,其写作风格混杂了魔幻写实、哥特式与女性主义。2006年众多女性读者在英国掀起一股卡特作品回顾热潮。在两年后的《泰晤士报》战后50位英国最伟大作家评选中,安吉拉卡特位居第十。《马戏团...
叙事视角在当代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作为一种研究角度, 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将作品的分析带入了更加广阔的视野。本文以叙事视角的方式对美国当代作家唐·德里罗的《白噪音》进行的分析呈现出该作品的艺术特征与表达效果。...
叙事视角是把叙述者对故事的感知经验局限于某一个局部主体意识,从而把整个叙述置于这个局部主体意识的能力范围之内。从宏观意义上,叙述视角可以分为两大类:全知视角和有限叙述视角。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创造性地将两者相结合,用多种叙述手法,在不...
一、引言对于叙事修辞的研究有两大重要分支,一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一是新亚里士多德学派或称芝加哥学派的批评,后者研究形式与情绪影响之间的关系,其代表人物韦恩布思认为叙事作品是一种修辞行为,需要关注作者、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他对叙事作品...
乔纳森萨福兰弗尔(JonathanSafranFoer,1970-)是美国中间代代表作家。其小说《特别响,非常近》(ExtremelyLoudandIncrediblyClose,2005)不仅揭示遭受恐怖袭击后普通美国人的创伤记忆、心理承受和救赎轨迹,而且反思生命意义、深度观照历史并使...
《圣经》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被视为西方的精神文明支柱、社会伦理观的基石.长期以来,其深刻的社会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除了作为宗教教义以外,其内容的文学性也被许多学者作以人文解读.将圣经作为文学着作意味着暂时无视其宗教经典性质,回避其神学意识形态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