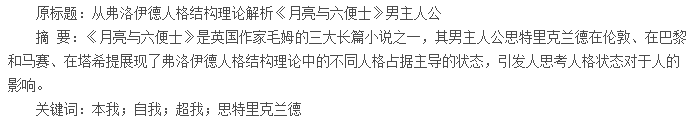
《月亮与六便士》是毛姆于 1919 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为了追求艺术而放弃优渥的生活,由伦敦一个证券交易所的股票经纪人出走为一名流浪的画者,最终定居于塔希提,并创作出不朽画作的故事。本文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出发,分析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为追求艺术所经历的三个阶段,探究其人格发展过程。
一、在伦敦的证券经纪人——自我占据主导地位
自我遵循现实原则,它是理智而谨慎的,让人遵照社会的法则行事,引导着人避开会碰触社会准则的事,它让个体的人成为社会所要求的“正常人”。此外,“自我企图用外部世界的影响对本我和它的趋向施加压力,努力用现实原则代替在本我中自由地占支配地位的快乐原则”[1]213,自我为遵循社会的法则而对本我施加压力,努力压制本我的欲望,让人符合社会的规范而不至于成为异类。当思特里克兰德还是证券经纪人时,他的人格是由自我主导的,本我被自我压抑着。没人看得出来,他对绘画有那样执着的追求,也没人能想到他身上具有那么大的艺术创造力,其妻对他的评价是“他不太爱说话,对文学艺术一点儿也不感兴趣”[2]27。而作为叙事者的“我”也丝毫看不出他身上有什么奇特之处,“我”甚至连他这一生都预料好了,“我”想象着他们夫妇二人体面地生活,不受到任何灾祸的干扰,等他们年老时,依然富足安详,最终寿终正寝,安乐地走完一生。从旁观者的视角,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思特里克兰德遵循着现实社会的准则,按照社会的轨迹在活动,在大多数人眼中,他是一个平庸无奇的人,他既不显得狂放不羁、遭人唾弃,也不显得高尚无私、令人敬仰。他的本我被压抑,超我也并不凸显。
在这一时期,思特里克兰德的本我虽被自我压抑,但自我在屈服现实的基础上还是曲折地满足了本我。“它(自我)既以大部分的精力来控制和压抑发自本我的非理性的冲动,又迂回地给予本我以适当的满足,”[3]虽然思特里克兰德不得不赚钱养家,但是他在持续一年的时间里瞒着所有人下班后去学画画,这是自我迂回满足本我的证明,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他的人格是自我占据主导。
二、在巴黎、马赛的流浪画者——本我占据主导地位
“自我首要地是一种躯体自我。”[1]216弗洛伊德认为自我之所以由部分本我发展而来,最首要的原因是受到知觉系统的影响。人的躯体是一种现实生活中的存在状态,人处于社会现实中,必然不能脱离躯体而活动,人类的心理活动也植根于躯体之中,正是脱离不了社会需求的躯体使得本我对社会现实作出妥协,从而发展出了自我。而已经在巴黎呆了一段时间的思特里克兰德压根不在意除了画画之外的事情,躯体的欲望给他带来的只有厌烦。
当“我”刚到巴黎去找他时,他住在巴黎肮脏的小旅馆里,整个人不修边幅,对于食物也没有太大的需求,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衣食住行对他而言根本无关紧要,他只要能画画即可。他整个身心都让绘画的欲望所驱使。可见自我在思特里克兰德的人格结构中,已不再占有主要地位。弗洛伊德将本我比喻成“一口充满了沸腾着兴奋剂的大锅”[4]65,这口大锅充满了来自本能的能量,它没有组织来管理,当然也没有共同的意志来主宰,它混杂着欲望,遵循快乐原则,只管感情用事。而此时的思特里克兰德正是受本我的控制,本我中的欲望在他的体内叫嚣着要得到满足、获得释放,终于使得看似平庸的他抛妻弃子、远走他乡,打破了自我的掌控。“我怀疑是否在他的灵魂中深深埋藏着某种创作的欲望,这种欲望尽管为他的生活环境所掩盖,却一直在毫不留情地膨胀壮大,正像肿瘤在有机组织中不断长大一样,直到最后完全把他控制住,逼得他必须采取行动,毫无反抗能力。”[2]78荣格将这种不由自主的创作命名为“自主情结”,他认为有些艺术家的创作欲望十分迫切,以至于这种欲望会贪婪地吞噬他们的人性,驱使他们去创造,即使牺牲了身体健康,破坏了普通人该有的幸福也无所畏惧。思特里克兰德的创作欲望如此强烈,他只想去追逐它、满足它,随着自己的本能去释放它,而不管它会不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灾难,他完全为这种欲望所掌控。
弗洛伊德用骑手和马的关系来比喻自我和本我之间的关联,“马提供运动能量,而骑手具有决定目标和引导这个强健动物的活动的特权。但在自我和本我之间,却常出现不理想的情形:骑手被迫引导马在马自己想走的路上奔驰”[4]69,思特里克兰德的自我与本我正处于这种不理想的状态。在通常情况下,本我、自我和超我应该协调一致。自我力图在本我、超我以及现实世界中维持平衡。而本我是混沌的,它不知晓价值判断,同样也没有善恶,更无所谓道德,本我代表的是一种放纵的激情。思特里克兰德被本我支配,他根本不在乎是非对错,他的一切所为都是随心所欲。他想绘画,便毫不在意其它,终于导致躯体的自我对他进行了报复,他病倒了。然而他的这次生病没有给自己带来不幸,却给别人的家庭带来了灭顶般的灾难。“我”的朋友,巴黎的一位画家施特略夫,虽然画技一般、画作庸俗,可却拥有极高的艺术鉴别力,并且为人热诚、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宽容大度。施特略夫看出了思特里克兰德的绘画才能,知道他的困境,热心地将他的画推荐给画商,可思特里克兰德对施特略夫却十分粗暴。甚至当施特略夫愿将家里的画室与他共用时,他却粗鲁地将施特略夫推出去,独占了画室。由于肉欲和创作欲望的驱使,思特里克兰德还占有了施特略夫的妻子勃朗什,且在利用完勃朗什做人体模特完成画作后,又无情地抛弃她,使得她吞草酸自杀而他对此却无动于衷,即使在勃朗什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没有探望过她。对施特略夫的痛苦他更是无所谓,甚至还以一种鄙夷的态度去看待。一个家庭就这样被他随心所欲地践踏,一个生命就这样被他无情地摧毁。而发生这一切的缘由,都只不过是他的一时兴起。本我的力量在他身上如此明显地凸显出来。他遵从着本性中的肉欲,丝毫不顾及旁人的感受,放纵欲望所造成的后果他根本不关心,只管自己发泄。在马赛时,他依旧我行我素,他的本我在他的人格结构中仍然占主导地位。
然而思特里克兰德毕竟生活在文明社会中,他对自我的控制力虽然松懈了,不能管制好本我,但当本我不去叫嚣着寻求满足的时候,自我仍发挥着它的最大功用,努力做到它所代表的理性与常识。
他在巴黎钱用光了的时候做过向导,找过一个翻译卖药广告的工作,甚至还当过油漆工。在马赛穷困潦倒时,他也只能为了食物和住宿问题到处奔波。因此,这一时期本我在思特里克兰德的人格中占据主导,然而他的自我并没有丧失,仍发挥着作用。
三、在塔希提的画家——超我占据主导地位
“通过理想形成,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理生活的最低级部分的东西发生改变,根据我们的价值尺度变为人类心理的最高级部分的东西”[1]228。在巴黎与思特里克兰德的一次谈话中,“我”透过思特里克兰德的手势和支离破碎的语言理解到他对于在一个理想世界绘画的渴望。他希望置身在一座被大海环绕的小岛中的幽谷里,深思并画出他一直追逐的东西。最终思特里克兰德美梦成真,塔希提成了他的理想之所,他也真的在这里创作出了不朽的作品。原先单纯的创作欲望转化成了超我中那包含着人类崇高意义的理想,在对理想的不懈追求中,思特里克兰德完成了不朽画作,且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可见,在塔希提、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他的人格是超我占据主导的。
虽然思特里克兰德在塔希提成了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但他并没有如弗洛伊德人格结构中的超我所应该表现的那样正直善良、乐于奉献。他只顾自己画画,而让妻子爱塔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同时还要满足他那突如其来的情欲。就常人看来,爱塔简直就是他赖以生存的机器和泄欲工具。此外,在完成那幅充满了人类原始生命力量的壁画,弥留之际的思特里克兰德竟然要求爱塔在他死后烧掉画作,而这仅仅是因为他已追逐到了自己一直想要得到的作品,他毫不顾及这幅巨制对整个人类艺术创造的价值。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超我该是无私的、崇高的。思特里克兰德追求理想、为了理想而经受了许多艰辛,他的超我此时是凸显的,可从他对于爱塔和画作的态度来看,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他依旧是一个自私、简单、粗暴的人,而这样矛盾的局面和毛姆对人性的理解及毛姆的自由观、人生观密不可分。毛姆认为人性是多样的,他在《决定论与唯我论》一文中称:“不过,康德的那句格言,我却不大能接受。他说,人的行为必须遵循一种普遍律令。我是坚信人性的多样性的,因此不能相信他的这一要求是合理的。”[5]
在《月亮与六便士》中他借助“我”之口说道:“我那时候还不了解人性多么矛盾,我不知道真挚中含有多少做作,高尚中蕴藏着多少卑鄙,或者,即使在邪恶里也找的到美德。”[2]56-57
可见,毛姆对人性的至善至美是持否定的观点的,他质疑绝对的恶,也怀疑绝对的善,在他看来,人是复杂的。因而在塑造思特里克兰德这一人物时,他虽然把思特里克兰德的艺术追求之旅描写地十分艰辛不易,可却并没有将思特里克兰德塑造成一个逆境中奋进的英雄伟人形象,只是直白地把他写成一个追求伟大艺术的恶棍。此外,毛姆崇尚自由,认为世俗标准会限制人的发展,将人变为社会规则的奴隶,只有摆脱尘俗的牢笼,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正因如此,毛姆笔下的思特里克兰德才那么不注重物质生活,家庭、情欲都是他的负担,他肆无忌惮地去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拥有绝对的自由,他人的死活与他却毫不相关;也正是由此,远离资本主义文明世界来到塔希提这一原始文明之地的他才实现自己的理想。思特里克兰德在塔希提时人格中超我的外部表现和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超我的阐释之所以存在落差,很大程度上都与毛姆的自由观和生存观有关。
四、结语
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纵观思特里克兰德的一生,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在伦敦时,他像大多数人一样遵循社会规则做人、做事,自我在其人格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巴黎和马赛,他自私自利、粗野残暴、我行我素、任意放纵欲望,这一时期他的人格是本我占据主导地位;而到了塔希提,爱塔为他提供了一个安身之所,他可以自由绘画并且将塔希提作为创作的灵感之源,最终,他的超我获得了发挥,创作出了伟大画作。
当然,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本身也有不合理之处,如将人与社会二者的矛盾看作是不可调和的,社会只是为了要压制人的本能而存在的,而人只有完全摆脱社会的束缚和限制,才可获得自由并实现自身欲望。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人格状态都是自我占据主导,人无法脱离社会去生活。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人们很难做到为了追求理想而抛开一切,就如曾经原始文明的塔希提也早就成为工业文明国家,成为现今的旅游胜地。但人们依旧可以在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平衡状态下去追求个性的解放,这是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解析《月亮与六便士》男主人公带给现代人的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1] 弗洛伊德. 自我与本我[M]. 林尘, 等, 译. 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11.
[2] 毛姆. 月亮与六便士[M]. 傅惟慈, 译. 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09.
[3] 车文博. 弗洛伊德文集[M].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4:108.
[4]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论[M]. 郭本禹,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5] 毛姆. 毛姆读书随笔[M]. 刘文荣,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9: 41.
观察到现代社会金钱至上、欲望泛滥以及科技进步造成的人的主体性削弱的影响,不少作家热衷于表现一群游离在梦幻与现实之间的边缘人。将毛姆《月亮和六便士》中的思特里克兰德同索尔贝娄《雨王亨德森》的同名主人公进行对照,显而易见的是二者作为现代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