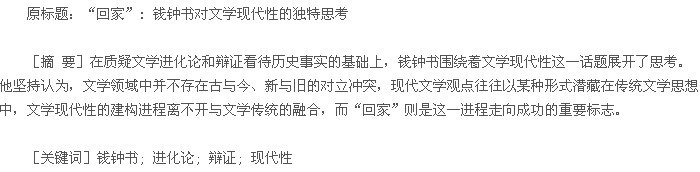
在《说“回家”》一文中,钱钟书对“回家”这一比喻的中西文化意蕴进行了深入发掘。在他看来,“中西比喻的相同,并非偶然……它表示出人类思想和推理时一种实在的境界”。这种“实在的境界”主要表现为“回复原来”: “所谓回复原来,只指心的情境而说,心的内容经过这番考索,添了一个新观念,当然比原来丰富了些。但是我们千辛万苦的新发现,常常给我们一种似曾相识,旧物重逢的印象。我们发现了以后,忍不住惊叹说‘原来不过如此!’”
细观《谈艺录》等论著不难发现,“回家”作为“一种实在的境界”,不仅昭示钱钟书对人类思想和推理惯常状态的理解,而且可以用来比喻其对文学现代性的思考: 现代文学话语与传统文学思想并不是格格不入的,前者完全可以从后者那里找到“回家”的感觉,这正是文学现代性建构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关于文学进化论
新文化运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关于文学现代性的讨论一直同对文学进化论的关注如影随形。所以,在对文学现代性进行思考的过程中,钱钟书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文学进化论。
在《谈艺录》中,钱钟书将清代学者焦循和法国学者伯吕纳吉埃尔关于文体递变的言论并置一处展开平行比较,在对二人观点的批驳中表达对文学进化论的质疑。焦循认为,随着音乐要素的淡出,诗走上了一条渐趋衰微的道路,“诗亡于宋而遁于词,词亡于元而遁于曲”。按照这种思路,词的兴盛是以诗的消亡为前提的,曲的兴盛是以词的消亡为代价的。在钱钟书看来,焦循的观点与伯吕纳吉埃尔所主张的“推陈出新”的“文体演变论”颇为类似。但二者都违背了显而易见的文学史事实: “夫文体递变,非必如物体之有新陈代谢,后继则须前仆。”
譬如,唐代古文大盛,但是风行于六朝的骈文并未因此断绝,而是“一线绵延……而忽盛于清; 骈散并峙,各放光明……”不同时代滋生的文体完全可以同时并存、交相辉映,文学领域中原本就不存在古与今、新与旧之间的冲突。
如此,钱钟书虽然没有对文学进化论的缺陷进行专门论述,但文学进化论赖以成立的基础已经在他的寥寥数语间轰然倒塌。
钱钟书对文学进化论的缺陷论述得最集中的作品,当属其批驳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的《论复古》一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的撰写过程中,郭绍虞始终保持着洞悉历史前进目标、明了历史演变规律的智者姿态,将魏晋南北朝的纯文学观念尊为代表文学发展方向的“‘正确’的观念”,而将唐宋儒者的复古主张视为进步文学观念的对立面加以批判,认为其在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历程中属于一种“逆流”和倒退。对于郭绍虞以历史进化论审视文学批评史的做法,钱钟书在《论复古》一文中给予了毫不留情的驳斥。在他看来,将历史进化论应用到文学领域是极为不妥的,因为历史进化论属于“事实进化”,指的是由简至繁、由单纯至错综的现实演变过程,而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受制于人丰富微妙的主观心灵世界,其创作、接受和批评都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与“事实进化”不同,“文学进化”包含着事实叙述之外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文学进化”的内涵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 不仅指“后来的文学作品比先起的文学作品内容上来得复杂,结构上来得细密”; 而且指“后来的文学作品比先起的文学作品价值上来得好,能引起更大或更高的美感”。前者属于存在判断,是文学史层面的问题; 后者属于价值判断,是文学批评层面的问题。“这两个意义是要分清楚的”,不能等量齐观,也不具备因果关系。富有文学阅读经验和文学鉴赏力的人都会承认,后出现的内容丰富结构复杂的文学作品并不一定比先出现的内容结构较为简单的文学作品拥有更高的审美价值,“‘后来居上’这句话至少在价值论里是难说的”。譬如,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当然比五代刘昫的《旧唐书·文苑传序》拥有更为精博的内质,“但是在‘外形’的优美上,郭先生也高出于刘昫么? 恐怕郭先生自己就要谦让未遑的”。存在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导致文学进化论在具体操作上的虚妄性。
在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殊性,否定文学进化论可行性的前提下,钱钟书进一步对作为文学进化论基础的历史进化论展开了质疑和反思: “即使退一步专就‘历史事实’而论,对于‘进化’两字也得斟酌。‘进化’包含着目标; 除非我们能确定知道事物所趋向的最后目标,我们不能仓促地把一切转变认为进化。”
确定“事物所趋向的最后目标”是树立进化标准的必要前提,但是,自然现象和历史事实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瞬息不停,“事物所趋向的最后目标”永远无法成为一个恒定的存在,更何况以人类现有的理性能力也实在难以认清自然和文明的最终走向,“即使对天演极抱乐观的生物学家像 Julian Huxley,对文明的进步极抱乐观的史学家像 J. B. Bury 都不敢确定天演的目标”。可见,郭绍虞等人所坚持的历史发展趋向和历史进化标准不过是他们在“无穷尽、难捉摸的历史演变里”,“依照自己的好恶”所生发出来的“个人主义”想象,“无论如何,不能算是历史观”。用郭绍虞所主张的魏晋文学观念来衡量,唐宋的“复古”论自然可以被视为“逆流”或“退化”,但是如果“古典主义翻过身来( 像在现代英国文学中一样) ”,“主张魏晋的文学观念似乎也有被评为‘逆流’的希望”。如此,在钱钟书步步深入的剖析中,历史进化论本身的功利性、主观性和非历史性渐渐暴露出来,以历史进化论为基础的文学进化论亦随之丧失了合理性与合法性。
在抽空文学进化论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基础上,钱钟书更为明确地指出,过去与现在并非格格不入,历史演变本来就是世代相承连绵不断的,更高级、更有意义、更富有美感的文学形态不一定都在历史的前方维度,那些来自过去发展阶段的文学形态在现在和将来还会有存在的价值。要建立起经得住历史考验的现代文学,首先就必须处理好新旧文学之间的衔接关系。
二、对于历史的辩证态度
细加探讨不难发现,钱钟书对文学进化论、历史进化论的批驳同他对历史的辩证态度紧密相关。在1933年发表的《旁观者》一文中,钱钟书明确系统地表述了他对历史的理解。在他看来,历史并不像某些论者所认定的那样,昭示着事实发展的客观进程和必然趋势。
因为历史事实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野蛮的事实; 一是史家的事实。前者是瞬息即逝的原初事件; 后者是诉诸文字的叙述文本。我们今天通过文献记录所看到的历史事实都是史家的事实,所谓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亦是形形色色的史家根据各自认定的是非标准,通过归纳、联想等思维方式和逻辑手段建立起来的因果关系。但实际上,历史事件的发生和运行并不会严格遵循这些人为建立的因果关系,一旦历史上出现新的“野蛮事实”时,史家所设定好的客观进程和必然趋势就会受到挑战,历史似乎就成了“淘气捣乱的小孩子”,“给我们的不透风、不漏水的严密理论系统搠上大大小小的窟窿”。这些“大大小小的窟窿”颠覆了史家自以为是的归纳和总结,而且提醒人们应摒弃那种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的线性历史观,转而站在相对主义的立场上,以更加辩证的态度对待形形色色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事件。
具体而言,在钱钟书的理解中,要建立对历史的辩证态度,至少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其一,摒弃后来居上、今是昨非的成见,充分尊重前人的成就。在钱钟书看来,能了解“过去的现在性”亦是历史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面对“过去”,我们不能总是以现时代的标准来衡量它的成败优劣,而应将其置于其所处的具体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和评析: “假使一个古代思想家值得我们的研究,我们应当尊敬他为他的时代的先驱者,而不宜奚落他为我们的时代的落伍者”,任何事物的发生和存在都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只有对来自“过去”的观照对象报以足够的尊重,将其置入其所处的具体历史语境之中进行意义还原,才有可能将其从当代话语的暴政中解放出来,洞悉和理解其本质特征和历史价值。若是将其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就会使其丧失原有的面貌,沦为一种静态的抽象存在。当现时代的观照者怀着后来居上的优越感,以现代眼光对这种静态的抽象存在进行任意阐释和随意剪裁时,他们和“过去”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遥远而陌生,自然也就无法真正了解“过去”的价值和其中所潜藏的“现在性”。
其二,充分注意到历史事实的复杂性和独特性,摒弃以偏概全、因个人的价值取向而任意裁剪和图解历史事实的做法。钱钟书坚持认为,只有在不曲解、不误会历史事实的前提下,才有望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传统,否则就会自说自话,贻笑大方。1932 年,周作人出版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将中国文学史视为载道、言志两大文学流派交替循环、此消彼长的发展过程: “中国文学始终是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起伏者,过去如此,将来也总如此。”
在周作人看来,言志派的思想艺术成就要大大优于载道派,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同明代公安派、竟陵派反对载道、主张言志的文学运动“很有些相像的地方”,一言以蔽之,“新文学的基本观念是‘言志’”。如此,周作人就从历史的层面为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找到了根源和依据,强化新文学发生必然性与合法性。同年,钱钟书撰写书评,对周作人从既定概念出发切割历史事实的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批评史中只有“诗”、“文”、“词”、“曲”等许多零碎的门类,并不存在“文学”这个综合性的概念; 而且,这些门类“分茅设,各有各的规律和使命”,其各自的特征和价值,不能代表文学的总体特征和价值。“文以载道”的“文”,特指“古文”或散文,并不能将其扩展为近现代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周作人将“文”理解为“文学”,无疑是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所谓的“文以载道”,专指的是将古文或散文视为说理的工具。相形之下,作为“‘古文’之余事”的诗词“品类( genre) 较低,目的仅在乎发表主观的感情———‘言志’”。同一个文人作文时专注于“载道”,作诗时却“往往‘抒写性灵’”,“载道”和“言志”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更无所谓两派之分。如此,钱钟书站在丰富可靠的历史事实基础上,通过对“文”、“诗”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博稽详考的分析,指出了“载道”、“言志”二分法的主观性和虚妄性,打破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人为预设的文学发展结构秩序,在客观上为文学史研究开拓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思想空间。
三、关于文学现代性
在质疑否定文学进化论和辩证看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钱钟书对文学现代性提出了既不同于文化激进主义者又有别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见解。如果说文化激进主义者坚持新优旧劣的立场,机械搬运西方文化标尺的做法必然会导致对民族身份建构问题的忽视和回避,使民族文化身份面临着被他者化的危险; 那么,文化保守主义者坚守传统本位,轻视外来思想的心态也势必会影响对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正确评价,从而陷入敝帚自珍的误区。钱钟书对文学现代性的理解,摒弃了在古今之间进行非此即彼选择而造成的扬西抑中或扬中抑西倾向,体现了一种开阔的视野和健全的心态,从而能更全面地把握住了文学现代性的内涵。
在钱钟书看来,所有的历史都有其内在的连续性,“形成现代的因子,早潜伏在过去的时代中”。文学现代性并不是一个凝定的与过去形成鲜明对照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不断解体又不断重建的历史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来自过去的、现在萌生的和有待将来出现的文学思想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正是由于这种联系和作用,才导致了文学现代性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现代文学并不是对传统文学的简单替代,在传统文学面前,现代文学并不具有话语优先权,更不能以断裂的方式对传统文学进行彻底的否定。文学现代性建构是一个与传统文学相互融合、不断更新的过程,推动这一过程的,既有在传统文学基础上有所变异的因素,又有与传统文学保持一致的因素。较之传统文学,现代文学固然有发展、有变化,但更有似变而非变之理。
结合钱钟书对“易”的论述,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体会他对文学现代建构过程中“变”与“不变”的辩证认识。在《管锥编·周易正义·论易之三名》一节中,钱钟书从哲学高度对“易”的内涵进行了阐述,认为“易”一字而兼有“变易”、“不易”、“简易”这些不同的内涵。
尽管“变易”与“不易”之间,“简易”与“不易”之间,存在着意义上的矛盾对立,正所谓“‘变易’与‘不易’、‘简易’,背出分训也”。但是,这些意义最终都会有机地统一在“易”这个富有表现力的哲学范畴之中,正所谓“‘易一名而含三义’者,兼背出与并行之分训而同時合训也”。这种奇妙的统一现象说明了三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呼应、相互转化的神秘关系,在《老子》、《庄子》、《列子》、《前赤壁赋》、古希腊哲学著作、中世纪哲学著作、歌德诗歌等中西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中,处处可见对这一神秘关系的探寻和体认。从这些探寻和体认中,不难看到宇宙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但是,变动之中也有常则。“常”与“变”都是宇宙运动过程中的根本事实。正如“不易”总是与“变易”如影随形一样,现代性的离于传统和归于传统也是相伴相生的。后来在《老子王弼注》一文中,钱钟书又将老子的言论同黑格尔的观点联系在一起,对“离”与“归”的辩证统一作了进一步阐述。老子认为,“反者,道之动 ……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其中的“反”有两个意思:一是“正反”的“反”,指的是“违反”; 二是“往反( 返) ”的“反”,指的是“回反( 返) ( ‘回’亦有逆与还两义,常作还义) ”。《老子》所说的“反”融贯了“违反”和“往反( 返) ”两种意义,“即正、反而合,观‘逝曰远,远曰反’可知……”这一观点与黑格尔在《哲学史》中的见解颇有神似之处: “黑格尔《哲学史》论‘精神’之运展为‘离于己’而即‘归于己’,‘异于己’以‘复 于 己’…… 词 意 甚 类 老 子 之‘逝 曰 远,远 曰反’”。天下事物,原本就是定中有变,变中有定。文学现代性的建构进程也是如此,它一方面会改变传统,另一方面又同传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于现代文学的建构者来说,重要的不是通过强行切断这些联系去赋予现代文学新质,而是善于发现和利用这些联系,通过在可变性和不变性之间维持一种均衡的关系来成功促成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化。
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证明,现代文学思想的诞生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幻觉,它往往是以一定的形式潜藏在传统文学思想中,通过不断地回归传统汲取养料来获得向未来开放的动力,与传统文学的彻底决裂将会导致现代文学失去萌芽和生长的土壤,无法获得长足的进步。就这一意义而言,真正成功的文学革命必然与“复古”紧密相关: “复古本身就是一种革新或革命……若是不顾民族的保守性、历史的连续性,而把一个绝然新异的思想或作风介绍进来,这个革新定不会十分成功。”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传统中的很多要素都具有超时间的永恒价值,追求现代性的文学革命不能以抛弃传统为代价,如果硬性割断与民族传统的脐带联系,文学革命就会成为空中楼阁,而鲜有成功的希望。
以上从三个方面探讨了钱钟书对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钱钟书的思考在客观上为弘扬传统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提供了一种较为合理的依据,但这决不意味着他要无原则地回归和退守传统。
在面对传统时,钱钟书从未流露出唯古是从的怀旧心态; 恰恰相反,他关注传统的深层动力在于如何发展现在和如何完善现代文学思想。林毓生曾说: “一个传统若有很大的转变潜能,在有利的历史适然条件之下,传统的符号及价值系统经过重新的解释与建构,会成为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仍可维持文化的认同。”
钱钟书从传统文学中着力发掘的,就是这种具有“很大的转变潜能”,可以对未来文学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的成分。关于这一点,他在《古典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一文中曾经有过清晰的表述: “古典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过去东西里的现实意义。”
“回家”作为钱钟书对文学现代性的思考方式,并不是对传统文学进行不加辨析的简单重复,而是以一种现代意识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因而体现出一种新质的回归和具有超越性的回归。
[参 考 文 献]
[1]钱钟书. 人生边上的边上[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钱钟书. 谈艺录[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3]钱钟书. 七缀集[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4]周作人.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5]钱钟书. 管锥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6]林毓生. 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一在罗宗强的文学思想史研究中,历史还原是他反复提及的核心理念。这个理念是针对当今古代文学思想史和古代文论研究中某些对古人的过度阐释和不当转化而发的。他反对用现代的理论任意附会、装扮古人,把古人文学思想不当地现代化。在1999年发表于《文艺研究》...
郭绍虞先生在1980年11月5日《人民日报》撰文,他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时我国多民族文艺理论研究现状:较多注意汉民族的理论而较少注意兄弟民族的理论。这种情况,近年来已有所改变兄弟民族的文艺理论也有所发现。但是,总的说来,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不够,还需要有人...
文学评论是运用文学理论现象进行研究,探讨,揭示文学的发展规律,以指导文学创作的实践活动。下面我们就为大家精选几篇关于文学评论论文范文,供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一、引言。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的盛行,给经典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文学经典在不断的平面化、娱乐化和商业化过程中,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崇高的审美价值以及高尚的人文关怀等价值被不断削弱。在这种情况下,经典文学陷入了尴尬的生存境地。然而,大众文...
第1章米勒对文学语言和文本的认识在漫长的中西文论长河中,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围绕文学是什么所进行的思索从未停止过,它一直伴随着人们探索文学意义的脚步前行。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存在,其自身一直散发着神秘而不确定的光彩,这种光彩使得人们很难...
一、文学史如何可能?谈论文学理论的历史,还是要从文学的历史说起。这是一个大问题,需要专门谈,但我想在这里提示一个大意。学界都熟悉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这个说法受一种三分的逻辑所支配:历史=个别;哲...
作为作家的沈从文,用抒情、唯美、自然的笔触,创作了大量引人注目的小说,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作为批评家的沈从文,用平静优美的感悟式的散文化语言表达了他对评论对象的品味。从他的《沫沫集》等一系列批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
学术思辨最终总是要同现实的人生发生关系,这是大多数人认同的道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认定,理论研究的...
近年的文学地理学研究, 已经展示出蓬勃的活力, 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极具发展潜力的学术增长点。但是在其学科归属、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建设尤其理论体系建构等方面还需要进行更为深层的理论探索。...
勒克莱齐奥是法国当代作家,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23岁时出版的第一部小说《诉讼笔录》荣获法国雷诺多文学大奖,至今已经出版包括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和翻译等在内的多体裁作品四十余部。他的作品被译为至少17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