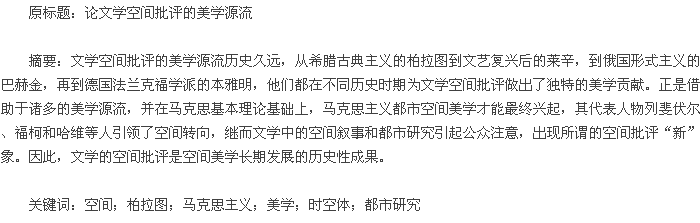
文学中的空间理念来源于人们对空间的审美体验。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始终在空间里展开。古希腊时期,各学派对空间尽管持有不同的甚至彼此矛盾的见解①,但共同的认识基础是把空间视为盛载天地万物的容器,这与中国古人“上下四方为宇”的空间概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1]。与人们对时间的“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审美体验相比,空间“被当做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2],充其量就是盛载四方万物的容器。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全球化进程带来的时空压缩,使现代人对空间产生了新的审美体验,人类认知传统上的线性时间思维范式开始发生变化,更多地让位于立体化的空间思维范式,空间一改既往作为万物容器的隐性存在,开始以显在的强大的实体力量介入现代人的生产、生活和生存经验之维,古老的“空间”被现代人类重新审度体认,这就是“空间转向”。在这一转向的过程中,各种空间理念得到论证与阐释,并被源源不断地运用到文学批评中,形成文学空间批评热潮。从表象上看,文学空间批评是伴随着空间转向发生的审美认知,但事实却有着浮脉千古的美学发展历程,源流久远。厘清美学源流已成为当下文学空间批评研究亟待解决的基础性问题。那么,文学空间批评到底有着怎样的美学源流?
一、文学空间批评的古典美学源流
文学空间批评审美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柏拉图把空间中万物存在的极致原则上升为永恒不变的理念。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认为世界是美的,造物主以永恒不变的理念模型创造出万物生存的宇宙。在柏拉图看来,空间作为存在者和变化者之外的第三者,在世界生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它像真实的存在那样是不会消失的,为万物提供一个场所[3]。存在者就是理念世界,变化者就是现象世界,第三者则是空间。可见,空间在柏拉图这里被视为既不同于感性的现象世界,又不同于抽象的“理念世界”,是既先于这两者又包容了他们的第三者存在域。柏拉图关于“第三者”的思想,可以在后现代空间理论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关于空间的划分[4](39),尤其是索亚(Edward Soja)的“第三空间”里寻求到思想跨越历史遗留下来的蛛丝马迹[5]。另外,柏拉图对美的着名追问,就是力图在空间中通过现象世界的生活美感,达于理念世界的“美的本质”。柏拉图的作为“第三者”的空间在功能上,既为存在者和变化者提供信息交流,又为感性上升到理性构建了通道。作为信息融汇的所在,空间是一个信息混杂和交织的场域,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文学艺术作品同时对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的兼收并蓄。文学艺术作品对美的表现,在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诞生前,一直是在深层次上追求着柏拉图理念世界的本质美。艺术作品对理念世界的本质美的追求,以亚里士多德文学作品可以净化心灵世界的主张为创作目的。但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出现了对审美的逆转,很多时候恰恰以审丑为手段,在创作目的上变亚里士多德的净化心灵为安抚心灵。尤其是在后现代作家看来,文学空间是多元的存在,空间里的“美”与“丑”都是真实的存在,都表现了现代人真实的生活现状或真实可能的未来状态,甚至作品本身就被认为是世界的一部分,因为在尼采的上帝死了、巴特的作者死了和福柯的人之死之后,作品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自在自为性,即作品作为存在物而自在。这样在美和丑彼此独立或交织的多元并置中,印证了迈克·克朗(Mike Crang)所说的文学作品不再是一面反映世界的镜子,而是成为一种“地理景观”[6],由此文学成为一种在惯常的线性时间维度之外的立体的空间维度的存在物。
事实上,经历了古希腊争论不休的时空观之后,文学走过了漫长的以线性时间为主体向度的历史行程。中世纪的欧洲被教会所统治,基督教神学制约着人们的空间观。上帝创造世界,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天堂、人间和地狱构成了文学作品中泛化的空间理念。
英雄史诗、宗教剧和骑士文学作品中的地点只作为情节展开的场所而出现,作品中的空间感相对于时间感确实显得凝固、呆板和稳定。但是,到文艺复兴时期,情形发生了改变。随着哥伦布和麦哲伦在地理上的大发现,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在天文学上的大发现,马丁·路德在宗教上的改革,全面冲击了中世纪以来宗教神学的统治,人们渴望重新接续古希腊罗马的科学与文明,布鲁诺在他的着作《论本原与太一》中宣称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而非宇宙的中心,宇宙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是无限的。文艺复兴时期新的时空观刺激着人类的艺术思维,空间美学获得进一步发展。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被从故纸堆里挖出,16 世纪意大利的卡斯维特罗据此提出戏剧“三整一律”的创作原则,即时间整一律、地点整一律和行动整一律[7]。到了 17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戏剧理论家波瓦洛把其进一步概括为“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充实”的三一律原则[8]。其实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并未提及任何“地点一律”的问题,所以新古典主义的三一律有着极其重要的空间美学意义: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戏剧创作理念中将地点和时间并提。当把地点与时间并置的时候,这个地点就已经超越了作为故事发生的场所的简单意义,而是具有了空间的本体论意义,这预示着故事被置于时空与社会构成的三维视域中展开。人们已经认识到空间对戏剧的结构美具有实质性的作用,这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崭新的空间美学意识。
对文学领域空间美学的反向建构得益于 18 世纪的德国戏剧家和批评家莱辛,他在《拉奥孔》中明确地阐述道:“一切物体不仅在空间中存在,而且也在时间中存在。”[9](182)可见莱辛看待事物的视界是立体的,且就在他立体的视域坐标中,他清晰地标记了文学和造型艺术的具体位置②,他说:“在空间中并列的符号是线条和颜色,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符号是语言。”“绘画用空间中的形体和颜色而诗却用时间中发出的声音。”[9](82)“时间上的先后承续属于诗人的领域,而空间则属于画家的领域。”[9](97)莱辛认为在空间中运用形状和颜色是画家的特长,而在时间中使用声音符号则是作家的特长。因此他反对“诗中表现为描绘狂”及“画中表现为寓意狂”的行为[9](181),即反对不能抓住艺术体裁特长的过于疯狂的跨界行为。莱辛提倡爽朗生动的文学氛围,力求以高扬的真挚的情感激发教育人民,显然新古典主义三一律的刻板教条必须被清除。
为此他首先通过《拉奥孔》辨析“诗”与“画”的界限,明确文学艺术的界限标准,为打造新兴资产阶级的市民剧扫清障碍,为他接下来的《汉堡剧评》奠定理论基础。但是他并不反对文学中有绘画式的场景,也不否认绘画中有文学的表述,他只是反对不能在整体上把握住体裁本身特性的拙劣创作。对于文学空间美学的独特意义是,在莱辛条分缕析的雄辩过程中,文学的空间属性也就在造型艺术空间的对照下,在学理上获得了反向生成。因为辩驳之所以可能,恰说明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诗中确实有画的因素。既然莱辛辨明了画的空间属性,且莱辛本人也承认诗中有画的因素,那么文学自然就有了空间因素,在莱辛与新古典主义诗画一致论派的持续争论中,文学空间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在场的在场式的表达,由此他们的论战亦成为文学空间批评的一部分。
对于文学和艺术的空间批评来说,莱辛的影响深远。20 世纪 50 年代苏珊·朗格(Susan Langer)继续了《拉奥孔》的思想脉络,把文学视为时间性艺术,绘画等视为空间性艺术。在造型艺术的空间研究方面,她区分了生活空间和艺术空间,认为绘画空间“不仅仅是由色彩组成的,还是一种创造的空间”,并把这种创造的艺术空间称为“虚幻空间”,朗格认为虚幻空间是造型艺术的基本所在,这种空间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是自成一体的独立存在[10]。20 世纪的另一位形式主义美学大师巴赫金也曾满怀虔敬地说:“文学形象的时空体原则,最早是莱辛在其着作《拉奥孔》中十分明确揭示出来的。”[11]尽管莱辛的论述并没有达到巴赫金所说的“十分明确”的程度,需要巴赫金接下来用自己的理解加以阐释,但是这样的评价足以证明莱辛对文学空间批评的贡献。可以肯定地说:莱辛是近现代文学空间批评史上第一座引人注目的丰碑。
二、文学空间批评的形式主义
美学源流莱辛之后的 19 世纪迎来了“资本主义的盛世”[12](2),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中,“世界”成为一个更具有地理实体意义的概念,世界化的思维正在逐步走入大众对认知的期待视野。在康德提出了宇宙生成论的星云说、黑格尔出版了《精神现象学》的这个时代里,人们对空间的思索已经由外及内,空间变得越来越具体生动,越来越与个体人生息息相关,空间不再是“虚空”,不再是简单的容器,也不再是简单的场所,而是成为具有了历史意义的实体性存在,空间具有了某种可期待的能量和创造力。正因如此,1827 年歌德才会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1847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会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13](63)。空间具有的天然的范围化结构化的属性,再加上对立体空间意识的强化,改变了人们悠久的以时间接续为特征的线性思维秩序,开启了人们立体化多维的结构主义思维范式,1916 年出版的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便成为这一思维新范式的最强大的承运儿。索绪尔正是通过对语言的共时语言学、历时语言学与地理语言学的研究,以时空交叉的立体坐标维度,建立起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的学说或显在或潜在地影响了整个 20 世纪的文学批评。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下,20 世纪前三十年俄罗斯盛行起形式主义文学批评,该批评流派为文学空间批评注入了形式主义美学源流,尤其是直接影响了文学空间的叙事批评。罗曼·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和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大家。其中巴赫金对空间批评的贡献最明显,他提出了“时空体”(chronotope)的概念。1938年巴赫金发表了独具空间批评方法论意义的长篇论文,即《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文中巴赫金首先站在时空的双重维度上,提出了有别于传统的文学新观念,他说:“文学把握现实的历史时间与空间,把握展现在时空中的现实的历史的人。”
[11](274)在他看来文学的关键就是文学形象,而把握住文学形象的关键就是把握住文学中的时空。为了更好地把握住文学的时空,他专门借助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了“时空体”,他定义道:“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我们将之称为时空体。”
[11](274)巴赫金提出“时空体”的美学意义在于,第一次明确地在合法性上把文学审美确认为是时空中的整体性的存在。其对后来文学批评的深远影响是,将文学文本批评引入到社会历史语境的时空之中,在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初露文化批评的端倪。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巴赫金的这篇文章要早于美国的空间批评家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1945 年发表的《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也早于法国的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1955 年发表的《文学空间》和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1957 年发表的《空间的诗学》。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对峙的历史原因,巴赫金直到 60 年代中期才引起英美学界的普遍关注,这使得巴赫金没有及时地在文学空间批评上取得应有的历史地位,倒是美国批评家弗兰克被学界给予了高度重视。尤其是在目前中国学界,诸如“自约瑟夫·弗兰克的《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发表以来,空间问题逐步受到理论界的重视”这类来自名家的表态颇具代表性[14],巴赫金的贡献被弗兰克所遮蔽。虽然由于弗兰克所拥有的语言和国家地位优势,确实对现代社会的文学空间批评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但是在文学空间批评的历史上,巴赫金才是真正的现代空间批评的前驱者,其开创性的历史地位理应还原历史的本真。
巴赫金认为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11](275)。巴赫金以此阐明了文学作品中时间和空间的不可分割性,这恰恰是相对于莱辛理论的一个逆转。
文学在巴赫金时代已不复是线性时间中的情节叙事,而是在时空中立体式的真实存在,从这点出发 20 世纪末迈克·克朗的文学景观说呼之欲出。人的活动离不开时空体,时空体决定了文学中人的形象。并且正如巴赫金所说:“这个人的形象,总是在很大程度上时空化了的。”[11](275)巴赫金按照文学体裁分类,探查论证了希腊小说、罗马传记、民间文学、骑士小说、田园诗中的时空体,将时空体作为区分叙事类型的基础,开创了空间叙事的形式主义美学研究的滥觞。在对各种文学体裁的论证中,巴赫金使用了“道路时空体”“城堡时空体”“沙龙客厅时空体”“广场时空体”等,其对空间场所的类型化关注,可以在法国人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里找到共鸣。而且,巴赫金注意到了各种文学体裁对时间与空间交织安排的结构技巧,他使用了后来在空间批评中被广泛应用的词语“并置”“倒置”“换位”及“有机时间”“传记时间”“传奇时间”“圆周时间”和“超时间”等,来论述作品通过对时间的处理来完成对空间的安排;同时,他也注意到历史时间只有在相应的空间中才有意义。在巴赫金的论述中,可以非常明晰地发现在其结构主义的形式逻辑背后,还有形式与内容相结合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使得时空体超越了形式主义的美学追求,拥有了更深层次上的文化意蕴,这是为什么巴赫金的理论在当下的空间文化批评语境中仍然保有生命力的秘密所在。当代的文学空间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批评。
关于弗兰克与巴赫金的成就何者先何者后的问题,亦可从理论渊源上获得佐证。在理论渊源上有据可查,俄国形式主义美学批评影响了美国文学的空间批评,这一影响至少可以追溯到雅各布森。雅各布森是俄国形式主义美学举世公认的重量级人物,也是一位享誉世界的美学大师,他曾经于 1941 年与德国新康德“马堡学派的集大成者”符号美学大师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er )同船避难美国纽约。无疑,这是一次在形式主义美学史上颇有意义的学术迁徙,卡西尔在美国有了日后着名的门徒苏珊·朗格,朗格开拓出了艺术空间的一片符号美学天地;雅各布森则将俄国形式主义美学的影响更全面地带到了美国,进而影响了美国的新批评,自然也就影响了新批评流派的弗兰克。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性”的把握正好切合了新批评对文本作为文学研究本体的强调,这种影响力在弗兰克的《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中可以找到近乎完美的痕迹。弗兰克对作品空间形式美学的关注和论述,天然含有形式主义的成分,而其以文学作品的细读为分析的方法则是新批评的典型手法。正是在对《尤利西斯》《包法利夫人》,尤其是《夜间的丛林》的细节研读和对比上,弗兰克挖掘出了作品如何打破正常时间的顺序来获取空间美学效果的技巧[15]。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毕生致力于研究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弗兰克,是否直接阅读过同样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专家的巴赫金的俄文原着,也不知道巴赫金是否通过上个世纪 20 年代就成立的巴赫金小组成员或者他本人的朋友、学生或其他什么人,将有关时空体理论的信息带往美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过美国的弗兰克。
即使弗兰克丝毫未受到巴赫金时空体的影响,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也必须得承认,那就是巴赫金的空间美学研究在历史时间上确实早于弗兰克;且俄国形式主义美学也确实早于英美新批评;再有随着冷战思维的隐退,意识形态壁垒的倾颓,全球化时代的最终来临,巴赫金多元价值对话体系中的公共空间的广场狂欢、独语及复调等理论的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劲,跨越了国别和语言的障碍,直接影响到当下英美文学的空间批评。鉴于以上三方面,故本文将俄国形式主义,而非英美新批评作为文学空间批评的主要美学源流。
三、文学空间批评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源流
在文学空间批评领域,到目前为止成果最丰厚,影响力最壮阔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流派。该流派代表人物列斐伏尔、福柯、哈维(David Harvey)、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索亚等人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地理空间观,分别在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地理学等方面取得成就。
马克思恩格斯的空间观及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19 世纪中叶即准确预言了全球化问题:“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13](31?32)显然在他们看来空间的世界性即全球化转型来源于资本不断扩张的本质,这种扩张运作后来成为列斐伏尔理论中的空间生产行为。此外,全球化带来文化同一性的危机,出现相对的文化荒芜和精神失重,地域间的文化表征既没有深度又没有距离,于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的空间批判顺势崛起,本雅明的“废墟”③、詹姆逊的“超空间”④、波德里亚的“没影点”⑤、吉登斯的“脱域”⑥等空间理念应运而生。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较早地从社会关系角度,发现了空间中统治与被统治的地域关系,包括城乡空间的对立,东西方空间的对立等问题,“资本主义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13](32)在他们看来,正是资本主义经济造成了空间的权力关系。这一论断可以视为 1978 年萨义德《东方主义》的精要提纲,也足以为后殖民空间理论家对西方文化进行知识解码、权力话语批判和他者身份研究提供的思想动力源,更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空间美学都市文化研究的先河。
齐美尔对西马都市空间美学流派的形成具有开拓之功。他最先将文化批评引入到了文学空间批评的美学领域。是齐美尔最先注意到了都市时尚与现代性的关系,并且影响了后来本雅明对巴黎的都市观察[16]。
虽然齐美尔本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作为那个时代德国着名的社会学家,早期形式主义美学家,给予了西马最重要奠基人卢卡奇衣钵的老师,确实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西马的先驱性人物。其对都市空间的研究,以他最着名的货币社会论为基础,他认为货币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封建制度,催生了现代民主,决定了人的自我价值和自我设计[17]。从他认为经济发展决定社会制度变革的观点上,可以发现齐美尔深受马克思的影响。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齐美尔从个体对个性的追求与社会强势力量的冲突谈起,论述了在“货币经济中心”的大都会,货币强悍的文化权势力量。货币经济所具有的社会化大生产特征,带来都市人的情感麻木与模式化生存,导致都市人自我认证(identity)的脆弱,个性扁平,缺乏色彩,对周围表现出泛泛的自私、冷漠、消极、排斥和厌世的态度(the blasé attitude),人性在都市生活中呈现出变异的病态[18](414)。在齐美尔看来,这些都市病症是个体与群体在都市空间生存中彼此冲突或隔绝才导致的精神疾病,它使人性自我处于支离破碎中。他的学生卢卡奇进一步论述了都市病,并最终提出“物化”的理念,这一理念与后来发现的马克思《1844 年经济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理念相得益彰。在文学上,法国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展现出都市的现代性特征,借助诗歌形象化的语言应和了齐美尔对现代都市的论证,患了都市病的各式人物充斥了他对巴黎的吟咏,无处不在的“死亡拟态”勾勒出以“新奇”为价值的现代性面孔;这些阴郁的具有“现代美”的怪异诗歌,在本雅明看来“具有美的不可转让的品质”[12](51),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对现代性都市生存空间的倦怠,对往昔灵光闪烁的田园牧歌式生存空间的缅怀。
瓦尔特·本雅明,20 世纪 30 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市美学流派毫无争议的代表性人物,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干将,以《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为文学的空间批评树立了又一座丰碑。面对着资本主义经济向帝国主义发展所导致的空间变迁,本雅明深怀着一种浓郁的乡愁,将资本主义盛世时期威廉姆·布莱克《天真之歌》所吟咏的那种“刹那含永恒”的顿悟,转化为一种灵光消逝后的空间怅惘。1929 年本雅明为阿拉贡以歌剧院拱廊为背景的小说《巴黎的乡下人》所打动,他认为巴黎的拱廊是 19 世纪“最重要的建筑”,是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成就和象征,但是却在城市改建动迁中很快灰飞烟灭,成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中转瞬即逝的“废墟”[12](1)。拱廊的际遇给予本雅明强烈的认知刺激,这让本雅明有了一条与巴赫金不同的空间体验途径。本雅明以自己的敏锐,在资本主义盛世的发达之都巴黎的日常生活中,远在 30 年代,即捕获了资本主义文明的都市空间危机。通过拱廊的历史痕迹,在资本主义盛世的灵韵消退的第一刻,他即真实体验到卢卡奇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下的“物化”和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人的“异化”。在他的分别写于 1935 年和 1939 年的两份针对巴黎的研究提纲《拱廊计划》中,本雅明探究了文学艺术作品中巴黎的街垒、街道、拱廊、私室和世界博览会,可以看到生产物的片刻繁华映照着波德莱尔诗歌中都市病的丑态,展现了现代都市遭遇的空间挤压和人性异化。本雅明对 19 世纪首都巴黎的研究,远比巴赫金对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的“小省城”要具体生动,且充满了文化批判的味道。对于形式主义批评家巴赫金来说,把握作品的文学性是批评的第一要领;但是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来说,揭露文学作品中资本主义弊端才是第一要务,由此他的都市批评更重视文学的社会历史意义,继齐美尔之后,本雅明进一步在文化批评领域拓展了西马的都市美学。
20 世纪 70 年代后,在列斐伏尔和福柯的引领下,马克思主义空间美学被注入了经济批判能量和政治权力话语批判因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并直接为当代的文学空间批评提供了权力话语批判的动力。列斐伏尔的一个具体的贡献就在于在马克思实践观的基础上,明确辨析了“空间”的理念,牢牢地将空间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他认为传统认识上的“空间”,是欧几里德几何式的认知,是数学家概念性的发明,而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则与现实和社会紧密相连。
他说:“(空间)在数学和现实——即实体的和社会的现实——的关系方面,并不明晰且存有裂痕。”[4](2)为了弥补这一裂痕,他强调了空间作为社会实体的生产功能。他为“空间”划分了三个概念,即“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Space)、“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4](39)。
其中,作为社会产物的空间的实践,指的是社会实体性生活空间;空间的表征是概念化的空间,属于科学家、城市规划专家、技术专家等的使用范畴,与实践紧密相关;表征的空间则既是实体的生活空间又是精神空间,它趋向于非语言的符号和象征系统,涵盖了哲学家、艺术家和作家的创作实践。这三个概念从不同的方式指向空间生产。在他看来“空间”首先是实体性的存在,它包含了社会也被社会所包含。而社会既是劳动生产的产物,又具有经济生产能力;因此空间也是劳动生产的产物,也具有经济生产能力。这样列斐伏尔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生产理论扩展到空间范畴。在列斐伏尔看来,剩余价值在特定的都市空间积累,空间作为聚集了各种经济元素的综合体,它超越了作为容器的形式性客体范畴,而成为涵盖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主客体性存在。同样数量的资本在不同空间的投入,会产生不同的利润,这说明资本在空间流通的过程中,扩大了剩余价值,空间具有了生产能力。空间具有生产能力是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最大成果。因为空间具有生产能力,列斐伏尔使我们更加明显地看到了不同空间之间彼此的对立、对抗与融合。
在他此后的着作《进入都市的权利》《从乡村到都市》和《空间与政治》中,提出现代生存状态下的空间权力问题,在理论发展上与福柯的空间权力话语批判可谓同脉相承。列斐伏尔在这些着作中集中展示了在空间生产过程中不断凸显出来的空间矛盾。这些矛盾比波德莱尔时代的“死亡拟态”更为令人窒息,20 世纪以来以恶化的空间生存为标记的异乌托邦小说(Dystopia Fictions)创作的繁荣便是这一历史境况的文学缩影。
促成了现代空间转向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美学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是福柯。列斐伏尔论证了空间的经济生产;福柯则揭示了空间的权力生产。20 世纪末的空间转向,主要就是建立在列斐伏尔引领的空间经济学和福柯引领的空间政治学的基础上,并最终转到詹姆逊、波德里亚、索亚等人的空间地理学方面。在文学的空间批评方面,福柯产生了更为直接更为深远的影响。在福柯的一系列着作中,几乎都包含着一种空间权力美学,体现着他对空间与权力的关系所展开的思考。例如,早在《疯癫与文明》的写作时,福柯就注意到了权力对所谓“不正常的人”所做的空间的隔离,即注意到了权力对空间的支配。接着在《词与物》中,通过对名画《宫中侍女》所做的结构主义美学分析,福柯则进一步注意到了空间所隐含的权力秩序问题。
福柯认为油画模仿着空间,这个空间又是敞开的,在画面表象与表象的背后存在着某种空间凝视,展现着某种空间权力秩序关系,它影响着画面中人物以及画家本身的目光凝视的方向[19],这种凝视有着福柯的“权力的眼睛”的最初显露[20]。继而在《规训与惩罚》中,“权力的眼睛”通过边沁的全景式监狱,获得了明确命名。福柯注意到在权力的中心点,即“权力的眼睛”所笼罩的空间中,“全景监狱”作为政治技术的象征,有着特定意义的空间分解与组合模式,其表征着权力关系的运转机制[21](230)。现代社会空间中的权力运行已经脱离了权力个体意义上的把控,而成为一种特定空间的关系体制,到底由谁站在全景监狱的了望塔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机制本身,它使“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21](227),把空间中的一切统辖在机制内。这种机制同样可以应用在生产、教育和生活领域,简直无所不在。权力关系的运转机制把人对权力的遵守充分内化,权力深入到人的精神空间,所以与封建制度相比,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对人的权力控制。这种以全景式为特征,以“权力的眼睛”为掌控的空间体系就是空间中的权力生产。福柯发现了现代社会权力运作的秘密,于是“空间”理念因福柯具有了明晰的权力等级秩序属性。福柯的空间权力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生存境况的秘密。作为权力机制主体和客体的人,因在都市空间中遭遇到各个向度的权力挤压,导致生存的自由空间越来越狭隘,精神空间也随之越来越贫乏。从波德莱尔的诗歌、乔伊斯的小说和奥尼尔的戏剧等现代文学表征来看,会发现人在空间化的机制生存中彼此阻隔,成为心灵上的“陌生人”,常常处于颓废的“死亡拟态”。经历了全球化带来的“时空压缩”,后现代文学作品中人的空间生存进一步恶化,相继出现波德里亚命名的消费社会中的种种无深度的“欲望”和人物支离破碎的心灵际遇,也就是出现詹姆逊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超空间”中的无标记的生活样态。正是源于福柯和其后继者的空间权力理论,现代社会人的“逼仄”的境况被不断地从文学作品中挖掘出来。可以肯定地说,福柯对空间权力的卓越发现,使得当下国外文学出现了空间权力话语批评潮流。福柯的空间权力美学也因此产生了广泛影响,并使得福柯的名字与“空间”变得连筋带骨。
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当下空间批评最显着的当代理论来源,以其社会批判的锋芒为文学空间中的都市文化研究和权力话语批判注入了持久人文关怀与理论力量。
综上,虽然在历史的相当长时间,空间美学或隐或显,并未形成滚滚洪流,甚至在各个历史时期难以用时间线性思维模式中的所谓“时代特征”来概括,但当下的文学空间批评的确有着可追溯千古的浮脉:
其开启于古希腊美学,承继于德国启蒙主义美学,初步繁荣于法兰克福学派,波及俄国形式主义美学、法国结构主义美学及英美新批评,最后聚集起英法美诸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批评大家的全体实力,在 20世纪末汇聚成整个西方世界的空间转向潮流,继而顺应时代发展的现实境况,在 21 世纪全方位显现出文学的空间批评热。文学空间批评所运用的理论包含多个源流,是空间美学长期发展的历史性成果,它反映了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加深的对各个时代空间生存的体验。
参考文献:
[1] 文子. 文子疏义(卷第八)[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344.
[2]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Other Writings, 1972—1979 [M].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1980: 70.
[3] 柏拉图. 蒂迈欧篇[M]. 谢文郁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6.
文学批评从古希腊时期的摹仿说一路走来,经过了实用说、表现说,虽然每一种理论都足以对一般的艺术进行令人满意的批评,但无可否认,它们在实际应用时都只考虑了艺术品和其外在参照物之间的关系。直到20世纪,理论家们才开始较为明确地认识到艺术品本身具有...
在数字阅读日常化的今天,网络文学已形成较大的阅读市场,正在创造新的文学美学,并对文学本身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由于网络文学出身、业态等特殊性,其审美特征中暴露出的价值偏离已引起业界关注,若不能做相应调适,将难以持续健康发展。一、网络文学的...
我们写出来的文章是用于别人品读的,只要品读就会给人以一定的思想启发和精神促进。不管是任何的作品均脱离不开这种过程。哲学类文章也好,理论性文章也罢。尤其是文学艺术的作家们创作出来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仅需要有人来阅读,而且还要达到让人爱看,...
一、汉语言文学的特征。(一)汉语言文学概念。汉语言文学,顾名思义,是涉及到人文社会方面学科内容的一个专业概念。我国历史文化悠久,自文字产生到如今已经传承了数千年,语言也在漫长的时间下不断演变进化,最终形成了我国通用的语言--汉语,并形成了...
到底应该如何概括和分析文学意蕴的强大功能呢?对于这个问题,理论界历来众说纷纭,笔者只想借助“隐秀”二字,发掘一个概括和分析文学意蕴功能的新视角。...
文化通常被认为是社会价值体系的总和,所以在语义学的上下义关系中,文化是上坐标词,政治文化和文学均为下义词。政治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文学属于人文科学范畴,这两个表面上看似没有必然联系的学科,却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产生交叉点并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
为了使自己的文学作品新颖独特、别具一格、更有魅力,获得更多的读者,作家在创作时往往会运用陌生化手法。陌生化手法会使读者在审美接受活动中有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在进行审美再造时也会获得更多的审美享受。文学陌生化理论是俄国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在《作...
学者普遍认为西方的现代化是一个异化的时代,表现在文学方面诸如:萨特的他人即地狱,加缪笔下的自我变成了局外人,卡夫卡书写的主人公永远进不去眼前的城堡,福克纳发出了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了喧哗与骚动等等。表现在哲学思想领域:马克思论述人在机器大工业...
在1979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提出文学艺术应根据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发展。党的作用不是发号施令,而是给文艺工作者提供条件繁荣文艺事业。问题是如何将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从政治话语转变为学术话语,文艺审美特征论作为一种新...
虚实,是一个宽泛而又复杂的范畴,它在中国哲学、美学、艺术理论等许多方面都有涉及。虚实是我国传统美学的审美原则,也是我国传统艺术的美学特点。虚实从传统文论角度看,既是文学作品的审美原则,也是作家创作的表现手段与方法,所以虚实方法的应运关系到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