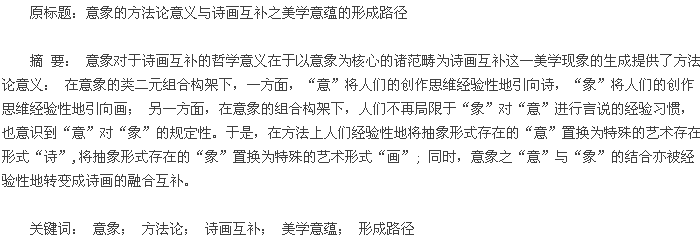
唐宋时人们已经从两方面认识到了意象的功能意义: 一是意象直接参与文本的建构,形成文艺之本体; 二是其方法论意义的呈现,它主要关涉到在“意”与“象”的组合结构模式下两者的互补性存在所提供的示范意义。虽然“‘意象’作为标示艺术本体的范畴,已经被美学家比较普遍地使用了”[1]265,但是意象对于诗画互补观念的美学意蕴主要不是从本体论层面彰显,而是从方法论层面敞开,其意义在于: 意象在构成上的互补性注定引领人们做由意到诗、由象到画的联想,由意象的类二元结构推衍到诗画互补性的形成( 此处使用类二元结构是为了同西方二元论思想区别开来) .把意联系于诗、把象联系于画的思想在北宋邵雍那里已经很明确了。清代叶燮的话亦证明这种推衍的可行性: “画者形也,形依情则深; 诗者情也,情附形则显。”( 《已畦文集》) 当代学者同样赞成这种推衍: “在诗画交融艺术实践的推助下,生成了‘诗中有画’的美学讲求,以及相应的诗性文学形象思维的‘造型’美特征,致使‘情景交融’一语几乎成为中国美学理论批评的经典术语。”[2]不过,意象对于诗画互补的方法论意义具体通过哪些路径实现呢?
笔者将从意象在创作中的地位、意象的类二元构成、意象之意与诗所达成的经验性联系、意象之象与画所达成的经验性联系等入手探讨。
一、意象在唐代文艺创作中本体地位的确立构成了诗画互补的认识基础
从《周易·系辞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以及“圣人立象尽意”等表述可知,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发现了言作为语词在表意方面的局限性,并确立了“立象尽意”的观念。深受《周易》影响的刘勰继承了《周易》对“言”、“象”所持的态度,他在《文心雕龙》中数次讲到“言”对意的言不由衷窘境: “言不尽意,圣人所难”( 《序志》) ; “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 《神思》) ; “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 《神思》) .刘勰认为解决这个窘境的方法就是“神用象通”,而这个“象”,刘勰称之为“意象”,它是文艺创作的依据,创作主体的“独照”之处就在于“窥意象而运斤”( 《神思》) .刘勰虽然只在《神思》篇中提到“意象”,但其文艺价值却是深远的: 刘勰将“立象以尽意”这一具有宗教巫术意味的哲学认识方式转化为文艺构思的一般原理,并将其概括为“意象”,在使之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的历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在唐代,文艺领域中“言不尽意”的情况亟待人们从理论层面予以解决。如孙过庭《书谱》云“夫心之所达,不易尽与名言; 言之所通,尚难形于纸墨”.张怀瓘《书议》说“可以心契,不可言宣”.对于言意之间的难题,佛禅自汉代传入以来就源源不断地给予人们如何超越语言缺陷的启示,这也为象与境作为意的表达手段起到了重要的渲染作用。佛教大抵主张超脱名言概念限制的直观,因为语言概念与真理正智始终是无缘的。“所谓佛祖拈花,迦叶微笑,维摩一默,皆是不依文字,尽传心法。”[3]
故而在禅宗中,鼓吹直观把握真理和贬黜语言功能的倾向一直存在。禅宗特别看重的“悟”或“觉”,某些时候就有“现观”、“现证”的意思。唐代特别是中唐及其后佛禅的诸多主张都与打破名言的限制有关: 一是“观心”.温州永嘉县玄觉对这一主张的改造很有影响。“观心”作为禅行的内容,北宗尤为重视,玄觉则作了特殊发挥。
首先他把所观的“心”规定为“一寂”或名“灵源”、“玄源”,认为一切深广功德全在“一心”[4]192.佛禅这种“观心”主张在文艺创作中影响很大。如宋之问《自衡阳至韶州谒能禅师》“物用益冲旷,心源日闲细”; 张璪《历代名画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刘禹锡《董氏武陵集记》“心源为炉,笔端为炭,锻炼元本,雕砻群形”等。二是“顿悟”.代表人物有洛阳荷泽寺的神会,他“教授门徒,唯令顿悟。他曾宣布: ‘我六大师,一一皆言单刀直入,直了见性,不言渐阶……’”[4]174三是“触境皆如”.提出者为江西禅的代表人物马祖道一,他说: “佛不远人,即心而证; 法无所着,触境皆如。”[4]252“触境皆如”意即任何“境”相都不外是心的产物。四是“即境即佛,是境作佛”.该语出自法眼宗的延寿,延寿评论当时的禅宗云: “今人只解即心即佛,是心作佛,不知即境即佛,是境作佛。”
[4]388上述佛教经典用语既体现了佛禅妄图超越语言的苦心孤诣,又表明了佛禅对“心”和“境”的高度重视,佛禅的礼佛过程本质上就是由“心”到“境”的穿越、升华。佛教这种悬置语言、以心叩境的办法倍受唐代文艺家们的推崇,如王维《山水诀》“悟理者不在多言”,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含蓄》“不着文字,尽得风流”.这一事实从皎然《诗式》亦可以获得证据。他说: “虽欲废言尚意,而典丽不得遗。”
我们分明感受到皎然在对“言”之典丽风格眷恋中所透露出来的无奈和纠结,但是“废言尚意”对他来说仍然是大前提。言所面临的问题为“象”的广泛介入文提供了契机。“意象”在唐代大放异彩,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意象”体现了儒家“立象尽意”的思想主旨; 二是“意象”大抵接近佛家所崇尚的以心叩境的精神内涵。因此,当有不同精神追求的人们面临共同的“言”问题的时候,“意象”自然成为普遍认可的一剂良药。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唐宋文艺家们多视“意象”为衡量文艺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诗歌理论如殷璠《河岳英灵集》“佳句辄来,唯论意象”,王昌龄《诗格》“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意象欲出,造化已奇”等。绘画理论如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特出意象”,邓椿《画继》“意象幽远”,董逌《广川画跋》“笔力超诣,而意象得之”等。书法理论如宋高宗《思陵翰墨志》“风骨意象皆存在”,董更《书录》“意象高古”等。
二、意象的类二元结构为诗画的互补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实践认识依据
唐宋时人们对意象的构成已经形成共识: 意象的结构模式不仅是诗画的基本构成要素,而且这种结构模式本身就是互补性的存在。意象的类二元构成意识最早可以追述到王弼的言意之辨,它为诗画的互补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可行性。这种观念首先在诗歌领域里体现出来,人们认为“诗”是一个由“意”和“象”建构而成的类二元结构的统一体。如白居易着《金针诗格》曾言: “诗有内外意。一曰内意,欲尽其理。理,谓义理之理,美、刺、箴、诲之类是也。二曰外意,欲尽其象。象,谓物象之象,日月、山河、虫鱼、草木之类是也。内外含蓄,方入诗格。”
[5]463在这种结构模式里,“内意”和“外意”之间、“意”和“象”之间的组合明显具有构成上的互文性,这就昭示着它们对于诗画互补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 这种组合结构为诗画的融合确立了方法上的召唤结构。从白居易的语意看,“内意”属于诗性范畴,承担了“诗”的言志、美刺等功能,属于诗性的表现之一; 而“外意”则属于绘画视觉性的范畴,承担了“立象尽意”的功能。
“诗有内外意”的见解与唐代佛教唯识宗经义《成唯识论》的影响分不开。唯识宗就把自体相( 又称阿赖耶识) 描述为“因缘力故自体生时,内变为种及有根身,外变为器”( 《成唯识论》)[6]390,也即是说“恒久相续,不断转变”的自体相“能取外界之境,发内界之识”
1.从唯识宗重要概念“第二能变识,即第七末那识( 前六识为: 眼、耳、鼻、舌、身、意) ”[6]391看,可以推知诗应当属于末那识,即“‘意’识,‘思量’之义”[6]391.所谓诗意就是用诗“思量”.基于对自体相特性及末那识的认识,白居易作了替换嫁接: 把“自体相”置换为诗,将“自体相”内变的“种子根身”、外变的“器世间”分别置换为内、外之意,或者说将人们对“自体相”内、外之识转化为内、外之意。到了中唐以后,六识被通称为“见闻知觉”四识: 眼识曰“见”,耳识曰“闻”,鼻、舌、身三识曰“觉”,意识曰“知”.“‘见闻知觉之性’就是全部世俗认识的概括,也可以简称为‘知’、‘知性’等”[4]233.不仅如此,当时的南方禅释“心”为“见闻知觉之性”,并把它视作“佛性”.按照佛教的观点,“诗”既属于‘知性’的范畴,又是佛性的体现,这也是为什么诗能与禅结缘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当时人们以类二元结构的思维去观照意象时已经注意到意与视觉形象性的协调问题。如徐寅《雅道机要》就讲到人们在追求视觉形象性时忽视了诗性的问题。他说: “凡为语须搜觅,未得句先须令在象前,象生意后,斯为上手 矣。不 得 一 向 只 构 物 象,属 对 全 无 意味。”[5]464最具有革命意义的是徐寅明确注意到在意象的相互关系中,“意”不再被动地被“象”所规定,“意”同样对“象”有制约、补充作用,这种作用表现为“意”赋予“象”更丰富的意味,即后来所说的诗意。可以说,白居易、徐寅等人对意象结构的辩证认识已经构成了诗画互补观念的普遍性原理。
把绘画视为意与象的统一体的观念在唐宋时同样存在。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就表明了绘画是外在造化之形和内在心中之意的统一体的思想。王维《裴右丞写真赞》有“凝情取象”的见解,他认为绘画就是“情”与“象”的融合。从结构关系和构思过程看,情、象就是意、象的另一种表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王维明确将情与象( 或意与象) 置入类二元结构的关系中。《林泉高致》从意和象两个维度对山水画提出要求: “画见其大象而不为斩刻之形,则云气之态度活矣。……画见其大意而不为刻画之迹,则烟岚之景象正矣。”《宣和画谱》同样流露出如是思维,花鸟叙论一节说绘事与诗相表里,只不过绘事是通过图绘寄寓兴意罢了,故而作者认为花鸟之性“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唐代以前绘画创作的关注点多为形与神的统一问题,随着山水、花鸟画表现技法的成熟,唐宋形神的统一问题逐渐被转化为意与形、象的协调、统一问题,人们意识到神或者气韵的生成最终要落实为“意”的传达。如张彦远说“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 《历代名画记》) ,北宋刘道醇说“精神完则意出”( 《宋朝名画评》) ,郭若虚认为神生于用笔,意又先于用笔,故“笔周意内,画尽意在,像应神全”( 《图画见闻志》) ,可见,神最终生于意。沈括《梦溪笔谈·书画》认为: “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而“神会”的关捩又在于“得心应手,意到便成”.从南宋陈郁对形、神、心关系的探讨犹可见出,人们对这一转换认识的自觉性: “盖写其形必传其神,传其神必写其心”( 《藏一话腴》) ; 反之,就会造成“意”与“象”的割裂,他以创作屈原肖像画为例阐明了这一弊端:“夫写屈原之形而肖矣,倘笔无行吟泽畔,怀忠不平之意,亦非灵均”( 《藏一话腴》) .“意”与“象”的统一问题也始终是后世的画家们要考虑的重要课题,明代王履的观点犹具代表性: “画虽状形主乎意,意不足谓之非形可也。虽然意在形,舍形何所求意? 故得其形者,意溢乎形,失其形者形乎哉。”( 《华山图序》)
克罗齐在《美学》的开篇就谈到:“人类的知识总是分为两种:要么是直观的知识,要么是逻辑的知识;通过想象获得的知识或者通过智力获得的知识;个人的知识或者宇宙的知识;关于个别事物的知识或者关于不同事物之间关系的知识。...
意象说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系统的诗学理论形态,不少学者对其产生和发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梳理,普遍认为《易传》阴阳二元结构思想和立象以尽意观物取象以及魏晋时期王弼等玄学家对言、象、意三者关系的哲学探讨为意象说的形成奠定了哲学理论基...
易象作为一个符号体系, 它的每一种排列组合形式都是具有一定寓意的。要悟出“象外之意”, 必须充分认识易象的象征手法和譬喻手法, 它们使易象具有象内与象外、形 (象) 与意的结构特征。在易象符号“解码”产生意义过程中, 以卦象为做出判断的依据, 但是又不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