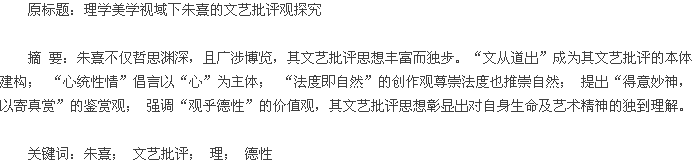
朱熹不仅理学思想博而有统、精深通贯,且广涉博览、独出古今,正如钱穆先生所言: “盖朱子之为学,格物必精,游艺不苟,虽曰余事,实皆一贯。本末精粗,兼而赅之。昔太宰问于子贡曰: 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闻之,曰: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云: 吾不试,故艺。后世学者,惟朱子其庶几焉。其曰余事,乃谦言之,犹孔子之谓君子不多也。”[1]( P344)钱先生对朱熹的评价可谓中肯,朱熹在艺术方面不仅多方涉猎,而且留下了丰富的文艺批评思想。
一、“文从道出”之本体观
朱熹的文艺批评思想建立在理学基础之上,“理”是宇宙万物之根本,具有本体地位,在“理”与“道”的问题上,朱熹认为: “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2]( P103)“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3]( P2755)“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4]( P1573)朱熹的“理”与“道”都是从本体意义上而言说的,“道”即“理”,“理”或“道”既是物之所以然之故,也自然是所当然之则,即本体论和价值论是统一的。朱熹正是在他的哲学思想上阐释了其文艺本体论思想。
朱熹明确提出“文皆从道中流出”,“道者,文之根本; 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5]( P3319)道是文之本,文是道之枝叶,所以出之于道的文自然要体现道,呈现道,这即是朱熹的“文道合一”“文道两得”观,依此,朱熹批评了唐代韩愈、柳宗元及宋初柳开、欧阳修等古文革新运动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等观点,修正了周敦颐和二程贬低文之地位的思想倾向,尤其批评了苏轼的“文与道俱”说,“今东坡之言曰: ‘无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如东坡之说,则是二本,非一本矣。”[5]( P3319)朱熹这里强调“文道合一”,反对苏轼的文道为二的观点。朱熹对“文”有多处阐释,其基本涵义包括: “天之文”: 即阴阳刚柔相交而形成的天地四时之更迭、经天纬地之条理、万物山川之物理等天地之道和自然之理; “社会之文”: 即君臣之仪、经籍义理等礼乐制度; “艺之文”: 即诗文六艺等。后二者都应属于“人之文”,因此,“文”的概念涵纳着天人及其关系,天人为一整体,都根源于“道”.朱熹认为艺是文的一部分,“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
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2]( P121)朱熹基本从“六艺”之说定位“艺”,但又明确不止于此,而且朱熹对“艺”之功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艺是“至理所寓”,人们“日用之不可阙者”; 虽然朱熹认为艺是小道末节,但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尤其是德性之养的功能,盖艺虽末节,然亦事理之当然,莫不各有自然之则焉。曰‘游于艺’者,特欲其随事应物各不悖于理而已。不悖于理,则吾之德性固得其养,然初非期于为是以养之也。“张子曰: ‘艺者,曰为之分义也',详味此句,便见得艺是合有之物,非必为其可以养德性而后游之也。”[4]( P1368)因此,在朱熹的视野中,“艺”虽然不及“道、仁、德”重要,但对“艺”仍给予足够的重视,据此,他批评程门弟子上蔡贬抑轻视艺之观点,“虽然,艺亦不可不去理会。如礼乐射御书数,一件事理会不得,此心便觉滞碍。惟是一一去理会,这道理脉络方始一一流通,无那个滞碍。……’游于艺‘一句,比上三句稍轻,然不可大段轻说。如上蔡云: ’有之不害为小人,无之不害为君子‘,则是太轻了。”[5]( P866)朱熹立基于文艺本体之存在,修正了前人观点之不足,肯定了艺术的价值存在,这对艺术地位的确立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心统性情”之主体观
“心统性情”首出张载,但张载对此未充分展开论述,而朱熹将这一命题纳入到他的哲学体系中,依此阐发了其文艺主体观。
朱熹的“心统性情”之“心”包含两个方面,一为“道心”,一为“人心”.“道心”是自其天理备具、随处发见而言; “人心”是自其有所谋虑而言。“道心”本于“天理”,是圆善之心; “人心”则是出于“形气之私”,是人之情欲。但朱熹并没有因此否定人心,而是承认其自然性的一面,只是要以道心为一身之主来统摄主宰,从而归乎纯正至善。朱熹之“心统性情”之“统”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兼”“包”之义,心兼体用,未发为性为体,已发为情为用,然而“体用一源”,这里之“心”是涵纳性情两个方面。
“统”之另一方面的意义是指统摄主宰之意,这是朱熹此命题所强调的主要意义。朱熹的“心统性情”是要以“心”来主宰统摄性情,也就是“天理”通过“心”来实现对人之现实生命的统领和主宰,实质上,是要对容易偏执泛滥之情欲进行规约,“心统性情”在现实层面主要还是强调“心”对“情”之主宰之义。
朱熹以“心”来评书品画,倡言胸怀本趣之自得,强调作品之“写意”“写神”,执着于胸次之涵泳,诸多渊丰之品评,都是以“心”为核心而展开的。“心”在朱熹的思想中是作为精神主体而存在的,建基于此,“心”也就成为朱熹文艺批评思想中所指涉的文艺主体,这一主体既可是创作者,也可是接受者。
朱熹在对书画的批评中提出“谛玩心画”的观点,“杜公以草书名家,而其楷法清劲,亦自可爱。谛玩心画,如见其人”[6]( P3953)。在朱熹的思想中,书法作品即为“心画”,从中可见作者其人。“至于心画之妙,刊勒尤精,其凛然不可犯之色,尚足以为激贪立懦之助。”[6]( P3882)正是因为书艺能够写心,所以才能有“激贪立懦之助”,也就是说,创作者的心性能够通过这种“心画”通达接受者的心中,在二者的交流互动中从本根上起到人品德性之助。这种潜移默化之功也正是朱熹所言心画之“妙”处。朱熹以心评书画着眼于道德功利,这有利于道心的发见流行和主宰统摄,从而将这些艺术形式落实到了德性之本根,但从中也可看出,朱熹将这些艺术归根于人之生命的内在,并建基于“天理”之自然,强调其德性也表明这些艺术形式具有无遮蔽的心灵沟通交流之功。
朱熹主张心对性情的统摄和主宰并不意味着压抑或否定情欲的表达,而是提倡从心出发的真性情,他提出的“感物道情”即是以发乎真情作为批评的标准,如朱熹就批评《毛诗序》对《诗经》的穿凿附会的理解,指出《诗经》是出于真情的抒发表达,而不是以“美刺”为目的,他明确提出应该“去《序》观诗,以诗观诗”,这已经是深入到艺术自身来评价艺术了。朱熹也以“感物道情”的观点来评价屈原的作品,认为屈原的《天问》正是因为屈子看到了庙堂上楚国的天地山川,因之满腔悲愤涌动而书其壁上,这完1唯一的判定尺度,真情实感与艺术感染力都是其品评依据。
三、“法度即自然”之创作观
朱熹认为文艺创作一定要讲求法度,以“端楷”为标准,而不能任意放纵,如同做人之“方正”,朱熹极力赞誉“端庄厚重”之书法,“蔡公大字盖多见之,其行笔结体往往不同,岂以年岁有早晚,功力有浅深故邪? 岩壑老人多见法书,笔法高妙,独称此为劲健奇作,当非虚语”[6]( P3954)。朱熹推崇古法之法度,同时也注重书法之功力,笔法之精妙。朱熹批评那些过于纵意狂怪之作,苏轼、黄庭坚和米芾等人的艺术创作即在他批评之列,“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5]( P3336)。“至于黄、米而欹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近岁朱鸿胪、喻工部者出,乃能超然远览,追迹元常于千载之上,斯已奇矣。”[6]( P3868)朱熹认为“字字有法度”,米芾、黄庭坚的欹倾之字受到朱熹的否定也是自然之事。朱熹的《朱子语类》中有一段是对艺术法度的讨论,反映了朱熹的这种艺术观。
邹德父楷书大学,今人写得如此,亦是难得。只是黄鲁直书自谓人所莫及,自今观之,亦是有好处; 但自家既是写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 须要得恁欹斜则甚? 又他也非不知端楷为是,但自要如此写; 亦非不知做人诚实端悫为是,但自要恁地放纵。……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则。及至米元章黄鲁直诸人出来,便不肯恁地。要之,这便是世态衰下,其为人亦然[5]( P3338)。
此段批评黄鲁直虽自知做人要诚实端悫,创作要讲究“端楷”,但却任由自己放纵而为,这在朱熹看来,正是世态衰下、人心惟危的表现。朱熹是以“立人立世”的儒家思想谈论法度的,因此更关注文艺创作的道德意义和社会价值。
朱熹秉持文艺创作“法度”的同时,也倡导“自然”原则。朱熹思想中的“自然”是指“自然而然”之本性,朱熹将这种自然性归属于“天理”,“天理”流行自有自然之妙,因此说,他是将文艺创作中的自然性归根于最高的具有终极价值的“天理”,从“理”出发建构他的文艺批评本体,从而支撑文艺创作自然性的批评观。
朱熹强调“文从道流出”“文自胸中流出”.他曾批评苏轼及其弟子“刻意为之”“一向求巧”之弊,主张自然、平淡、真味之作品,推崇陶渊明平淡自然之诗作。他认为作诗不多吟,不少吟,亦不不吟,亦不必吟。“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但不用多作,盖便是陷溺尔。当其不应事时,平淡自摄,岂不胜如思量诗句? 至其真味发溢,又却与寻常好吟者不同。”[5]( P3333)完全是不假思量,自然从胸中涌出,这样才能有“真味”之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