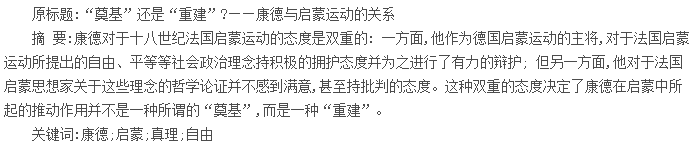
法国启蒙思想家提出的自由、平等等社会政治理念对康德哲学具有重大意义,它们直接促成了康德哲学从前批判时期向批判时期的转变。康德垂暮之年回忆《纯粹理性批判》的发端史时披露,正是卢梭关于自由的二律背反(即人生来是自由的,但又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 促使他转入理性批判的工作,因为他要通过理性批判来澄清理性自己反对自己这样的荒唐事。
不过,康德对于法国启蒙思想家在自由等理念方面所作出的论证并不感到满意。他在《回答这个问题: 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委婉地对拉美特利“人是机器”的哲学命题提出了批评,认为这将威胁到人的尊严。他说: “政府发现,按照人的尊严———人并不仅仅是机器———来对待人,对政府自己也是有利的。”
关于康德与启蒙的关系,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是把康德排除在启蒙思想家的阵营之外。比如托马斯 · 汉金斯 (Thomas L.Hankins) 认为,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作为完美智力的理性向作为自然规律的理性的转换造成的”,这种转换的结果使得启蒙思想家在以自然的规律来为人的自由进行论证时必然会碰到两个无法解决的悖论: 其一,自然规律就其是纯粹描述性的而言,它所揭示的只是“什么”而非“应当”,所以启蒙思想家试图从自然科学中提取道德规范的做法并没有成功的希望,至于他们想以此来建立一门“客观的”道德科学,那更是不可能; 其二,当启蒙思想家将自然的必然性规律运用于人并认为人的自由是不可剥夺的人权时,他们会再次遭遇必然与自由的内在矛盾。
显然,托马斯·汉金斯在作这番评论时并没有把康德考虑在启蒙思想家的行列之内,因为在康德那里,自然与自由这两个领域的界限是泾渭分明的。再比如,阿马蒂亚·森(Amatya Sen) 在其《正义的理念》一书中对启蒙主义者片面夸大理性的作用提出了质疑。他说: “当代的政治研究也普遍认为,启蒙运动夸大了理智的作用。事实上,有人认为,正是启蒙运动灌输到现代思想中的对于理智的过度依赖,导致了后启蒙时期种种罪恶的习性。”
但这显然也是把康德排除在启蒙运动行列之外的,因为康德的理性批判本身就是对人类理性之界限的限制。
另一种观点与此相对立,认为康德哲学是对启蒙理念的“奠基”。比如,奥立沃·休尔兹(Oliver R.Scholz) 在其《康德的启蒙方案: 重构与辩护》(Kant'sAufklrungsprogramm: Rekonstruktion und Verteidigung)一文中指出: “康德的全部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都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对启蒙理念的奠基。”
他认为康德哲学主要是通过四个理念来完成这种奠基的,即自由理念、理性的自我认识理念、自然序列与自由序列的合目的性理念以及世界主义理念。显然,这四个理念涵盖了康德哲学的整个体系,因此,奥立沃·休尔兹的观点实际上是把整个康德哲学都归属到启蒙思想之下。
将康德哲学排除在启蒙运动外,显然与史实相悖,因而不足为论,但把康德哲学视为对启蒙的奠基也很成问题,因为康德与启蒙的关系之最根本的方面并不在于他为启蒙运动提供了辩护与论证,而在于他通过对理性的批判对启蒙理念中的一些根本问题进行的反思与修正。这种反思与修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认识方面针对启蒙思想家将理性“自然规律化”的倾向进行了遏制; 二是在自由理念方面针对启蒙思想家把自由与幸福捆绑在一起的做法进行了抵制,并把自由与合法则性熔铸在一起,使自由演变为自律。从这两方面来看,康德在启蒙方面所做的工作与其说是“奠基”,不如说是“重建”,或者说,他对启蒙的推动并不是“顺向的”(奠基) ,而是“逆向的”(重建) 。
一、启蒙的口号与纯粹理性批判
康德对启蒙的重建工作是从重新解读启蒙的口号(即“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 ”) 开始的。他要通过这种方式返回到启蒙运动的起点上去,并将启蒙理念纳入到理性批判的进程中来。康德关于启蒙的专门论著只有 1784 年发表的一篇小短文,即《回答这个问题: 什么是启蒙?》。除了这篇论文外,康德还在至少两个地方谈到所谓的“真正的启蒙”(wahren Aufklrung; die eigentliche Aufklrung) :一是在 1790 年的《判断力批判》中,二是在 1794 年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什么是启蒙?”以及“什么是真正的启蒙?”的问题的提出,这本身就表明他对“启蒙”的理解不同于法国启蒙思想家,否则他就没有必要作此一问,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放弃启蒙的理念,因此他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启蒙的口号进行重新解读。
法国启蒙思想家在提出“要敢于认识”这一口号时,其根本出发点是与追求尘世的快乐和幸福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尚杰先生指出: “卢梭的自由概念决不仅仅是一个词,或简单地归结为一种风格,他的自由之真谛乃是幸福。”“反对基督教只是追求快乐过程的一个副产品,因为宗教限制人们的快乐,不恰当地规范了人们的行为界限。”“自由与平等的性质不仅是道德政治的,更是经济的。”
虽然在启蒙思想家那里对于幸福的理解存在着差异,比如伏尔泰崇尚财富,而卢梭则认为财富所带来的快乐会麻痹人的灵魂,但是,启蒙思想家对于幸福的义无反顾的追求与康德哲学对于法则的无比崇敬还是格格不入的(虽然康德也并不排斥人们对幸福的追求) 。正因为如此,所以康德要正本清源,重新解释究竟什么是启蒙、什么是真正的启蒙以及什么是“要敢于认识”。那什么是启蒙呢? 康德说: “启蒙就是人从归咎于其自身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来。”他解释说,所谓“未成年状态”(Unmündigkeit) ,就是指未经别人的指导就不敢运用自己的知性的状态。因此,启蒙的口号“要敢于认识”其实也就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知性”。
康德将“启蒙”与“要敢于认识”联系在一起,这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没有对启蒙及其口号作出任何实质性的改动,但他毕竟通过这一关联而将启蒙的口号悄悄地转换成一个批判哲学的命题。因此,对于他而言,并非批判哲学需要被归属到启蒙之下,相反,启蒙只有被纳入到批判哲学之下才会真正有利于时代精神的发展。人类为什么“不敢”运用自己的知性(或理性) ?
康德认为,其原因在于懒惰和怯懦。一方面,未成年状态是一种受监护的状态,在此状态下,一切都由别人来操心而用不着自己去烦神。他举例说,我可以通过一本书来取代我自己拥有知性,通过一位牧师来取代我自己拥有良知,通过一位医生取代我自己对饮食起居的评判,总之,我们将一切都交付给监护人,因而可以处于一种十分舒适的状态之下。但康德指出,这种状态只能使人变得像家畜一样越来越愚蠢。另一方面,有些人天生就是喜欢成为别人的监护人。他们通过各种阻吓的手段阻止被监护人走出这种受监护的状态,久而久之,他们使被监护人逐渐喜欢上这种受监护的状态。康德不无讽刺地说,这种喜欢受监护的人即便得到了自由,他们也会因为没有绝对的把握去成功地跳过一条极窄的水沟而不习惯于这种自由。
不过他同时也指出,毕竟有少数有精神修养的人从这种受监护的状态中走了出来。
那如何正确运用自己的知性? 康德提到了理性的公开运用与私下运用: 前者是指一个人以学者的身份发表言论,后者是指一个人以公职的身份发表言论。例如,一位牧师,即便他对当前教会制度的缺陷感到不满,但他作为一位神职人员仍然有义务服从这一制度,他所发表的言论也必须与他的牧师身份相符合,这时,他的言论就属于“理性的私下运用”。但这位牧师也可以通过学者的身份向社会发表他个人的言论,包括批判当前的教会制度与体制,他有充分的自由与责任将自己对教会的看法传达给公众,这时,他的言论就属于“理性的公开运用”。
无论理性的公开运用还是私下运用,都是理性在公开场合下的运用。康德之所以作此区分,是因为他认为以特定公职岗位的身份来发表公开言论,由于必然受到该岗位的职责限制,所以是理性的狭隘运用(也即私下的运用) ; 相反,以学者的身份发表的公开言论,是出于理性的独立思考的产物,并且它是以个人的名义公开发表的,因而要为之承担责任,这就突破了公职岗位的狭隘性。
康德还进一步指出,理性的公开运用实际上也就是学者通过“自己思维”,将思维成果向公众摆明,以供其讨论。因此,他也把启蒙的含义解释成“自己思维”(Selbstdenken) 或“使用自己的理性”(sich seinereigenen Vernunft bedienen) 。在《什么叫做在思维中确定方向?》一文中,康德指出,启蒙并非表现在知识上,而是表现在使用自己的理性上,因为那些知识丰富的人往往在使用自己理性方面很少得到启蒙; 而所谓“使用自己的理性”,也就是指我们对于那些应当接受的东西,要去问一问我们接受它们的根据是什么,我们从接受的东西那里产生出来的规则能否成为理性应用的一条普遍原理。他认为,启蒙运动就其强调“使用自己的理性”而言,实际上是“认识能力的使用中的一个否定原理”。
这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接受什么,都不要盲从,都要先使用自己的理性,即“自己思维”。他说: “自己思维就叫做在自己本身中(也就是说,在其自己的理性中) 寻找真理的至上试金石; 而在任何时候都自己思维的准则就是启蒙。”在《形而上学反思录》中,他也说了类似的话: “被启蒙(aufgeklrt seyn) 就是: 自己思维,在自身中、即在原理中去寻找真理的(至上的) 试金石。”
在这些地方,康德将“自己思维”与“真理的试金石”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什么是启蒙的问题与他的真理论关联到一起。
二、真理的试金石与理论领域中的启蒙
为什么说“自己思维”就是在自身中寻找真理的试金石呢? 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明确康德在真理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康德所主张的是一种符合论的真理观,即真理是知识与对象的符合。由于对象是理性做出来的现象,而非与理性毫不相干的自在之物,所以这种“符合”实际上也就是现象符合于知识,而非知识符合于现象,此即康德所谓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那么,作为现象的对象究竟是如何与知识符合的呢? 康德通过对理性的批判,为我们揭示出这种真理性认识的内在机制,即: 判断力通过想象力(先验图型) 的中介作用以及理性概念(先验理念) 的范导性作用,而将知性范畴运用于感性材料之上。从这种内在机制可以看出,一个真理性判断的做出,实际上是理性之诸认识机能的一个“合力”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判断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与“真理”密切相关的“正确”与“错误”正是在判断力作用的环节产生出来的。康德认为,判断力所可能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把先验理念偷运到知识的领域中来。他说: “一切偷换的错误任何时候都必须归咎于判断力的缺乏,而决不能归咎于知性或是理性。”
不过,康德同时也认为,判断力的这种错误是可以通过不断训练而得到克服的,因为,虽然对于个体来说,是判断力天生的,但它毕竟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而逐渐变得成熟起来。这样一来,真理也就完全成了理性内部的事情(即真理只能是理性的真理) ,因而检验真理的试金石当然也只能在理性的内部去发现。但这与启蒙(使用自己的理性或自己思维) 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指出,“自己思维”的对立面就是“迷信”,启蒙就是破除这种迷信。
他说: “第一条准则(指自己思维———引者) 是一个永不被动的理性的准则。对被动的理性、因而对理性的他律的偏好就叫作成见; 而一切成见中最大的成见是,把自然界想象为不服从知性通过自己的本质规律为它奠定基础的那些规则的,这就是迷信。从迷信中解放出来就叫作启蒙。”
在这里,康德把那种以为自然界可以不服从知性原理的观点说成是迷信,因此,启蒙就是要改变人们在这一问题上成见,而将他们引导到批判哲学的轨道上来。这样,启蒙与纯粹理性批判的工作就贯通起来了。从这里我们也不难发现,康德其实是把启蒙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变革而纳入其批判哲学体系中来的。也就是说,康德对理性的批判,不仅包括对理性的诸要素分析,也包括对理性本身之运用的规定,即对我们的思维方式的规定。他除了把“自己思维”视为知性的准则外,还把“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思维”视为判断力的准则,把“在任何时候都与自己一致地思维”视为理性的准则,而这些都是“思维方式的准则”。他说: “在这里我们谈的不是认识能力,而是合目的性地运用认识能力的思维方式。”
在他看来,如果我们改变了以往的认识方式,即不把自然界看成是自在之物,而是把它看成是现象,那么我们也就抛弃了一切认识中的最大成见,就可以从迷信中解放出来而成为被启蒙的人。这样,我们也就可以到我们的理性自身中去寻找到真理的试金石了。
当然,康德也看到,试图通过启蒙来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人在认识中,对于作为超越者的理念总有一股不可遏制的冲动,因此要“在思维方式中,(尤其在公众的思维方式中) 保持和确立这种单纯否定的东西(它构成真正的启蒙) 是很困难的。”
但是,无论这种启蒙有多么困难,它也要进行下去。因为只有在思维方式上破除这个最大的成见,人类的认识才不至于陷入先验的幻相之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康德把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称为“真正的启蒙”(die eigentliche Aufklrung) 。
由此,康德的启蒙概念在理论理性领域就与法国启蒙思想家表现出不同的取向了。在康德这里,“要敢于认识”所强调的并不是理性可以在认识中一往无前地无限制扩展,而是相反,理性必须为自己的认识范围设定界限,即把自己严格地限定在现象的范围内。但这样一来,康德所谓的通过启蒙(自己思维、使用自己的理性) 而在理性中所寻找的真理,就根本不是什么“绝对的”真理(即关于自在之物的真理) ,而只是在现象中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真理,也即自然科学的真理。对于自然科学来说,这或许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自然科学由此便抛开一切超越者的纠缠而可以轻装前进了; 但是,康德对不可知领域的划分本身毕竟是对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一个极大限制,这对于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在试图通过自然规律来解释一切(包括自由与道德) 时所体现出来的理性无所不能的立场不啻为当头一棒。
不过,康德取消了绝对真理,这与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在反对外在权威的根本目标上并未发生冲突。因为对绝对真理的放弃,这本身就具有反教会的性质。在《圣经》中,上帝始终都与真理联系在一起、甚至与之等同,而现在只有在自然科学中才有真理可言,上帝在认识领域只能作为一个不可知的先验理念发挥着范导性的作用,这就是对教会权威的否定。
总之,就理论领域而言,康德对启蒙的态度实际上是双重的: 我们既要敢于认识,又要明确了解认识的界限。换言之,我们既要敢于进行科学认识,向一切未知领域进军,但同时也要清楚,这些认识无论进展到多远,它们所获得的都不过是现象界的真理,不过是由理性为自然立法而得出的真理。只有明确了这一点,人类才会真正脱离其未成熟状态而获得“真正的启蒙”。
三、自由的合法则性与实践领域中的启蒙
法国启蒙思想家提出了“要敢于认识”的口号,但这一口号却是以“自由”为前提的,即后者是作为前者的条件被提出来的。这也就是说,只要政府允许公民具有言论和出版自由,那么公民也就敢于认识和探索真理了。同样,康德说: “但公众启蒙其自身却更有可能; 甚至只要允许他们自由,启蒙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启蒙所需要的无非只是自由。”
这种作为“自己思维”之条件的自由,康德将它界定为“在所有事务中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康德认为,公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是不应当受到限制的。他说: “作为一个学者……,牧师在公开运用他的理性时便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
但这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 学者的言论也并非一定正确,那么,学者的无限制的自由会不会对共同体的利益造成危害? 而共同体为了维护其根本利益,是否应当对学者的这种言论自由加以限制? 在这一问题上,康德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他认为,如果共同体作出了这种限制,那么它就在做出一种“违反人性的犯罪行为”,因为人性之“原初的规定(天职) ”(ursprüngliche Bestimmung) 就在于启蒙上的不断进步。
这也就是说,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这是出于人性自身的需要,而理性之运用在自由程度上的不断扩展,则是出于人性不断进步的需要,所以学者的自由是不应当受到限制的。
康德的这番言论很容易让人把他与法国革命中一些激进的自由斗士混为一谈,但这仅仅是一个错觉。康德是理性主义者,他对自由的理解完全是按理性的自律原则进行的,因此他越强调学者的言论自由,其实也就越是强调学者的自律。自由等同于自律,这是康德“实践自由”概念的实质。
正因为如此,从自由这一角度来看康德对待启蒙的态度也就明显不同于法国启蒙思想家。他本人也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在自由的问题上也提出了所谓的“真正的启蒙”。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他说: “在这种统一的理性宗教中,教师可以解释所有那些规章制度和诫命的目的,直到能够随着时间的进展,借助于越来越被接受的真正的启蒙(一种从道德的自由产生的合法则性) ,在每一个人都同意的情况下,把一种令人屈辱的强制手段的形式,更换为一种符合道德宗教的尊严的教会形式,即更换为一种自由信仰的形式。”
这里所说的“真正的启蒙”用的是“wahren Aufklrung”,即从一种“真”的含义上来理解的启蒙。“真”(wahr) 与“假”(falsch) 是相对的。难道他认为法国思想家的启蒙是“假的启蒙”吗? 康德当然没有这样说,但他的这种表达本身的确是耐人寻味的。不论他是否作此理解,有一点还是很明确的,即他对于自由的理解完全不同于法国启蒙思想家。
因为他把这种“真的启蒙”与“一种从道德的自由产生的合法则性”直接等同了起来,这也就是说,与康德在理论理性领域限定理性的界限相一致,他在社会政治领域(实践理性领域) 同样也对人的自由进行了限制,因为他认为只有把这种言论自由理解为“合法则性”(Gesetzlichkeit) ,启蒙才有可能成为“真的(wahren) 启蒙”。
在《回答这个问题: 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康德多次提及普鲁士国王腓德烈二世说过的一句话: 可以发牢骚,不论发多少牢骚,不论对什么而发,但是要听话! (rsonniert,so viel ihr wollt,und worüber ihrwollt; aber gehorcht! ) 康德试图通过这句话来表达他在言论自由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一方面,学者的言论自由是不可限制的; 另一方面,这种言论自由必须是合法则性的。他还说: “一种较大程度的公民自由似乎有利于人民的精神自由,但却给它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限制; 与此相反,一种较小程度的公民自由却给这种精神获得了尽其一切能力展开自己的空间。”
这也就是说,自由的程度越大,合法则性的程度也就越高,这才是精神的真正自由,因此言论自由并不需要那种没有任何约束的我行我素,而应始终以合法则性作为它的指导原则。在《什么叫做在思维中确定方向?》一文中,康德对此作了解释。他首先指出人的“思维的自由”是不可被剥夺的,但同时也指出,这种自由必须受到“良知的强制”,否则思维的自由必将会受损,一切最终都只能成为“玩笑”。他说: “思维中的自由也意味着理性除了它自己为自己立的法则之外,不服从任何别的法则; 而其对立面则是理性的一种无法则应用的准则……。因此,所解释的思维中的无法则性(从由理性而来的限制解放出来) 不可避免的后果是: 思维的自由最终由此受损,并且由于绝不是不幸,而是真正的自负对此负有责任,而在该词的本义上成为玩笑。”
四、结语
在启蒙问题上,康德一方面认同法国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即要敢于认识,敢于独立思考,不要为外在的权威所吓倒,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对法国启蒙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以“什么是真正的启蒙?”的发问对启蒙的理论基础进行了重建或改造。这种被改造的启蒙虽然不再具有激进的革命性,但这也正好符合康德对于革命的一般看法。他说: “通过一场革命,也许将摆脱个人的独裁和利欲熏心的或者惟重权势的压迫,但却绝不会实现思维方式的真正改革; 而是无论新的成见还是旧的成见都成为无思想的广大群众的学步带。”
对于康德而言,“思维方式的真正变革”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他对于法国启蒙运动的反思至今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向善的禀赋与趋恶的倾向1793年出版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是康德晚年的一部重要的宗教哲学着作,与三大批判不同,这是一部专门探讨宗教问题的着作,系统地表述了康德的道德神学思想.可以说,在三大批判中基本形成的道德神学思想,在这本书里才系统而全面...
学术界通常将启蒙运动理解为理性的启蒙,这是因为人们秉持一个先入为主且不言自明的观念,认为启蒙运动理所当然地意指法国启蒙运动。如果将启蒙运动的光环仅仅聚焦于法国,不免会遗漏那段历史留下的其他瑰宝。回顾18世纪的欧洲,不是法国,恰恰是英国在各国...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做出了现象与自在之物的区分,并且将这样一种区分也用于对自我的认识上,从而认为可以通过内感官获得关于主体的现象的知识,但那作为自在之物的自我则无法被我们所认识。然而更具有吸引力的是,康德并不满足于这样两种自我,他说:...
一、学识修养:渊博的学识安提斯泰尼是昔尼克或古希腊犬儒学派奠基人。生于约公元前446年,逝于公元前366年,死于肺痨,当时只有他的朋友兼学生第欧根尼在旁。年轻时参军,成为义务兵。后来追随智者高尔吉亚,跟从他学修辞学。①高尔吉亚是一位较苏格...
把自由概念视为现代政治哲学的根基,是政治思想的常识。自由概念根本上与自然概念内在相关,而自然概念的政治哲学意义却常被忽视,这种忽视是当今政治思想混乱的根本原因,各种自由主义之间、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诸多争执多由此而起。如何从哲学上确立...
关于认识论的一切分析和诠证都要从主体方面入手,主体必然成为认识论的根本前提和基本课题,关于主体问题的分析是区别不同哲学的方法问题。这里的主体是指一种有意识、思维的、感觉的、认识和行动的本质,它同一般意义上的人的概念是不等的,主体概念是基于...
一、康德的二律背反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理性(reason)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境地。一方面,理性以感性(sensibility)和知性(understanding)为基础,处于认识的最高层次;另一方面理性不可避免地对人施加某种误导作用,以至产生超验幻象。这种困局的极端形式...
从根本上说,康德的法权概念是一个奠基在实践理性之上的自由概念,只不过这不是一个内在的道德自律意义上的自由概念,而是一个外在的法治社会意义上的自由概念。...
《纯粹理性批判》(以下简称《纯批》)不仅是康德最重要的着作,也是西方哲学史乃至整个人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着作之一.目前,《纯批》已有六个不同的中文译本:一是胡仁源译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也是最早的中译本;二是蓝公武译本,1957年由三联书店初版,19...
从理论与实践上解释宇宙的创生奇点与膨胀本性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就象古人无法了解地球的形状和运动方式一样,因为宇宙太大,并且还存有我们无法感知的物质,比如黑洞只能间接论证其存在。所以我们只能从哲学角度推测宇宙的起源。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