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三毛是20世纪80年代最富有传奇色彩的知名女作家。她丰富奇异的生命历程,洒脱不羁的个性特征,使她的作品拥有一种独特的魅力。研读三毛的作品,发现死亡意识是其挥之不去的存在。论文将从死亡意识这一视角切入三毛文本,解析死亡意识在其文本中的外在显现,即直面死亡、死亡预期与死亡超越,由此试图反观三毛生命意识的闪光点,以及思考其死亡意识可能的积极意义。并且,将三毛的死亡意识回归到她独特的现实经历与宗教情怀两方面,作追本溯源的探究。
关键词:三毛 死亡意识 生命意识 爱 宗教
The consciousness of death in Sanmao's production
Abstract: Sanmao is the most legendary of famous writer in the 1980s. Her richand singular journey of life and unrestrained personality, make her works have aunique charm. By studing her works, we could find the obviously existence ofdeath consciousness. The present thesis, in a perspective of Sanmao's text, triesto clarify the external appearance about "the consciousness of death": to be faced withdeath; to expect the death; to go beyond the death. Then, readers could haveawareness of the glittering contrast in her life and think about the positive sense of herdeath conscious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duction of her death consciousnesscould traces back to the reality of her unique experience and religious feelings.
Key Words:Sanmao; Death consciousness; Life consciousness; Love; Religion
目 录
一、引言
二、死亡意识的文本显现
(一)直面死亡
(二)死亡预期
(三)死亡超越
三、死亡意识的价值追问
(一)“爱”的生命哲学
(二)拥抱自我
四、死亡意识的产生原因
(一)宗教情怀下的死亡思索
(二)现实生活中的死亡阴影
五、结语
参考文献
一、引言
三毛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最富有传奇色彩的知名女作家。她虽然只活了四十八个春秋,但因其丰富而奇异的生命历程,洒脱而不羁的个性特征,一度为海峡两岸读者甚至海外华人读者所喜爱,并在华人圈中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三毛热”。
三毛一生都执着于追求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她常年流浪异乡,写作也只钟情于一个“我”,最后还以一条丝袜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长期以来关于三毛的研究,也多数着眼于三毛的死因探寻、流浪情结以及“我执”创作三个方面,而对于她渗透在生命内里的死亡意识的研究则相对甚少。虽然不少学者认为,在三毛的作品中确实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死亡意识,但专题性研究不多,大多只是涉及而已。有迹可循的谈论三毛死亡意识这一话题的文章在期刊网上仅找到一篇,即罗明誉所写的《谈三毛散文中的死亡意识》(《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这篇论文,作者从死亡哲学的角度解读了三毛和她散文的死亡意识,并归结出“三毛式”死亡意识的特点:“死以继生,生以死结”。
本文在勘察、梳理诸多研究三毛散文的文献基础上,以三毛文本为切入点,对三毛的死亡意识试图作一个系统性阐述。首先对三毛作品中死亡意识的表现形态做出研究,挖掘出死亡意识背后所观照的生存意义以及对其生命走向的可能性影响,并结合其现实经历与宗教情怀浅探三毛死亡意识产生的原因。从而对以往的三毛研究做一个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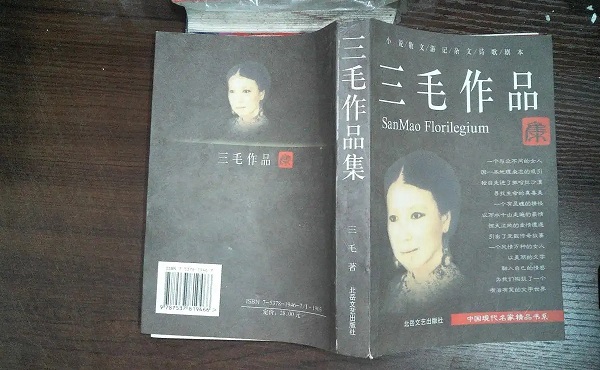
二、死亡意识的文本显现
从原始人类超出动物界之日起,“死”与“生”便是人类无可逃避的话题。
“死亡”作为最高的哲学问题与最高的美学问题,吸引着艺术家们进行诗意的沉思与哲学化的想象,甚至于“以死的冲动去自我实现生命的价值意义,从而达到最本真的存在。”在此基础上,死亡意识一进入文学领域就受到了众多文学创作者的喜爱,并有很多的理论着述问世。譬如,方长安的《死亡之维与新诗研究反思》、霍俊明《死亡现场言说的背后——试论新时期小说的死亡意识》、施津菊《新时期诗歌的死亡意识流变》等自觉将死亡意识纳入现当代文学不可漠视的关键词之一。更有肖百容的学术专着《直面与超越——20 世纪中国文学死亡主题研究》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死亡主题作了系统、全面的阐述。对于“死亡意识”的界定,鲁枢元、童庆炳等人在其编辑的《文艺心理学大辞典》中认为死亡意识是“人类精神对死之本质、方式与价值等问题的自觉与思辨的心理活动。”而人作为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存在物能在死亡中找到更有意义的生存方式。在徐成森《当代散文中的死亡意识》一文中,更是指出死亡意识“能荡涤人的灵魂,携领人们升入超越世俗的崇高境界,以一种宗教般的虔诚来审视生命,审视自身。”尤其是对于文人而言,它是“拷问自身价值和追问民族品性的契机”。三毛作为一个“我执”性格突出的女性作家,在她的许多作品中都透露出深刻的死亡意识。这些关于死亡的思考,既有面对死亡时的绝望与孤独感,也有作为一个较为先进的思想者所特有的抗争意识。
纵观三毛的所有作品,大体上可以将她的死亡意识分为直面死亡、死亡预期和死亡超越三种表现形态。而从这些形态中,我们可以看到三毛在与死亡共舞时所独有的生命体验与生命感悟。
(一)直面死亡
我这里所谈论的“直面死亡”,并非指三毛自身的生命受到了死亡的威胁(虽然三毛确实曾有多次收到死神的请帖),而是指在她的一生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他人之死。他人的死亡仪式是认识死亡的开始,它是人们原始性的死亡经验。三毛对死亡的体验也是从他人之死上获得的。这些原初性的死亡认知,给了三毛直面死亡时的震撼与情感上的强烈波动,同时也为她今后思考生思考死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素材。可以说三毛的死亡意识就是由他人之死开始萌发的。
三毛在她极其年幼的时候,就接触到了死亡。她父亲曾谈到关于三毛小时看杀羊的事,他说当时的三毛“对于年节时的杀羊,她最感兴趣,从头到尾盯住杀的过程,看完不动声色,脸上有一种满意的表情。”(《我家老二——三小姐》)一个如此年幼的孩子,面对死亡不仅没有一点恐惧,反而有一种满意的表情,这不得不让人惊讶。或者说,死亡意识的种子从三毛孩提时代就已种下了。
随后,死亡阴影一直伴随三毛左右。面对好友 S 的自杀,三毛第一次歇斯底里的喊出那句惊世骇俗的话来——“我要把一件事情在心里对付清楚——我要绞死自己,绞死爱情。”(《极乐鸟》)可见,三毛在懵懂的年龄就已受到死亡的诱惑。后来,经历未婚夫的猝死、师母的病逝、荷西的意外身亡,以及撒哈拉沙漠里那些鲜活生命的骤逝,三毛一次又一次地直面到死亡鲜血淋漓的一面。无处不在的死亡景象,观照在她的作品中,就呈现出诡秘而伤痛的死亡文字。
他人的死亡,一方面使三毛体会到生命的无常与死亡的悲剧性,另一方面,使她因着死亡的创伤性记忆激发了她创作的动机,在晦涩的死亡背景下对于生的思索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同时生命的短促无常也让三毛领悟到活着是多么的不容易,生命亦是如此可贵。
(二)死亡预期
死亡预期,是指三毛在获得大量的他人之死的感性素材的基础上,从理性角度来审视与思考本己死亡的心理状态,是一种对死亡的期待感。他人之死,让三毛直接接触到死之世界,并给她的死亡观增添了非理性上的感悟,而三毛通过对本己死亡的思考,则在理智与非理智的碰撞中,逐渐建构起她的死亡大厦的轮廓。纵观她的所有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三毛对于本己死亡的预期有着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从初始的恐惧到中间的达观,直至最后的“渴望死”。
少年时期的三毛,孤僻、倔强又冷漠,在其父亲陈嗣庆《我家老二——三小姐》中也曾谈到“三毛小时候很独立,也很冷淡,她不玩任何女孩子的游戏,她也不跟别的孩子玩。在她两岁时,我们重庆的住家附近有一座荒坟,别的小孩不敢过去,她总是去坟边玩泥巴。”如此怪异的性格和离群索居的生活,使得三毛幼时充斥着一种鲜明的孤独感。而对于挣不脱的成长的无力感,使得她用来感知周围事物的心灵更加敏感而纤细。在《蝴蝶的颜色》一文中,小小的三毛如此写道:“每天面对着老师的口红和丝袜,总使我对于成长这件事充满了巨大的渴望和悲伤。”对于囚禁于书本和学校的三毛而言,二十岁意味着可以挣脱牢笼,二十岁就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然而,当时的三毛“才只有这么小”。
渴望成长而不得的无奈,使得三毛内心充满了无法排遣的苦闷:
“想到二十岁是那么的遥远,我猜我是活不到穿丝袜的年纪就要死了,那么漫长的等待,是一个没有尽头的隧道,四周没有东西可以摸触而只是灰色雾气形成的隧道,而我一直踩空,没有地方可以着力,我走不到那个二十岁……。”《雨季不再来·蝴蝶的颜色》
当时的三毛正值花季年龄,但是对于生命却充满了“走不到二十岁”的悲观情绪。这种长不大、冲不出去只能死在桎梏中的恐惧,使得三毛朦胧地感受到死亡的无情威胁。在这种极具个人情绪的片段遐想中我们可以依稀看到少年时期的三毛对于死亡的初步摸索。
后来,随着个人阅历的成熟与观念领域的广度加深,经历过无数次的生离死别的考验,三毛逐渐摆脱了少年时期的“维特之烦恼”,对于生命与死亡这一组永恒命题的透视与内诉也更加深刻。尤其是撒哈拉之行后,三毛的死亡观逐渐豁达起来。对于死亡,更是秉持着一种坦然而淡定的态度:
“我的朋友,我想再问你一句已经问过的话,有谁,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孤独的生,不是孤独的死?青春结伴,我已有过,是感恩,是满足,没有遗憾。”《梦里花落知多少·明日又天涯》
蒙太捏说过,生命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长短,而在于我们怎样利用它。在三毛看来,她的一生喜怒哀乐尝遍又活得自由自在,因而属于她的这份生命厚度已经足够充实而深刻,所以,面对死亡的恐惧也早已消散。她可以坦然地说“没有遗憾”,甚而去追寻一种“自由的死”的生存方式。三毛始终在追求一份生命的完满,体现在她的死亡意识上就是“生以死结”。这样的想法,影响到后来,使得三毛在后期产生一种“渴望死”的执念。在她后期的很多作品中,三毛不止一次的去设想她的死亡情景:
“我很方便就可以用这一支笔把那个叫做三毛的女人杀掉,因为已经厌死了她,给她安排死在座谈会上好了,‘因为那里人多’——她说着说着,突然倒了下去,麦克风嘭的撞到了地上,发出一阵巨响,接着一切都寂静了,那个三毛,动也不动的死了。大家看见这一幕先是呆掉了,等到发觉她是真的死了时,镁光灯才拚命无情的闪亮起来。有人开始鼓掌,觉得三毛死对了地方,‘因为恰好给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她又一向诚实,连死也不假装——。”《梦里花落知多少·云在青山月在天》
三毛以如此冷静而触目惊心的笔触来叙说自己的死亡场景,犹如一个旁观者,在目睹一个与她毫无相关的人的死亡事件,而自己只是作为理性的记录者而存在。虽然在这篇文中,三毛主要是表达了她不堪世俗纷扰的苦闷,但字里行间的“渴死”情绪是令人无法忽视的。因而,当三毛最后用一条丝袜结束自己的生命时,我们或许可以把它当做是三毛“渴望死”的有力证明。
死亡预期,是三毛在清醒的意识下剖析自身命运的一种思考方式,是在本己之死的必然性的背景下,对死亡所作出的初步的抗争与痛苦的思索。在这种热烈的内心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三毛对个体价值不懈的探寻。
(三)死亡超越
面对生命中存在的困惑与求不得的悲伤,死亡可以说是另一种希望与超脱。
三毛在经历了直面他人之死与预期本己死亡之后,对生命和生活的理解存在着较之生命或者说不死这种终极价值更深一层次上的领悟。“对死亡恐惧的征服和直面死亡的承担即是对死亡的超越。”三毛一生都是在追寻这种超越死亡的生活方式,无论是看淡生死的豁达,还是敢于承担那些“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的勇气,她以自己“跑出一般人生活着的轨道”的个性化心态来追问死亡的“非终极性”,并作出了对死亡的挑战。从文本上看来,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生命的永恒重现中实现死亡的超越。尼采认为,“一切都永恒的回还,我们也无数次的回还,一切与我们同在。”三毛也坚信生命的永恒性。在她看来,人能够在这无限循环的生命圈中肯定自己,祝福自己,找到生命的答案。而死亡只不过是人生的一个中转站。
在《厄瓜多尔纪行》中,三毛讲述了一个前世今生的故事。那个名叫“哈娃”的印第安加那基姑娘,在银湖之滨展开了她短暂的一生。继承了外祖父药师的身份,秉承神的旨意,无偿的为村民们治病,却只因偷吃了几条禁忌的银鱼而遭受神的惩罚,怀着未出生的孩子一同陨去,与深爱她的丈夫永久别离。
在那样一个凄美的故事里,三毛认为自己就是那位姑娘的转世。而当三毛今生第一次来到银湖时,就有一种“看了只是觉得归乡”(《银湖之滨——今生》)的感觉。三毛将自我游离于生命躯体之外,灵魂皈依于那片理想的净土。三毛通过这个虚构的世界探寻生死之谜:
“夜间的高原,天寒地冻,而我的心思,在这儿,简化到零。但愿永不回到世界上去,旅程便在银湖之滨做个了断,那个叫做三毛的人,从此消失吧”《银湖之滨——今生》
现实生活中,无解的爱情希望破灭,困于心灵囹圄的三毛,从杜撰的这一个前世中寻求生命的奥义。死的人会去向何处?生的人又自将何来?前世的自己在心爱之人怀中逝去,而今世却换了另一人早先离开。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我们的生命也将这样一轮轮继续下去,那么死亡又有何惧怕?三毛最终定下结论:“生与死有爱就隔不开” 。
第二,勇于接受生命的承担。三毛将死亡作为考验生命韧度的契机,是上帝赋予的能力。她认为超越死亡就是要勇敢地担起生命的责任。这在她《梦里花落知多少》的一篇文章《归》中可以得到佐证。
当时的三毛经历了丈夫荷西的意外身亡。对于之前正身处于一段异常幸福的日子里的三毛而言,始料未及的死亡到来,使她切身体会到生命仿佛是一场生死的交替,宁静总会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而幸福总是那么短短的一瞬:
“苍天,你不说话,对我,天地间最大的奥秘是荷西,而你,不说什么的收了回去,只让我泪眼仰望晴空。”《梦里花落知多少·梦里花落知多少》
面对至爱之人的死亡,三毛在经历了一次次对死神的扣问与心理沉淀之后,获得了超越死亡的力量,那就是“生的责任”。在《归》一文中,三毛领悟到,人立于世,不是单一的个体,而是与周围许许多多的生命体联系在一起的。父母、师长、亲友、读者,很多人与她休戚与共,而她的爱人荷西只是这么多人中的一个。因而,这个世界还是有她生存于世的意义。她说,“我们来到这个生命和躯体里必然是有使命的,越是艰难的事情便越当去超越它,命运并不是个荒谬的玩笑。”(《归》)在与命运抗争的时候,她明了“毕竟,先走的是比较幸福的,留下来的,也并不是强者,可是,在这彻心的苦,切肤的疼痛里,我仍是要说——‘为了爱的缘故,这永别的苦杯,还是让我来喝下吧!’我愿意在父亲、母亲、丈夫的生命圆环里做最后离世的一个……”(《不死鸟》)
生命的使命感促使三毛挣脱开死亡的枷锁,在父母亲情的感召及友人的劝说下,暗咽下死别时的碎心又碎心,化作“不死鸟”继续前行。在台湾定居后,三毛马不停蹄的在大学授课,到公众间去演讲,她还开办了三毛信箱来回馈读者,不厌其烦地告诉她的读者学会去爱人、爱自己。三毛通过广施博爱的方式来支持自己生命的燃烧。
三、死亡意识的价值追问
在三毛死亡意识的外在显现中,我们可以看到三毛一步一步迈进死之世界并对其进行理性的思考与探索,甚至以自我生命历程为参照来尝试超越死亡的大门。而“生”与“死”本来就如一对孪生的兄弟,三毛在思考着死的时候可以说也是她在从死亡身上观照自我的生命价值,是想在死亡的命题中找寻自己生存于世的方式与意义。
美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保罗·蒂利希认为“‘存在’是生命,是绵延,是创造;而‘非存在’就是包含在生命中的死亡,包含在绵延中的停顿,包含在创造中的毁灭。”他将“存在”看作是克服“非存在”的永恒斗争,把对死亡的肯定从属于对生命的肯定,而三毛恰恰把前后的位置调整了一下,在她看来,正是“非存在”使得“存在”有了意义,正是通过对死亡的肯定,生命的价值才得到了确认。三毛从死亡身上得到了痛苦而隐忍的情感体验,将体验死亡作为最深刻的体验存在的方式。她一方面确立了以“爱”为中心的生存哲学,以摆脱死亡的可怖性;另一方面,她则是执着的探索“成就之死”,即通过追寻“情感的归依”与“自我生命的展现”来赋予自己新的生存意义。
(一)“爱”的生命哲学
三毛说,“爱,是人类唯一的救赎,它的力量,超越死亡。”(《爱,是人类唯一的救赎》)。这是好友 Irene 来信告诉三毛自己的父亲去世时三毛在回信中安慰友人所说的。在三毛看来,“在这世界上,没有人能单独地消失,除非记得他的人,全都一同死去”(《爱,是人类唯一的救赎》)。因而,死亡并不是一件令人悲伤恐惧的事,而爱是克服对死亡的恐惧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
三毛生性善良,在家里又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影响。同时因对基督与佛教的喜爱,使她深知“爱‘人’”这一大义。所以,对“爱”的信仰,是她一生的处世宗旨,也是她抗争死亡、寻求生死之谜的方式。在她答高雄的听讲者问题时,她引用过《哥林多前书》里的一段话来诠释“什么是爱”: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已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这一段话阐释了三毛一生中对爱的定义,也是三毛践行“爱”的生命哲学的要义。“忍耐、恩慈、包容、相信”,一向是她为人处事的原则。在三毛的一生中,充满了痛苦与难题,是“爱”让她找回自己存在于世的意义,更是帮助她在情感上接受死亡,在理智的达观后衷心赞美生命的甜美。
对三毛“爱”的生命哲学的阐释,可以首先从她对待亲情、友情以及爱情的态度上来看。尤其在亲情方面。三毛小时性格极端孤僻,又常常做一些常人觉得怪异的举动,而对于这个令他人头痛的二女儿,三毛的父母却给予了最大的包容。所以,三毛一生都怀揣着深深的歉疚与无尽的感激。在《背影》一文中,三毛道尽了父母对她无私的关怀:
“母亲踏着的青石板,是一片又一片碎掉的心,她几乎步伐踉跄了,可是手上的重担却不肯放下来交给我,我知道,只要我活着一天,她便不肯委屈我一秒。
回忆到这儿,我突然热泪如倾,爱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那么辛酸那么苦痛,只要还能握住它,到死还是不肯放弃,到死也是甘心。”《梦里花落知多少·背影》
当时失去丈夫的三毛正遭受晴天霹雳的痛楚,但坚守在她旁边的父母那苍老的背影却成了三毛心中永远的丰碑。父母对她的拳拳爱女之心,让她挣扎出死亡的阴影,重拾生活下去的勇气。也正因此,三毛更是坚定了以“爱”为中心的生存哲学。她希望用他人给与的爱来构筑自己的堡垒,以传播这份爱的方式来抵抗来自外界的苦海的沉沦与死亡的侵袭。
三毛摆脱了狭窄的自我空间,将那颗博爱世人的心高举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之上,以此来不断追寻对于生死的堪破与人生价值的追求。这也是三毛“爱”
的哲学的真谛所在。在原始的撒哈拉沙漠居住时,三毛与当地的沙哈拉威人一向是平等相处。她从不以为那些“沙黑毕”(奴隶)是低等人群,也没有浅薄的种族优越感。她忍耐着那些“芳邻”有借无还的行为,并耐心教给她们知识;她照顾着贫苦的一无所有的哑奴一家,并为哑奴有一颗感恩的心而感到感动;她甚至只因监牢里犯人对荷西一句善意的“告诉”而特地置备下珍贵的可乐与烟来感谢。因为“每一粒沙地里的石子。我尚且知道珍爱它,每一次日出和日落,我都舍不得忘怀,更何况,这一张张活生生的脸孔,我又如何能在回忆里抹去他们。”(《搭车客》)三毛以一颗赤子之心来给予沙漠上的这些人尊重与爱护。在她看来,生命的光彩在这些挣扎着生活下去的人们身上得到了最大的彰显,没有什么比生命的生气更令人感动的了。此时的三毛把目光投向芸芸众生,并付诸于深沉博大的人类之爱,因此,爱让她找到超越死亡的力量,更是找寻到生存于世的意义。
(二)拥抱自我
生与死的二元对立使得人类只有在强烈的死亡意识催促下才会更加珍惜现有的生命,才会懂得如何在短暂的一生中维护生命的尊严与保全个体的完整性与独立。三毛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现代知识女性。她的一生又伴随着无处不在的死亡阴影,因而,她对保有自我、坚持自己的本性生活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执着。
“你不可改变我”不仅是当时新女性话语的集中体现,更是三毛终身追求的目标。
“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世界上‘放弃’我们,除非我们自暴自弃。我们是属于自己的,并不属于他人。”《谈心之十四》
作为一个女人,三毛将爱情、婚姻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这必须是在保有自我的前提之下。她明白地说,“我不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支持者,但是我极不愿在婚后失去独立的人格和内心的自由自在化,所以我一再强调,婚后我还是‘我行我素’,要不然不结婚。”(《沙漠中的饭店》)她充分尊重着荷西的独特性格,同时也从不停下追求自我的脚步。即使生活在物质条件极其恶劣的沙漠中,她也力所能及地按照自己的个性来打造属于他们的“罗马”:棺材板铺上厚海绵垫就是一张长沙发,快腐烂的羊皮用“色伯”硝出来就成了一张坐垫,还有大汽水瓶插上一把野地荆棘,就有痛苦的诗意……(《白手起家》)三毛一向跳出常人所走的轨道,活出属于自己的本真色彩,就如她自己所有的那份固执“别人指定的东西,我就不爱去看它。”(《天梯》)
三毛的那份保有自我的清醒与内心的自由自在,使得三毛对于人世的真相更是有着天才般的直觉与敏锐。她意识到“生活,是一种缓缓如夏日流水般地前进,我们不要焦急我们三十岁的时候,不应该去急五十岁的事情,我们生的时候,不必去期望死的来临,这一切,总会来的。”对于死亡,三毛更是透着一份冷静与自持。这份强烈的自我觉醒意识,使得三毛看破了生死之谜,找到了自我生存于世的方式。这是三毛从死亡身上观照到的生命价值的另一种追寻。
四、死亡意识的产生原因
死亡意识是三毛作品中挥之不去的存在。那么什么才导致了三毛作品中死亡意识的如影随形?我们可以试图从三毛的宗教情怀与独特的现实经历两个方面作一个理性上的追根溯源。
(一)宗教情怀下的死亡思索
死亡与宗教一直是形影不离的。当代着名分析—科学哲学家罗素认为“对死亡的恐惧是宗教的基础。”根据罗素的观点,如果能破除宗教信条的迷信,对死亡的一些恐惧自然不复存在。然而,作为芸芸众生的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死亡的恐惧仍可能时常缠绕心头,宗教的信仰仍是最可靠的精神慰藉”三毛死亡意识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她宗教信仰上的影响。三毛自认为是个基督徒,然而对于佛教文化亦是情有独钟。在她的一生中,关于生命、死亡、爱情、痛苦,都浸润着基督教文化与佛教文化两种文化的影响。
有关生死之谜,她相信着佛教中的因果缘起论,同时也坚信耶稣给以生命洗礼予以重生。
基督教是三毛死亡意识产生的重要来源之一。三毛从小浸染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氛围中,她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母亲告诉我:‘妹妹,我们要相信耶稣,信耶稣可以得永生。’我很认真地又一次点头。在我学讲话的时候,爸爸妈妈伯伯嬷嬷——我的大伯母,是共同存在的大人物,还有一位就是耶稣。我实在不知道它是谁,怎么每天晚上睡觉以前,母亲总是带了头要我们小孩子闭上眼睛,然后母亲就开始‘求你——求你——求你——’了呢?于是,我了然了,耶稣是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正如只有我看见过门房婆婆口中飞出去的白蛾一样,别人是看不见的。所以耶稣是一种比飞蛾更奇妙的东西,因为连我也看不见,一次也没有见过。”《但有旧欢新怨———金陵记》
上帝、耶稣、圣经、十字架等对于三毛来说是异常熟悉与特别的。这些独特的语汇和意象,潜移默化地植根于三毛的精神世界中,不仅丰富了三毛的想象空间,更是开阔了她的死亡境界。可以说,三毛对于死亡的达观态度也部分受到基督教永生观念的影响。基督教相信,每个人都是耶稣精神共同体的一部分,都因为信仰耶稣基督而得到永生。就如基督教对死亡的回答那样:“在耶稣基督中复活。”死亡是永生的开始,是进入上帝殿堂的开始,没有死亡便没有永生,那么死亡又有何畏惧?所以,三毛面对身边至亲之人的死亡,依靠对永生的信仰而慢慢收拾起破碎的心,直至能够坦然面对死亡。就如《不死鸟》中所说:“总有那么一天,在超越我们时空的地方,会有六张手臂,温柔平和的将我迎入永恒,那时候,我会又哭又笑的喊着他们——爸爸、妈妈、荷西,然后没有回顾的狂奔过去。”三毛寄希望于在永恒的时空里与业已离世的人重聚。
对上帝的信仰,另一方面使三毛忠诚的秉承上帝的旨意来恒爱世人:
“感谢上帝,给了我永恒的信仰,他迎我平安地归来,又要带着我一路飞到北非我丈夫的身边去。我何其有幸,在亲情、友情和爱情上,一样都不缺乏。
我虽然掌握着我生命小船的舵,但是在黑暗里,替我挂上了那颗在静静闪烁的指路星的,却是我的神。他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在我心的深处,没有惧怕,没有悲哀,有的只是一丝别离的怅然。
因为上帝恒久不变的大爱,我就能学习着去爱每一个人,每一个世上的一草一木一沙。”《撒哈拉的故事·回乡小笺》
在上述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三毛对于自身命运痛苦的关照在与神灵的际遇中获得心灵的安宁,她努力朝着神指引的方向前进,去体悟自我的生命历程。基督教以人格至上、牺牲宽容、平等博爱、赎罪忏悔为精神要义,三毛就身践力行地去爱“每一个人”,爱“世上的一草一木一沙”。
在三毛的作品中,还时常流露出对佛教的喜爱。这不仅与佛教是台湾地区信仰者最多的宗教有关,更因为佛家思想契合了三毛的人生经历。三毛一生都不平顺,尤其在情感路上颇为坎坷。根据佛教理论,人的一生都被苦海包围,即为佛经中的“苦谛”说,它包括了“生、老、病、死、爱别离、怨僧会、求不得等痛苦”而三毛一生正是尝尽这些苦楚,所以佛教教义轻易就拨动了她的心弦,她尝试用佛学所提倡的淡泊与宁静去化解人生的苦痛。
菩萨微笑,问:“你哭什么?”
我说:“苦海无边。”
菩萨又说:“你悟了吗?”
我不能回答,一时间热泪狂流出来。
我在弥勒菩萨的脚下哀哀痛哭不肯起身。
又听见说:“不肯走,就来吧。”
我说:“好。”
这时候,心里的尘埃被冲洗得干干净净,我跪在光光亮亮的洞里,再没有了激动的情绪。多久的时间过去了,我不知道。
“请菩萨安排,感动研究所,让我留下来做一个扫洞子的人。”我说。
菩萨叹了口气:“不在这里。你去人群里再过过,不要拒绝他们。放心放心,再有你回来的时候。”《万水千山走遍·夜半逾城—敦煌记》
出世与入世,菩萨告诉三毛须放开心房,继续在红尘中的修行。因为人身来到这世上极为难得,而人生又短促无常,足以说明生命可贵,所以要懂得珍惜人生,爱护生命。这种关爱不仅讲求爱护人的生命,更要将关爱延及人类以外的各种生物。在三毛的作品中明显的表现出了对生命的珍爱:三毛看见碗中有蚂蚁,就故意在碗周围放上糖,以勾引它们出来,甚至是给它们铺出一条糖路,引诱它们逃生。因为三毛认为,她没有去剥夺一个没有攻击她生命的生命的权利。自然界的各种生命都进入了三毛关怀的视野,因而对于蚂蚁这类微小的生命都使得三毛怜惜。
(二)现实生活中的死亡阴影
作家的生活经历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在作品中,成为影响其创作的重要因素。
三毛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女子,她独特的生活经历是研究其死亡意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这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疾病的困扰。三毛在作品中描写死亡,和她的身体状况也有关系。
三毛有过敏性鼻炎、痉挛性胃痛、剧烈呕吐、下体流血,身体上的病痛,使得三毛直接接触到生命的脆弱与隐忍。
“病人的一个显着特征,是往往不得不从其日常生活中被隔离出来,失去同自然、自我、同伴和精神世界的真正联系。因此,疾病而有的情感意态带给文学创作的影响,可能是使之受到妨害而局限在一个特定的领域,没有超出个人身心或自己主观范围内,成为自我的回音般的呻吟;或能在创造过程中将自己的主观经验赋于普遍意义,既表露出一种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观照和守护,又从中透出对我们生存情状的感悟和省察。”
对于身患疾病的作家来说,疾病和死亡始终威胁着他们的生命,给他们的心理造成重创。三毛之所以在作品中大量地描写死亡,不能不说是与她在生活中的疾病带来的创伤经验密切相关的。而且,我们从她的死亡描写中,还能感受到心灵深处的恐惧,这也是疾病和死亡给她心理留下的残余物。恐惧死亡是人类普遍的心态,三毛毕竟也是普通人,她不可能完全超越人的最基本的思维定式和精神素质。因此,在面对死亡时也会表现出恐惧的心理。1991 年 1 月,三毛住院期间曾写过一封信给倪竹青老人,信中写道:
“我非常累,写不动信,一周瘦一公斤。快速地十二月两度入院。……寿衣想来很好看,我到是也去做几件备着。人生一场,劳劳碌碌,也不过转眼成空。”
在给倪竹青老人的这封信件中,三毛详细诉说了以前未告知人的病清,而且明显流露出厌世与自杀之念。疾病不仅给三毛带来了身体上的痛苦,同时因这时时相随的隐痛,更是带来了精神上的压抑与苦闷。而三毛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尝试运用文字来超越身体的痛苦,用创作中宣泄的愉悦来抵抗疾病带来的精神创伤,是她身为作家这样一类孤独的思索者潜意识支配下的行为。可以说,三毛身体上的苦痛,使她有了产生死亡意识的契机,甚而影响到她的整个创作历程烙印下死亡这一印记。
第二,流浪的经历,尤其是撒哈拉之行。三毛一生走遍了世界 59 个国家,从西班牙到撒哈拉沙漠,从中南美到加纳利群岛,从台湾到祖国大陆。在这接连不断的漂泊中,没有哪一次能像撒哈拉那样给三毛“乡愁”似的感觉。奔赴撒哈拉,是她厌倦城市文明的一场出走。
“高度文明的社会,我住过,看透,也尝够了,我的感动不是没有,我的生活方式,多多少少也受到它们的影响,但是我始终没有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将我的心也留下来给我居住的城市。”《撒哈拉沙漠·白手起家》
现代文明给人类带来巨大的便利之时,高速膨胀的物质文明与呈荒原状态的精神文明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得三毛困顿于这个灯红酒绿的社会。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与孤独感迫使三毛渴望逃离城市的喧嚣,因而那片还未被现代文明侵染的半原始土地——撒哈拉沙漠——成为了三毛诗意的栖息地。尽管物质上极其匮乏,环境恶劣,但是原始文明的古朴自然以及当地人独特的生命方式,点燃了三毛的生命激情。在这段旅程中,三毛强烈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对于自己的生存方式与生命意义有了全新的体悟,死亡意识更是得到了思想上的升华。
生与死的交替,是这片土地上最鲜明的活动。“如梦如幻又如鬼魅似的海市蜃楼,连绵平滑温柔得如同女人胴体的沙丘,迎面如雨似的狂风沙,焦裂的大地,向天空伸长着手臂呼唤嘶叫的仙人掌,千万年前枯干了的河床,黑色的山峦,深蓝到冻住了的长空,满布乱石的荒野……”(《收魂记》)原始的荒漠中携刻着森森的死亡之气,带给三毛一场死亡阴影下的视觉冲击。但是,这些景象毕竟是死物,唯有人情最能震撼人心。遥远而清晰的“沙漠大屠杀”还近在眼前,而那个沙漠军曹却毅然放弃了个人仇恨“在最危急的时候,用自己的生命扑向死亡,去换取了这几个他一向视做仇人的沙哈拉威的孩子性命”(《沙漠军曹》),这种跨越了种族界限与个人仇恨的人性光辉,使得三毛的内心深受震动;而另一方面好友巴西里、奥菲鲁阿、沙伊达的惨死,却让三毛看到了殖民统治下的沙哈拉威人人性尊严的丧失与自相残杀的愚昧。在令人顿足的痛惜之下发出了对死的感叹:“是的,总是死了,真是死了,无论是短短的几日,还是长长的一生,哭、笑、爱、憎,梦里梦外颠颠倒倒,竟都有它消失的一日。”(《哭泣的骆驼》)
三毛开拓了一个空前的、许多人难以想象的,却是极真实的生活领域,死亡在这片沙漠上扎根生长,三毛亦是在这片到处有着生有着死的土地上屡屡受到来自灵魂的冲击。在这片土地上,死亡是习以为常的,不仅是生物还有人的生命都短促无常。可能前一刻还在你面前的人在下一刻就已毫无生息。也正因此,生命在死亡的映衬下更显张力。与此同时,这里跨越了不同种族之间的生命接续,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撒哈拉沙漠,不仅是三毛获取死亡材料的重要阵地,更以它独特而丰富的生存方式提升了三毛的精神世界与生命意识。在这片半原始的土地上,三毛在死亡的随行下不断完善自我价值的追问。
第三,爱情的毁灭。有关爱情,三毛说过:“我的写作生活,就是我的爱情生活,我的人生观就是我的爱情观。”可见,三毛是一个主情主义作家,她的创作灵感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她的爱情观与爱情生活。也正因此,三毛文本中的死亡意识也颇受她的情感经历影响。
三毛一生情路坎坷,初恋失意,未婚夫又猝死,多次的爱情寻觅最终落得碎心遍地。而当三毛认为终于找到能够执手到老的荷西时,为期六年的短暂婚姻却成为了她日后痛苦的根源。荷西的意外去世,给三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三毛的好友张君默曾因此感叹过:“命运象一根拔河的绳子,你只能握住一半。”而三毛的确曾经紧紧地握住了一半,却是给拔倒了,而且还一头栽进了深渊。一句“再也不会有三毛,他死了我也死了”的话,反映出来的是三毛刻骨蚀心的痛。
荷西的离开,不仅打乱了三毛的全部生活节奏,更是影响到她的创作中来。
从后来的《梦里花落知多少》、《背影》等集子中可以看出,三毛的创作风格一改撒哈拉沙漠时期的轻快明朗,带着明显的创伤性的痛苦与晦涩。而在这个时期,“梦”这个词也频繁出现在作品中。三毛还常常幻听,能看到别人所不能看到的东西,所有神秘的物事在作品里交织成一种玄之又玄的气息。
我仿佛又突然置身在那座空旷的大厦里,我一在那儿,惊惶的感觉便无可名状的淹了上来,没有什么东西害我,可是那无边无际的惧怕,却是渗透到皮肤里,几乎彻骨。
我并不是一个人,四周围着我的是一群影子似的亲人,知道他们爱我,我却仍是说不出的不安,我感觉到他们,可是看不清谁是谁,其中没有荷西,因为没有他在的感觉。
好似不能与四周的人交谈,我们没有语言,我们只是彼此紧靠着,等着那最后的一刻。我知道,是要送我走,我们在无名的恐惧里等着别离。 《梦里花落知多少·梦里梦外》
从以上文字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三毛内心的彷徨与独身一人的恐惧。在那一段漫长的等待“别离”的时间里,三毛一步步地接近终点,就像是一场死亡的献祭。“有人上车,有人下车,好似只有我,是驶向终站唯一的乘客。”(《梦里梦外》)句子里透露出的是三毛对于现实生活中生离死别的迷惘与困惑,而“我”的“唯一”性更是指向她个人在生命旅途中所负有的孤独感与死亡带来的精神负重。整篇文章现实与梦境交替出现,一度让三毛产生“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的怪诞想法。也是在做这种怪圈中,三毛不断地进行她的死亡意识的建构与完善,更是找寻到人生苦痛的根源——“苦海无边”。
爱情的破灭,使三毛经历了人生的大痛,甚至让她的生命几度面临死亡的威胁。生之无奈与死之诱惑使她不断地徘徊于自毁与重建之间。死亡意识的思考因此达到了顶峰。
五、结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是死亡意识全面苏醒的时代。在诸多文学作品中,作家们直接以死亡为书写对象,表达着现代人面对死亡时的态度与思考,即从死亡反观生存的意义。而台湾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陆的影响。
三毛作为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不仅因为她独特的个人经历打上死亡意识的印记,从而表现和完成她个人角度关于生命意义的追问,而且,通过她对死亡意识的书写,更是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台湾的都市人群面对高度发展的城市文明与呈荒原状态的精神文明之间产生的巨大落差所导致的迷惘与烦闷。因此,研究她作品中的死亡意识并非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
本文从三毛的文本出发,对三毛在作品里呈现出来的直面死亡、死亡预期以及死亡超越三种死亡意识的外在显现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进而去追问她关照在死亡意识中的个体的生命价值,即用“爱”来撑起个体的生命世界,并以保有自我的方式来进行生存意义的思索。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到三毛作品中的死亡意识的大体建构。在此基础上,从三毛的宗教情怀与个人经历两个方面来试图对她的死亡意识的产生进行探究,则进一步的弄清了三毛死亡意识的前因后果,在总体上获得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有她的死亡意识的理论阐述。
三毛虽然以一条丝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我们并不能因她最终走上自毁之路而否认她对于生命的热诚与珍爱。就如她自己评价的那样:“我的这一生,丰富、鲜明、坎坷,也幸福,我很满意。”(《流星雨·假如。还有。人生。》)三毛将自己无私的大爱洒向人间,她保有自己鲜明的人格,她是生命实在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她的一生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思考:面对人世间生老病死的大痛,如何才能求得内心的安宁与人格的完整?作为一个知识女性,生活在这样一个生活价值混乱的世界中,如何才能走向生命的自我实现?这些都是值得要研究者们仔细考究与认真探寻的。
参考文献
陆士清:透明的黄玫瑰--论三毛的散文创作,《台湾文学新论》,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43-353 页。
陆士清(杨幼力、孙永超):《三毛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 年 6月版。
山石:《三毛三毛》,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 年版。
三毛等:《三毛昨日、今日、明日》,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 年 1 月版。
刘兰芳:《美丽与哀愁--一个真实的三毛》,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年3 月版。
潘向黎:《阅读大地的女人》,台北业强出版社,1992 年 1 月版。
赵章云:《在西撒哈拉踏寻三毛的足迹》,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 年版。
孙利天:《死亡意识》,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4 月版。
颜翔林:《死亡美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年 10 月版。
段德智:《死亡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 8 月版。
刘自然:死亡意识,《南京大学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 年第 5 期。
论文将从死亡意识这一视角切入三毛文本,解析死亡意识在其文本中的外在显现,即直面死亡、死亡预期与死亡超越,由此试图反观三毛生命意识的闪光点,以及思考其死亡意识可能的积极意义。...
本文着重于对于爱情观的分析,分析爱情必然离不开人,三毛在《滚滚红尘》的前言中提到过“在剧中人——能才、韶华、月凤、谷音、容生嫂嫂以及余老板的性格中,我惊见自己的影子。”...
萧红的小说里描写最出色的除了女性就是农民,她用富有诗意的语言和深沉的基调写出了东北黑土地农民特有的生命意识---残忍而又坚强。...
萧红是一个寂寞而敏感的女作家,她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没有因自己身为女性而屈服,而是以柔弱的身躯反抗着,用焦灼的双眸追寻着,以细腻的笔体呐喊着。她以抒情化、散文化的笔调探寻着生命的意义,她将自己对生命的思考融入景物的描写、氛围的营造中,以蕴藉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