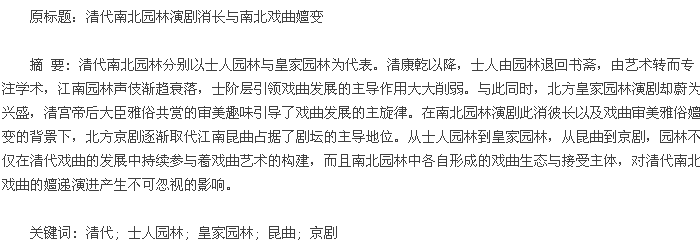
明代中叶以后,在江南造园风潮推动之下,士人园林作为戏曲的重要资源和标记参与了戏曲艺术的构建,以昆曲为代表,戏曲艺术深刻地契入士人园林文化之中。清代康乾年间以后,江南士人园林声伎渐趋衰落,北方皇家园林演剧却日益兴盛,在南北园林演剧此消彼长以及戏曲雅俗嬗变的背景下,北方的京剧逐渐取代江南的昆曲,占据了剧坛的主导地位。从士人园林到皇家园林,从昆曲到京剧,清代南北园林演剧的消长成为南北戏曲嬗变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这一点却被学界所忽略。作为一种综合艺术,戏曲的发展有其复杂现象和具体变化,尚不能简单地将南北园林演剧的消长视为南北戏曲嬗变的注解,但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戏曲各种声腔剧种的兴衰变化。因此,将园林演剧消长作为戏曲艺术发展演变的一个视角,透过对清代南北园林演剧消长盛衰的探讨,可更加细微地把握到当时南北戏曲嬗变的某些具体面相。
一、士人园林声伎的消衰与昆曲的沉寂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江南士阶层造园之风大盛。士人继承前代园林的传统,结合社会文化脉络,以“芥子纳须弥”的艺术匠心与技法兴造私家园林,不仅将婆娑大千世界摄入片石曲水之中,而且将由历史传承而来的士文化艺术体系囊括无余。在士人园林文化的引导下,失去勾栏的城市逐渐将戏曲演出场所移向私家园林,演剧风格亦由勾栏的喧嚣酣畅转入园林的清幽绵邈,并由此陶冶出典雅唯美、清丽婉转的昆曲水磨调。在士人园林声伎风潮促动下,昆曲艺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最终演变为代表士阶层情感规范与审美情趣的艺术形式。
①然而,自清代康乾年间始,江南士人园林声伎却渐趋衰落,昆曲也日益沉寂。江南士人园林声伎的消衰,固然与清廷的政权干预及其戏曲政策有直接关系,深层原因却是支撑园林声伎的士文化的衰落。明代中叶以后,士阶层的实践方向已从朝廷转移到社会,他们积极开拓社会和文化空间,以此来参与文化竞争,构建文化理想,确认其社会地位,并证实其文化的优越性。兴盛一时的园林声伎即显示了他们这一方面的努力。清康乾年间,在强有力的政权干预下,士阶层自明中叶以来获得的文化和社会空间大大压缩,社会角色与价值取向发生改变,他们从园林退回书斋,由艺术转而专注学术,士人间的社交亦由诗酒觞咏、顾曲观剧,一变而为相互砥砺、磋谈学问。
在此一时期,清廷虽增加了科考中举的名额,士绅队伍不断扩大,但由于满、汉八旗贵族子弟垄断了相当数量的官职,大多数士人并未获得更多出仕的机会,只有进士才有望得到朝廷的任用,且还需等待在职官员致仕。这导致众多举人及其他较低科名者转而另觅发展空间,他们开始放弃科举功名的征逐,到江南书院以及层次较低的学堂任教,江南地区专业化学术团体由此形成。其中,杭世骏、全祖望、戴震、钱大昕、章学诚等人堪称那个时代江南学者的代表,通过投身学术和教育,他们不仅用以修身齐家,还获得了很高的学术声望和影响。
同时,明清易代对士阶层心灵造成的巨大冲击波长久不能平复,士人确信“只有反省前代学术的失败,才能为哲学和精神的复兴,以及有效解决现实问题找到出路”。
[1]清廷为了巩固统治,也有目的地大兴修书之风,笼络博学鸿儒整理文化遗产。这一措施客观上抓住了此一时期士人的文化心理,江南士人“抱故国之憾,心思气力,无所放泄,乃一注于学问”,[2]一些在明亡前有着园林逸乐生活的士人,相当一部分都或深或浅地加入到了学术研究之中,学术成果斐然。如尤侗、陈维崧、朱彝尊、杭世骏等参与了清廷类书、丛书的编纂以及古书的考证、校雠、辑佚和注释等工作; 谈迁、张岱、查继佐、傅维鳞、吴伟业等则以个人的力量修史着述,分别着有《国榷》《石匮书》《罪惟录》《明书》《绥寇纪略》等。
与士人园林声伎的衰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清康乾年间商贾阶层园林蓄乐风气勃然兴起,其中尤以扬州鹾贾为最。清康熙以后,关乎国计民生的盐业从鼎革之际的颓势中复苏,蒸蒸日上。当时,扬州聚集了来自各地的盐商,其中徽商实力最强,他们垄断盐业,富可敌国,且贾而好儒。扬州为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自古有筑园传统,至清康乾年间,扬州园林臻于极盛,故此,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六云: “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
[3]明代中叶以后,竞筑园林乃江南士阶层的生活好尚,而到了清康乾年间,扬州园林多为盐商所造,前期以汪懋麟“百尺梧桐阁”、马曰璐“小玲珑山馆”最具代表性,后期则以江春“康山草堂”最负盛名。
扬州盐商“虽为贾人,而言论风旨雅有士人标格”[4],他们大多濡染诗文雅乐,为突显自身的社会地位及文化影响,纷纷仿效明代士人主持风雅艺事。园林即是扬州盐商展现其风雅生活的重要场所,而顾曲观剧是他们园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大盐商江春酷嗜昆曲,时与士人、曲家往来,“秋声馆”即为江春家班于“康山草堂”搬演昆曲的主要场所,曲家蒋士铨、金兆燕则常年馆于其间编演昆曲。蒋士铨作有《康山草堂观剧》诗五首,袁枚则有《扬州秋声馆即事寄江鹤亭方伯,兼简汪献西》诗八首,[5]“康山草堂”演剧活动之盛可见一斑。马曰璐的“小玲珑山馆”亦吸引着江南的文人士子,一时间士人趋之若鹜。其中曲家厉鹗半生寄食其中,为马氏家班编排昆曲,并曾于乾隆初次南巡时作有《迎銮新曲》进呈。
扬州盐商的园林声伎之风对清代昆曲的兴盛有推波助澜之效,推动了雅部昆曲的持续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花部乱弹亦在扬州盐商的审美趣味主导下迅速崛起。扬州盐商例蓄花部和雅部两种戏班。江春除了在其康山草堂中自组昆曲家班“德音班”,且蓄有花部家班“春台班”,春台班诸腔齐奏,“演《思凡》一出,始则昆腔,继则梆子、罗罗、弋阳、二簧”,[6]在当时扬州盐商中影响很大。此后扬州的皖籍盐商多有仿效者,蓄养的花部家班以安庆二簧调艺人为主,即后人所称的“徽班”。扬州盐商以其雄厚财富引领了清康乾年间园林声伎的发展,他们这种亦俗亦雅的艺术趣味终将影响到戏曲艺术雅俗嬗变的走向。
始于乾隆年间的花、雅争胜,已透露出戏曲雅俗嬗递的信息。早在乾隆九年( 1744) ,徐孝常为张坚《梦中缘》传奇作序即云: “长安梨园称盛,管弦相应,远近不绝。子弟装饰,备极靡丽。台榭辉煌,观者叠股倚肩,饮食若吸鲸填壑。而所好惟秦声、啰、弋,厌听吴骚。闻歌昆曲,辄哄然散去。”
[7]而到了乾隆二十一年( 1756) ,李声振《百戏竹枝词·吴音》诗云: “阳春院本记昆江,南北相承宫谱双。清客几人公瑾顾? 空劳逐字水磨腔。”
[8]乾隆四十九年( 1784) ,檀萃《杂吟》诗云: “丝弦竞发杂敲梆,西曲二簧纷乱哤。酒馆旗亭都走遍,更无人肯听昆腔。”
[9]道光八年( 1828) ,张际亮的诗注云: “今都下徽班皆习乱弹,偶演昆曲,亦不佳。”
[10]这些反映出乾隆末至道光初社会审美趣味丕变,花部乱弹较之雅部昆曲已在北京剧坛占据了明显优势,人们喜观乱弹、厌听昆曲,形成普遍风气,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明代中叶以后,经魏良辅改良后的昆曲契合着士阶层的情感规范与审美趣味。这一清柔婉折的声腔剧种,经士人园林多年的浸染、陶冶,已与民间曲乐渐行渐远,成为一种高度典雅化的士人艺术。至清乾隆年间,市民阶层尤其是富贾豪商日益崛起,昆曲那种“宁不通俗,不肯伤雅”[11]的风格显然与他们的文化品位与欣赏趣味有所抵牾,各种地方声腔剧种遂迅速发展。对花、雅二部演出在民间产生不同反响的原因,焦循《花部农谭》有详细记载: “盖吴音繁缛,其曲虽极谐于律,而听者使未睹本文,无不茫然不知所谓。……花部原本于元剧,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 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 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
[12]与此同时,随着士阶层文化和社会空间的压缩,士人由艺术转而追求学术,昆曲在日益远离市民大众的同时,也逐渐失去士阶层这一接受主体,由此日益沉寂,进而黯淡无闻了。
二、皇家园林演剧的兴盛与京剧的崛起
从士人园林到商贾园林,从雅部昆曲到花部乱弹,清初的戏曲生态、接受主体及雅俗趣味发生着令人瞩目的变化。然而,花部乱弹虽在此期的花、雅争胜中取得优势地位,仍属于各地梨园兴起的野腔俗调的地方戏,尚保持着较为原始、质朴的面貌,它在清代剧坛进一步的崛起,还有待于聚合、衍生为一种更趋成熟的全国性剧种。北方皇家园林的恢弘气势与清宫帝后大臣的戏曲趣味,为花部乱弹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清代宫廷演剧在明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乾隆年间,国力强盛,世风奢靡,清宫演剧臻于鼎盛。
乾隆帝本人十分好戏,据昭梿《啸亭杂录》载,“乾隆初,纯皇帝以海宇升平,命张文敏制诸院本进呈,以备乐部演习,凡各节令皆奏演。”
[13]此处提及的“院本”,泛指杂剧、传奇。当各种声腔剧目进呈清宫,自然需要专门的机构掌管宫廷戏曲演出事务,乾隆五年( 1740) ,清廷正式设立“南府”,负责宫廷的演剧事宜。乾隆十六年( 1751) ,乾隆帝令苏州织造遴选昆曲名伶入京,充任南府教习。
南巡时,乾隆又谕选江南伶人供奉内廷,并开设“外学”储之。此外,清廷还于景山设立机构,储备苏州民间艺人,俗称“苏州巷”。据王芷章《清升平署档案》载,当时南府供职人数约在一千四五百左右; 景山虽与南府并称,但其规模略逊于南府,供职人数当在千人上下。
[14]乾隆帝谙熟演剧之道,深知园林之于演剧的重要性,故而他常于皇家园林中观戏。诗人赵翼于乾隆二十一年( 1756) 入军机处,曾两次扈从乾隆到塞北秋猎,其《檐曝杂记》卷一记录避暑山庄清音阁大戏台演出节庆大戏的情景: “戏台阔九筵,凡三层。……高下凡九层,列坐几千人,而台仍绰有余地。”
[15]这里所记“高下凡九层,列坐几千人”恐夸饰之语,言不及实,但亦可说明清宫帝后大臣对园林演剧的热衷。
每逢乾隆寿辰,清宫都要在避暑山庄大戏台举行隆重的演剧活动。乾隆四十五年( 1780) ,乾隆帝七十寿辰,参与庆典的朝鲜使节朴趾源在其《热河日记》中翔实记载了其时清音阁的演剧场景: “八月十三日,乃皇帝万寿节,前三日后三日皆设戏,千官五更赴阙候驾,卯正入班听戏,未正罢出。……每设一本,呈戏之人无虑数百。”
[16]朴趾源所记此次祝寿演出的剧本共有 81 种。其中“呈戏之人无虑数百”说明演剧的规模与排场。而从“卯正”至“未正”的演出时间来看,每天观戏八小时,可知清皇家园林演剧之盛。
乾隆五十五年( 1790) ,乾隆帝八十寿辰,清廷举行了大型的祝厘活动,圆明园同乐园大戏台、避暑山庄清音阁大戏台的寿辰演剧一连演了十天。洪亮吉为此作有 36 首《万寿乐歌》,其中第 33首描绘当时演出连台本戏《升平宝筏》的场面: “三层楼,百盘砌,上干青云下无际。上有立部伎、坐部伎,其下回皇陈百戏。蟠天际地不足名,特赐大乐名升平。考声动复关民事,不特寿人兼济世。万方一日登春台,快看宝筏从天来。”[17]诗中表现了乾隆帝好大喜功,在演剧方面大肆铺张,以彰显皇家奢华富丽、至高无上的风范。
清代皇家园林上演的剧种繁多,不断呈现出新的局面,总体上表现为从昆弋并演到乱弹( 西皮二黄) 为主的演变过程。起初,清廷对那些新兴的民间乱弹戏无疑持排斥态度,指擿其所演“非狭邪蝶亵,即怪诞悖乱之事。于风俗人心,殊有关系”,[18]有关禁毁花部戏曲的谕令即是明证。而对于昆、弋戏,清廷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认为其虽已非古乐正音,仍颇为古雅,“节奏腔调,犹有五音遗意; 即其扮演故事,亦有谈忠说孝,尚足以观感劝惩”。
[19]加之弋戏步入清宫之际,又经过了词臣张照等人的雅化,多为风花雪月之词,登山临水之作,因此得到了更多的认肯,嘉庆初年下旨查禁花部诸腔,独保留了弋腔一种。大臣翁同龢曾对清宫的弋戏大为赞许,认为“宫内戏皆用高腔( 即指弋腔) ,高腔者尾声曳长,众人皆和,有古意”。
[20]在当时古乐不存、乱弹纷起的情况下,尚有“古意”的昆、弋戏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故而清廷视其为“雅音”,设立南府并开设外学,对其加以扶持。道光七年( 1827) ,南府改组为“升平署”,裁撤外学。自南府至升平署时期,清宫演出剧目甚夥,但不外昆、弋两个剧种,乱弹戏仅偶有出现。据清升平署档案记载,道光以前尚未见有乱弹戏出现,道光五年( 1825) 正月十六,同乐园承应,曾有乱弹戏《长板坡》的演出记于当时的南府档案。
升平署设立之初,亦有乱弹戏演出,但数量并不见多。
乾隆年间的花、雅争胜开启了徽班进京的序幕,道光以后,昆、弋戏在京城逐渐呈式微趋势,徽调“二黄”却声名日隆。道光十年( 1830) 左右,“西皮”“二黄”合唱的楚调入京,在京城徽班中迅速唱响。这种皮黄“新声”不仅受到普通市民的喜爱,也逐渐得到清宫帝后大臣的青睐。年轻的咸丰帝听惯了一成不变的昆、弋戏,对二黄产生了极大兴趣,据《清稗类钞》记载: “文宗在位,每喜于政暇审音,尝谓西昆音多缓惰,柔逾于刚,独黄冈、黄陂居全国之中,高而不折,扬而不漫。乃召二黄诸子弟为供奉,按其节奏,自为校定,摘疵索瑕,伶人畏服。”[21]咸丰五年( 1855) 以后,清廷陆续从徽班中挑选教习与伶人,皇家园林中承应的乱弹戏有所增加,陆续上演了《贾家楼》《瓦口关》《蜈蚣岭》等乱弹戏。咸丰十年( 1860) ,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行宫避暑山庄,一年后驾崩。
据朱家溍先生的研究,在这短短一年中,避暑山庄清音阁大戏台共演出弋腔、昆腔、乱弹三百余种,其中乱弹戏有《金锁阵》《三岔口》《朱仙镇》《叫关》《送亲演礼》《望儿楼》《青石山》《采石矶》等一百种,占整个演出剧目的三分之一,与道光初年至咸丰初年相比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22]可见,皮黄戏在咸丰年间的皇家园林中获得较大的发展机遇。
咸丰帝喜好二黄,对慈禧太后影响很深,舞榭歌台、笙歌不辍的宫廷生活,养成了她惯听皮黄的戏曲趣味。同光时期,慈禧太后主政,宫中演戏之风日盛。至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光绪帝皆推崇皮黄戏,选入升平署供奉的大多是以皮黄为主兼演昆、弋的名伶,皇家园林中上演的皮黄戏比重在不断增加。慈禧不喜昆、弋戏,曾传旨将梨园昆、弋戏翻改为皮黄戏。“光绪年间从昆腔、弋腔老本有不少改编成西皮二黄本,例如《十五贯》、《搜山打车》、《绒花记》、《双钉记》、《混元盒》、《双合印》、《义侠传》、《香帕记》等本戏。连台本戏有《西征义传》、《忠义传》等,都是十余本的戏。最大的是《昭代萧韶》六十本。”《昭代萧韶》原为乾隆年间的承应大戏,乾嘉时以昆、弋腔于皇家园林中多次上演,光绪二十四年( 1898) 五月初六日,清廷下旨将其翻改为皮黄戏排演: “王得祥传旨: 着本署排《昭代萧韶》,俱改乱弹曲白。人不敷用着外学上角,再不敷用着本宫上角。”[23]慈禧对皮黄戏的倡导、扶持,无疑对皮黄戏的飞跃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到了光绪后期,皇家园林中演出的皮黄戏剧增,占至全部演出剧目的十之八九。慈禧酷嗜观剧,据史料遗闻载,“光绪前,惟遇令节万寿,内廷始传旨演剧,赐王公大臣共入座。自孝钦柄政,乃大变其例,一月之中,传演多至数次,虽极寒暑靡间”。
[24]颐乐殿位于颐和园中德和园大戏台对面,专为慈禧看戏所建。颐乐殿中承应的剧目,除每天开场一出是弋腔戏,《胭脂雪》是昆腔戏外,其余均是皮黄戏。可见,光绪后期皇家园林中已是皮黄戏的天下了。
道光末咸丰间,成长于皇家园林中的皮黄戏已传到与北京邻近的天津,同治六年( 1867) 又由天津传到上海,逐渐流播全国,成为一个日臻成熟的全国性剧种。皮黄戏因源于北京,便被北京以外地区的人称作“京剧”。
三、南北园林与南北戏曲
清王朝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曾出现过“康乾盛世”的短暂辉煌。当时的清朝国都北京,皇权统治依然牢固,工商业的兴起,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文化生活异常活跃,这就为戏曲的繁荣提供了适应的气候和土壤。昆曲自产生之后的二百年间,在江南士人园林中常演不衰,士阶层多少年浸淫其间、情趣不减,且在清康乾年间得以跻身皇家园林之中,成为帝后大臣的佐欢之乐。然而,乾隆帝虽雅好风流,对江南园林和昆曲充满兴趣,帝王的立场和审美终究不同于文人雅士。乾隆朝以后,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清王朝无可挽回地走向衰颓,末世之中,迫切需要一种鼓荡人心的戏曲艺术来发人奋进,婉转舒缓、幽怨感伤的昆曲难以担当使命,身处末世的清代君臣最终选择了京剧。自此,铿锵韵律代替了缓歌慢弦,帝王将相代替了才子佳人,激越的锣鼓、昂扬的声腔,苍凉中带着热切的企盼,回响在帝国晚期最后的戏曲舞台———园林大戏台。
相比较而言,深情绵邈的昆曲承载着士阶层的情感与趣味,热切激越的京剧则吐露了末世君臣的立场和心声。就士阶层的欣赏趣味来说,即使在京剧如日中天之时,颇具艺文素养的高雅之士大都认为京剧风格粗犷不够精美; 而就帝王家的审美立场来说,昆曲虽颇为典雅精致,非庸夫俗子所能欣赏,毕竟不像京剧那般使人血气为之动荡,足以发勇往直前之志。对于昆曲与京剧此消彼长的原因,徐珂《清稗类钞》分析道:
昆剧之为物,含有文学、美术( 如《浣纱记》所演西子之舞) 两种性质,自非庸夫俗子所能解。前之所以尚能流行者,以无他种之戏剧起而代之耳。自徽调入而稍稍衰微,至京剧盛而遂无立足地矣。此非昆剧之罪也,大抵常人之情,喜动而恶静,昆剧以笛为主,而皮黄则大锣大鼓,五音杂奏; 昆剧多雍容揖让之气,而皮黄则多《四杰村》,《蜡庙》等跌打之作也。
昆曲以笛为主,辅以笙、箫、三弦等,诉说了文人雅士的冷逸与孤傲,闲适与自我,是代表士阶层最高审美范型的“雅乐”; 京剧则大锣大鼓,五音杂奏,传达的是粗犷质地的“俗乐”,然而这样的“俗乐”富于变化,节奏感强,使人情绪激昂、意气风发,契合着清代帝王的审美趣味。因此,在皇家主导戏曲主旋律的时代,锣鼓激越、韵律铿锵的京剧逐渐后来居上,最终发展成为日臻成熟的全国性剧种。
清代宫廷演剧多见于皇家园林的戏台之上,这些园林戏台是戏曲艺术适应清宫演剧的需要而产生,它反过来又推动了戏曲艺术臻于登峰造极。清代宫廷戏的编撰即是根据皇家园林戏台的环境和条件而确定的,康乾以后的皇帝经常组织词臣编撰大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满足皇家园林戏台演出的需要,发挥更好的舞台效果。像乾隆年间张照等人奉敕所编的那些上天入地、充满神奇色彩的连台本戏,就充分考虑到圆明园同乐园大戏台的演出特点。为适应京剧观演的要求,光绪年间建造的皇家园林戏台又与以往有所不同。专为慈禧看戏所建的颐和园德和园大戏台有三层,高达 21 米,底层的戏台宽 17 米,戏台的顶板有天井,台底设地井,可按照剧情需要,演员由天井下降,或由地井钻出。戏台下面有水井,既可增加演唱时的聚音和共鸣作用,又可供演出时制造喷水效果。戏台二层设有绞车架,演出时可上下配合,同时表演有水法、戏法等的大切末戏。这样的戏台,即是为了适应更为复杂的京剧演出的需要。慈禧酷嗜京剧,她驻德和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大戏台对面的颐乐殿中观剧,并由皇帝、后妃、命妇陪同,一同赏戏的王公大臣则按爵位高低分列东西两侧廊中看戏,这样就构成整个剧场“绕广院之四面,面面不相连属”[26]的演剧规模,场面之宏大与戏台之壮观交相辉映,充分彰显皇家气派。
在占地较广、规模宏大的德和园大戏台表演戏曲,更适宜声调铿锵高亢、集唱念做打于一体的京剧,于此戏台演出精致典雅的昆剧,显然较不适宜,这从光绪三十四年( 1908) 三月中旬接连三天宫中演剧的戏单可见一斑:十五日,颐乐殿承应: 《万花争艳》、本《战成都》、本《钱塘县》、《打金枝》、《艳阳楼》、《烈火旗》、《胭脂雪》、《定军山》、《溪皇庄》、《马上缘》、本《火云洞》。
十六日,颐乐殿承应: 《喜洽祥和》、《钓金龟》、《战长沙》、本《金钱豹》、《霓虹关》、《蝴蝶梦》、《朱砂痣》、《铁笼山》、《宝莲灯》、《二进宫》、本《百花山》。
十七日,颐乐殿承应: 《天官祝福》、本《孝感天》、《樊城》、《韶关》、《武文华》、《樊江关》、《梅降雪》、《群英会》、《入府》、《长坂坡》、《青石山》。
[27]上述颐乐殿承应剧目,除每天开场一出戏是弋腔戏,《胭脂雪》是昆腔戏外,其余都是京剧。帝后大臣对京剧的喜爱成就了颐和园德和园大戏台,反过来,颐和园德和园大戏台又对京剧在北京的成长壮大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
而昆曲发展到后期,演出场所越来越趋向小众化的士人园林。在士人园林中表演昆曲,因为近距离观赏之故,昆曲曲韵也就愈加柔和细腻,抽秘逞妍。此种清俊绵邈的昆曲越来越不适于喧嚣的大众场合表演,却能于静谧的士人园林中游刃有余。明人王骥德在《曲律》中论及“曲之亨”,认为戏曲之兴隆取决于“华堂、青楼、名园、水亭、雪阁、画舫、花下、柳边”等演剧场所,[28]于士人园林中聆听昆曲,可悠闲地欣赏“风入松”的悠扬清音、“蝶恋花”的婆娑丽影、“西江月”的江上清辉,士人园林成为一个集视觉、听觉等感官审美于一体的幽雅胜境。
有了园林,昆曲才愈加流丽悠远,有了昆曲,园林也更添旖旎情致。文人雅士无疑深谙此道,园林与声伎二者的结合体现了他们特有的文化品位与审美追求。苏州自古就是水乡泽国,正是水乡孕育出吴越歌舞、吴侬软语; 明代中叶以后苏州园林遍地,也正是苏州园林陶冶出细腻绵邈、婉转悠扬的昆曲水磨调。徐渭《南词叙录》之所以称“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听之最足荡人”的昆曲“止行于吴中”,[29]因为只有苏州园林,才最适于昆曲水磨调的生存发展,出了苏州园林,终无法体味昆曲水磨腔的真正韵味。
南北戏曲与南北园林自来风神迥异。就戏曲而言,由于宋金对峙,南北阻隔,便出现了北曲杂剧和南曲戏文两种类型,它们各自的艺术特色,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臻于成熟。明代曲家魏良辅即从音乐的角度分述南北曲的不同特征: “北曲与南曲,大相悬绝,有磨调、弦索调之分。北曲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故词情多而声情少。南曲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故词情少而声情多。北力在弦索,宜和歌,故气易粗。南力在磨调,宜独奏,故气易弱。”
[30]徐渭则从审美感受的角度对南北曲加以区分: “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于鼓怒也,所谓‘其声噍杀以立怨’是已; 南曲则纡徐绵眇,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是已。”[31]他们的判断,是符合后来南北戏曲发展的实际的。
就园林而言,北方皇家园林与江南士人园林的风格也是大不相同。气势壮观宏伟的清代皇家园林,继承了秦汉以来皇家园林体象天地、包蕴山海的兴造格局,体现出北方山水共有的壮美风神。
清代皇家园林虽也曾效仿江南园林,但终究彰显的是皇家的风范与气度,其规模之宏敞,丘堑之幽深,草木之清佳,亭台楼阁之具备,均非江南园林可比。而江南士人园林虽在规模上远不及皇家园林,却运用须弥芥子、以小见大的匠心与技法,将大千世界缩入“壶中天地”,实乃江南风韵和士人情趣相互融合渗透的典范,园林中那些写意的片石、曲水、曲径、回廊等,俨然是江南风韵的体现; 而清秀的幽篁,傲雪的梅花,高洁的荷花,均为寄托士人情趣而设。
虽然园林与戏曲分属不同艺术门类,但其审美效应却有内在的相通之处。北方园林与北曲风格相似,同属壮美一格,皇家园林所引发的审美想象,正如京剧的铿锵炳朗,激越飞扬,这既是北方性情的豪放风调,也是清代帝后大臣的审美立场。而江南园林与南曲品性相通,同属清丽一格。江南园林所引发的审美效应,也正像昆曲的深情绵邈,清丽婉转,这既是江南情韵的柔美风致,又是士阶层的审美情趣。正如江南士人园林中无法孕育出慷慨激昂的京剧一样,北方皇家园林中亦不具清丽悠扬的昆曲生长的土壤。总的来说,幽雅精致的江南士人园林如同淡妆轻描、浅吟低唱的昆曲,壮美宏丽的北方皇家园林则好似浓墨重彩、激扬酣畅的京剧,故而作为南北戏曲的代表,昆曲与京剧在南北园林的代表———士人园林与皇家园林中对应着各自适宜的生态环境与接受群体。
以上从宏观上分析了清代南北园林演剧的消长对南北戏曲嬗变的影响,可以得知,中国戏曲的发展固然是基于戏曲艺术内部的发展规律,但亦与文化生态与接受群体有密切的关联。清乾隆年间,自明中叶以来盛极一时的士文化渐趋衰落,对应着这一文化生态的还有作为士阶层情感规范与审美趣味的江南士人园林与昆曲的衰微。与此同时,代表帝王家的立场与审美的京剧却在北方的皇家园林内外成长壮大,由此揭橥中国戏曲发展新阶段的到来。从士人园林到皇家园林,从士阶层到帝王家,南北园林中各自形成的戏曲生态与接受主体,对清代南北戏曲的嬗递演进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所谓制度,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可以说制度既包括显性的法律法规,又包括隐性的风俗习惯。既可以表现为强制下达的条文,又可以表现为潜移默化的习俗.又如项阳所说,有些制度被刻意强调,比较彰显,但并非只有显性规定才是制度。有些...
前言清代内廷演剧对于清代戏曲史的意义,近年受到较多的肯定.有关档案文献的影印出版,则为推进相关研究提供了条件.2011年,《国家图书馆藏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就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这批档案文献为朱希祖旧藏,后归北京图书馆.周...
京剧形成于清代后期的北京,因地域而得名,20世纪30年代已享誉中外。距今已有近200年历史,是中国现今最大的戏曲剧种。京剧艺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最引以为豪的戏曲艺术形式之一。京剧里,有生、旦、净、丑四个扮演不同年龄、身...
清中后期, 表彰“循吏”事迹的“循吏剧”大量涌现, 虽然很少上演, 但并不妨碍其成为士人文化的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