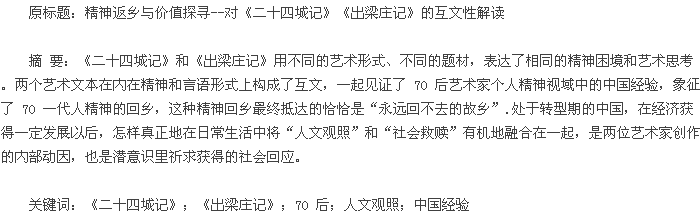
《二十四城记》是贾樟柯执导、2008 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出梁庄记》是学者梁鸿出版于 2013年的一部纪实文学作品。《二十四城记》是贾樟柯《三峡好人》之后对四川的又一次深层言说,只不过它有别于我们想象中一般意义上的电影,它没有“故事”,很少动态的影像画面,几乎弃绝了“表演”的成分而是不断地让人物“静静地说”,它遥远地偏离了我们的“期待视野”,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当前主流电影叙事的一次解构。《出梁庄记》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梁鸿正是凭借它斩获 2013 年第 11 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在《出梁庄记》之前,梁鸿还有一部《中国在梁庄》(2010 年),它们构成梁鸿“梁庄系列”的姊妹篇。梁鸿的书写对象是豫南的一个村庄:梁庄。作者走访了很多人,书中充满大量的由这些人的录音转化的文字。作者交代背景和“被走访者”,剩下的就是让他们“静静地说”.
这两部艺术品最显着的共同特征是“让他们说”,只不过说的内容不同而已:前者说出了一个国营军事工厂的前世今生,以及这背后三四代人的世事变迁、人情冷暖;后者说出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与现状,以及这背后的人事纠葛、寂冷萧条。虽然摆在面前的是“军工”和“农村”,但如果合起来看,大致可以看出那些繁华背后的萧条、辉煌背后的惨败、热闹背后的凄清以及速度背后的缓慢、变化背后的恒在。而这一切,都是用“记”的方式说出的。
一、记:70 后精神回乡的见证
“记”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字,作为一种体裁和书写类型,在文学中更是古已有之、广为用之。《说文》:言,记,疏也,即分条记录或分条陈述的意思。《广雅》:言,记,识也。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第二十五》中记载“记之言志,进己志也”,即是说,记就是把言语记下来,是为了向上进献自己的意志。在日常的意义上,笔记、日记、游记等侧重于用文字记录、记载,而“记”作为一种叙事文体,在文学中得到了更加广泛的运用。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它是想象力发挥作用的虚构的产物,比如着名的古典小说《红楼梦》,它最初的名字便是《石头记》。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史记》《西厢记》《西游记》《老残游记》等,构成了中国文学重要的部分。“记”同样贯通了西方的文化历史,《圣经》里便有《出埃及记》《约伯记》等,承载了叙列故事、言行的重要体式。在西方文学传统中,英国作家笛福《鲁滨孙漂流记》、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等,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构成一个伟大的文学序列。因为中国有深厚而绵长的“史传”传统,所以后世的“记”多半与“史”有扯不断的联系。“修史”以“明鉴”,便是“记”昨日之事而汲取教训,鉴明当下,以照未来。不妨说,“记”是为了更好地“计”.历史的车轮进入现代中国,“记”同样参与了中国文学的历史书写。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及当代中国文学以宗璞的《南行记》《东藏记》等为代表的书写,同样构建了“记”这种文体对历史、时代的回应序列①。
两部作品的作者都是所谓的 70 后艺术家②。不同于“知青一代”的“下乡体验”与“时间之伤”,也不同于 60 一代的“文革记忆”和“文化热肠”,70 一代是尴尬的,又是严重错位的。
时代赋予他们的身体记忆和灵魂创伤必定是独特的。向前,他们比不上那些出生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无比辉煌的“时代弄潮儿”;向后,他们又比 80 后们多了些历史的重负和难以卸脱的沉重--这正是他们的尴尬。霍俊明用“尴尬的一代”命名那些70后诗人--这几乎可以用来指涉一代人,他们中的“代言者”替整整一代人说出了隐秘的心声。他们艰难地周转在城市生存和农村记忆之间、斡旋于前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夹在缓慢蜗行的中国和飞速发展的中国之间,从童年、少年一路走来,忽然间“人到中年”,竟然成了无根--生存之根、精神之根--的人。梁鸿在书中描述了一个名叫梁磊的青年,他从梁庄走出,考入重点大学,然后到南方工作,梁鸿在书中对他的言说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己、甚至是对整整一代人的言说,“他看到的、听到的和他所经历的,都使他无法找到亮光来支撑行动。他和他的同代人,经历了这个国度最大的变幻,他们在前现代那一刻出生,在日新月异的巨变中经历童年和少年,等长大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已经是一个后现代社会的超越景观。而此时的他们,感受最深刻的不是景观的宏大耀眼,而是这景观背后的支离破碎。”[1]217贾樟柯被誉为“第六代导演”的中坚,他的电影语言独树一帜,电影风格奇崛而艰涩。他善于通过慢镜头来细腻、精准地书写底层人生存的艰难。而今的电影艺术,有太多“炫”、太多的特技与空幻,而贾樟柯是一个电影艺术的“逆行者”,他一直在做着“电影的减法”,到了《二十四城记》,这种减法甚至已经减到了无穷小。正是在这种近乎笨拙的叙述中,贾樟柯奇迹般地钻进了中国社会的地心。相对于贾樟柯,梁鸿的知名度要小很多。梁鸿是最近十年在文学学术界渐渐闻名的。这位来自河南的女学者,她的“成长故事是与贫穷而安静的乡村生活紧紧缠绕在一起的”,经过不懈的努力,从贫穷的河南小村庄一路杀到了北京,在着名学者王富仁门下读完博士,就职于北京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以河南文学研究和乡土文学研究而着称。
两位作者在世俗的眼光中都有些背离他们表层的文化身份,贾樟柯本可以在成名之后像某些导演一样,好好地娱乐一把;梁鸿也本可以在“亭子间”“象牙塔”里好好做自己的学问,为什么偏要寻这苦差事?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曾提出“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的概念,旨在撞开“传统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的“学院牢笼”和“孤闭意识”,以积极应对社会事务,有机地融入社会。以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西马”理论家针对“文化工业”展开的文化批判,正是“有机知识分子”的强力实践。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商品文化、大众文化在中国迅速蔓延,当 70 后艺术家登上艺术舞台、展开艺术活动时,正与其不期而遇。
随着对历史、时代的深入探询与观照,70 后正不断地朝“有机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向。他们不满于自身的“体制”和“身份”,甚至肆无忌惮地僭越,以便更加“有机”地融入这个社会。正如70 后学者霍俊明所言,“当 70 后一代人渐渐过了而立之年向不惑之年走近的时候,黑暗中门缝里透露出来的依稀的灯光让他们不能不集体地面对往事、回首乡村,反观来路,而越是在物欲化的城市里,这种回望的姿势越是频繁而深入。”
这正是 70 后一代人的精神表征。他们是“夹缝”中的一代,他们没有 80 后、90 后那种“娱乐至死”的精神气质,也没有早一代人那样坚固、执拗的精神之根,所以他们只能不停地寻找。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返回,向着空间和时间索要答案,这是一种精神之渴。贾樟柯和梁鸿把对历史现实的反思与叩问,融进了最为古老的艺术体式中--用“记”的方式撕开盛世中国的华丽面纱,呈现出那些背后的、看不见的中国细节。
二、“工”与“农”:中国故事与中国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迎来高速发展,一个崭新的中国飞速前进,反映在艺术上,那些表现时代变迁、历史前行的作品尤其多。然而在“中国”这个庞然大物飞步疾走之时,除了那个更高更美的中国形象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身后的“看不见”的中国形象,它可能就藏匿在前者的身后,在时代的主流中,它很容易被遗忘。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盲视”使得一些艺术家不断地产生“回望”的念头。那是一种反抗遮蔽的内心冲动,是历史深处的“呼愁”①在叫喊,这代人,毫无意外地和这个形象相遇了。“这一代人以自己特有的青春与成长,见证了中国社会自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历史巨变,也深刻地体会了生活本身的急速变化对人的生存观念的强力制约。”[3]
和其他同类题材的艺术文本相比较,他们关注的角度更加独特、更加内在。同是关注中国的工业变迁,我们之前有所谓的“改革文学”,集中于最尖锐的问题,突出主要人物,注重宏大叙事,但它们很少真正从一个普通工人的角度、用普通工人的眼睛去观照;农村乡土题材的文学一直很热,但梁鸿的这一系列着作却更加真实,它直接洞彻了农民内心的黑洞和无法企及的绝望,写出了“生活挫折对内部精神的挤压”.梁鸿的“梁庄”系列的“最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借助对乡村农民和‘农民工’生活的表现,让乡村说出了自己的声音。”[4]
电影《白鹿原》改编自陈忠实经典同名长篇小说。故事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以田小娥与三个白、鹿长辈(族长白嘉轩、乡约鹿子霖、长工鹿三)之间的是是非非及其与白、鹿两姓子弟之间的情感纠葛为叙述主体,描绘了白、鹿两大家族祖...
当毒品开始侵入更多人的生活,不再是印象中的流氓、混混的专属物时,它带给社会将是巨大的灾难,尤其是毒品侵害一个国家的青少年,这种悲凉异常突出。《毒品》向观众展示了一个庞大的毒品之网,让人看后只觉得心有余悸。究竟影片是有什么魔法...
电影《时间机器》是根据英国科幻小说家乔治威尔斯(GeorgeWells)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该影片由西蒙威尔斯(SimonWells)执导,盖皮尔斯(GuyPearce)主演。影片讲述了大学应用机械工程系青年教师亚历山大哈迪根博士在一次约会中遭遇抢劫,深爱的女友...
小说《崩溃》(ThingsFallApart)尼日利亚裔美国著名作家齐诺瓦阿切比(ChinwaAchebe)的代表作,1959年发表后立即获得英国最高文学奖布克奖。至今,本书在世界的销售已经超过1100万册,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一切都崩溃了,价值已难持守,世界上...
中国当代儿童电影的电影改编需要重新建构适合其美学特质的诗性传统.而艺术诗性的建构离不开具体的美的艺术形式,如电影中生动美丽的艺术形象、唯美清新的电影画面,清新的构图和细腻真挚的情感呈现.儿童电影以朴真唯美、灵动自然的本色创作来体现当代儿童电影...
现代科学技术随着时代的不断革新与发展,愈发的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高科技,大制作,高投入,电影创作上跨国或跨地区合作,已成为欧美电影在20世纪80、90年代的一个特色标签。但在这些光影背后,欧美国家的电影无论在历史背景、本体的艺术表达、观众的...
一、介绍电影《蒙娜丽莎的微笑》以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为背景,故事发生在1953-1954年期间的卫斯理女子学院。影片讲述了一位毕业于加州伯克利大学的艺术史女教师凯瑟琳和女学生们,在卫斯理女子学院如何通过摆脱男性强加在她们身上的身份天使和魔鬼,...
摘要盘点新世纪以来大陆青春校园电影,电影创作者跨越了特殊时期意识形态思想倾向的约束,以传播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为己任,传承延伸大陆电影艺术精华为责任,将镜头对准当下流行文化与娱乐元素,以不同与往时的青春回忆为主线、隐含观众,通过拍...
电影《霸王别姬》和《梅兰芳》拍摄的时间整整相隔了十六年,十六年时光流转,物是人非:陈凯歌的导演梦在《霸王别姬》之后起起伏伏,甚难出彩;哥哥张国荣斯人已逝,百转千回的程蝶衣只能在银幕上反复品咂;2008年《梅兰芳》的上映让影界认为陈凯歌想要回归...
题目:中国电影营销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目录摘要(详见正文)一、中国电影的营销现状(一)中国电影营销方式(二)近年中国电影营销成果(三)认清现实,中国电影营销只是进入了启蒙时代二、中国电影营销存在的问题三、试析发展中国电影营销的对策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