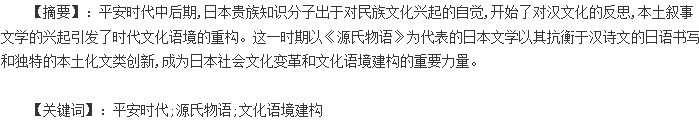
在由美国当代着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大卫·达姆若什(David Damrosch)主编的《朗曼世界文学文选》(2008版)中,日本古典名着《源氏物语》(1007年)赫然在列,与中国等东方民族的众多经典一起,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世界文学“不平等的整体”的局面,构成了与西方文学经典的多声腔合鸣。这是21世纪初期以来美国学术界兴起的“世界文学史新建构”(A New Construc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History)的文学思潮的具体体现。
实际上,除了《源氏物语》这样代表着平安朝文学最高成就、并且早已被公认为世界性经典的文学瑰宝之外,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年)还产生了《竹取物语》《古今和歌集》《土佐日记》《落洼物语》
《蜻蛉日记》《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记》《荣花物语》《更级日记》、《堤中纳言物语》《大镜》《今昔物语集》等等众多的民族文学作品,它们成为日本意识形态由“汉风”、“唐风”向“和风”、“国风”转变的突破口。
一、平安时代以文学为核心的文化转向
日本平安初期正值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最昌盛的唐代,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落差使得当时的日本想要避免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中灭亡的命运,就不得不向社会变革寻求生路,也不得不对先进的异国文化采取开放的态度。由于地理等原因,当时的日本除了汉文化外,尚未与其他发达的文明发生直接的接触,日本统治者自然地选择了繁荣、强盛、文明的隋唐封建国家作为他们进行社会变革和文化选择的范本,并由此完成了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飞跃。
平安初期被日本史学家称为“国风暗黑时代”,即日本的民族文化在外来的大陆文化的强大辐射之下低迷、消沉,处于边缘位置。这一时期,日本民族对于大唐物质文化的仰慕达到了极点,他们不仅在政治文化方面竭力效仿中国,而且对于中国生产的物品也非常喜爱,大量的唐货进入日本导致白银大量流出,使日本在对外贸易方面一直处于逆差的状态。从唐进口的物品中不仅有货物,还有“唐钱”。当时的日本钱币不仅在质量上无法与唐钱相提并论,流通中也有诸多不便,因此唐钱在日本大受欢迎,这就更加导致了日本货币体制的混乱,对本已面临危机的日本经济和政治无疑是雪上加霜。
文学上平安前期汉文学依然盛行,和文学只是“青萍之末”。根据“各民族文化交往中的高文学形态必胜”的原则,古代在处于不同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阶段的文学交往中,主要表现为高形态文学向低形态文学的渗透。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极度不平衡,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借鉴就不仅仅是被“渗透”的问题,而是表现为对汉文学的全面移植。日本最早的书面文学作品集《怀风藻》(751年)是用汉字并且借用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形式完成的汉诗集。平安初期在《怀风藻》的基础上,还产生了奉嵯峨天皇(786-842年,809-823年在位)之命编纂的《凌云集》(814年)、《文华秀丽集》(818年)以及奉淳和天皇(786-840年,823-833年在位)之命编纂的《经国集》(827年)三部汉诗集,这三部汉诗集也因此被称为“敕撰三集”。
然而,正如戴季陶所说,“我们要看得见日本的文明建设,是在很低的民族部落时代,硬用人为的功夫,模仿中国最统一最发达的盛唐文化。”“硬用人为的功夫”表明当时的日本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接受和利用是清醒的、自觉的,同时也是为了民族发展的需要迫不得已的。可以说,高度发达的汉唐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日本的民族自我意识,形成了“国风意识”产生的强大动力,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又强化了日本对于民族文化建构和认同的需要。
因此,当9世纪后半期,中国先后发生“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各地藩镇割据,唐王朝日薄西山,摇摇欲坠;而日本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和摄关政治的加强,原来仿照唐朝建立的律令政治体制逐渐土崩瓦解之时,日本贵族和知识分子出于对民族文化兴起和发展的强烈自觉,随即开始了对汉文化的反思,“脱汉”风潮由此而起。
公元894年(即唐昭宗乾宁元年、日本宽平六年)成为日本民族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新任遣唐使、着名汉学家菅原道真(845-903)引用日本在唐学问僧中灌的报告上奏天皇,以“大唐凋敝”,“海陆多阻”为由,建议朝廷停止遣唐使的派遣。宇多天皇(867-931年,日本第59代天皇,887-897年在位)接受了这一建议,两国官方关系遂告中断。
但是显然,废止遣唐使的真正原因,除了“大唐凋敝”,“海陆多阻”以外,更重要的是出于日本本土发展的需要。如上所述,自奈良时代大规模地输入大唐文化以来,日本的民族文化长期被排除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这种文化上的“集体无意识”甚至导致了日本的经济面临崩溃。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从商品、金融、文化等多方面入手,但这是短期内难以完成的,而从国家政策上先行杜绝外国政治经济的威胁则相对比校容易。因此,废止遣唐使只是一种政治策略,以菅原道真为首的日本贵族和上层知识分子更迫切关注的是民族文化的建构和文化主体性的认同。其中,由于“文化认同是在话语实践中进行的,在种种象征认同形态中,语言和文学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即语言和文学具有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功能,作为民族文化核心组成部分的文学担任着重要的精神职责,必然成为文化变革和建构的重要力量。“和风意识”的萌发是日本民族文化的一次跃迁。
二、平安假名文学的“和风意识”
日本民族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是和歌总集《万叶集》(759年)的诞生。和歌是日本的民族诗歌。民族诗歌在唤醒和激发民族意识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众所周知,《万叶集》这部规模宏大的和歌集产生的年代,日本还没有本国的文字---这是日本民族文学发展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它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沟通的最大障碍。因此,日本应记录和歌的需要而产生了最古老的文字“万叶假名”,这是一种用汉字的读音来记录日本语语音的文字,它看上去是汉字,读起来却是日本语。《万叶集》中所有的和歌都用“万叶假名”表记而成,而这种文化语言和文化事实之间的偏差使得那个时候的日本民族文化还很难有与外来文化进行抗衡的实力。
但是,经过漫长的近300年遣隋使和遣唐使的派遣,日本在思想、文化方面已经逐步走向成熟,并开始进入了独立的本土文化发展阶段。也就是说,随着日本的成长,大唐影响开始退潮,民族文化意识开始觉醒,标志仍然是文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汉字已经日本化,“万叶假名”发展为日本的表音文字符号“假名”,它已是书写日本语的成熟的书面符号系统了,所以,“假名”真声。假名的运用,表明了日语的进步和使用日语的日本族群的进步。
日本在平安中后期呈现出了力图摆脱唐文化的影响、努力确立本民族文化风格的特征,这首先表现为日本文学逐渐摆脱了汉文学的影响,出现了完全用假名创作的文学作品,使真正意义上的日本文学随着“日本语”符号体系的完成粉墨登场。以往精通汉文的只限于贵族和僧侣,广大下层民众很难掌握或根本没有条件来学习汉文,假名这种表音文字的出现,则使文化知识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从而为日本文化的本土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平安中后期“敕撰”的不再是汉诗集,而是《古今集》、《后撰集》、《拾遗集》等和歌总集。平安“和文学”的繁荣标志着日本本土文化的真正开端。
文化的主体性往往是通过语言来建构的,各民族语言在民族文化的建构过程中都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欧洲自11世纪以后,各民族近代语言逐渐兴起,许多民间文学作品开始用民族语言进行创作。意大利诗人但丁的宏伟诗篇《神曲》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神曲》创作之前,但丁在他的理论着作《论俗语》中已经从理论上阐述了“俗语”(即民族语言)的优越性。他强调“俗语”优越于作为官方书面语言的拉丁语。事实上,语言的问题是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各民族开始用近代地方语言创作文学作品时所面临的一个普遍的、重要的问题,当时的作家和理论家们对这个问题都特别关心。这一时期的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人都通过他们的作品确立了自己民族语言的规范,从而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建构者。几乎同一时期的日本也一样。“平假名”虽然直到近代仍然主要由妇女使用,但以《源氏物语》作者紫式部为代表的平安贵族妇女,在日语符号体系力图取代汉语符号体系成为民族文化载体这个问题上进行的努力,成为日本民族文化形成的一个突破口。
假名文学除了能够使日本人更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以外,更重要的可以使日本文学摆脱汉文学的影响,达到真正的独创。日本文学史上最着名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和《竹取物语》、《古今和歌集》、《伊势物语》、《土佐日记》、《蜻蛉日记》、《枕草子》等作品,均用无标点符号亦无汉字的平假名写作。相对于汉诗文的博学精深,假名文学优美流畅、清新细腻。不仅如此,《源氏物语》中还多次专门谈论“假名”文字的的兴起和在贵族中的逐渐流行。如第十七回《赛画》,藤壶皇后将后宫嫔妃中善绘画鉴赏者分左右两方进行比赛,品评各自所收藏的书画,但全都精妙无比,一时难以判定优劣,直到最后一轮比赛,左方拿出源氏被贬须磨时所作的画,大家看到所画之地的荒凉遥远,尤其是“各处写着变体的草书汉字和假名的题词”,这些题词“不是用汉文写的正式的详细日记,而是在记叙中夹着富有风趣的诗歌”时,才都觉得这画压倒一切;又如第三十二回《梅枝》写源氏亲自挑选女儿明石女公子入宫的物品,跟紫姬有一段关于假名书法的议论:“世风日下,万事不及古代。只有假名的书法,今世进步无量。……到了近代,才有假名书法的妙手相继问世。”
源氏自己就是假名书法的妙手:
“各种古歌浮现脑际,他(指源氏,笔者注)就随心所欲地用假名写出,或用草体,或用普通体,无不异常秀美”
等等。推崇假名不是作者的随意而为,特别强调“用假名写出”而“不是用汉文写的”,一是表明在当时汉字汉文确实仍然具有正统地位,二是表明作者已经有了以“假名”与“汉文”相抗衡的意识,“假名”与“汉文”在《源氏物语》的这些描写中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
三、平安文学文体的“和风”特点
一个民族特有的文体可以作为社会全体成员特定的文化记忆而流传下去。平安中期起,日本大量出现了主要以宫廷生活为舞台的和歌、随笔、物语及日记文学等运用日本独有的文学体裁进行创作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在时间中的记忆与各种文化心态下的再记忆。
“文体”的概念虽然主要是指文章的类别、体式,但它的含义非常复杂和丰富,童庆炳先生指出,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中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他认为对“文体”的定义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理解,“从表层看,文体是作品的语言秩序、语言体式,从里层看,文体负载着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作家、批评家的个体的人格内涵。”
这种概括超越了传统文体学对文学进行形式分类的研究范畴,洞察到了文学形式与内容的有机性。确实,文体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还是内容的“格栅”。蓬勃兴起的和歌、物语、日记文学等无疑在民族文学还是蛮荒之地的日本树立了一根灿烂的标尺,演示了谛视和摹写、培育心灵之花的路径与方法。从文体意识的角度来说,在日本民族寻求国家出路的背景下,和歌、物语、日记文学作者往往把创作当成一种文化甚至政治使命,用一种迥异于汉诗文的写作方式和话语方式,将他们所理解的文体意识,在文本写作中转化为一种文化精神,这些文学样式也逐渐地成为了民族文化符号性的存在。
例如,早期原始形态的日本和歌并没有统一的格律形式,它只是一种散漫的、朴素的,依靠口耳相传的歌谣,由于它便于咏诵而深得人们的喜爱。但是唐风东渐,日本的民族文学面临中国文学以及日本汉文学的严重挑战,能否建构一种更适合表达民族情感的新文体,事关日本民族文学的生死存亡。
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具有统一形式的全新形态的和歌应运而生了。当时的日本贵族文人根据日语本身的特点和日本人接受的程度,当然也不得不以最为完美、最为流行的汉诗为蓝本,将原先杂乱无章的歌谣,经过筛选、重组,固定了它的形式。于是,具有独特日本民族风情,又能够和汉诗相抗衡的文学样式便逐渐形成了。“和歌汉诗”如同一车之两轮,一鸟之两翼,同属于日本古代文学遗产的两大诗歌系统。平安中后期的《古今和歌集》(914)、《后撰和歌集》(951)、《拾遗和歌集》(1005-1007)等都是奉天皇之命编纂的和歌集,它们的编纂完成既恢复了日本民族诗歌的地位,又表明当时的日本统治者和贵族知识分子力图使它具备与汉诗抗衡的实力。
民族文学样式的形成,往往有一个长期的积累和发展过程,适合于这个民族的地理环境、物质条件和思想意识的文学样式总是由简到繁(或由繁到简),由杂乱到整齐,由有序到无序地在一次次自然淘汰的过程中逐渐地被固定下来。和歌样式的形成却不太一样,它是在外来文学繁荣的刺激和推动下,在较短时间内创造出来的,但是这同样是符合民族文学发展规律的,因为民族文学首先必须生存下去,然后才能得到发展。
平安物语和日记文学也产生于这一时期,作为叙事文学,都显现出叙事的纪实性和单一性特点,而缺乏内在的统一性和艺术的完美性。这是一种文体形成初期时不完善的表现。《源氏物语》虽然最先将虚构物语与歌物语结合起来,细腻的心理描写使作品的文学性大大地增强了,但重史实的特点依然鲜明。《源氏物语》第一到第四十帖(“帖”类似于中国章回小说的“回”)写主人公光源氏从出生到去世的生活经历,虽然重点写光源氏与几位女性的恋爱纠葛,但完全按照时间顺序安排的结构,基本上类似于人物年谱,这一方面固然是作者的写作策略选择,即在创作方法上继承了物语的现实主义传统,如在第二十五回《萤》中,作者借光源氏之口说道:“原来故事小说,虽然并非如实记载某一个人的事迹,但不论善恶,都是世间真人真事。观之不足,听之不足,但觉此种情节不能笼闭在一人心中,必须传告后世之人,于是执笔写作。……这些都是真人真事,并非世外之谈。中国小说与日本小说各异。”
仿佛作品是对真人真事的记载;另一方面作品故事线索的单一性也由此显现,不能不说这类物语文学与古希腊《荷马史诗》等同样为大型文学作品的结构能力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然而,这段话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作者明确表示了“物语”这种文体与中国小说的不同。
纵观日本平安文学史,还有一类“汉诗”与“和歌”两种文体合编成集的形式。如菅原道真编辑的《新撰万叶集》(893年)、大江千里奉敕编纂的《句题和歌》(894年)、藤原公任编撰的《和汉朗咏集》(1012年)等集子,它们创造性地将汉诗(包括唐诗和日本人所作汉诗)与和歌并列编辑,形成了鲜明的跨文化特征。这种新的“版式语言”象征着汉诗、和歌“符号地位”的此消彼长。在日本汉诗的创作水准还不可能达到中国诗歌那样的高度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大胆尝试和创新之举,这些汉诗与和歌合编的集子显示了中国文学审美趣味和日本文学审美趣味相交融的特色。然而编纂它们的真正目的恐怕还不止于此,日本人实际上是为了说明汉诗与和歌是可以相通的,或者说,和歌完全可以与汉诗媲美。而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我们会发现更加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日语吸收了大量的汉语词汇,书面语的形式也来源于汉语。汉语无疑是当时的强势语言,是较高的语码,而日语则是较低的语码。因此,平等并行的编排版式揭示了两个语码的“地形学”变迁---日语和汉语终于“平等”了。这种通过文体体现出的“和风”意识使日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得到了强调。
综上所述,日本的民族文化主体性是在外来作用与内在需求的结合中,在“和风意识”率先觉醒的贵族知识分子创作的民族文学作品中逐渐形成的。因此,我们应当将日本平安时期的文学置于世界文学发展的语境中去深入探寻,而不应当对它们进行居高临下的阐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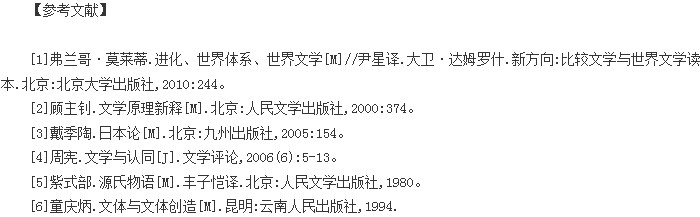
底层文学是21世纪初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而中国文学又是东方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相比西方文学,讨论东方文学视域下的底层文学对中国文学更具亲缘性和启发性。从东方文学史来看,从上古埃及的劳动歌谣到中古印度的故事文学以及阿拉伯的市...
1绪论1.1研究的目的及意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韩国①的书面文字一直使用汉字。直到李朝时期世宗大王即位后,于公元1446年颁布了韩国文字《训民正音》。但官方文字仍然使用汉字,直至1919年韩国为日本吞并后,韩文才取代汉字的地位。韩国汉文小说,...
《源氏物语》以日本平安王朝为背景,描写了主人公源氏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小说刻画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她们坎坷、悲惨的命运,无不让人惋惜。当时长期存在的访妻婚,也导致了这一悲剧的发生。...
摘要清末民初,大量日本人到中国旅游,并撰写了不少游记作品。这些游记详细叙述了作者的游览行踪、沿途见闻及所到之处的山川景物、历史沿革、地理状况、风俗民情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文化不可多得的文献。这些游记中,有部分与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