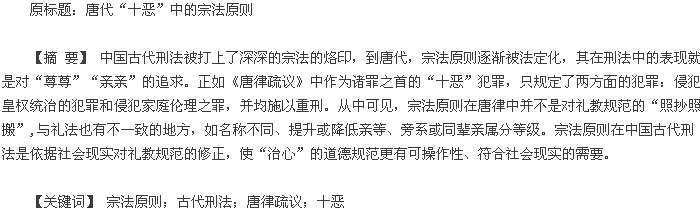
一、前言
自西汉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德礼成为政教之本。刑法也是德主刑辅,体现儒家思想,这也使得中国古代刑法被打上了深深的宗法的烙印。到唐代,礼法结合在唐代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宗法原则逐渐被法定化。同时,“尊尊”“亲亲”成为刑法重要的价值目标,并置于诸罪之首的“十恶”犯罪之中。本文就以《唐律疏议》之“十恶”为核心考察宗法原则在中国古代刑法中的体现。《唐律疏议》中“十恶”犯罪在侵犯家庭伦理方面的犯罪主要有:“恶逆”“不孝”“不睦”“内乱”以及部分“不义”中的内容。依据犯罪客体不同,可分为三类:侵犯亲属人身和财产权利的犯罪、违背同居相隐不为罪原则的犯罪以及居丧期间违背礼教的犯罪。
与前朝相比,宗法原则在唐律体现地更系统、更充分,而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例如“十恶”犯罪的律文在礼教规范中均有对应之处,对侵犯家庭伦理之罪更是“准五服以制罪”.但唐律中的宗法原则不是对礼教规范的“照抄照搬”,与礼法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如名称不同、提升或降低亲等、旁系或同辈亲属分等级。宗法原则在中国古代刑法是依据社会现实对礼教规范的修正,使“治心”的道德规范更有可操作性、符合社会现实的需要。
二、侵犯亲属人身、财产权利之罪的加重处罚
“十恶”犯罪中,对侵犯亲属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加重处罚的立法目的主要体现在严惩卑幼犯尊长,主要涉及家庭关系内的亲属相犯和婚姻关系内的亲属相犯,共同点都是卑幼犯尊长者入“十恶”,重于同类犯罪。
1.家庭关系内的卑幼犯尊长加重处罚。《唐律疏议》根据亲等的不同、犯罪行为的轻重、犯罪性质的严重程度,对家庭关系内的卑幼犯尊长的犯罪列入不同的“十恶”种类。
比如,谋杀祖父母、父母入“恶逆”,谋杀缌麻以上亲入“不睦”;殴祖父母、父母入“恶逆”,骂祖父母、父母入“不睦”;若亲属间通奸入“内乱”,子孙供养有阙入“不孝”.虽上述内容分属“十恶”的不同犯罪种类,但共同之处是在量刑上均重于同类犯罪。
(1)父祖与子孙相犯《唐律疏议·斗讼律》第 329、348 条规定父祖与子孙间相犯的不同处刑。子孙犯祖父母、父母在犯罪种类上列入“十恶”之“恶逆”,在刑罚上处刑更重、起刑点低。
(2)亲属间相奸亲属之间通奸是严重违背伦理道德的乱伦行为,历代都是重罚的对象。《唐律疏议》中“十恶”之“内乱”是关于《唐律疏议·杂律》总第 412、413 条规定的亲属间相奸,它与《唐律疏议·杂律》规定的常人之间的通奸相比,处罚更重。与前代相比,唐律依据不同的亲等对亲属间的通奸罪规定了不同的处罚,对犯罪人身份的区分更细,涉及的亲属范围更广。并且亲属间通奸罪不同与一般亲属间的犯罪。亲属间的通奸罪不论尊卑,只是论服制,服制越近,处罚越重,即不论卑幼犯尊长还是尊长犯卑幼均加重处罚。
(3)家庭关系内的财产犯罪《唐律疏议·户婚律》总第 155 条规定:“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并且列入“十恶”之“不孝”.《唐律疏议·户婚律》总第 156 条规定:“居父母丧(二十七个月内),生子及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
在唐代,统治者鼓励同籍共居,反对分家析户。这不仅可以维护儒家孝义、防止子孙有亏侍养外,还可以防止降低户等、流失赋役。
2.婚姻关系内的卑幼犯尊长加重处罚。婚姻关系内的卑幼犯尊长加重处罚,主要指妻犯夫而加重处罚。《唐律疏议·斗讼律》总第 325、326 条规定了对殴夫的处罚。与前代相比,《唐律疏议》增加了对犯罪行为的告诉权的规范,夫殴妻者,须妻告,然可立罪;妻殴夫者,须夫告,然可立罪。
这也表明若妻子殴打丈夫,虽入“十恶”之“不睦”,但由于丈夫没有控告,妻子也可能不会受罚。妻、媵、妾殴夫属“十恶”之“不睦”,量刑重于凡人相犯七等或八等刑;反之,若夫殴妻、媵、妾则轻于前者九等或十等刑。这主要源于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对等,三、违背同居相隐不为罪原则的加重处罚控告丈夫、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违背了同居相隐不为罪的原则,属“十恶”之“不睦”.同居相隐不为罪原则是指在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可以相互隐匿犯罪,若违反隐匿义务告发犯罪,告发者获罪受罚。它涉及控告与举证二方面,其思想根基可以追溯至西周时期的“亲亲”.在同居相隐不为罪的发展中,适用同居相隐不为罪原则的人群范围在逐步扩大,这同时表明违背此原则应受处罚的人群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到唐代,这种扩大的趋势仍在延续。
1。《唐律疏议》中违背同居相隐不为罪的加重处罚。《唐律疏议·名例律》总第 46 条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与前代相比,《唐律疏议》进一步扩大同居相隐不为罪的适用范围,从前代要求有服扩大到了无服,并且只要属于大功以上亲,无论是否同居共财,都应容隐犯罪。
对于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这类属于小功以下亲,相互隐匿犯罪,虽不免罪,也可比一般人隐匿犯罪减轻三等处罚。同时“部曲、奴婢,身系于主”,应为主隐罪。表面上,扩大为他人隐匿犯罪的人群范围是放宽刑罚,实则不然。因为在扩大具有隐匿权利的人群范围的同时,具有隐匿义务的人群范围也扩大了,一旦应隐而不隐时,可处罚的范围也随之扩大。所以,扩大同居相隐不为罪的适用范围实际上是扩大了承担义务的人群范围,加重了刑罚。
《唐律疏议》与前代律典一样,在规定应隐匿犯罪的同时,还规定了很多应该揭发犯罪的例外情形。例如:
(1)子孙、部曲、奴婢告发谋反、大逆、谋叛以上罪,勿论。
(2)嫡、继、慈母杀自己的父亲,子孙告发之,勿论。
(3)养父母杀生父母,子孙告发之,勿论。
(4)继母杀被父休弃的、自己的生母,子孙告发之,勿论。
(5)被父休弃的嫡、继、慈、养母犯罪,子孙告发之,勿论。
(6)若因为自己犯罪,案发受审,随答辨顺带供出父祖之罪,不属告父祖之罪。
四、居丧期间违背礼教之罪的加重处罚
《唐律疏议》将礼教的“丧事主哀”的心理规范转化为规范守丧者的外部行为,以实现和监督守丧者的“心哀”,维护了礼教。对居丧期间相同的、违背礼教的行为,《唐律疏议》根据侵害对象的不同亲等处刑不等。如居父母丧,嫁娶、作乐、释吉服(在礼制规范中,服饰包括平常所穿的“吉服”和居丧时生者为死者守丧所穿的“凶服”)、匿不举哀者,与居夫丧期间犯此行为相比,二者处刑一致,但适用的“十恶”种类不同,前者是“不孝”,后者是“不义”.并且犯父母、夫者重于犯余亲,尊卑、长幼、亲等之差影响着刑罚的轻重,贯彻着轻罚尊长、重处卑幼;亲等越近,处罚越重。这些违背礼教、本属道德调整范围的行为也归为犯罪之列,扩大了刑法调整的范围,是一种变相的加重刑罚。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唐律疏议》将不同的丧服等级(表明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亲属关系和尊卑关系) 作为量刑标准,是《唐律疏议》作为法律规范与礼教规范的重合之处,是儒法结合的另一重要体现。但《唐律疏议》更侧重于家庭,这与礼教规范侧重于家族有所不同,并且二者在名称、亲等、旁系亲属和同辈亲属是否分等级等方面亦有不同。从中可见礼法结合既有重合又有分离,表现了唐代在将礼教法定化的过程中,又进行了有益的补充。
五、余论
宗法原则的本质在于其维护的等级性,实现等级的根本目标在于维护皇权专制统治。所以,体现宗法原则的侵犯家庭伦理之犯罪被列入“十恶”,除了维护人伦道德之外,更是维护君主专制主义的延伸,是关乎君主的社稷之道。在犯上与犯长之间,孔子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所以,有血缘关系的“犯上”被列入“十恶”和无血缘关系的“犯上”也被列入“十恶”(如上文提到的杀本属府主、刺史、县令、现受业师,或吏卒杀本部五品以上官长者均入“十恶”之“不义”),其最终目的都是为维护以皇权为代表的专制统治。因此,历代律典在维护君主专制统治时皆同时维护家庭内部的上下有序。正如陈顾远先生所言“:中国向之视为罪大恶极者,不出两类。
其一,关于叛逆之犯罪行为,此为维持家天下之地位,不得不严也;其二,关于反伦之犯罪行为,此为有助君纲之树立,不得不重也。”
故唐律中的“十恶”犯罪从“国”与“家”两个角度规定了十种严重的犯罪,可归结为“尊尊”“亲亲”四个字,其本质是惩治危害君主专制统治秩序之犯罪,这种危害包括直接的侵害与拟制的侵害,拟制的侵害包括有血缘关系的犯上和无血缘关系的犯上。
[参 考 文 献]
[1]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927.
[2]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236.334.
[3]礼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0:.1514.
[4]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0.10.
[5]陈顾远。中国法制史[M].北京:商务印务馆,1934.296.
儒家学人从西晋始,通过八议、官当等,重建了封建特权;通过重罪十条强调确认君权、长老权,其中最主要的谋反、谋大逆、谋叛等条目,接受了经韩非子解释过的老子君道;以礼入法的主体成果准五服以制罪,核定笞、杖、徒、流、死二十等(五、五、五、三、二)...
一、引言:研究核心与解释工具---田皮权与用益物权明清时期一份地权可能分成田底权和田面权,有的地方称其为田骨权和田皮权,田皮权能够独立于田骨权,对土地享有占有、耕作、转让等权利.在这个时期的民间文献和官府的文告中均出现了田皮(田面)、田骨(田底)的字...
我国传统法治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清代纪昀等在编撰《四库全书?唐律疏议?提要》中的说法:《风俗通》称《皋陶谟》虞造律,《尚书大传》称夏刑三千五百,是为言律之始。其后魏李悝着《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
《唐律疏议》是唐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学着作,关于其性质、由来、版本及存在的问题,学界已经有所涉及或探讨①,本文即在此基础上朝前推进。在论述的过程中,有的观点可能会和通说有所不同,有的则是对前人之说的阐发和补充,但无论如何,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