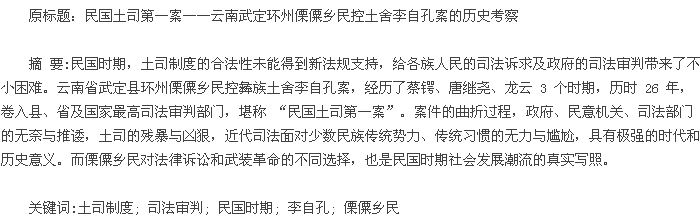
辛亥革命爆发,皇帝被推翻,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各族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土司统治斗争。斗争的方式既有武装反抗,也有司法途径的法律诉讼。由于新兴的民国政府始终未能对封建王朝有机组成部分的土司制度制订出明确的政策法规,宣告其存废,土司制度的合法性未能得到新法规的支持,成为民族国家体制下的残留形态。① 这就给各族人民的司法诉求及民国政府的司法审判带来了不小的困难,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时代发展潮流的选择。
各族人民反抗土司统治,以云南省武定县环州傈僳乡民与彝族土舍的斗争最具代表性。时间从 1912 年至 1937 年,历时 26 年,经历了云南地方政府蔡锷、唐继尧、龙云 3 个时期; 斗争方式包括法律诉讼与武装反抗,二者互为交织; 卷入的部门先后有武定州、武定县、云南省行政公署、云南巡按使署、云南省议会、云南高等审检厅、云南高等审判厅、北京大理院、云南省财政厅等; 原告为傈僳族,被告为黑彝土舍。因此,称其为 “民国土司第一案”应不为过。但是,由于资料缺乏,该问题长期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20 世纪 50 年代进行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对此予以了较大关注,② 但其着眼点是各族人民武装反抗土司统治的斗争,对其进行的法律诉讼,仅认为只是各族农民 “投靠官府取得胜利的幻想”,③ “遭到军阀政府的拒绝”。④ 本文转换角度,拟就环州傈僳乡民控土舍李自孔案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为民国时期土司制度的研究提供一份新的成果。
一、因循: 新原告与旧司法的冲突
清末金沙江南岸的武定直隶州,据 《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五》记载,保留有勒品土巡捕李氏、环州土舍李氏、暮连乡土舍那氏、汤郎马土巡检金氏 4 家土司,其中勒品土巡捕为武职,其余为文职。环州位于武定县西北,明代安纳因征讨武定凤氏土司有功,于嘉靖四十四年( 1565 年) 授环州土舍,传三世,改姓李。入清仍授土舍世职,咸同年间曾获土知州衔。管地东至暮连乡河 50 里,南至高桥 70 里,西至元谋县界 50 里,北至四川界碑塘 70 里。
光绪二十一年 ( 1895 年) ,武定直隶州第15 世土舍李自孔袭职,辖区包括环州周围的 97村,金沙江外 28 村 ( 属江驿县) ,元谋县东部18 庄 ( 约 300 余村) ,共 400 余村。所属居民有彝、傈僳、傣和汉人,其中环州周围 41 村有傈僳人居住。土舍对傈僳人的统治较为苛暴,如遇见土舍,必须磕 3 个头; 不能盖楼房,只能盖矮房; 不能穿棉布,只能穿麻布,裤长不能过膝;不许养狗,不许种桔子、核桃、黄果、栗子等树; 不准读书,不准骑马,等等。清末基督教传入环州地区,傈僳人民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开始出现不满土司的统治和剥削的情结。辛亥革命爆发后,云南都督蔡锷实行征兵制及短期兵役法,环州傈僳青年李万华、李春发、白如一、罗一等参加了滇军,受到辛亥革命民主主义的洗礼。他们退伍后,在家乡宣传说:我们到了蒙自、安宁一带,都没有什么土司,孙中山也在闹革命,打倒皇帝,李土司家这样统治我们,一定要打倒才行。
于是约集各村人民控告土司。最初是 15 个村起来告发,不久发展到 51 村,后江外 28 村也给了不少资助,共有 79 村。村村推出代表,共同商议与土司斗争。1912 年冬月 11 日,15 村人民呈文武定州,要求废除土司的苛捐杂税和各种特权剥削。知州刘宗泽于腊月 26 日传集双方对审,多次调解未果,未能作出判决。 “在这次对审中,土司根本说不出什么道理,讲不过人民。”李自孔坐在被告席上,面对历代以来被视作 “奴才”傈僳人的侃侃而谈,与自己平起平坐,并毫不留情地指责自己,其尴尬和恼怒可想而知。①1913 年 4 月,武定直隶州改设武定县,刘宗泽改任县知事。傈僳人民继续向武定县控告李自孔,刘宗泽判了一次,普玉廷等不服。复诉经前县再判,李春发等仍不服,叠诉于县,并诉于巡按使署,县知事张世勋于 1915 年 6 月 15 日作出一审判决,双方 “各立簿据,陈请盖印,共相遵守”。②在这一时期的控告中,有 5 点是值得注意的: 其一,原告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有思想,有主张,不再是封建时代的蒙冤小民。据地质学家丁文江 1914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14 日在武定县城及环州的考察,经县知事张世勋安排,正在县城告状的 16 位傈僳人造访了丁文江的寓所,“他们的装束完全与汉人一样,为首发言的一位,说得很好的汉话。……这一位傈僳就是民国元年被征去的兵,新近退伍回来。他在军队里两年,眼界当然高了许多,所以就当了反对土舍的首领”。当丁文江问他原因时,这位傈僳人在中央来的 “委员”面前,毫不怯场,侃侃而谈:
从前的老规矩,我们傈僳是奴才,他们罗婺是主人。田地是他们的,我们只能当他们的佃户。不但田地如此,而且我们的生命财产一切都在主人手里,他要我们死,我们就不敢活。现在的这一个李土舍,年纪很轻,遇事胡为。向我们傈僳照例的要钱还不算,而且常常到人家来骚扰,甚至抢夺人家的妇女。前几年来了两个基督教内地会的牧师,一个姓郭,一个姓王。到傈僳地方传教。他们看到我们受罗婺欺负,很为不平。这两年来,许多傈僳都入了教。渐渐不肯听土舍指挥。李土舍因此常常派差役到这种村子里来拿人去乱打,所以我们才到县里来告他,请县长保护我们。当丁文江要给他们测量身体时,傈僳人很怀疑,还是那位退伍士兵解释自己在军队常常测量,他们才勉强配合。③其二,傈僳人的控告,不再是个人或几个人的事情,而是 15 村、51 村、79 村的联合行为。人员方面包括傈僳、彝、傣、汉等民众。领头人以农民为主,后来也有地主参加。他们还在环州东街坡成立团保分局,推李贵荣为负责人,领导民众进行控告和诉讼。其三,控告案的背后原因,除辛亥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外。基督教内地会郭、王两位牧师和傈僳人大量入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曾任土舍护钤的李自孔母亲自氏说:这些人原是我们罗婺的奴才,相传十四代,从来没有反抗。自从郭、王两位牧师来了,他们纷纷的入教,就渐渐的不容易管束了。几个月以前有从省城退伍的兵回到这里来,他们就叫大家抗租。他们说在兵营里面,傈僳和大家一样,不但夷家不敢欺负他们,连汉家对他们都很客气,为甚么再当土舍的奴才。丁文江也注意到基督教的影响,他特别到内地会在武定一带的大本营洒普山拜访两位牧师。其中郭牧师是澳洲人,并不欢迎丁的到访,王牧师夫妇新婚从英国来。其四,被告方面毫无进入民国的新气象,蛮横、颟顸、僵化而固执,对社会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皇朝时代。李土舍家 “原来是个衙门,有大堂、二堂。堂上放着有公案、朱笔、签筒。两边还有刑具。”李自孔袭职时 “身中材,面黄白,无发”。① “酷爱放牧耕地,还爱学习元谋花灯,演唱弹奏。”② 丁文江描述:他才二十七岁,穿一身青布的短褂裤,裤管极大。光着头,赤着脚,一幅黑脸,满脸的横肉。我问他话他一句不答,他带来的差役说: “土舍年纪轻,不懂事,汉话也不大懂得,请委员原谅。”我给他照了一个相,他红着脸坐在凳上,一言不发,却又不走。直等到我对他的跟人下逐客令,他才局局躅躅的走了出去。教育程度和应变能力均极差,又任性妄为,年轻好玩,其统治能力可想而知。他的母亲自氏认为丁文江是 “汉官”,她 “穿了寻常的汉装,黑布裹头,说得很好的汉话”。她向丁文江请求: 傈僳 “近来竟敢到县里告我们了,委员!请你写封信给张大老爷,把他们打几十板子就没有事了。”这应该是当时大多数土司的普遍看法,仍然是封建皇权统治下的习惯性思维。略显例外的是土舍夫人李玉兰,字佩秋,用洋式名片,20 岁 左 右,暮 连 土 舍 的 女 儿,本 姓 糯( 那) ,在昆明女学堂读过书。③ “上下都是省城的时装,脚不过五寸,大概是缠过的。头发结着一条大辫子,拖在背后。桌子上有玻璃镜子、雪花膏、刀牌的纸烟和 《三国演义》。墙上挂着许多照相。”1914 年底,丁文江在昆明遇到张世勋,说案子已经了结,因为土舍夫人 “人很明白,傈僳都爱戴她。正打着官司的时候,土舍太太出来调停,居然发生了效力”。于是丁文江感叹: “我方才知道昆明念过书的女子,究竟不同。”④ 但她与土舍感情不和,一脸的病容,并不能给土舍家带来任何新知识和新思想。其五,尤为重要的是,案件的审理者不管是知州还是县知事,都是传统的大老爷断案,又没有涉及土司制度的新政策法规可以遵循,新原告与旧司法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三方的诉求和目标完全不在同一个层面,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因循旧制,拖延且敷衍了事,以致人民普遍认为州、县官员 “惧怕土司”,“不敢判决”。前举刘宗泽的两次判决,张世勋的第一审判决,均是不同程度减轻土司对人民的剥削,完全不触及土司制度本身,也就是土地的所有权,反而强调“环州乡土民管束权仍属土舍”。张世勋的调停,得到李玉兰的支持,发生短暂效力,仅只是遵循彝族传统文化中女性在战争和纠纷中的调解作用而已。
二、审判: 新司法与旧传统的抵触
民国建立后,结束了 “笞杖之讯”的封建审判制度,规定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原则。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实行公开审判、律师辩护等司法制度。云南地方政府先后成立了审判局、云南高等审检厅、云南司法司、云南司法厅、云南高等审判厅等机构,实行四级三审制,或三级三审制。除昆明曾成立地方审检厅、初级审检厅外,各县公署均为第一审,这是无法逾越的环节。
武定州、县不能解决问题,具有新思想的傈僳原告们赴省上诉,请愿上访。他们 “屡次呈控高等审捡厅,未蒙提讯,只批县查办”,以致“吁诉无门”。⑤ 1913 年 8 月,李春发、普玉廷、马仕洪、雍兴顺等以 “合乡四十一村夷民众”的名义赴省议会请愿,公诉土司李自孔、李鸿勋、李大少爷、土目李正堂、杨宗保等 8 人,恶目王四先生、杨绍安等 9 人 ( “钧系该土署大小头目人等”) 。其 《请愿书》开宗明义, “为土族残民,生灵涂炭,恳请提议,以拯边民而维社会事。”并列举李自孔罪名,一是 “常供之外,杂派土物名目,极其苛细”; 二是 “因讼敲磕”,勒索六百余金; 三是 “借办学堂,勒派巨款”;四是违禁种烟,置民涂炭; 五是报复谋杀,杀死告状人退伍傈僳士兵李万年。⑥ 所附 《环洲乡土司苛磕乡民等清折》,极为冗长琐细,详细列举41 村夷民所承担的正粮、苛派及因讼敲索各项。
并将 1913 年 4~6 月土署头目等敲索干堂达绿村等 7 村银钱及费用银 300 余元,逐项列呈。① 省议会接到 《请愿书》后,“当经审查报告,提出会议。佥谓土司苛派土民,久成惯例。反正以后,均经一律革除,与民更始。”土司追拿枪毙李万年等, “为法律所不容”。于是 “转咨民政长饬催,速为查办,并严禁土司苛派,以苏民困。案经公决,相应将原书、原折咨请贵民政长查核,并希见复。”民政长罗佩金复函省议会,“其土司种种苛派,是否属真,应饬由新任武定县张世勋认真查明严禁,以纾民困。”② 同时指令张世勋 “迅速认真查办,分别呈报核夺。毋稍宕延徇饰。切切。”③面对如此强大的压力,张世勋仍拖延至1914 年 6 月 15 日离职前 ( 新县知事于 16 日到任) 才作出一审判决。
环州乡土民管束权仍属土舍,各佃收租纳粮,仍照旧办理。前收粮银壹两加收三钱,再酌减为每两加收一钱五分。一切赢余陋规,由土舍自行添足报解,不准再立库房名目,于一钱五分之外,格外加收。馔佃前系两年一收,以后按年分上一半。随租杂款,照刘前任判决清单,再行酌减。折征佃谷立名不正,类于摊派,应定为让三收七。
其余夫役细礼暨不正当之苛派,违体制之礼节,悉行取消。并将分别存留租物,各立簿据,陈请盖印,共相遵守。④对于这次来之不易的判决结果,双方似乎均未遵守。“马仕洪等不服,控诉到”云南高等审判厅,仍然没有得到积极回应。1914 年,环州乡民在东街坡成立团保分局,推李贵荣为负责人,向云南高等审判厅、北京大理院控告,走上了类似封建王朝 “告御状”的老路。北京大理院接到控告后,批回云南高等审判厅审理。至此,环州傈僳乡民控土舍李自孔案,终于进入了民国新的司法审判体系。
在这一时期的控告中,有 3 点是值得注意的: 其一,土舍对于傈僳乡民的控告,采取了极为残酷的报复措施。李自孔 “贿串”刘宗泽,派人 “率差百余人,各执枪械,严拿诉讼人等,滥用非刑,威逼苛索”,⑤ 共敲去银钱、牲畜约在 600 余金。同时又派人追杀控告土舍的傈僳首领,将退伍兵李万年抓获枪毙,幸免者只能逃往省城控告。因此,当丁文江 1914 年五月的武定县城见到告状的 16 位傈僳人时,为首者曾称“请县长保护我们”,应是实情。由于李自孔的暴虐、嚣张,刘宗泽的软弱、纵容,原被告双方均没有了退路,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其二,原告方在请愿时,充分注意到了新的时代和新的司法体制,循序渐进,灵活多变。除“屡次呈请执法机关提省执讯”外,他们还向云南省议会请愿,并在 《请愿书》中强调,“况值此民国共和,五族一家,岂能再有此奴隶牛( 马) 等等事乎? 若不呈请究办,将来养痈成患,社会何堪设想?”⑥ 最后直接向国家最高司法部门大理院控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其三,民国政府虽然建立起了一套现代司法审判制度,但大多停留在大城市和发达地区。云南各级司法、民意和行政部门,在涉及无法可依的少数民族土司问题时,新司法与旧传统严重抵触,仍多推诿,甚至敷衍了事。如原告 “屡次呈控高等审捡厅”, “均承批因武定县候案”; ⑦云南省议会论及土目杀害李万年时,认为 “尤属惨无人道,为法律所不容”。但 “事关刑事诉讼,既经该民等来省上诉,自应听候司法机关拟办,本会实未便越俎”。仅只是 “转咨民政长饬催 ( 武定县) ,速为查办”。⑧ 民政长罗佩金论及李万年被杀,“事关刑事诉讼,本公署亦未便越俎外”。指令武定县知事迅速认真查办 “土司种种苛派”。⑨ 似乎将李万年被杀归入司法部门,土司苛派归入行政部门。但不管如何归并,武定县均是第一关,各部门不约而同将责任推到县政府,新的司法审判制度不出昆明,没能深入到广大县级基层政权,这应该是环州乡民控李自孔案悬宕拖延的症结所在。
三、折中: 无力触动旧制度的司法判决
北京大理院批回后,迫使云南高等审判厅民事庭走向前台,接手案件。由审判长推事周安和、推事胡寅旭、书记官王述典面对这个烫手的山芋。由于资料缺乏,我们不知道周安和等人的调查、取证及调解过程,也不知道原被告双方进行了怎样的活动与陈述。1915 年 10 月 31 日( 距震动天下的云南护国首义爆发仅 43 天) ,周安和等匆忙作出控字第 169 号民事判决。其内容主要是:
控诉人: 马仕洪、李太光、雍兴顺、李春发、普玉廷、白如云、普兆宽、李自之、白在明、普忠林,暨武定县环州 51 村民众。
被控诉人: 土司李自孔,未到案。代理人郭宗扬,系该土司之头目; 李洪勋,系该土司之堂侄。
右控诉人: 因土官虐民霸产案,不服武定县民国四年六月十五日第一审之判决,声明控诉,审理判决如左。
主文: 原判变更。环州乡土民仍暂由土舍管束,各土民应缴租谷银粮,仍暂由土舍经理。除应缴条银正供外,不准巧立名目,格外加征。所有从前一切赢余陋规以及馔佃杂派等项,一概豁免。控诉讼费归两造平均负担。
事实: 描述了 1912 年冬以来的诉讼过程。
理由: 控诉人逐一提出不服一审判决四条,并阐明理由。即 51 村人民所种土地为土司所有,折征佃谷收 7 让 3,仍征收馔佃,仍征收杂派。判决书称: “此案争点,一在土地所有权,二在浮收苛派。”对土地所有权,控诉人称系该先辈自行开垦,但不能举出确切证据, “自应维持现状”。对于浮收苛派,原审附条款 12 条,控诉人当庭供称不服者,高等审判厅认逐条进行驳诘。
如第四条,每年随征杂物,属于苛派性质,“有专制陋习”,“专制既经铲除,苛征自应豁免”。“控诉人第四论点,不得谓无理由。
应将此条删除。”第 3 条,每年上纳租粮及折征银钱,由佃户自行上纳,土舍直接自办。“控诉人供称期限太短,请求更改。期限长短,于控诉人无甚损失,应仍其旧。”第 6 条,佃谷不能全免,应定为收 7 让 3。
佃谷属于苛派,“控诉人第二论点,不得谓无理由。此条应即删除。”第 7 条,51 村上纳钱粮,随征夫马团费,有无不定。 “夫马乃前清专制之陋习,剥削小民之弊政”,“民国成立,一律革除。”“随征团费,实系浮征苛派,不能听其仍行征收,应将此条删除。”第 8 条,征收馔佃, “该土舍巧立名目,任意苛征”, “控诉人第三论点,亦不得谓无理由。应将此条末句馔佃二字删去。”其第 2 条涉及馔佃折银,第 3 条涉及夫团薪贴,“查系苛派浮收,均应从删。”
更正条例: 每年征收正当租粮,由土官直接办理,由佃户自行上纳。 “酌定旧历冬月初五日起至初十日止,为上纳期间。”土舍、土民争讼以来,有未上租粮及旧例随征杂款租纳钱者。息讼之后, “酌定为三年摊还,并囗囗只收粮租,不收杂款杂物。囗土署库房,永远裁革。”兴讼后没有取消土舍对夷众的管束权,“则各村夷民及附村居住夷民,自当仍暂管束。如有不法,囗囗调查属实,在佃户一经禀明查实,当受惩戒。”
土署陋规既经废除,头目自不适用。土署雇用人役,所需薪水工食, “由土舍自行筹给,不得向佃户需索。”保卫团应设保董,由 51 村按烟户自行公举办理。 “保董职权内应办各事,凡关于统一江务事项,仍归土舍兼团统一办理。”①在检讨审判过程和判决书中,我们注意到:
其一,折中主义是判决的中心取向。土舍方面,保留了土地所有权。“本案系争土地所有权,两造不能提出确切证据,证明属于何人,自应维持现状。”同时,保留土舍对环州乡民的管束权,强调 “约束较管辖意稍轻,然统系上有囗,当以土舍为纲领,一切行政方能统一”。仅将一审判决中 “环州乡土民管束权仍属土舍”,修改为“环州乡土民仍暂由土舍管束”。此外,自争讼以来未上租粮的乡民,规定三年摊还; 保留土舍兼办团务,统一办理金沙江防务。村民方面,废除了一系列浮收苛派剥削,如随征杂物、佃谷、夫马费、随征团费,馔佃及相关的折银、夫团薪贴。规定佃户自行上纳每年租粮及折征银钱,土舍直接自办,不准土幕、头目干预。土舍库房、土署雇用人役薪水工食等陋规,一并废止。
其二,高等审判厅的判决,仅只是针对一审判决的审理。法庭并未进行新的调查取证,改弦更张,而是抓住控诉人不服一审判决的内容,略作调整,稍示安抚,以求敷衍了事,借以应付北京大理院和控诉方。因此,判决书几乎抄袭了一审判决的内容,挪移删削,补充变通,完成了这一 “艰巨”的任务。
其三,由于民国政府未对封建王朝有机组成部分的土司制度制订出明确的政策法规,宣告其存废,各级审判机构和法官们无法可依,始终无力触动旧的封建制度残留,这也是李土舍们在同类司法诉讼中态度嚣张,而法官们的判决却是折中、因循的症结所在。通观一审、二审判决书全文,始终未见任何一条适用法律条文。对于土地所有权的判决,根据是双方不能提出确切证据;对于土舍约束夷众之权,却是 “稽之志乘”; 对于废除各种浮收苛派,仅是反复强调 “专制既经铲除,苛征自应豁免”、 “有专制陋习”、 “违体制之礼节”、“前清专制之陋习……民国成立,一律废除”。这些冠冕堂皇的用语,用在政府公文中则可,用在法律判决文书中,却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也不能作为法律判决的依据。
其四,前举省议会、省行政公署均将土舍派人杀害傈僳退伍兵李万年一事推给司法机关,归入刑事诉讼。但武定县的一审判决却采取回避态度,明显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 “惧怕”土司之嫌。案件进入云南省最高司法机关后,仍然对追杀控诉人一事回避不谈,避重就轻,将案件归入民事庭审理,其取向耐人深思。
四、革命: 环州及其附近乡民进入时代发展潮流
判决书下达后,于 11 月 9 日由发吏萧维汉送达马仕洪等收执。虽然有诸多缺陷和不满,但村民还是对这份 “告御状”后来自云南最高司法机关的判决寄予了较大的期望。江内、江外51 村共同议决,于 1916 年 7 月将判决书全文泐石立于典莫村,“以垂不朽云耳”。
但李自孔等并未遵守,仍然向人民收取摊派。他还多次变卖田产,向各级官府和司法机关疏通,又上诉至北京大理院。同时向云南都督府状诉 “恶佃恃教,抗租不纳”。都督府认为此案已经云南高等审判厅判决并转送大理院审理,“自应静候院判”,驳回李自孔要求 “饬县提讯审判”的请求。① 此后大理院又发回云南高等审判厅复审,判决农民仍出馔佃费。② 由于南北纷争,战争不断,云南省政府无暇兼顾,各种判决形同空文,环州地区各族人民展开了武装反抗土司统治的斗争。
由于辛亥革命的影响,傈僳人民与土司的纷争一开始就有 “抗租”的特点。控告开始后,土舍对傈僳领头人进行了残酷的追杀,并因讼敲索。41 村乡民组织了武装,进行自卫还击。
1916 年云南高等审判厅的判决没有得到执行,司法途径的法律诉讼完全失败,各村人民停止向土舍缴纳租粮和门户钱。于是土舍派出武装多次抢收乡民庄稼,遭到自卫武装的坚决抵抗。自1919 年开始,大规模的武装反抗开始了,环州各族乡民走上了革命斗争的道路。据 20 世纪 50年代的调查,③ 1919 年,李自孔妻那兰芳 ( 即李玉兰) 勾结四川土匪杨天福,率兵抢劫环州,逼迫 41 村投降土舍。人民起而反抗,省城也派军队围剿,历时两年,打败了杨天福; 1923 年,李自孔二夫人李姨娘勾结四川土匪杨级三抢掠79 村,被自卫武装打退; 1925 年,李姨娘勾结四川会理土匪邬德润企图抢掠 79 村,被自卫武装击退。同时,土舍不断派出武装到处催收粮款,逼收门户钱,自卫武装起而抵抗,多次打击土舍势力。面对双方冲突的不断扩大,武定县政府派人调解,逮捕了土舍师爷蒋秉成。土舍不服,勾结四川土匪李凤美抢掠 79 村,骚扰达四五年之久。后因李凤美绑架了外国牧师王怀仁等3 人,省政府派兵围剿,与自卫武装配合,剿灭了李凤美部。
这一时期,由于土舍的烧杀抢掠,乡民派出李春发等到武定县控告。其时武定县已设立县司法公署,司法官由省委派,县长兼任主任推事官。经过现场勘验,判决取消村民上纳土舍的租粮、门户钱、馔佃和劳役,烧毁房屋自己修理,应缴政府的耕地税由附近村庄代缴 3 年,第一次从法律的角度否定了土司的土地所有权。土舍不服,继续抢收乡民庄稼,抢劫牲畜。1931 年 2月,那兰芳与县政府抢收烟亩罚金,引起土舍与41 村民众的抢劫械斗,历时两年多。
1934 年 5 月,随着云南土地清丈工作的展开,武定县成立清丈分处,开始清丈土地。1935年 12 月工作结束,那兰芳宣布环州 41 村土地属于土舍,遭到乡民的强烈反对,计划联合控告。
1937 年,省财政厅派杨祖镛到环州、慕莲二乡颁发土地执照。其时李自孔已经去世,其子李鸿缨 1930 年袭职,① 无力缴纳执照费。杨祖镛邀集 41 村乡民代表与土舍谈判,自己从中调解。
41 村不再要求土舍赔偿 1930 年抢劫的损失,并拿出旧滇币 1 万元,作为土舍出卖土地的 “划押费”,土地执照上填写当时耕种田地的乡民姓名,土司被迫接受。至此,历时 26 年之后,农民获得了土地业权执照,土舍放弃了土地所有权。
1935 年中央红军长征经过武定县 8 区 1 镇,击毙县长周自得,打开监狱,释放 150 多名“犯人”。红军砸碎了慕莲土司署大厅上的匾额,打开仓库将粮食、衣服等分给农民,并在大照壁上写下 “打富济贫、杀官安民”的大幅标语,②这进一步鼓舞了各村乡民反抗土司统治的斗争。面对时代的滚滚洪流,环州及其附近的部分土司身不由己,纷纷卷入革命潮流之中。
慕莲土舍那维新,原名休,字焕民,1922年袭职。14 岁考入天津南开中学,高中毕业后回乡,不愿袭土司职,并劝母亲授田于民。他在土署大堂贴了一副对联: “这土司不过草莽之臣,享祖先现成福耳; 真丈夫当存鸿鹄之志,为人民谋幸福也! ”后离家去昆明,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 5 分校学习。毕业后被任命为元 ( 谋)武 ( 定) 江防司令。任职期间,“励精图治,刷新政治”,常与地方土豪摩擦,甚至在江边提出“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③禄劝汤郎马土巡检金宇晖,名洪照。在昆明完成初中学业,1939 年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 5分校第 18 期,毕业后在滇军中任排长。期间,与中共地下党员张天祥结识,接受革命思想影响。1946 年脱离滇军,回归故乡。1947 年冬,主动派人寻找张天祥,在张的指示下,以保护家园为名,组建一支 50 余人的私人武装。1949年,金洪照派人联系,将自己的武装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 3 支队 25 团 ( 团长张天祥) 直属游击大队,亦称 “金大队”、 “禄劝游击大队”,任大队长。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 月 4 日,禄劝县临时人民政府在撒营盘成立,出任主席。④到了 1949 年 11 月,环州土舍李鸿缨也率卫队及部分佃农参加云南讨蒋自救军金江支队( 后称马烈大队) 。1950 年 1 月下旬,在元谋县城改编后回家。⑤ 4 月,参与组织 “环州反共救国军独立团”,即 “反共救国军第 3 路军滇北军”⑥ 6 月,被人民解放军武定军分区 16 团围歼,李鸿缨被枪决。至此,环州土司的历史终结。
综上讨论,环州傈僳乡民控土舍李自孔案及武装反抗斗争,是民国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印证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仍然是土地问题。傈僳乡民对土舍的控告及其反复、拖延,最后不了了之,是民国时期各级政府对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缺乏整体考量,未能制定出相应政策法规的真实反映。
其间的曲折过程,政府、民意机关、司法部门的无奈与推诿,土司的残暴与凶狠,近代司法面对少数民族传统势力、传统习惯时的无力与尴尬,傈僳乡民遭受的苦难与他们不屈不挠的抗争,均具有极强的时代和历史意义。而一改落后甚至愚昧面貌、祖祖辈辈处于 “奴仆”地位的傈僳乡民,具有了新思想、新主张,他们对司法途径的法律诉讼和武装革命的不同选择,也是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潮流的真实写照,尤足发人深省。
导言本文旨在通过对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相关立法和司法进行考察,对婚姻法制中变迁内容较多、独具特色的几种主要法制在这两时期的适用情况加以分析,呈现民国婚姻法制基本变迁的脉络及本质。另外,本文的论述还将结合彼时的社会现状,以期对...
第二章民国时期婚姻效力变迁民国婚姻效力的变迁主要体现在夫妻关系中,作为妻的女性在婚姻中身份和财产上地位的变化。在沿袭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夫妻关系中,受夫妻一体主义影响,强调妻对夫的服从,妻没有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而是被夫吸收。妻在身份上和财...
法官惩戒制度在清末修律的筹备计划中已有弃旧革新之议,民初,沿此路径曾制定过专门的《司法官惩戒法》。但是,在旧文化与新制度的激烈碰撞中,法官惩戒制度并没有实践的政治空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按照五权分立的理念,制定了《公务员惩戒法》,形成了...
在河北省档案馆珍藏有民国时期河北高等法院档案,这批档案起止时间为1913年1949年,共计10多万卷。档案按民事、刑事、行政性质分类,内容涉及河北高等法院和伪高法及部分分院所形成的诉讼档案和文书档案,内容较丰富。本期要介绍的珍贵档案是:民国河北高等...
在中国传统的婚姻关系里, 女性的地位是低于男性的, 男尊女卑可以说是传统婚姻家庭关系的特征。相比较男性, 女性权益既少又无法得到强有力的保障。...
第四章民国时期婚姻法制变迁的启示民国正处于一个破坏告成,建设伊始的时期,法律必然面临着近代化的问题。除了传统经济制度瓦解、政权更迭频繁、社会比较动荡、外来文化和近代文明不断冲击等大背景的影响之外,就法律本身来说,法律移植和法律继承也是影...
土地征收法规在技术层面上的完善是解决征地纠纷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在中国的征地立法中普遍存在概念不清晰的现象,大量政治性词汇进入法律,而且是作为操作性词汇使用的[1],使政治和法律混为一谈,尤其是征地中至关重要的三个主体土地所有者、土地需...
在中国,版权观念古已有之,但并没有形成一种普遍性的观念。自从清末《大清着作权律》颁行后,出版企业和作者的版权观念才逐渐增强,并渐为普及。进入民国,沐润着晚清出版业的春风,民国出版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大小出版企业相互竞争,积极角逐,因此,也就...
近代以来,西风东渐,随着西方民法的一夫一妻制理念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女权运动的兴起,妾制越来越受到舆论的抨击,被认为是封建糟粕的表现之一,废除妾制的呼声不断高涨。然尽管废除妾制已成为共识,但在立法上则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明令禁止,即规定纳妾...
结论以妇女运动作为催化剂,通过对固有法和继受法、国家法和习惯法的整合,民国时期基本实现了婚姻法制的近代化,尽管这种近代化基本还停留在表象上而非实质上。民国时期,由于经济基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思想观念也正在荏苒代谢。因为社会现实与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