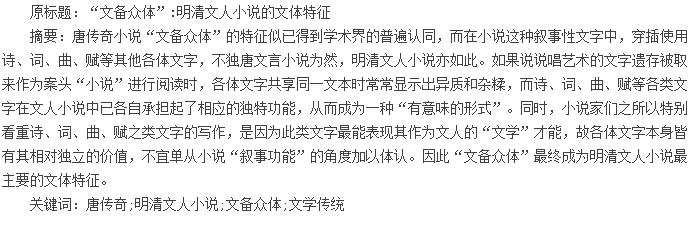
南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中述及唐人传奇小说时有一段研究者们耳熟能详的论述:“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
近代以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等名家著作对此段文字均有征引,故唐传奇“文备众体”的文体特征似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其实,在小说这种叙事性文字中,穿插使用诗、词、曲、赋等其他各体文字,不独唐文言小说为然,宋元以后的白话小说亦如此,尤其是诗赋的韵散结合,特别明显。
当然,一般小说史所谓白话小说,从其性质而言应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可称为“话本”,此类较多保存了说唱作为场上口头艺术时的面貌;第二类可称为“世代累积型”小说,此类文字最初也是说唱艺术的遗存,但大多经历了明清文人程度不一的加工和改造;第三类可称为“明清文人小说”,此类文字虽然也存在版本异同问题,但如文人诗词一样,应视为作家的独立创作。故就其实质来看,前两类本宜视为说唱艺术的文字遗存或说唱艺术的文学改造,而不宜径直视为“小说”,唯独第三类才是真正意义的中国小说。
从表面形式来看,明清文人写作的“小说”与前两类“小说”———“说唱”的文字遗存及其再加工,并没有显著差异。因为小说的写作者们大都有意模仿“说唱”的形式惯例,故诗、词、文、赋以及其他各类文字仍然在文人写作的小说中普遍使用着,这其中与书坊主的作用很有关系①。对此种现象,西方学者大多持批评态度。如曾任哈佛大学教授的毕晓普(J.L.Bishop)曾直白:“中国的传统小说的局限之一,在于滥用诗词。这种传统在乍兴的时候,插入的诗词或许有特定的功能,后来却只是‘有诗为证’,徒能拖延高潮的到来,乃至仅为虚饰,无关要旨。”②在大多数西方学者看来,中国文人小说中插入的各体诗、文对于小说叙事而言是外在的、异质性的,它们扰乱了小说叙事的正常进行,使小说文体显得驳杂不纯。
但从总体看,与前两类“小说”相比,明清文人小说中插用的诗、词、曲、赋以及其他各体文字已经明显减少,早期小说话本和讲史平话中各类诗文频频插入、连篇累牍、与散文叙述部分难分主次、使阅读难以顺利进行的情形绝少发生。然而,数量减少只是一种外在的现象,更为关键的在于,作为形式惯例而运用的诗、词、曲、赋等各类文字在中国文人小说中已各自承担起了相应的独特功能,从而成为中国文人小说的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换言之,“文备众体”已真正成为明清文人小说最主要的文体特征。
诗、词、曲、赋等各体文字从其在小说中所处位置来说,主要分为题目、首尾和正文三类情况。以下我们可分别讨论其在小说文体中的意义。
一、文人小说的“题目”
文人小说的“题目”滥觞自“说话”的题目。“说话”的题目一般是单句,字数不定,用以提示故事内容,如“豫章城双渐赶苏卿”、“齐兵伐燕得胜”、“燕王拜乐毅为帅伐齐”等。但自晚明起,文人小说无论短篇拟话本还是长篇章回的题目,普遍采用一联对偶句的形式。如拟话本集《鼓掌绝尘》、《鸳鸯针》等,长篇章回如《续英烈传》、《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等皆如是,入清以后则更为普遍(当然也仍有沿用单句为题目的,如艾衲居士所作拟话本集《豆棚闲话》,但为数甚少)。
当文人小说题目的形式由单句衍为一联对偶句之后,其基本功能仍是提示故事内容,但实际效果却更为复杂巧妙。文人拟话本小说一般篇幅短小,不分章回,基本上是演述一人一事的生活小故事。以一联偶句作为题目,相对于单句而言,无疑提供了从两个不同角度提示故事内容的可能性,从而大大提高了题目所包含的信息量。如李渔所作拟话本集《无声戏》中有一篇题为“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谭楚玉和刘藐姑分别为故事的男女主人公,谭楚玉为亲近刘藐姑而以旧家子弟身份入戏班学戏,刘藐姑为谭楚玉守节假戏真做而跳入江中逃婚。这样的题目分别从男女主人公这两个角度,双线并举,为我们提示了故事的主要内容。
在单句衍为双句加大了题目信息含量的同时,对偶的句式则非常有利于突显对比、照映的效果,而善恶果报的对比、照应恰恰是大多数短篇拟话本小说情节构思的模式,故而题目与故事显得极为贴合。如李渔拟话本集《无声戏》中有一小说,题目为“妻妾败纲常,梅香完节操”。故事说的是明朝靖历之间有一秀士名马麟如,身边有正妻罗氏,妾莫氏(生有一子)和通房丫环碧莲。一次麟如大病,自思不保,便把妻妾三人唤至床前,询问自家死后,三人作何打算。罗氏莫氏极言必定守节抚孤,还出言贬讽碧莲:“只有守寡的妻妾,没有守寡的梅香”,碧莲并不辩白。麟如被妻妾美言所惑,病愈之后厚待妻妾而冷落碧莲。但妻妾误听传言,以为麟如已死,不但不肯出资敛葬,更亟亟抛家弃子以求再嫁,倒是丫环碧莲安心守寡抚孤。数年之后,麟如归家,真相得以大白。反观题目“妻妾败纲常,梅香完节操”,妻妾三人的德行作为显现无疑,有力地突出了对比讽刺的效果。其他如清初拟话本小说集《五色石》中“投崖女捐生却得生,脱梏囚赠死是起死”等,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明末《鸳鸯针》、《鼓掌绝尘》等之后,一些拟话本小说突破了单回体制,篇幅增至数回、十数回,而章回小说的篇幅通常有数十回乃至百回之多。这些小说故事情节复杂,人物众多,为了紧凑有致地演述故事,一般采取每一回安排两个相对独立的情节单元的布局方式。与单篇小说题目用意在于通过增加角度以“扩展”信息量不同,章回小说的回目更着意于“概括”,两句回目分别概括对应的两个情节单元,回回如此,便详细而整饬地提供出整部章回作品的人物出场顺序、主要事件和情节进展线索,从而为阅读容量极大、纷繁复杂的章回作品起到必要的导航作用。如明末拟话本小说集《鼓掌绝尘》,题“古吴金木散人编”,全书分风、花、雪、月四集,每集十回,自成起讫,各演述一个故事。以《风集》为例,其十回回目如下:第一回小儿童题咏梅花观,老道士指引凤凰山;第二回杨柳岸奇逢丽女,玉凫舟巧合新诗;第三回两书生乘戏访娇姿,二姊妹观诗送纨扇;第四回作良媒一股凤头钗,传幽谜半幅花笺纸;第五回难遮掩识破巧机关,怎堤防漏洩春消息;第六回缔良缘私越百花轩,改乔装夜奔巴陵道;第七回宽宏相国衣饰赏姬,地理先生店房认子;第八回泥塑周仓威灵传柬,情投朋友萍水相逢;第九回老堪舆惊报状元郎,众乡绅喜建叔清院;第十回夫共妇百年偕老,弟和兄一傍联登。细绎这十个回目,我们可以看到,小说的四位主人公“两书生”(巴陵书生杜开先及其友康公子)和“二姊妹”(相国府乐妓韩玉姿及其姐韩蕙姿)之间相遇相慕、诗书赠答、私许夜奔以至蒙相国成全,终得“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整个过程历呈目前,完整分明。
夏志清曾对中国章回小说的回目做过这样的批评:“更有甚者,从晚明起,还要在每一回之前加上一联对偶句作回目,以撮述这一回的内容。因此,在一回的篇幅详细写一件事也嫌不够的情况下,小说家因为回目的关系很容易把两件事包括进去。”如果说中国文人小说中没有结构布局失当的情况,那是不现实的,然而夏氏完全看不到章回小说题目的意义与作用,也显然失之偏颇。
二、文人小说的首尾诗词
明清文人小说的篇首、篇尾诗词(章回小说中通常称为“回前诗”和“回末联语”)都来源于民间说唱艺术的开场和散场诗词。开场、散场诗词是说唱艺人应场上表演的现实需要而设置的,尤其是开场诗词,数量极大,但与所讲述的故事并无必要关联。文人小说沿承说唱体制,保留了设置篇首、篇尾诗词的惯例,但从数量而言,已大大减少,通常篇首基本稳定在一首诗(或词)或一诗一词,篇尾则是一首诗或一联偶句。而且,篇首、篇尾诗词作为文人小说的形式体制之一,是就宏观而言,并不是每部作品都谨遵体例。实际情况是有的有篇首而无篇尾,如李渔的拟话本;也有的有篇尾而无篇首,如清代章回小说《歧路灯》;更多的情况则是灵活取舍,前回篇尾、篇首俱全,后回则或缺篇首、或缺篇尾。如取《红楼梦》现存十余种版本合配,篇首、篇尾诗词仍不完整。这些情况都可以说明文人小说的编写者、评阅者并不认为篇首、篇尾诗词是一定必要的。
虽然并不是每篇小说都谨遵体例,篇首、篇尾齐全,但篇首、篇尾诗词在文人小说中确实承担着自身特有的功能。它们首先是文人小说的一种明显的结构标志,标志着文人小说之一篇或一回之起(首)、讫(尾)。对于长篇章回而言,回首诗与回末联语使每一章回自成一体,对文人小说的叙述节奏起着宏观的调节作用。选择诗词韵语作为文人小说起讫的标志,是对说话艺术惯例的沿承,然而作为文人小说篇首、篇尾的诗词韵语,已不再独立于小说叙事之外,而是试图以诗词韵语的特殊形式对小说叙事提供某种帮助。
与篇首、篇尾诗词在文人小说中所占据的位置相应,它们对于小说叙事的基本功能简单说就是引出故事和总结故事。先说篇首诗词。拟话本延承“小说”旧制,通常由一篇诗词引发一小段议论,有时附加一个相关的短小故事作为“入话”,以引出正话故事。整个“入话”的主要任务是交待小说的创作意图,或暗中自陈“卖点”或动人之处。如李渔拟话本集《十二楼》中有一篇题为《合影楼》,篇首用【虞美人】词曰:“世间欲断钟情路,男女分开住。掘条深堑在中间,使他终身不度是非关。堑深又怕能生事,水满情偏炽。绿波惯会做红娘,不见御沟流出墨痕香?”从这首词中透露的消息,读者约略可以知道,这可能是一则男女情事,这对青年男女被刻意挖掘的深堑相互阻隔,不料原本为阻隔而设的深堑,却成了联系姻缘的“红娘”,二人借水传书、往来赠答,几经波折,终成眷属。这首篇首词浅白机智,如蜻蜓点水般提撮了故事的主要情节、主要矛盾、主要机关,然而只露机巧而不详就里,引起读者急于进入正文的兴趣。
除了自陈佳构以为卖点之外,拟话本小说还普遍采用“反弹琵琶”的方式、摆脱窠臼或陈规,引起读者阅读兴趣。如清顺治年间署名酌玄亭主人的拟话本小说集《照世杯》中有一篇“七松原弄假成真”,篇首为一首古风:“美人家住莫愁村,蓬头粗服朝与昏。门前车马似流水,户内不惊鸳鸯魂。座中一目识豪杰,无限相思少言说。有情不遂莫若死,背灯独扣芙蓉结。”这首古风是才子赠给妓女的。
众人都道妓女情假、情滥、情薄,此篇小说的作者偏道妓女情真、情专、情厚,篇首古风中所呈现的便是一位身在青楼却忠贞不二的佳人形象。
与拟话本不同,长篇章回在回前诗之后并不附加议论或小故事,而是直接进入故事叙述。与此相应,章回小说的回前诗基于所在章回的故事内容,侧重阐发此回的精神、义理。如《红楼梦》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回首诗曰:“捐躯报国恩,未报躯犹在。眼底物多情,君恩或可待。”自家性命多么可贵,眼前财物多么诱人,有这两样在前,国家之重托、君王之恩义且暂置一边。此诗表面上用极端体谅贾雨村处境的口吻,实则以反语冷冷地揭出了贾雨村一类的“忠正之士”空言忠君报国,实则尸位素餐、趋利避害,极其虚伪。读者凭借这首诗可以明白此回题旨之所在,并且在领悟了作者由此传递出来的情感态度之后,带着一种审视的眼光进入此回故事的阅读,从而得到更为深刻的感受和认识。如果在读过本回之后,再重新体会回首诗,则更感回首诗画龙点睛之妙。
由于章回小说回回相接、环环相扣,一些回前诗并不限于提点所在章回的内容、精神,而可以起到照应前后相关情节的作用。如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回首题曰:“朝叩富儿门,富儿犹未足。虽无千金酬,嗟彼胜骨肉。”刘姥姥到贾府求告,凤姐尚在刘姥姥面前哭穷,最后用其微不足道的二十两银子接济刘姥姥。然而刘姥姥感恩不忘,在凤姐之女遭难时援救她脱离火坑,其行为和情谊胜于骨肉之情。这首诗中透露出来的贫与富、丕与泰、亲与仇、施与报之间的微妙关系,尤足深思。诗中所蕴含着的巧姐的因果,经纬前后相关情节,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阈,使其对这一个情节片断能有更深刻的把握。
与篇首相比,文人小说篇尾的形式与功能都更为单纯。其形式大多是一联对偶句,也有用一首诗的。设置篇尾诗(回末联语)的基本用意在于总结、提点,总结是就故事内容而言,提点则指阐发议论,一般二者兼有,或有所侧重。如《西湖二集》第一卷“吴越王再世索江山”,篇尾“后人有诗为证”:“吴越偏安仅一隅,宋朝南渡又何殊?一王一帝同年寿,始信投胎事不诬。”这首诗列举了吴越王与宋高宗诸多相同、相似之处,以证吴越王投胎转世、索取南宋江山的故事并非虚妄。
与章回小说的篇首诗词相似,回末联语有时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清李绿园《歧路灯》第一回“念先泽千里伸孝思,虑后裔一掌寓慈情”,回末诗曰:“万念无如爱子真,遗安煞是费精神。若云失学从愚子,骄惰性成怨谁人。”前两句承上,言谭孝移爱子之心真、望子成龙之心切;后两句启下,预示谭子失学骄惰、沦为败家之子。
可见,文人小说的篇首、篇尾诗词作为文人小说文体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对文人小说的结构体制还是小说叙事而言,都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从而成为中国文人小说极富意味的一种形式因素。
三、文人小说正文中的诗文
篇首、篇尾之外的部分,也就是文人小说主体部分,也广泛运用了诗、词、曲、赋等各类文字。这些诗文按其形式来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有诗为证”、“有词曰”、“但见”、“正是”、“古语云”等为“引头”引出的各类诗文,文人小说中的这类诗文都是沿承“说唱”惯例,以说话人口吻道出,姑且称为“说话人诗文”。另一类是小说故事人物之题咏赠答,这些诗文出于故事人物之口,为与“说话人诗文”相区别,姑且称为“人物诗文”。
1.说话人诗文。相比于“话本”或“世代累积型”作品,文人小说中的“说话人诗文”数量大幅度减少。大多数小说家已注意到“话本”或“世代累积型”作品中各类“说话人诗文”既多且滥的弊病,故他们在使用此类诗文时非常谨慎。最典型是《红楼梦》中的两处“夫子自道”,恰好表明了这种态度。《红楼梦》第十七回至第十八回写到元春归省的盛况,作者有言:“本欲作一篇《灯月赋》、《省亲颂》,以志今日之事,但又恐入了别书的俗套。按此时之景,即作一赋一赞,也不能形容得尽其妙。即不作赋赞,其豪华富丽,观者诸公亦可想而知矣。所以倒是省了这工夫纸墨,且说正经的为是。”在曹雪芹等人眼中,赋、赞之类皆为“俗套”、“闲文”,能免则免,实在大有干系之处才谨慎用之。
然而“说话人诗文”数量减少,只是宏观的、外在的现象,更重要的在于,文人小说中的“说话人诗文”与小说整体显得更为和谐。在“话本”或“世代累积型”作品中,“说话人诗文”多为陈言套语,而文人小说中的“说话人诗文”大都是小说作者为小说故事、人物量身定做的,它们是小说描人状物、铺陈场景或抒发议论的独特方式。李渔的拟话本在设置这类诗文方面尤为用心,所作多机智奇巧,富有表现力,分别举描摹人、物,敷陈场景的三例。《无声戏》集之“清官不受扒灰谤,义士难伸窃妇冤”篇中有一篇描人形貌的【西江月】词云:“面似退光黑漆,发如卷累金丝。鼻中有涕眼多脂,满脸密麻兼痣。劣相般般俱备,谁知更有微疵:瞳仁内有好花枝,睁着把官斜视。”此词描摹知府眼中丑男赵旭郎的形貌,李渔自出心裁,极尽揶揄之能事,读来此人如立目前,谐趣横生。
《无声戏》中另一篇名为“连鬼骗有故倾家受人欺无心落局”,故事说王继轩之子王竺生被当地赌头王小山设计引诱,沉迷赌场,以致倾家荡产,王继轩气绝身亡,然阴魂不散变作赌徒报复王小山,以假银元(冥银)充作真银元,最终使王小山也财去人亡。李渔设计了两首词分别描写真银元和假银元:小山一看,只见:银光闪烁,宝色陆离。大锭如舡,只只无人横野渡,万形似月,溶溶如水映长天。面上无丝不到头,细如蛛网,脚根有眼皆通腹,密若蜂窠。将来布满袛园,尽可购成福地。若是叠为阿堵,也堪围住行人。
仔细一看,你道是甚么东西?有【西江月】词为证:硬纸一层作骨,外糊锡箔如银。原来面上细丝纹,都是盗痕板印。看去自应五两,秤来不上三分。下炉一试假和真,变作蝴蝶满空飞尽。上引两首词即是形容王小山等发现鬼魂带来的四箱真银元一夜之间变成假银元的状况,前首描状真银元,后首描状假银元,银色、丝文、斤两等各方面句句紧扣,处处照应,小山面对真银元的乐极美极,与之后面对假银元疑惑幻灭的心理状态亦显现无遗。
除了描写之外,“说话人诗文”还经常被用于阐发议论,“正是”、“古语云”之类引头引出的诗词韵语即多为此而设。如《歧路灯》第三十三回“谭绍闻滥交匪类,张绳祖计诱赌场”说宦门子弟谭绍闻失于学养、交友不淑,以致愈加堕落,意欲脱身而不得,陷入受奸小要挟的窘境,作者用“正是”引出四句诗来评议这种情形:“自来良贱隔云泥,何事鹤雏入鸭栖?只为陷身坑坎里,秽污谁许判高低。”又如《红楼梦》第二十六回“蜂腰桥设言传蜜意,潇湘馆春困发幽情”,写黛玉夜访宝玉,不料却吃了闭门羹,心中甚是悲戚,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呜咽不已,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鸟栖鸦不忍闻此悲声,俱飞起远避。此处曹雪芹用了一句:“真是:花魂默默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这句虽也是小说作者对于某段故事情节抒发的议论,然而这样的议论与小说情境颇为融合,非但不会使读者“脱出情境”,倒是愈加点染了小说的情境与氛围,令人唏嘘不已。这种阅读感受,和“三言”中常见的动辄“真是:牛羊入屠户之家,一脚脚踏上死路”或“正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之类,一雅一俗,趣味迥异。
文人小说中“说话人诗文”之所以与小说整体显得较为和谐,还有一点尤为重要,“话本”或“世代累积型”作品中的“说话人诗文”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说话人”对于故事、人物所作的描写和议论,而在很多文人小说作品中,这些诗文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视角的“内化”,即不以外在的“说话人”的角度进行描状、议论,而转化为某故事人物之所见、所感,从而与故事更加融为一体。如上引【西江月】词所描摹的赵旭郎的丑貌,是从主审县官眼中见出;那真假银元的形状,也是假王小山之眼所见。另如《儒林外史》中历来颇为人所称道的“马二先生游西湖”一段,无论描人、状物、写景、议论,都已完全内化为马二先生的视角,堪称浑成。可见,文人对于作为形式惯例沿承下来“说话人诗文”是有所反思、有所取舍、有所改造的,这种巧妙利用使得“说话人诗文”与小说叙事联系更加紧密甚或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
2.人物诗文。除了上述“说话人诗文”,小说正文还有一类“人物诗文”,即以小说故事人物之口写作的诗、词、曲、赋之类文字。对“话本”或“世代累积型”作品而言,此类诗文大多直接摘抄自史传、类书、笔记和各类诗词文集或诗文选集,而文人小说中的“人物诗文”多为作者独创。与上文所述文人对待“说话人诗文”的谨慎规避态度不同,文人小说无论是短篇拟话本还是长篇章回,都显示出文人对各类“人物诗文”的浓厚兴趣和用心经营。
文人小说中的“人物诗文”,是中国传统社会知识阶层生活的重要表现。在中国传统社会,吟诗作赋、题咏赠答是知识阶层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赋诗言志、登高为赋,是士大夫阶层才学修养的身份标志。除写诗作赋以显才情之外,熟练掌握当日社会实际应用的各类文体(如奏表、柬札、颂铭等)也是必不可少的。文人小说的题材如果涉及这一阶层的日常生活,那么,小说家以小说故事人物的口吻写作各类诗文,原属“写实”,是极其自然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中国文人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人物诗文”。最为典型的如《红楼梦》,所用诗文种类很多、数量很大,“文学”类如诗、词、歌、赋、对联、灯谜、酒令、戏文、琴曲,实用文如铭诔、笺札、单帖、簿册、卜辞、呈底批文等。又如《歧路灯》,诗赞词赋酒令之类也有,但各种实用文体极多,堪称全备,如信函、书札、柬帖、捷报、告示、章疏奏折、御批、箴铭、吊簿、封条、约单、关文、县票、禀词等,格式规范、严整。即便是极少插用诗文的《儒林外史》,铭旌、关文、牌票、文书、邸、禀帖之类实用文体也偶尔可见,而其末回几乎全由上谕、奏疏、圣旨、榜文、祝文等连缀而成,正如“卧闲草堂”所评:“一上谕、一奏疏、一祭文,三篇鼎峙,以结全部大书,缀以词句,如太史公自序。”
文人小说中的“人物诗文”,是小说表现人物的直接手段。人物诗文出自小说人物之口,是人物情性、学养、才情最直接的外化,故小说家常常借助这些人物诗文直接表现人物,而且以诗文表现人物常常比仅描写外在言行更为深入、微妙。在“人物诗文”运用方面堪称典范的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而大观园内宝玉及众女子的吟诗作对、题咏赠答乃至灯谜酒令,“就是各人的小照”。黛玉之自恋自伤、宝钗之平和雍容、湘云之娇憨豪放、妙玉之孤高自傲,等等,都与各人的诗文相表里。前人论述已备,不复赘述。
“人物诗文”既是人物性情最直接的外化,故高明的小说家每每使用“人物诗文”来暗示人物命运,从而使“人物诗文”成为小说情节设置、整体布局的一种独特机关。仍以《红楼梦》为例。大观园中宝玉及众女子的口吟手书,无一不是暗寓玄机的谶语,它们都暗含着各人既定的命运。这些人物诗文与僧道口中的诗词、太虚幻境中《红楼梦》十二曲及众女子的判词遥遥呼应。它们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使得整个小说容量极大而又浑然一体。
综上所述,诗、词、歌、赋之类的文字在中国文人小说的题目、首尾及正文中各有其用,它们是文人小说的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在标志结构、表现人物、推进情节、渲染意境等多方面多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然而,纵观中国文人小说史上的无数作品,我们很容易发现,差异是广泛存在的。同是著名拟话本,李渔的作品相比于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各类诗文用的就多些,而后者很少;同是著名章回,《红楼梦》中诗文极多,而《儒林外史》则通篇流利的散体白话,几乎没有任何诗文。同是多用诗文,李渔话本和《红楼梦》中的诗文与小说情节、情境相融相生,而大量二三流的作品未必达到这样的效果。
可见,当文人小说已经成为文人熟练掌握以叙述故事、表情达意的书面文体之后,各类诗文的插用实质是作为一种形式惯例而存在,至于实际写作时用与不用、如何使用,往往出于观念的差异或能力高下之别,因而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效果的差异性。如曹雪芹虽然曾借贾母之口对才子佳人小说中的诗、词、文、赋颇有批评,谓之“情诗艳赋”。但那主要是因为才子佳人小说中的诗、赋等文字多水平不高,格调较低。如果其中的诗、词、文、赋确实写得得体,有品味,也很容易赢得时人的称赞。清代著名学者何焯曾云:“仆诗何足道!《梅花》诸咏,《平山冷雁》之体,乃蒙称说,惶愧!”虽是自谦,不乏对此类小说的赞许。小说家们之所以特别看重诗、词、曲、赋之类文字的写作,主要是因为此类文字最能表现其作为文人的“文学”才能,而“文学”才能恰是当时人衡量其作品最为重要的标准。虚构人物、布置情节等固然易取悦受者,但诗、词、曲、赋类文字可更直接表现其文才,获得文人的首肯。
故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白话小说中的诗、词、曲、赋等各体文字皆有其相对独立的价值,不宜单从小说“叙事功能”的角度加以体认。而且,如果小说的接受者缺少诗、词、曲、赋方面修养,不能欣赏作者的锦心妙笔,那么小说中插用的这些文字就很容易被视为累赘之物。这也就是说,中国白话小说中诗、词、歌、赋类文字的价值或评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文学”修养或“小说”观念。对现代或西方的读者而言,这些诗、词、歌、赋类文字的价值也最易被置疑。
从真正意义的中国小说———“明清文人小说”的演进历史来看,自明中叶《金瓶梅》的问世至清中叶《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名著的产生,在二百余年的历史推移中,诗、词、曲、赋等各体文字与小说叙事的和谐程度乃至小说文本整体的“整一性”,就总体而言,显然是渐次提高的。其间虽有高明与平庸之别,精益求精与率尔操觚之异,但从总体来看,诗、词、曲、赋等各体文字大多已成为文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除此以外,诗书画一体还融入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叙事模式之中,“文备众体”也成为这些文人小说的最主要的文体特征。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仅仅从西方或现代叙事学的标准,仅仅其艺术水准亦因此有高下之别,许多“文人小说”文本的驳杂不一也是勿庸讳言的。但这恰恰提醒我们应努力去理解历史的复杂性,而不是笼统地加之以“非整一性”的定评。
“陋”的本义是狭窄、狭小,如“陋,厄陕也”;“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陋”的本义引申,可指知识浅薄,如“少见曰陋”。“陋”的其他引申义还有偏僻、边远,又有粗劣之意,还有粗俗、野鄙的意思。...
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谈及语言的音乐性问题:语言的音节越多,它的重读就越少,它就越合理,它的乐感就越少,它通过书写而损害的东西就越少,它对需要的表达就越清楚。它就是北欧语言。作为孤立语,古代的文言恰恰与德里达此处的北欧拼音语言相反,具有很...
元代文学研究发展至今,要求我们必须以通观性眼光,对各体文学进行整理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元代文学诗、文、词、散曲、杂剧等各体文学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创获,但也存在着各自叙述、互不关联的问题。学界虽有纠正文体彼此割裂、互不关联问题的意愿...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起源于民间说书,说书不但为通俗小说确立了两种基本文体形态话本体和章回体,还奠定了通俗小说说书化的叙事传统。这一传统被现代研究者所重视,在小说史的架构中,宋元明清的通俗小说基本上都在这一传统中被描述。在这一主导思路下,人们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