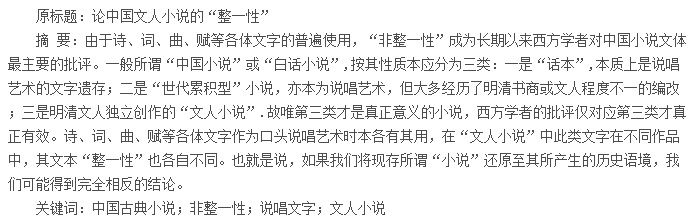
一、自福楼拜、亨利·詹姆斯之后,西方现代小说理论倾向于把小说视为自律自足的艺术品,坚持以“一贯”、“统一”作为小说创作和批评的基本原则,要求风格与内容、形式与功能的和谐一致。若以这种标准来衡量,中国古典小说很容易令人失望。“非整一性”(Heterogeneous)的本义是指事物异质混合的性质,曾任哈佛大学教授的毕晓普(J. L. Bishop)1956年首次将其用于中国小说批评:“长篇小说的早期渊源对自身最为显着的影响,也许是情节上非整一的和插曲的性质,这也是使西方最感困惑的地方。”[1]
认为中国小说缺乏“整一性”的并不限于毕氏一人,着名汉学家、中国小说研究界泰斗人物夏志清教授曾有一段更为人所熟知的话:小说的现代读者是在福楼拜与亨利·詹姆斯的实践和理论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期望得到一个首尾一贯的观点,一个由独具匠心的艺术大师构想出来的对人生的一致印象,以及一种完全与作者对待其题材的情感态度相谐和的独特的风格;他厌恶作者的公然说教和枝节话,厌恶作品杂乱无章的结构以及分散他注意力的其他种种笨拙的表现方式。……我们不能指望中国的白话小说以其脱胎于说书人的低微出身能满足现代高格调的欣赏口味。
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在其《中国文学艺术精华》一书中介绍中国长篇小说的若干特点时,列于首位的就是“非整一性”①,并作了更为具体的描述:在语言上,某些古典长篇小说是以一种简练的文言写成,而在对话中却用了更为口语化的语言;另一些则用白话来叙述,而用诗与骈文来描写和评述,另外还有许多诗词、散曲、书信以及诸如此类的文字,它们以自身的成份出现在小说情节中,而不是作为叙述本身的一部分。[3](P72-73)在大多数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白话小说中插入的各体诗、文对于小说叙事而言是外在的、异质性的,它们扰乱了小说叙事的正常进行,使小说文体显得博杂不纯。
对于诗、词、曲、赋等各类文字在小说文本中的插用现象或西方学者“非整一性”的批评,也有学者持肯定态度,甚至为之辩护。西方学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浦安迪(Andrew H. Plaks),他把“诗、词、曲、歌的引录和插叙”视为“中国奇书修辞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4](P107-114)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台湾学者侯健即有专文《有诗为证、白秀英和水浒传》对毕晓普视诗词为赘疣的观点提出反驳。[5](P146-160)陈平原也认为中国古典小说引录大量诗词“自有其美学功能”[6](P488).但总体而言,过去中国学者包括部分西方学者对“非整一性”批评的应对,大多仅着眼于论证诗、词、曲、赋等文字的“叙事功能”,试图把各体文字都纳入叙事学的框架内去解释,这实际上不自觉地陷入批评者所划定的逻辑线路,故其反批评势必劳而少功,更难切理恹心。
西方学者之所以对中国小说有“非整一性”的批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大多对中国小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小说创作观念缺少必要的理解和同情。如果将中国小说还原至其所产生的历史语境,我们也许可以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
若从语言形式来看,所谓中国小说可分为两大类: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由于真正意义的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相比在总体数量上微不足道,而且西方学者有关中国小说“非整一性”的批评都是针对白话小说而言的,故本文所谓“中国小说”实等同于白话小说,但正是这个“中国小说”或“白话小说”也仍有待进一步进行澄清和界定。
学术界在讨论中国白话小说起源问题时,大多追溯至更早些时候的说唱艺术。根据相关史料,自中唐以来,作为商业经济的伴随物,在城市、乡镇产生了一些职业性的说唱艺人。其所述故事,有的可一次讲完,即后世所谓短篇“话本小说”;有的(多为讲史类)要分多次才能讲完,后世所谓长篇“章回小说”即本源于此。当时的说唱艺人在讲说故事时,主要依赖其素日积累和临场发挥,只有少数讲话人才会有说话的底本,即所谓“话本”.但这些“话本”已大多亡佚,较多保存当时说唱艺术风貌、可视为真正意义的“话本”的作品,除敦煌文献中所存为数不多的“变文”外,主要是元明以来陆续钞、刻的被称为“诗话”、“词话”、“话本”一类的文献。现存最早的“话本”是明嘉靖年间洪楩编刊的《六十家小说》(又称《清平山堂话本》)和万历年间熊龙峰刊印的单行本小说(合称《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尽管这两种集子中所收未必都是宋元旧貌,其间体例、风格不一,误文夺字颇多,显然较多保留着搜集得来时的面貌。冯梦龙编辑的《古今小说》(通称“三言”),一般认为其中的《喻世明言》和《警世通言》中收集旧本较多。现存最早的讲史“平话”皆为元刊本,即《新编五代史平话》等八种。一般认为,上述文献可能相对较多保存了“宋元旧貌”.
自明中叶以来,随着商品经济更进一步的发展,儒家礼教束缚的松弛以及印刷业、刊刻业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以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为主要读物的读者群。故自明中叶以来先后产生了冯梦龙、凌蒙初、李渔等一大批通俗文学家。这些文人有的热心于小说、戏曲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有的则亲自投身于小说、戏曲的模仿和写作。长篇章回体小说最具代表性的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其明清版本甚多,多经不同文人及书商删改、润色。短篇小说代表性的如冯梦龙编辑的“三言”中的部分作品等,其中有许多都经冯梦龙等文人较多的整理和删订。因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长篇以及“三言”类小说集所收小说都是由话本、平话之类整理而来,它们在相当长时期内“文无定本”,而是经过若干代人长时期的不断积累修订,故学界称这类作品为“世代累积型”小说。
而当“世代累积型”小说产生和形成时,文人模仿说唱艺术特别是“世代累积型”小说的形式惯例而写作的“文人小说”也大量产生。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小说,就短篇(所谓“拟话本”)而言,冯梦龙编纂的“三言”之中就有一部分,尤其是《醒世恒言》基本上是文人根据现成的笔记小说和传奇小说所提供的故事而进行的改写,应该算作文人创作。凌蒙初则受书商怂恿先后编成“二拍”.“三言二拍”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话本小说文体趋于定型。受“三言二拍”影响,同时或稍后还有一批文人拟话本集,如陆人龙《型世言》、周楫《西湖二集》、金木散人《鼓掌绝尘》等。入清以后,话本小说从数量上看大大超过明代。从顺治到乾隆的话本集今存世有三十余种,其中水平较高的都是较有名气的文人的作品,如李渔《无声戏》、《十二楼》,艾衲居士《豆棚闲话》,徐述夔《五色石》等。同时,下层文人为满足娱乐市场需要制造了大批色情作品,如《一片情》、《弁而钗》、《风流悟》等。就长篇(章回)而言,明代中晚期涌现了一大批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章回作品。《金瓶梅词话》一般被视为最早的文人独立写作的小说,在其问世前后,除《西游记》、《西洋记》 等神魔类及史传类小说外,还产生了一大批效仿《金瓶梅词话》的邪狎类小说,如《浪史》、《禅真逸史》、《玉闺红》等。入清后则有《醒世姻缘传》、《水浒后传》、《女仙外史》等长篇问世,乾隆朝时更产生了《儒林外史》、《红楼梦》一类的长篇杰作。此外,明嘉靖以后出现了大量以才子佳人为题材而又略有色情笔墨的中篇章回小说,如《钟情丽集》等。承晚明浮艳之风,清初几十年出现了很多艳情小说,如《肉蒲团》等。才子佳人小说也在此种氛围中盛行,代表性的如《平山冷燕》、《玉娇梨》等。
以上提及的短篇拟话本或中、长篇章回作品皆应划入“文人小说”范畴之内。故从中国小说的形成及发展历史来看,今人所谓的“中国小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可称为“话本”,此类较多保存了说唱作为场上口头艺术时的面貌;第二类可称为“世代累积型”小说,此类文字最初也是说唱艺术的遗存,但大多经历了明清文人程度不一的加工和改造;第三类可称为“文人小说”.
就其实质来看,前两类本宜视为说唱艺术的文字遗存或说唱艺术的文学改造,而不宜径直视为“小说”,唯独第三类才是真正意义的中国小说。
在“话本”和“世代累积型”小说这两类文献中,诗、词、文、赋等各类文字确实频频插入、数量极大,批评其文本“非整一性”也基本符合事实。但如前所述,这两类文献本不宜视为“小说”,此类文字从本质而言,乃属“说唱”的文字遗存,故我们在分析其中诗、词、文、赋等各类文字的使用时,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其作为在场说唱艺术时可能承担的功能。
从宋人罗烨所编《醉翁谈录》来看,当时称职的说唱艺人须有多方面的修养、技能,所谓“曰得词”、“念得诗”、“说得话”、“使得砌”,若能如此必须饱读诗书、博学多才。[7](P1).书场的听众多是不识文字的下层民众,而他们一般对上流社会的“雅”文化怀有极高的仰慕,诗、词、曲、赋作为上流社会“雅”文化的重要标志,说书人在讲说故事时若能灵活穿插敷衍,自能博得听众的认可和尊重。同时,对说唱这种场上艺术而言,诗、词、曲、赋等各体文字也各有其用。唐宋以来的民间说唱往往是在瓦子勾栏等公共场合进行,在正式故事(“正话”)开讲之前,说唱艺人通常先吟唱或念诵一些诗词,阐发一通议论,间或讲一些与正话相关的短小故事,借以招徕听众,到适当时刻才“言归正传”“.正话”之前的那些诗词、议论便是所谓“入话”,额外的小故事便是所谓“头回”.如《西湖三塔记》讲述宋淳熙年间少年奚宣赞清明节游西湖,为三怪所迷惑事。因这场故事起自游西湖,说话人开场便吟咏了大量描写西湖景致的诗词,甚至还有好几段数百字形容西湖山水物产的赋。
开场之后进入正话故事的讲述,说话人一般也不是一说到底,而是一有机会便穿插诗文唱、念,一方面显示其才识技艺,另一方面也避免了一味讲述可能带来的枯燥单调。如现存宋人话本《刎颈鸳鸯会》讲述蒋淑贞前后与四个男子通奸,最后被丈夫杀死的故事。此篇正话中插入商调【醋葫芦】鼓子词十篇,故事情节发展一步便插入一篇,每篇前用“奉劳歌伴,先听格律,后听芜词”和“奉劳歌伴,再和前声”之语引出。
说唱的过程除了上述入话、正话之外,还有散场。散场的形式,主要是诗词,称为散场诗,也有诗词之外加一些议论或叙述的。散场诗一般是一两首,浅白通俗,或是撮述故事情节,使听众经历过烦琐的故事讲述之后,最终形成一个整体的印象;或是交代人物结局,标明说话人劝善惩恶的价值取向和教化意图。如《碾玉观音》结尾,以“后人评论得好”引出四句韵语作为收束:“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郭排军禁不住闲磕牙;璩秀娘舍不得生眷属,崔待招撇不脱鬼冤家。”[8](P14)相对“话本”而言,“世代累积型”小说中诗、词、曲、赋等各体文字的插用明显减少。这是因为“世代累积型”小说虽然本质上也是说唱艺术的反映,但随着接受方式从场上到案头的转变,其文字编改都不得不以适应阅读需要为第一目标,故删减或润饰场上说唱遗留下来的大量诗词歌赋便是编改的重中之重。如明嘉靖时着名文人汪道昆为《水浒全传》所作序中说: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各以妖异之语引于其首,以为之艳。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去致语,独存本传。余犹及见《灯花婆婆》数种,极其蒜酪。[9](P167)他说的《水浒》,当是元明之际流行的“词话”本水浒。郭勋削去的致语就是古本《水浒》中每回之前的“妖异之语”及诗、词等骈词俪语类文字,所提及的“蒜酪”,正是指诗、词、曲、赋类文字。①如前所述,虽然今日“话本”和“世代累积型”小说都被视为“小说”,作为阅读的文本,其中插用的诗、词等各类文字的确常常显得累赘不堪,但它们本宜视为场上艺术的文字遗存,只要我们将其还原至原始情境,其中诗、词、文、赋类文字仍可以得到相当的理解,而这一点恰恰是西方学者所忽略的。所以,西方学者“非整一性”的批评,若要真正落到实处,应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真正意义的“文人小说”,即明清文人独立创作的“拟话本”和中、长篇章回体小说。
从形式来看,明清文人独立写作的“小说”与前一类“小说”--“说唱”的文字遗存,并没有显着差异。因为小说的写作者们大都有意模仿“说唱”的形式惯例,故诗、词、文、赋以及其他各类文字仍然在文人写作的小说中普遍使用。但从总体看,文人小说中插用的诗、词、曲、赋以及其他各体文字已经明显减少,早期小说话本和讲史平话中各类诗文频频插入、不计其数、与散文叙述部分难分主次、使阅读难以顺利进行的情形绝少发生。然而,数量减少只是一种外在的现象,更为关键的在于,作为形式惯例而使用的诗、词、曲、赋等各类文字在中国白话小说中已各自承担起了相应的独特功能,从而成为中国白话小说的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化为小说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正是其与“话本”、“世代累积型”作品迥然有别的地方。
“文人小说”沿承说唱旧制,保留了设置篇首、篇尾诗词的惯例,但从数量而言,已大大减少,通常篇首基本稳定在一首诗(或词)或一诗一词,篇尾则是一首诗或一联偶句。值得指出的是,篇首、篇尾诗词作为白话小说的形式体制,是就宏观而言,并非每部作品皆然。实际情况是有的有篇首而无篇尾,如李渔的拟话本;也有的有篇尾而无篇首,如清代章回小说《歧路灯》;更多的情况则是灵活取舍,前回篇尾、篇首俱全,后回则或缺篇首,或缺篇尾。取《红楼梦》现存十余种版本合配,篇首、篇尾诗词仍不完整。这说明白话小说的编写者们并不认为篇首、篇尾诗词是一定必要的。
虽然篇首、篇尾诗词并非通例,但凡有篇首、篇尾诗词者,无不在小说中承担特有功能。它们首先是白话小说的一种明显的结构标志,标志着白话小说起(首)、讫(尾)。对于长篇章回而言,回首诗与回末联语使每一章回自成一单位。选择诗词韵语作为白话小说起、讫的标志,固然可以说是对说话艺术惯例的沿承,然而作为白话小说篇首、篇尾的诗词韵语,已不再独立于小说叙事之外,而是试图以诗词韵语的特殊形式对小说叙事提供某种帮助。
篇首、篇尾诗词对于小说叙事的基本功能简单说就是引出故事和总结故事。先说篇首诗词。拟话本延承“小说”旧制,通常由一篇诗词引发一小段议论,有时附加一个相关的短小故事,作为“入话”,以引出正话故事。整个“入话”的主要任务是交代小说的创作意图或暗示小说的“卖点”.如李渔拟话本集《十二楼》中有一篇题为《合影楼》,篇首有一【虞美人】词曰:世间欲断钟情路,男女分开住。掘条深堑在中间,使他终身不度是非关。堑深又怕能生事,水满情偏炽。绿波惯会做红娘,不见御沟流出墨痕香?[10](P1)从这首词中透露的消息,读者约略可知,这可能是一则男女情事,这对青年男女被刻意挖掘的深堑相互阻隔,不料原本为阻隔而设的深堑,却成了联系姻缘的“红娘”,二人借水传递诗书和幽情。这首篇首词浅白机智,如蜻蜓点水般提撮了故事的主要情节、主要机关,暗藏悬念,引起读者亟亟进入正文的阅读兴趣。
与篇首相比,白话小说篇尾的形式与功能都更为单纯。其形式大多是一联对偶句,也有用一首诗的。设置篇尾诗(回末联语)的基本用意在于总结、提点,总结是就故事内容而言,提点则指阐发议论,一般二者兼有,或有所侧重。如《西湖二集》第一卷“吴越王再世索江山”,篇尾“后人有诗为证”云:吴越偏安仅一隅,宋朝南渡又何殊? 一王一帝同年寿,始信投胎事不诬。[11](P21)这首诗列举了吴越王与宋高宗诸多相同、相似之处,从而指出吴越王投胎转世、索取南宋江山的故事并非虚妄。与章回小说的篇首诗词相似,回末联语有时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清李绿园《歧路灯》第一回“念先泽千里伸孝思,虑后裔一掌寓慈情”,回末诗曰:
万念无如爱子真,遗安煞是费精神。若云失学从愚子,骄惰性成怨谁人?[12](P6)前两句承上,言谭孝移爱子之心真、望子成龙之心切;后两句启下,预示谭子失学骄惰、沦为败家之子。
篇首、篇尾之外的部分,也就是白话小说正文部分,也广泛运用了诗、词、文、赋等各类文字。这些文字按其形式来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有诗为证”、“有词曰”、“古语云”等引出的各类诗文,这类诗文都是以说话人口吻道出,我们姑且称为“说话人诗文”.另一类是出于故事人物之口,为与“说话人诗文”相区别,姑且称为“人物诗文”.
相比于“话本”或“世代累积型”作品,文人小说中的“说话人诗文”数量大幅度减少。明清的小说家们大多应已注意到“话本”或“世代累积型”小说中各类“说话人诗文”既多且滥的弊病,故他们在使用此类诗文时非常谨慎。如《红楼梦》中的两处“夫子自道”,恰好表明了这种态度。《红楼梦》第十七回至第十八回写到元春归省的盛况,作者有言:本欲作一篇《灯月赋》、《省亲颂》,以志今日之事,但又恐入了别书的俗套。按此时之景,即作一赋一赞,也不能形容得尽其妙。即不作赋赞,其豪华富丽,观者诸公亦可想而知矣。所以倒是省了这工夫纸墨,且说正经的为是。[13](P202)第五回宝玉梦入太虚幻境,初见警幻仙子仙姿绰约,有一段“有赋为证”凡二百四十八字,脂砚斋朱笔眉批曰:按此书凡例,本无赞赋闲文。前有宝玉二词,今复见此一赋,何也?盖此二人乃通部大纲,不得不用此套。前词却是作者别有深意,故见其妙;此赋则不见长,然亦不可无者也。[13](P72)在曹雪芹、脂砚斋等人眼中,赋、赞之类皆为“俗套”、“闲文”,能免则免,实在大有干系之处才谨慎用之。
在“话本”或“世代累积型”作品中,“说话人诗文”多为陈言套语,而文人小说中的“说话人诗文”大都是小说作者为小说故事、人物量身定做的,它们是小说描人状物、铺陈场景或抒发议论的独特方式。李渔的拟话本在设置这类诗文方面尤为用心,所作多机智奇巧富有表现力。《无声戏》集之“清官不受扒灰谤 义士难伸窃妇冤”篇中有一描人形貌的【西江月】词:面似退光黑漆,发如鬈累金丝。鼻中有涕眼多脂,满脸密麻兼痣。 劣相般般俱备,谁知更有微疵:瞳人内有好花枝,睁着把官斜视。[14](P75)描摹知府眼中丑男赵旭郎的形貌,自出心裁,极尽揶揄之能事,读来此人如立目前,谐趣横生。
文人小说中“说话人诗文”之所以与小说整体显得较为和谐,还有一点值得指出,“话本”或“世代累积型”作品中的“说话人诗文”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全知视角的“说话人”对于故事、人物所作的描写和议论,但在很多文人小说作品中,这些诗文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视角的“内化”,即不以外在的“说话人”的视角进行描述,而转化为某故事人物之所见所感,从而与故事更加融为一体。
如上引【西江月】词所描摹的赵旭郎的丑貌,是从主审县官眼中见出。
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文人小说中的“人物诗文”,恰是传统中国知识阶层生活的真实反映。吟诗作赋、题咏赠答,本是传统社会知识阶层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文人小说的题材既然涉及这一阶层的日常生活,小说家以小说故事人物的口吻写作各类诗文,原属“写实”,是极其自然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中国白话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人物诗文”.最为典型的如《红楼梦》,所用诗文种类很多、数量很大,“文学”类如诗、词、歌、赋、对联、灯谜、酒令、戏文、琴曲,实用文如铭诔、笺札、单帖、簿册、卜辞、呈底批文等。即便是极少插用诗文的《儒林外史》,铭旌、关文、牌票、文书、邸、禀贴之类实用文体也偶尔可见,而其末回几乎全由上谕、奏疏、圣旨、榜文、祝文等连缀而成。
“人物诗文”是小说表现人物的直接手段。人物诗文出自小说人物之口,是人物情性、学养、才情最直接的外化,故小说家常常借助这些人物诗文直接表现人物,而且以诗文表现人物常常比仅描写外在言行更为深入、微妙。在“人物诗文”运用方面堪称典范的是《红楼梦》,而大观园内宝玉及众女子的吟诗作对、题咏赠答乃至灯谜酒令,“就是各人的小照”[13]P264.黛玉之自恋自伤、宝钗之平和雍容、湘云之娇憨豪放、妙玉之孤高自傲等,都与各人的诗文相表里。此点前人论述已备,自不必赘述。
“人物诗文”既是人物性情最直接的外化,故高明的小说家每每使用“人物诗文”来暗示人物命运,从而使“人物诗文”成为小说情节设置、整体布局的一种独特机关。仍以《红楼梦》为例。大观园中宝玉及众女子的口吟手书,无一不是暗寓玄机的谶语,它们都暗含着各人既定的命运。这些人物诗文与僧道口中的诗词、太虚幻境中《红楼梦》十二曲及众女子的判词遥遥呼应。它们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使得整个小说容量极大而又浑然一体。
综上所述,诗、词、歌、赋之类的文字在白话小说的题目、首尾及正文中各有其用,它们是白话小说的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在标志结构、表现人物、推进情节、渲染意境等多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然而,纵观中国白话小说史上的无数作品,我们很容易发现,差异是广泛存在的。同是拟话本,李渔的作品相比于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各类诗文用的就多些,而后者很少;同是着名章回小说,《红楼梦》中诗文极多,而《儒林外史》则通篇是流利的散体白话,几乎没有任何诗文;同是多用诗文,李渔的拟话本和《红楼梦》中的诗文与小说情节、情境相融相生,而大量二三流的作品未必达到这样的效果。可见,当白话小说已经成为文人熟练掌握以叙述故事、表情达意的书面文体之后,各类诗文的插用实质是作为一种形式惯例而存在,至于实际写作时用与不用、如何使用,往往出于观念的差异或能力高下之别,因而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效果的差异性。
既然是否用诗文并不能成为评价小说优劣的必然标准,故关键问题就在于理解为何中国白话小说普遍地运用诗文,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所孕育出来的白话小说是否具有其自身的“整一性”,这种“整一性”又当如何衡量。这正是本论题所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
曹雪芹虽然曾借贾母之口对才子佳人小说中的诗、词、文、赋颇有批评,谓之“情诗艳赋”.但那主要是因为才子佳人小说中的诗、赋等文字多水平不高,格调较低。如果其中的诗、词、文、赋确实写得得体,有品位,也很容易赢得时人的称赞。清代着名学者何焯对《平山冷雁》等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各类诗文就极为推崇:仆诗何足道!《梅花》诸咏,《平山冷雁》之体,乃蒙称说,惶愧小说家们之所以特别看重诗、词、曲、赋之类文字的写作,主要是因为此类文字最能表现其作为文人的“文学”才能,而“文学”才能恰是当时人衡量其作品最为重要的标准。虚构人物、布置情节等固然易取悦观者,但诗、词、曲、赋类文字可更直接表现其文才,获得同侪之首肯。从这一意义上说,小说中的诗、词、曲、赋等各体文字皆有其独立价值,不宜单从小说“叙事功能”角度加以体认。而且,如果小说的接受者缺少诗、词、曲、赋方面的修养,不能欣赏作者的锦心妙笔,那么小说中插用的这些文字就很容易被视为累赘之物。也就是说,小说中诗词类文字的价值或评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文学”修养或“小说”观念。对现代或西方的读者而言,这些文字的价值也最易被质疑。与老辈汉学家相比,毕晓普等二战后的新一辈汉学家在中国古典文化修养以及阅读古籍的能力方面,都相对不如,这样当他们在阅读诗、词、曲、赋等最能反映中国“文学”传统的一类文字时,难免力不从心,也很容易从“纯粹”的叙事艺术角度得出“非整一性”的结论。
从真正意义的中国小说--“文人小说”的演进历史来看,自明中叶《金瓶梅》的问世至清中叶《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名着的产生,在二百余年的历史推移中,诗、词、曲、赋等各体文字与小说叙事的和谐程度乃至小说文本整体的“整一性”,就总体而言,显然是渐次提高的。当然,从“整一性”的角度看,自有高明与平庸之别、精益求精与率尔操觚之异,其艺术水准亦因此有高下之分,许多“文人小说”文本的博杂不一也毋庸讳言。但这恰恰提醒我们应努力去理解历史的复杂性,而不是笼统地加之以“非整一性”的定评。
参考文献:
[1] 毕晓普:《中国小说的若干局限》,载《远东季刊》1956年第2期。
[2]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
[3] 刘若愚:《中国文学艺术精华》,王镇远译,合肥:黄山书社,1989.
[4] 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5] 侯健:《有诗为证、白秀英和水浒传》,载宁宗一,鲁德才:《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台湾香港论着选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6]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载陈平原:《陈平原小说史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勒菲维尔(AdrewLefevere)[1]12-3在探讨中西方读者对待翻译的不同态度时,曾经指出西方读者在阅读翻译时,会越来越觉得原作伟大,而中国读者在阅读翻译时会觉得译作伟大,因为他们把译作当成了原作。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阅读取向显示了中西读者对待翻译的...
当前,奇幻类文学①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据《华西都市报》报道,在2013第八届中国作家富豪榜中,奇幻类文学的代表人物江南以2550万的年版税收入超过莫言的2400万版税收入而位居榜首。江南上榜的原因是写了小说《龙族》,《龙族》描写的是一个少年在...
三、话语选择在小说中,话语为叙述而存在,同时话语本身也具有存在价值。约翰盖利肖说: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你读一篇小说,发现它很有意思,而情节却并非有多么了不起的独创性;你会一遍又一遍地读某种类型的小说,其中出现的人物都是雷同的;你甚至渴望读这...
作为与读者交流的艺术,小说要实现其说服读者或相互认同的目的,必须依靠作者代理、文本现象和读者反应之间的协同作用。小说修辞的动态系统不仅包括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互动,更重要的是,这种互动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的。叙事不仅仅是故事,而且也...
引言.体验哲学(EmbodiedPhilosophy)一词最早为国内学者所熟知是源起于Lakoff和Johnson在1999年出版的着作《体验哲学---体验性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PhilosophyintheFlesh-TheEmbodiedMindanditsChallengetoWesternThought),在该书中Lakoff和Johnson详...
结语以上我们从隐含读者的视域出发,对小说写作中读者对作者的影响诸问题进行了分析。如果说,这些分析只是就事论事、或只触及现象的话,那么更深层次的分析就应该是,为什么作者总是逃脱不了读者的影响,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必须听命于读者?我们认...
词体文学自其随着燕乐的发展肇兴于唐代之始,就以其不同于诗、文的文体特征与文体传统,注定要经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伴随此的是词学的曲折进程。元代中期以后,词与音乐的关系完全分裂,北曲以绝对的优势取代词而成为一代之文学,迨至明代,世俗文学进一...
金宇澄的《繁花》从问世到得奖,一直引发着评论界对其小说技术和思想的深入开掘。这种兴趣和热情能够长期延续,当然与《繁花》的涵容丰富密不可分,但也是因为批评家面对这一阅读和研究对象,总有言不及义,或者意犹未尽之感。...
历史小说跨越历史和文学两个学科,其性质甚为特殊。它既是一种文学形式,有着与生俱来的虚构性和表现性,又处在历史学构造的强大话语背景之下,并深受其影响,形成了独特而复杂的叙事话语结构。话语是一定数目的陈述之间的散布系统,是对象、各类陈述行为、...
第一章绪论1.1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1.1.1研究背景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愈来愈快,我们的交流方式和传播渠道也愈加广泛,在这种环境背景下,我们的生活也在不断改善,新的传播媒介已经潜移默化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网络文学作为人们生活中的阅读需求,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