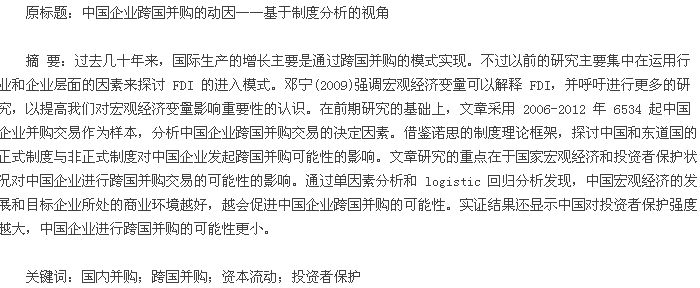
一、引言
按照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对跨国并购的定义,跨国并购包括跨国并购和跨国收购,其中跨国并购是指在当地企业和外国企业的资产和业务合并后建立一家新的实体或合并成为一家现有的企业;跨国收购是指收购一家现有的当地企业或外国子公司的控股股份,即 10%以上的股权。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跨国并购与一般并购的根本区别在于并购方和目标企业位于不同的国家/地区。由于跨国并购还是一种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无法简单的将跨国并购看作国内并购在地理上的扩展,从而直接把基于国内并购发展出来的并购理论直接用来解释跨国并购。特别是考虑到跨国并购需要面对更高的风险,完全有必要分析并购企业选择跨国并购而不是国内并购的原因。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运用行业和企业层面的因素来解释跨国并购的动因,但既然跨国并购同时被视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模式,那么显然不能简单地将宏观因素作为外部变量。
Rossi & Volpin(2004)在研究跨国并购的决定因素时就侧重于国家之间在法律和执法上的差异。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投资者保障越好的国家发起跨国并购的交易数量越多。这一结果表明,跨国并购通常是从投资者保护较好的国家到收购投资者保护较差的国家的并购,起到了对世界各地企业管制制度衔接的作用。在分析了拉美地区 1998-2004 年 868 例并购活动的基础上,Pablo(2009)发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对投资者的保障条件会影响企业发起跨国并购交易的可能性。这项研究认为,目标企业所在的国家有更好的经济和营商环境或资金成本比较高,会加大跨国并购的可能性;收购企业国家产权保护水平较低则会对跨国并购的可能性产生负面影响。Hyun & Kim(2010)则针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达国家对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并购交易进行研究,发现资本市场规模、贸易额、共同的语言和距离是跨国并购的显着动因。而Sun 等(2012)则基于邓宁的 OLI 范式开发出一个包括五个属性:国家产业禀赋、动态学习、价值创造、重构价值链、制度的便利和约束的比较所有权优势的框架来解释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跨国并购行为。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企业掀起了一股跨国并购的热潮。相应地,学术界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研究也逐渐关注起来。Rui & Yip(2008)采用战略意图的角度进行分析后认为中国企业战略性利用跨国并购来实现目标,如在充分利用制度激励和最小化制度约束的条件下,收购战略资源以抵消他们的竞争劣势,并利用其独特的所有权优势。在对 TCL 集团,京东方和联想三个案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Deng(2009)运用制度理论,以资源驱动模型来解释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发现中国企业跨国收购战略性资产,是中国独特的体制环境的必然逻辑结果。Yang(2009)则在以 1985-2006 年期间 671 家中国企业 1004起跨国并购交易为样本进行研究后,认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显着影响因素包括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失败的经验、监管的变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张建红等(2012)运用 2003-2009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数据对 36 个产业的国际化与其产业特征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产业海外并购的动机和能力与产业收益、产业的技术密集度、产业出口强度和产业规模呈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而与产业的劳动密集度呈显着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出口强度对要素密集度与海外并购的关系有显着的调节作用,而且对两种要素 (技术和劳动) 的调节作用方向相反。
就目前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动因的研究成果来看,虽然已经有学者关注到制度因素的影响,但是尚没有学者运用制度的观点将国内并购和跨国并购放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下研究。站在企业的视角上,选择国内并购还是跨国并购是一个企业战略问题,会受到宏观环境和自身条件的影响;但是站在宏观经济的角度上,企业为什么会选择成本显着较高的跨国并购,则必须抛开单个企业或产业的具体特征,寻找一个统一的解释。不同的制度安排会使个人和企业面临不确定性的时候,会更青睐特定类型的解决方案,从而形成固化的统一的特征。因此,文章尝试通过制度的视角来分析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
诺思(Douglass C. North,1994)认为制度是组织为追求进化和资源分配的目标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包括正式的规则 (如宪法、法律和法规)、非正式的限制 (行为公约和自律规范) 以及制度的执行机制。因此,文章认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在全面考虑其他宏观因素的前提下,不仅要考虑正式制度的影响,而且要需要考虑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要考虑由于我国和东道国各自制度环境的影响。另外,现有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动因的研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倾向是将跨国并购视为企业的战略选择或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选择,而没有将其和并购理论整合到一起,将国内并购和跨国并购放在一个框架下探讨。因此,文章的创新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基于诺思的制度观点,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来分析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另一方面是将国内并购和跨国并购放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下研究,而不是将跨国并购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进行分析。
二、理论分析和假设
Dunning & Lundan(2010)认为制度是跨国公司的优势之一。经营环境对企业能力的限制不仅是通过正式的制度,而且还通过包括如惯例、语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非正式制度。不同的制度会使个人和企业面临不确定性的时候,会更青睐特定类型的解决方案。而且企业动态能力的发展涉及投资和不可逆转性,因此跨国公司在母国的制度环境下形成的应对模式会在一定程度固化,从而形成动态优势。跨国公司会利用这种优势对外投资,获取收益。也就是说,制度会对企业是否进行跨国并购产生影响。另外,在国内看来似乎所有差异是企业或行业特有的,但是在跨国的背景下,有些差异已被证明是地缘性的。
如果假设企业没有受到各自国家制度环境的影响,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发起跨国并购的收购方企业在全球水平不是随机分布的,而是看似局限于特定区域。也就是说,有效的制度环境会对企业发起跨国并购有促进作用。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效率的量化分析主要是两种:一是案例分析,如对某一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的绩效进行量化分析,庄园制 (诺思)、船运制度 (诺思)、奴隶制度 (巴泽尔、福格尔) 等制度效率的分析都属于此类;二是模型分析,如用经济模型分析制度变量的经济效率,刘易斯的经济增长模型就属于此类 (卢现祥,2003)。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同制度安排下经济绩效是不同的。因此,文章认为一个国家 /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最能体现该国家 /地区的整体制度效率。Pablo(2009)就用投资国和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比来测试高增长的环境对跨国并购的促进作用。文章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体现了中国经济制度是有效率的,中国企业的成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实现途径和表现方式,而跨国并购是中国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的最快途径。因此文章提出假设 1:
假设 1:中国经济制度的效率会促进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
东道国的治理水平是跨国公司选址决策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对于不熟悉游戏规则的外国投资者来说,东道国的治理水平是一个重要的问题。Dunning & Lundan(2008)认为一个国家制度的内容和质量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程度和形式有重要影响。东道国制度会影响国外企业决定是否和如何进行直接投资。例如,东道国的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内容和质量会与知识寻求型的外国直接投资密切相关;东道国的财政激励手段可能会吸引效率寻求型的外国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拉丁美洲、亚洲或东欧,社会资本的质量和内容、犯罪、腐败和社会功能障碍的程度可能是外国投资者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Rossi & Volpin(2004)在对 49 个国家影响跨国并购的制度差异和管制水平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对投资者的保障程度会影响东道国跨国并购活动水平。更进一步来说,经济形势越好和对投资者更友好的东道国,跨国并购交易的可能性更大(Pablo,2009)。再加上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历史短、缺乏足够的经验和人才,因此更倾向于到制度更规范、对海外投资者更友好的东道国或地区,从而文章提出假设 2:
假设 2:东道国/地区的投资制度环境越好,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交易的可能性更大。
Rossi & Volpin (2004),Pablo(2009)等的研究成果表明投资国有更好的投资者保护制度会促进跨国并购交易,认为跨国并购是实现全球治理水平收敛的有效途径。而对于本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安排有利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从而产生对跨国并购的正面影响,比如中国政府控制着许多重要的工业和金融资源,金融市场被国有银行垄断,因此中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具有独特的融资的优势,特别是在大规模的并购交易(Sun,et al.,2012);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制度安排存在制度约束,企业为了突破制度约束,从而进行跨国并购(Deng,2009)。无论从正式的制度的角度,还是非正式制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投资制度和企业治理显然还达不到先进水平,而且从宏观上看也不存在资本过剩而寻求对外直接投资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企业早期一些高调跨国并购交易以失败告终之后,如 TCL 收购法国汤姆逊,上汽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德隆集团购买美国的穆雷等,中国企业已经学会避开涉及棘手整合的并购目标,如品牌、销售网络、商誉,而是专注于硬资产,如矿藏、石油储备,或最先进的技术和研发,从试图购买国外的市场份额,转向加强其在国内的市场份额(Williamson andRaman,2011)。因此,文章更倾向认为,中国投资制度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存在反向影响,为此文章提出假设 3:
假设 3:中国的投资制度环境越好,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交易的可能性越小。
三、实证检验
1. 样本选择
文章收集的中国企业并购交易样本观测期为 2006 年至2012 年,来自 Bureau van Dijk Editions Electroniques SA (简称BvD) 提供的 Zephyr 《全球并购交易分析库》。按照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和中国商务部的统计制度,中国大陆企业对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投资都属于对外直接投资。因此,文章将中国大陆企业之间的并购界定为国内并购,中国大陆企业发起的对大陆地区以外的企业的并购作为跨国并购。样本涉及的其他数据来自于 BvD 的 EIU Countrydata、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数据库。
在 2006 年至 2012 年期间,Zephyr 数据库收录的中国企业完成的并购交易共计 6658 起,其中国内并购交易 6212 起,跨国并购 446 起。按交易完成的时间分析 (见表 1),可以看出,虽然中国企业发起的并购仍然以国内并购为主,但是跨国并购交易总体数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不过无论是按交易数量,还是按照交易比重来看,增长并不稳定,反而呈现出明显的波动性,而且表现出与国内并购交易的增长波动高度的一致性,说明了跨国并购和国内并购整体上驱动因素有一定的共同性,而文章主要着重分析的是两者不同的动因。

按照发达国家跨国并购的经验,一般投资国企业率先进入的是地理接近、制度和文化环境类似的东道国/地区,然后伴随着经验的增长逐步向全球扩展。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的发展历程却有所不同。首先,按东道国/地区分析,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交易的前三位是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除了香港符合发达国家跨国并购的发展路径,其他两者都属于着名的国际避税港。如果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国际避税港名单对照,还可以发现百慕大和萨摩亚。总的来说,东道国 / 地区属于国际避税港的交易数量共计 120 起,占全部跨国并购交易量的 26.91%。显然,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交易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为了对外直接投资,而是一种避税行为。这部分交易显然不适合纳入分析的范围。其次,排除属于避税港的交易,则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交易的东道家/地区前三位是香港、美国、德国。如果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公布的发达经济体名单对照,东道国/地区属于发达经济体的交易数量共计 199 起,占全部跨国并购交易量的 44.62%。可以看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目标地区虽然偏好发达国家/地区,但是并不占主流,这和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中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跨国并购主要目标地区是发达国家/地区的观点又有所不同。
2. 变量的定义
文章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进行分析。因变量(CMA)是一个虚拟变量,如果并购是跨境的则为 1,否则为 0。在综合考虑样本的全面性、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尽量排除其他因素干扰的前提下,筛选后得到 6534 个样本,其中国内并购 6212 起,跨国并购 322 起。
为了能够描述各国不同制度环境对跨国并购的影响,Rossi& Volpin(2004)沿用了 La Porta 等(1998)设计的如会计准则指数、股东保护指数、执法质量 (法治) 指数、股东权利指数以及法律体系类别等一系列代理变量来衡量制度质量。Pablo(2009)则采用了 Dow Jones and the World Heritage Foundation 每年公布的经济自由指数(Economic Freedom Indexes)来衡量拉美各国的制度水平。而 Hyun & Kim(2010)采用了 Political Risk Services Group发布的 《国际国别风险指南》 中的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指标来评价各国的治理质量。可以看到,不仅对于采用哪些指标作为制度质量的代理指标是缺乏统一标准的,而且对于哪些类型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会对跨国并购产生影响也缺乏一致的观点。文章认为要衡量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对跨国并购的影响:首先要考虑整体经济制度是否有效,而经济增长是最能够体现一个经济体的整体效率,所以采用 GDP 实际增长率(以 2005 年为基期) 作为代理变量(CGDP)来衡量中国经济制度的整体效率。其次,需要侧重考察那些直接影响投资者并购决策的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即对投资者保护相关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因此在综合考虑指标权威性和综合性的基础上,最终选择世界银行按年度公布的 《营商环境报告》 中“投资者保护强度”(Strength of Investor Protection i-Index)指标作为代理变量(IPI)来衡量某一国家 / 地区对投资者来说的制度环境的优劣,该指标从 0 到 10 评分,分数越高则表明对投资者保护强度越大,同时将中国的“投资者保护强度”指标(CIPI)作为代理变量来衡量中国的投资制度环境。除此之外,文章还参考相关文献选择东道国的贷款年利率(LRAT),东道国和中国之间的贷款年利率之差(LRATB)作为控制变量。
3. 实证结果
(1) 描述性统计
表 2 给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该表可知,CMA的均值为 0.049281,说明中国企业发起的并购中只有约 5%的交易为跨国并购,也就是说现阶段中国企业并购的目标还是主要集中在国内。CGDP 的均值为 0.596840,说明中国宏观经济在以 2005 年为基期的情况下,实际经济增长率高达 60%,经济增长是强劲的。IPI 的均值为 5.066192,而 CIPI 的均值为4.955755,说明东道国/地区比中国的“投资者保护强度”高,即东道国/地区的投资制度环境比中国更有优势,而且观察最大和最小值,会发现东道国 / 地区的投资制度环境差异很大,这是由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目标地区范围广而导致的。LRAT的均值为 5.949242,而 LRATB 的均值为 0.005113,说明平均来说,东道国 / 地区比中国贷款年利率高,即东道国 / 地区的资本收益率比中国更高,但是如果观察 LRAT 的最大、最小值,会发现东道国贷款年利率波动幅度巨大,这是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目标地区多样化所造成的必然现象。
表 3 给出了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由表 3 可知,CMA 和 CGDP 的相关系数为正,但统计不显着,无法支持或否定假设 1,有待后面进一步的分析。CMA 和 IPI 在 1%水平下显着正相关,这与假设 2 的预期一致,即东道国对投资者保护程度越高,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可能性越高。CMA 和 CIPI 在 10%水平下显着负相关,这与假设 3 的预期一致,说明中国对投资者保护程度越高,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交易的可能性越小。


(2) 回归检验
表 4 中模型 1、2 和 3 均在 1%的水平上显着,而且所有回归结果的 Z 值都经过 Huber-White 稳健标准误差调整。由表 4可知,模型 2 和 3 中,CGDP 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着为正,说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越快,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可能性越大,也就是说中国宏观经济的增长会促进中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支持了假设 1。模型 1 和 3 中,IPI 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着为正,说明了东道国对投资者保护程度越大,越会相应增加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交易的可能性,这与假设 2 的预期一致。同时考虑到,IPI 的均值为 5.066192,而 CIPI 的均值为 4.955755,即总体而言,东道国/地区比中国的“投资者保护强度”高。中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这证明了中国目前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但是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交易中却无法利用在国内制度环境中形成的优势。一方面是因为对于并购交易来说,最重要的制度环境要素是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如信息披露、对管理层的监管、对少数股东的权益保护以及有利于投资者的法律制度等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相对而言,中国这方面的制度并不完善。由于中国在投资者保护方面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缺陷,对于中国企业的并购行为是一种限制,而不是激励,所以中国企业更倾向为了冲破这种束缚而直接到海外并购。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和国内并购不同,制约和影响跨国并购交易的除了经济方面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以外,还有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非经济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由于东道国家 / 地区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导致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受到阻挠,甚至直接被排斥的案例屡见不鲜,可以说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最大的问题是面临一个敌意的大环境,这是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跨国并购中所没有遇到的问题,这是地缘政治的延续而不是单纯的文化冲突。因此,中国企业在无法回避敌意大环境下,会更倾向选择对投资者更保护的国家/地区,是自然而符合逻辑的。这也解释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选择的目标企业分布:如果单独选择,首选当然是环境友善且最重视投资者保护的香港;但是最大分布地区还是虽然政治和意识形态与中国冲突不断但投资者保护程度高的 OECD 成员国,因为既然敌意环境不是企业个体能够解决和回避的,那么选择具备相对完善投资者保护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东道国/地区就是其次优选择。
模型 1 和 3 中,CIPI 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着为负,说明了中国对投资者保护程度越大,反而会相应减少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交易的可能性,这与假设 3 的预期一致。无论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是获取自然资源,还是为了进入海外市场,根本目的都是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中国企业缺乏跨国并购整合的经验,早期跨国并购失败也让收购企业吸取了经验和教训。
本来中国经济增长就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在本土扩张更能分享宏观经济增长的红利,如果中国企业投资制度环境比海外更好,中国企业显然在国内并购比跨国并购更能有利于企业盈利的增长。因此,中国投资制度环境越好,反而会减小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交易的可能性,特别是在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还远远领先于世界水平的时候。
控制变量中,LRAT 的系数在模型 1、2 和 3 中显着为正(显着性水平 1%),这说明东道国的贷款年利率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可能性正相关。LRATB 的系数在模型 1、2 和 3 中显着为负 (显着性水平 1%),这说明中国和东道国之间的贷款年利率之差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可能性负相关。跨国并购是资本国际流动的一种形式,必然是符合国际资本流动遵循的利率差原则,东道国的资本收益越高,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可能性就越高。

四、结论和不足
文章以 2006 年至 2012 年的中国企业 6534 起并购交易作为样本,主要基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视角对中国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动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经济制度的有效性会促进中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交易会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而增长。第二,东道国/地区的投资制度环境越好,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交易的可能性更大。第三,中国的投资制度环境越好,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交易的可能性越小。另外,东道国的贷款年利率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可能性正相关,东道国和中国之间的贷款年利率之差和目标企业的投资报酬率与中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可能性负相关。这些结果表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行为虽然遵循资本国际流动的一般规律,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本国的经济形式和东道国的制度环境。
文章的不足在于:跨国并购涉及投资国、东道国、投资企业和目标企业四方两对关系,因此受到宏观和微观因素的多方影响。而文章主要只分析了宏观因素的影响,没有将微观因素也纳入考虑,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卢现祥.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M].北京:发展出版,2003:224.
[2] Deng Ping. Why do Chinese firms tend to acquire strategic assets ininternational expansion? [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09(1):74-84.
[3] Dunning John H.,Lundan Arianna M.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dynamiccapabilities i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J].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2010,19(4):1225-1246.
[4] Dunning John H.,Lundan Sarianna. Institutions and the OLI paradigm of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8,25(4):573-593.
一、引言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大量的跨国公司在我国建立子公司,中国企业也不断拓展其海外市场,参与到国际金融市场中进行融资。同时,我国投资者也开始把目光投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市...
近年来,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相关问题,中央政府从战略层面上愈益重视。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走出去作为构建...
从宏观方面来讲,金融市场的高度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促进作用,其作用动力主要来源于为微观实体经济提供廉价的融资成本,因此,研究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应着重从微观角度,研究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中的企业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融资约束和预...
第4章风险解析4.1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现状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各国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与竞争频繁而激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这也给中国企业贯彻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等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与...
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而存在的,面对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必须维持生存并不断壮大,然而生存与壮大都必须以营利为基础。...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复关谈判的进行,我国重返关贸总协定已为期不远。一旦重返关贸总协定将对我国的国民经济产生全面、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我国吸引外商投资也将受到影响。一、复关为我国吸引外资提供的机遇1、复关后,我国要削减关税,进口...
第一章当代中国艺术品市场概述1.1现状与挑战我们研究中国艺术资本化的发展,就离不开艺术资本的发展,而艺术资本的发展又和艺术品市场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自古就有艺术品交换。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是一个资本运作从无到有,...
股份回购是指上市公司利用自有资金等方式从股票市场上购回本公司发行在外的部分股票的行为,最早起源于美国。得益于美国证券市场的快速成长,股份回购逐步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
第5章防控措施5.1应对国有企业内部风险: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责权利之间的关系要理清摆正。国有企业亏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企业负责人个人的直接利益与该企业经济效益责权利关系不对等所造成的。国有企业法人对企业没有所有权,只有经营权。企业...
投资作为中小企业决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面对市场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所暴露出的问题也更加突出。对此,当务之急是分析中小企业的投资现状,找出问题所在,并制定相应的解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