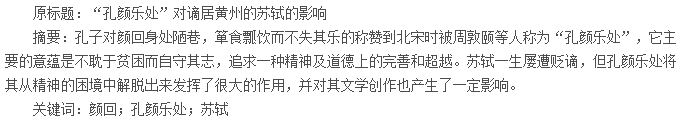
苏轼是传统文人的代表,他既有强烈的政治进取心,更有丰富的文学创作,“乌台诗案”是其一生进取转退的分界点。从谪居黄州开始,其早期“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一步步冷却,而渐趋于“性命之忧”。然而与一般士大夫遭贬谪之后显现的愤懑忧虑不同,苏轼被贬黄州,在经历过初期的失落之后,更表现出一种乐观通达。对他这种身处困厄之境却依旧怀有积极的姿态,有人解释为其政治热情减退后,由儒入佛入道,看破世事,自求达观。但是,正如李泽厚先生在论述“儒道互补”这一命题时所说,“庄老道家毕竟只是知识分子所找到的幻想的避难所和精神上的慰安处而已,他们生活、思想以至情感的主体,基本上仍然是儒家传统。”[1]
作为传统文人士大夫的代表,苏轼自然也摆脱不了这颠扑不破的框架,儒家思想始终存在他身上并发生作用,只是”乌台诗案“之后,其用世思想隐退,而体现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后者。更为重要的是,源于先秦,在宋朝被新儒家再次提出升华的“孔颜乐处”对其行为处事以及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孔颜乐处“的意蕴
“孔颜乐处”这一概念最初是在二程回忆其师周敦颐时提出的,曰:“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2],这说明作为理学开山鼻祖的周敦颐很看着“孔颜乐处”,因此经常让学生思考,撇开周敦颐对孔颜乐处的重视,我们先从先秦儒家着手,了解“孔颜乐处”最初的意义。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3]贤哉回也!一单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4]《论语》中这两条语录的重点在于颜回生存环境的恶劣———陋巷、箪食瓢饮,但后面紧跟“乐”字,就使两句话的意蕴发生大变化,且将主要意思集中在“乐”上。孔子称赞颜回虽然身在陋巷,只有粗茶淡饭但仍然不失其乐,这在常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富贵安乐是人之所欲,但颜回却身处贫困而不失其乐。同样是在颜回不与众同,贫困中自得其乐这个层面上,孔子给予赞赏。贫贱而不失其志不失其乐,反安然自守,这是被周敦颐称为“孔颜乐处”的主要内容,它给人一种精神上的引导,教人超越物质条件的贫乏,获得精神的快乐与升华,不汲汲于富贵名利。联系孔子一生的遭际,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遭受许多挫折,不但得不到诸侯王的任用,有时甚至还要受到别人的嘲笑,楚狂接舆和五谷不分的故事是最好的说明,但是面对这些艰难挫折,孔子依然不改其志,继续游历,以期重用,正是孔子自身的遭遇使得他对颜回的处境与行为深有同感,即而大加赞赏。可以说,孔颜乐处是儒家积极追求现实进取之外的另一条处世之道,当儒者在进取之路上失意和穷困潦倒时,还可以退回来,自守其志。这也就为后世的文人士大夫提供了一个精神避难所。
《论语》之后直至唐代,未有人再论述“孔颜乐处”,其原因盖为汉朝以后读经解经蔚然成风,儒者只是在经典中寻求微言大义以及对世道人心有教化作用的内容,而对“孔颜乐处”这样具有人性关怀的观念置之不顾。至韩愈提倡“道统”,李翱主张“复性”,儒学才渐渐回归于对人之心性的关照。但是于韩愈,孔颜乐处却并不是他所同意与赞赏的,在《闵己赋》:“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时势而则然;独闵闵其曷已兮,凭文章以自宣。昔颜氏之庶几兮,在隐约而平宽,固哲人之细事兮,夫子乃嗟叹其贤。恶饮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颐神而保年;有至圣而为之依归兮,又何不自得于艰难?……聊固守以静俟兮,诚不及古之人兮其焉悲!”这首赋的大致意思是说颜回不过一穷巷陋士,于人无益,于世无补,孔子称赞是由于自己不能达成志向,遂转而求精神胜利。虽在陋巷箪食瓢饮,却可以安神养年,并且有圣人可以依靠,没什么艰难的,反观自己,“欲为圣明除弊事”却无人赏识与爱怜。其中表现的是一种由羡慕到愤懑哀怨的感情,且对孔颜乐处不屑一顾与自身的经历和处境有密切关系。
到了北宋周敦颐,他“返回到《周易》,建立无及而太极的宇宙论体系,这成为其修养论的理论根基,而其人生的精神诉求就是在《论语》那里找到渊源的‘孔颜乐处’,达到与道为一的精神和乐世界。”[4]
面对孔颜所乐何事,周敦颐的回答是:“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5]
这即就是说,颜回追求的是“大道”,因此对世俗的富贵贫贱安之若素,处之若一。后来,程颢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又说“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历来的学人都认为这句话道出了“孔颜之乐”的精髓,那么,圣人之道是什么?我们认为,是不耽于贫困安乐而自守其志,追求一种精神及道德上的完善和超越。因此可以说,孔颜之乐并不是对现实存在的执着和占有,也不是单纯简单的心理体验,而是一种精神、内心上的针对“俗乐”的“雅乐”,是一种精神道德境界。同时,作为一种实践性的哲学,儒家不但希望人懂得这种“乐”,并且要积极的去实践,如果再能从实践中体会此乐,便可达到新儒家所说的“圣域”了。
苏轼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孔颜乐处”被重新检视的时代,更为重要的是,“孔颜乐处”是儒学原有的题中之义,苏轼不可能不知道,周敦颐、二程只是将这一学说明确化、理学化。苏轼一生多贫苦,政治上的失意和流放给精神带来创伤,而经济上的贫困又使其陷入更加现实的困境,但这并没有使他放任自流,自甘堕落,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反而可以看到乐观旷达的心理,不可否认,这有佛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但儒家思想,尤其是“孔颜乐处”在将他从困境中拯救出来时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这将是我们接下来着重讨论的问题。
二、“孔颜乐处”对谪居黄州时期苏轼的影响
前面从历史源流和当时思想分析了“孔颜乐处”,苏轼本人也有对孔颜乐处的论述,在徐州时,他曾应邀作《颜乐亭诗(并叙)》颜子之故居所谓陋巷者,有井存焉,而不在颜氏久矣。胶西太守孔君宗翰始得其地,浚治其井,作亭于其上,命之曰颜乐。昔夫子以箪食瓢饮贤颜子,而韩子乃以为哲人之细事,何哉?苏子曰:古之观人也,必于其小者观之,其大者容有伪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孰知箪食瓢饮之为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颜乐亭诗》以遗孔君,正韩子之说,且以自警云。
这其中提到“韩子之说”,正是上面所提到的,韩愈认为被孔子称赞的颜回之乐———“隐约而平宽”为哲人之细事,苏轼“正韩子之说”即是对韩愈观点的明确反对,那么就表示出,他对身处陋巷,箪食瓢饮而自得其乐的心态是赞赏的,因此他说“我求至乐,千载无偶。执瓢従之,忽焉在后”,即就是愿意效法颜回,以得至乐。
从他的诗词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孔颜乐处的接受与践行。
苏轼被贬黄州后,首先面对的就是生存问题,在《答秦太虚书》中他提到自己经济上的艰难: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
在经济困厄之外,苏轼面临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苦闷,元丰三年的《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中“江城地瘅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元丰五年的《寒食雨二首》中“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这些都体现出苏轼遭贬谪之后的苦闷、孤独,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精神的打击无疑要大得多。应该说政治上的失意是传统文人普遍遇到的一个人生困境,而对于苏轼,由于其“致君尧舜”的高大抱负的落空使这种失意更加严重,内心更为痛苦。然而面对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困境,苏轼在抱怨埋汰之后,另有一份泰然,如说“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顾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屡,放浪山水问,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这些都说明苏轼在贬谪黄州之后面临着与当日颜回一般之贫贱,却更多一份苦闷,但在内心深处却是与颜回之乐相通的,即超越了现实的困境,自为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达观与快乐。在《答李端叔书》中,他写道“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这说明苏轼在经历过乌台诗案的排挤打压之后,屡自反省,认为过去的策论都只是夸夸其谈,对于实际毫无用处,这有种幡然悔悟或者说大彻大悟的感觉。自此,他不在汲汲于富贵之得失。我们无法忽视掉佛老思想对他的影响,但是孔颜乐处无疑在将苏轼从现实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他的文学创作风格,也潜移默化的受到了孔颜乐处的影响。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满庭芳》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这些词都体现了他他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豪放旷达的人生态度,在这些作品里苏轼与自然是融为一体的,他好似成了自然的主人,也把真实的自己展现在自然面前,从内心深处忘记了在现实中的贫苦,把自己从束缚中解脱出来,心超越与万物的甄别之上,全然不理会困境失意,反而安之若素,豁达通脱,一幅宠辱皆忘、超然物外,与自然合为一体的至乐大乐的样子,读来令人心旷神怡,无怪前人称赞他拓宽了词境。
又如《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作者以空山明月般澄澈、空灵的心境,描绘出一幅富有诗情画意的月夜人间仙境图,把自己的身心完全融化到大自然中,忘却了世俗的荣辱得失和纷纷扰扰,表现了自己与造化神游的畅适愉悦,读来韵味无穷,令人神往。
所有这些都是超脱于现实的名利场转而求精神的自由之后的乐处,“箪瓢未足清欢足”、“箪瓢有内乐,轩冕无流瞩”,孔颜的箪瓢之乐最主要的即在于生存主体对外在环境的内向超越,苏轼无疑做到了这一点,因此不管是其为人还是创作都体现出乐观通达的景象,也因此他可以更自在的生存,游历,写作。
元丰五年(1082)七月,苏轼与朋友一起泛舟游赤壁,创作了文学史上着名的“赤壁三绝唱”。其中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将豪放风格发挥到了极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首词气象阔大,笔力飞动,雄浑豪放,气势磅礴。面对奔腾不息的长江水,词人心潮澎湃:遥想当年,风流儒雅,雄姿英发的周瑜在这里谈笑间歼灭了强大的敌军,何等地潇洒,何等地豪气冲天!词人自己也欣然神往,想要像他一样开创一番事业,可是壮志难酬,只落得“早生华发”。但词人并没有沉湎于此,而是跳出了个人狭小的圈子,超脱地看待这一切,人生如梦,世事无常,又何必在意一时的荣辱得失,是非成败?在同一时期创作的《赤壁赋》中苏轼运用了辩证的观点来看待政治失意和人生无常的苦闷,从而清除内心的痛苦(尽管那如怨、如泣、如诉的箫声传达出苏轼内心深处的苦闷与忧伤)。更有前后《赤壁赋》对人的渺小,宇宙的广博由衷的感叹,对生死的态度以及江海寄余生的想法都很好的映证了苏轼已经完全超脱出现实的浮名浮利。
他已经弃名缰利锁,摆脱尘世的纷扰羁绊而转向遁迹江湖,已经由身处困境而以一副旷达的心态获得了精神的自由,获得了高贵的精神境界。这便是孔颜之乐,是超脱,是蜕变于困境里的内心恬静安然。
苏轼是懂得并在积极实践孔颜之乐的,当不幸接二连三的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他没有就此消沉,而是苦中作乐,坚持对人生对事物怀着永恒的美好追求和热情赞美。他是具有胸怀和度量的仁者,在他身上自然有一种源于内心的仁德、沉静、达观、洒脱。当这种新儒家所倡导的“乐”与佛家的空幻虚无和道家的率性自然共同在他身上发生作用时,我们看到了他的旷达和超脱。张培恒和骆玉明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对此有中肯的论述:苏轼既严正又平和,既坚持了士大夫积极入世、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又保持了士大夫追求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与心灵境界的人格理想,把两者融为一体,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隐退、入世与出世、社会与个人那一类在士大夫心灵上历来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他为后来在类似社会条件下生存的文人提供了一种典范,因而获得了他们普遍的尊敬。
总之,苏轼作为一名儒家知识分子,在遭遇人生和事业的低谷时,儒学固有的“孔颜乐处”对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与佛老思想共同起作用,造就了苏轼乐观旷达的品性。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2] 程颢,程颐撰,潘富恩导读.二程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 杨杰.周敦颐“孔颜乐处”思想新探[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92-97.
[5] 周敦颐撰,梁绍辉,许荪铭点校.周敦颐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9.
[6] 苏轼.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 苏轼.薛瑞生笺证.东坡词编年鉴证[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本文重点以《红楼梦》中人物对话英译为出发点来进行讨论, 从言语行为理论的角度来对《红楼梦》中人物对话英译进行研究, 从而来提升翻译信息的对称性, 实现原意的有效传递。...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文学家。他22岁考取进士,名动天下。然其仕途坎坷,大起大落,一生之中多次遭遇贬谪,尤以元丰二年(1079)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为人生转折点。此次贬谪是苏轼仕途和人生的低谷,却也成了他文学创作的高峰。在黄州5年间他写下...
《文心雕龙物色》: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随着时间的推移,四时轮回,节序不断的变迁,心随物动,人们的内心不免有所感发。由此,节序逐渐成为诗人笔下诉诸的对象,成为诗人情感寄托的支点。据笔者统计,苏轼节序诗达103首之多,包含了诸如元日、上...
通过对苏轼文学作品、绘画作品和绘画题跋三个方面的分析和探讨,我们认为,“诗中有画”表现为苏轼诗文作品擅于通过营造、再现审美空间以呈现画面;“画中有诗”表现为其绘画作品笔墨语言蕴藉了宋代文人士夫普遍认同的文学意象。苏轼通过大量而具体的诗、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