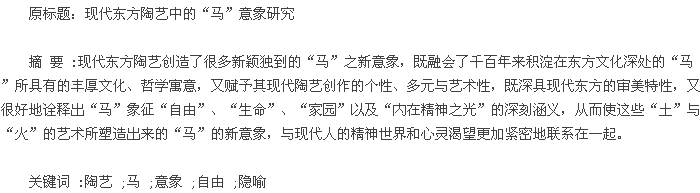
当马这种曾与人类历史和文明进程息息相关的动物的痕迹,被现代都市生活几乎完全抹去,它作为一种文化意象①也逐渐沉淀,似乎消隐。但文明的悖论是,科技和理性越发达,人的内心世界却越空虚-发展到极致的“理性”,从解放人性走向了奴役人性,从启蒙理性异化成为工具理性,于是陷入无尽欲望之流的现代人变得焦虑忧郁、躁动不安,并且对现代文明所造成的心灵伤痛束手无策。英国作家尼古拉斯·埃文斯在其名作《马语者》中,通过人与马、人与人之间破碎的亲情和友情关系的艰难修复,探讨了现代都市文明重压下人如何回归自然及性灵的问题,试图通过人向自然和原始野性的回归来抚慰受伤的现代心灵。
在此语境下,“马”作为原始野性和充沛生命力的象征重新出场,“人”与“马”的关系被赋予生命本源意义上的重新思考,“马”被视为引导心灵向自然和本真回归的重要媒介。
而在现代东方陶艺创作中,马,这一古老而丰富的文化意象,也不断被许多陶艺家进行新的诠释、获得新的意义。其中,尤以中国的朱乐耕、邱耿钰和日本的铃木治为优秀代表,他们就仿佛是现代东方陶艺的“马语者”,熟谙泥性且洞悉人性,以陶艺独特的材质和造型语言,创造许多独具现代东方特色的“马”意象。
在东方文化中,作为精神隐喻意义层面上的“马”,是与东方古老的哲学融为一体的,而在现代东方陶艺家手中,它们更被赋予了深刻的现代人文关怀。概括而言,现代东方陶艺中创作的“马”意象主要有如下三种 :
首先,“马”喻示着昂扬向上的生命热情和永不枯竭的生命力。在远古时代,对天地与人所拥有的充实强健的生命力的肯定,就见于《周易》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而杜甫的“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的骏马意象就集中体现了这种刚健乐观、自强不息的精神。
朱乐耕先生的马系列作品鲜明地体现出这种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刚健之美,与此同时,他又赋予了这些马儿自信、独立、坚定的新时代品格。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作品《风》(如图 1),以泥板成型的手法塑造出一匹匹气宇轩昂、傲然卓立的马,有别于必备马具之中国古代陶塑马的形象,这些去除了辔笼束缚的马儿们,以其阳刚和野性之美正欲迎风疾驰、啸腾,那份重获自由的兴奋和发现自己力量的骄傲,在充满活力的造型和釉色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红绿彩瓷板画。如其作品《新年》(如图 2)和《奔马》,就以洒脱自由、热情奔放的笔法和大俗大雅、对比强烈的色彩,赋予马儿一份浓烈鲜明、热情洋溢的生活气息,并以有力的线条、饱满的色彩与强烈的平面性,很好地强调和凸显出马形象中饱蕴的生命热力和积极品格。这种东方传统陶艺语言的成功现代转换,令其作品独具现代东方的审美特性。
朱乐耕采用现场泥片擀压、裁卷和成型的方法,让每一块泥都能印下手指的痕迹,印下艺术家创作之际的心情和感受,并在组合时顺应陶泥卷曲的特点而自由造型,将陶艺创作过程中的偶然性与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充分融为一体。如此,泥的真性与创作之率性的内在统一,便让灵感充沛自然地流淌过每一片陶泥,让这些马儿的形象鲜活灵动、仿佛呼之欲出,充分展现出“泥性”与“人性”的双重解放。与此同时,当充满现代感的亚光颜色釉被施于骏马之上,那温暖之色调、丰富之肌理与流动之痕迹,愈显其健美和生气勃勃,喻示着新时代独立、自信、自由的理想新形象。
这种昂扬乐观的新时代精神,还被朱乐耕以红绿彩瓷绘马的形式充分体现出来。有别于《风》之现代感非常强烈的自由成型手法和亚光釉装饰,朱先生创造性地运用红绿彩这种古老而富于民间艺术特色的东方瓷绘技法,通过与现代平面构成语言的结合,创作了很多马的红绿彩瓷板画。如其作品《新年》(如图 2)和《奔马》,就以洒脱自由、热情奔放的笔法和大俗大雅、对比强烈的色彩,赋予马儿一份浓烈鲜明、热情洋溢的生活气息,并以有力的线条、饱满的色彩与强烈的平面性,很好地强调和凸显出马形象中饱蕴的生命热力和积极品格。这种东方传统陶艺语言的成功现代转换,令其作品独具现代东方的审美特性。
其次“,马”还喻示着“大地”“、母亲”和“精神家园”.《周易》云“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又云“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1]其意为,正大、亨通、包容的大地使万物得以顺利生长,而性情柔顺、纯正的雌马具有与大地相类的德行,能够在广阔无垠的大地上尽情驰骋,正是承载、包孕万物的大地和母性的象征。
这种马儿所象征之大地母性的包容承载之美,则在日本陶艺家铃木治的陶艺作品中得到了新的表现。铃木治擅于创作有机抽象几何形式的马作品,在秉承东方文化中马之深厚文化意味的同时,为之赋予了浓厚的现代气质。
铃木治的作品《雪中的马》(如图 3),将马的形体抽象为几条直线和曲线的组合与变化,仿佛现代建筑物一般造型非常简洁明快,但在那色调淡雅的桔色躯体上轻轻飘落的数朵淡淡雪花,与马儿脖颈的一低一回,即刻营造出冬日粉雪扑面、朵花晶莹的温柔境界。低回的母马,仿佛是在静静地等候,又宛似在轻轻地呼唤,那种大地母亲般的温柔、坚韧与宽厚,似乡愁般慢慢弥散开来,萦绕在观者的心头,久久难以忘怀。
又如其作品《青瓷马》(如图 4),放弃了古典陶艺圆润的曲线和弧面之造型语言,而趋向于现代主义建筑般的抽象线性平面。以自然素朴未经修饰的泥片组合而成之抽象的几何形体的马,看似僵直冷硬,却因印压肌理与光滑表面的对比、釉色的深浅变化以及泥片参差不齐的边缘,而获得了手工之美。铃木治就是这样巧妙地将古陶传统与现代情感融为一体,在简洁的现代抽象形式中蕴含入丰富温暖的人性意味。
第三,“马”在东方文化中还隐喻着一种超凡脱俗的人格。孔子以“骥”比喻品德美好的贤才 :“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2]屈原在《离骚》中咏叹“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骐骥”在此成为诗人自身才能和高洁人格的化身。从《诗经·小雅》中的“皎皎白驹”、“其人如玉”,到唐代李贺《马诗》中的“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诗人的人生理想与骏马意象达成高度契合,“马”成为诗人守护心灵之光、不放弃理想追求的自我形象的写照。而这种对理想自我和内在品格的隐喻性“马”的创作,可见于朱乐耕与邱耿钰的作品之中。
朱乐耕先生的作品《行空的天马》系列(如图 5、6),富于创造性地运用影青釉这种源于宋代而有千年历史的青瓷工艺,并与现代陶艺创作技法相融合,创造出一种隐喻现代知识分子品格和自我形象之崭新的“马”意象 :
一匹纤瘦的白马静静踏在粼粼冰河之中,沉思着,时空仿佛倏然沉寂,历史宛如跃然而生 ;那覆盖在作品上晶莹透亮的青釉,令躁动的心灵自然沉静并忘我沉醉在那无边的纯粹之中。这是一匹孤独的白马,它在一片纯净的寥廓之中静静伫立,好像在倾听,又仿佛在沉思,看似安宁却又略带一份忧郁和孤寂的诗意。在超旷空灵、一尘不染的境界中,这匹如玉一般散发内在光辉的马,与一个睿智而平静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合二为一。在此,宋代影青与现代文明沉思碰撞激发的光芒所凝聚而成的全新的“马”意象,以其深刻的心灵启迪喻示理想人格对内在心灵之光的执着守护。
另一位中国陶艺家邱耿钰,则是一位善于运用陶土创造隐喻“飞翔之梦”的“马”之新意象的陶艺家。他的系列作品《马之梦》(如图 7 ~ 9)[3]运用粗犷的陶土材质和圆雕手法,将马塑造得谦逊而朴素、厚重且感性、沉稳而大气,如同巨石中凿出一样。而他往往舍弃整体、只取马头进行突出表现,这些马儿或微闭或半睁着眼睛,仿佛在深深沉思,又似在沉浸于梦乡,但它们头上的鸟儿或鬃毛之中的云纹和羽毛印记,却将它们内心深处对飞翔的渴望泄露无疑。
【摘要】:陶瓷制作在中国有十分悠久的历史,陶瓷艺术教育更是在历史的传承中有重要作用。随着当前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一味的关起门来自己发展必将被世界淘汰。陶瓷艺术教育与世界同步是必然的趋势,在这国际化当中陶瓷英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进一步认...
现代陶瓷艺术站在中国陶瓷文化这个巨人的肩膀上,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工艺技术,在陶瓷行业中不断融入新鲜血液。...
陶艺创作者们创造生活陶艺的目的归根结底也是为了人,具体地说是为了人的生活美好。人虽然从降生之日起开始生活,但生活的品质却在不断地提高。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是当时农业和定居生活的标志到当代生活陶艺是人类追求精神和物质的结合,陶瓷艺术给人类带来...
0引言现代陶瓷艺术不只是指在时间存在序列概念,它是一个融合了时空、风格、观念、思想等特点的造型艺术理念,在艺术领域和陶瓷领域具有普遍性。现代陶瓷艺术在继承传统陶瓷艺术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技、材料及工艺,融入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寻求各种艺术表...
中国陶瓷艺术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我们可以从陶瓷艺术审美中了解中国不同时期的文化内涵,探求民族文化精神。...
0引言在我国传统陶瓷装饰绘画发展历史上,清三代是一个重要发展及变革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国际视域等因素的影响,这一阶段产生了历代未曾出现的文化冲突局面。一方面,古典和传统的工艺技法及审美思想在其中扮演着基础性的角色;而另一方面,来...
0引言粉彩花鸟瓷画自康熙晚期诞生以来,其艺术风格的发展演变除了依存于其本身的艺术规律以外,更多地表现为在社会自然环境影响下而形成的时代风貌,是自然、社会人文以及工艺技术变迁等各种因素形成的整体环境融合的产物,反映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0引言人类本身就具有自然的属性,生来就与泥土相伴相依。中国先人在几千年前就利用泥土烧制出了优秀精湛的陶瓷制品,现今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需求,陶瓷产品已经发展成种类繁多,异彩纷呈的局面,陶瓷制品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建筑装饰、室内装饰、日常用品...
引言在现代社会里,我国陶瓷艺术深受人们的青睐。对于陶瓷这种器物而言,装饰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陶瓷装饰所用的材料有花纹、图案等,装饰材料的使用使得陶瓷美学性更加凸显。而陶瓷艺术装饰来源于我国传统文化,伴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转变,对我国传统的陶...
公共环境,一般是指室内及室外的公共区域的环境。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公共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陶瓷艺术在公共环境中的应用,能够增强公共环境的整体艺术气息,提高人们的审美认识,为人们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人们在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