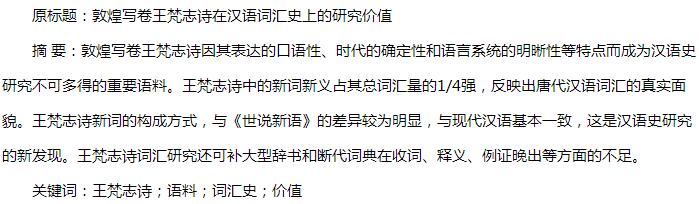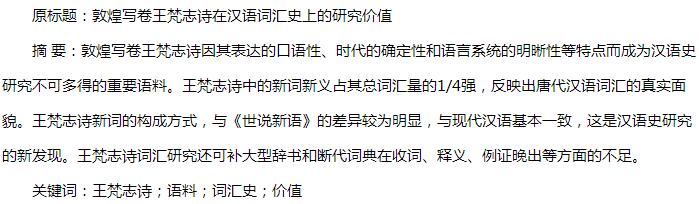
唐人王梵志,卫州黎阳人,生卒年不详。胡适推定他生活在 590-660 年之间[1],赵和平、邓文宽认为王梵志的活动上限是初唐武德年间,最迟不晚于开元二十六年[2](738)。王梵志诗在唐宋时影响广泛,唐代诗人王维、寒山、顾况、白居易、杜荀鹤、罗隐,宋代诗人苏轼、黄庭坚等均受其影响。唐皎然《诗式》、范摅《云溪友议》、五代何光远《鉴诫录》、宋释惠洪《冷斋夜话》等几十家传世文献均有称引。王梵志诗在中晚唐时还传到了日本①。元明以后渐趋沉寂,至清编《全唐诗》不传。
近代王梵志诗随着敦煌文献的发现而被人们重新认识。1920年,刘复赴法国巴黎留学,亲睹海外部分敦煌文献并加以抄录。1925 年,他把从巴黎抄回的136首王梵志诗编入《敦煌掇琐》发表,引起国内外学人的高度重视。此后,胡适、郑振铎、刘大杰、周一良、任半塘、张锡厚、项楚以及日本的矢吹庆辉、小沼胜卫、内田泉之助、入矢义高、神田喜一郎,法国的戴密微、吴其昱、魏普贤,俄国的孟列夫等国内外着名学者先后展开论说,一时掀起王梵志诗的研究热潮,王梵志诗在文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上的价值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本文拟从文献语料学的角度来探讨王梵志诗在汉语词汇史上的研究价值。
一、王梵志诗的语料价值
(一)文献的口语性
汉语史是关于汉语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汉语史研究主要是建立在历史上各个时代留存下来的文字材料的基础之上。用作汉语史研究的文字材料,也叫语料。汉语史包括汉语语音史、词汇史和语法史三个方面。
历史上留存下来的文字材料,大致看来,秦汉之前的属于文言;魏晋以降,文言、白话两条线。诚如许嘉璐所言:“文言,形成和定型于先秦到两汉。那时的口语和书面语基本一致。此后,口语和书面语局部分离,口语不断发展,而先秦两汉的语言则成为文人和官场的书面语,即文言,一直延用下来。”[3]魏晋以后的中古、近代汉语发展演变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汉语口语发展演变的历史,揭示中古、近代的汉语面貌主要通过那些反映当时的口语的文字材料来了解。文字材料的口语成分越高,语言的历史面貌就越真实,语料价值就越大。
王梵志诗根植民间,反映时俗生活,“具言时事,不浪虚谈”;因擅用百姓语言,“不守经典,皆陈俗语”而“远近传闻”.请看 001 首诗②:“遥看世间人,村坊安社邑。一家有死生,合村相就泣。张口哭他尸,不知身去急。本是长眠鬼,暂来地上立。欲似养儿毡,回干且就湿。前死深埋却,后死续即入。”诗中“遥看”、“世间”、“村坊”、“社邑”、“死生”、“合村”、“相就”、“长眠鬼”、“欲似”、“养儿毡”、“回干就湿”等就是产生于六朝以来的新词,新词多来源于百姓生活语言--口语。王梵志诗的口语性质,早为学者所肯定。郑振铎称王梵志诗是“真正的通俗诗”[4],日本内田泉之助认为王梵志“也许正是口语诗的先驱”[5],张锡厚认为王梵志诗“有着完全不同于格律诗的特点,既没有严格的句数局限,也不大着重平仄和对仗,俗语俚词皆可入诗,表现出明显的口语化倾向。”[6]项楚认为,王梵志诗“用民众的鲜活的口语写作”[7],汪维辉、胡波断言:“王梵志诗可以说是唐代最口语化的语料。”[8]王梵志诗中的大量的新词新义正是其口语化的具体表现。
(二)语料时代的确定性和语言系统的明晰性
袁宾曾指出:“比较起古代汉语来,近代汉语的文献语言在口语性、时代性和地域性三个方面表现得更为显着。”[9]可见,魏晋以后的汉语史研究,对语料的要求更为特别。一般认为,能够作为中古近代汉语史研究的文献语料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口语性;能确定大致的年代;能确定大致的语言系统。
除上文所论其口语性质外,王梵志诗的产生时代与语言系统也很清晰。
据项楚先生考证,冠名王梵志诗的虽非一人一时之作,但其产生时代较为清楚[10]12-21:三卷本203 首诗,其产生时代不晚于唐开元以后,法忍抄本69首诗成书于盛唐,一卷本92首诗成书于晚唐时期;散见的26首诗时代也较为清楚,从盛唐直到北宋初年。这就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了准确的时间参数。从王梵志诗产生的时代下线界定,我们可以整体地认定,390 首王梵志诗代表着有唐一代300年间的语言史实。也可以分卷研究,细化到初唐时期(三卷本 203 首王梵志诗)、盛唐时期(法忍抄本 69 首)、晚唐时期(一卷本 92 首,包括三卷本王梵志诗的《序》)。
王梵志诗属于唐代北方话系统,这可以从作者的出生地和诗的用韵情况来证明。从生长地来看,王梵志出生于“卫州黎阳”,即今河南浚县,地处中原,属于北方通语区。王梵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用当地鲜活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从用韵情况来看,蒋冀骋考证,王梵志诗“代表隋末唐初河南北部的实际语音”[11];张鸿魁考证,王梵志诗“是天下之中的河南一带的方言”、“是一种能为广大地区所接受的通语”[12].王梵志诗正是运用了北方通语,故能由中原传遍全国,其语言性质可以断定为唐代通语白话系统。
王梵志诗的语料价值,还体现在它的真实可靠性上。王梵志诗自十一世纪密封于敦煌藏经洞至近代,未经后人传抄刊刻,原汁原味,排除了后世手抄翻刻易出现的衍、脱、改、误等失真问题,文字材料真实可信。
王梵志诗的语料价值还可以从众多名家的研究中得到证实。如刘坚《古代白话文献选读》(商务印书馆,1999年)收录王梵志诗八首;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4 年)、刘坚及江蓝生等《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语文出版社,1992年)、袁宾《近代汉语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江蓝生、白维国译,中华书局,1995 年)、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等均把王梵志诗当成重要的书证材料。
蒋绍愚曾指出,王梵志诗“是研究唐五代时期这一近代汉语起点的最有价值的语料之一”[13],事实证明,此言不诬。下文主要从新词新义的产生、新词的构成方式以及王梵志诗词汇研究对大型辞书和断代词典在收词、释义、例证晚出等方面的贡献来看其在汉语词汇史上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