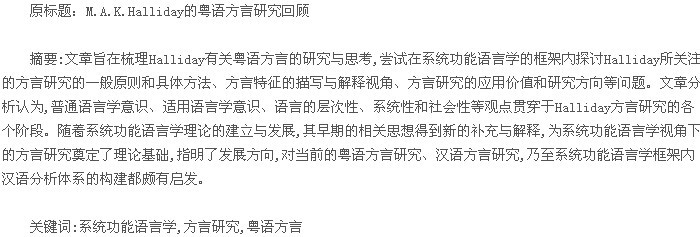
1.引言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M.A.K.Halliday基于伦敦学派奠基人J.R.Firth的理论发展而来的语言学理论。若以Halliday发表于1956年的“GrammaticalCategories in Modern Chinese”为起点,系统功能语言学发展至今已走过了近60年。在半个多世纪的探讨、检验中,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三大纯理功能、语篇分析、文体分析、语法隐喻、功能语法等方面(黄国文2009:871),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进行汉语研究的并不多见(如彭宣维2011),而探讨汉语方言的研究则更少。
但作为一门普通语言学和适用语言学理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包括汉语在内的人类语言(黄国文2006,2007)。而Halliday早期也做过汉语和粤语方言研究(见Webster 2005/2007)。
这些研究对日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我们能够看到王力先生的方言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对Halliday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从这些早期的方言研究中,我们业已可见Halliday的普通语言学和适用语言学意识,以及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一些基本立场,包括语言的层次性、系统性,强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对语言选择的重要性,语言的社会性(即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等。
本文将首先论述社会语言学中方言研究的两种研究路向。接着,通过文献梳理,总结Halliday有关粤语方言的研究与思考,归纳、探讨Halliday所关注的几个问题。本文分析认为,Halliday有关方言研究的思考散落于他不同时期的论文中,尽管未有相关的系统论述,但文献梳理的结果显示,Halliday的思考已经涉及到方言研究中的几个核心问题,包括方言研究的一般原则和具体方法、方言特征的描述与解释视角、方言研究的应用价值和研究方向等。
普通语言学意识、适用语言学意识、语言的层次性、系统性和社会性等观点贯穿于Halliday对方言研究的探讨与实践中。而随着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建立与发展,这些早期的方言研究思想得到新的补充与解释,为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方言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
2.方言研究的两种路向
方言是一种语言变体,简单地说,方言研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路向。第一条路向是描述,主要是对某一特定方言的内部特征进行描述,从语言学角度回答“方言是什么”,最终为方言的内部特征构建起一个完整、系统的描述框架。例如,陈渊泉(2001)关于汉语方言的连续变调模式的研究采用的就是这个路向。通常,采用这个路向的研究对方言的社会属性不作价值判断。这是根据汉语方言特点决定的。
Halliday(1956b/2007:225)曾指出,“中国的方言纯粹是区域性的问题,并不具备像英国的方言和‘口音’那样的社会内涵。每一个中国人无论社会地位或受教育水平如何,都说当地的方言(即这里所说的方言,不只是带有当地口音的标准语言而已)。”这一判断是基于他对194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认识作出的。现代社会的生活经验则告诉我们,带有方言口音的普通话或多或少暗示了说话者有限的教育水平或教育条件。尽管如此,相较于西方社会,中国社会对方言和口音的容忍度更高也是事实。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汉语语境更强调方言在社会交际中的凝聚力和纽带作用,而弱化了其与社会阶层的联系。需要说明的是,Halliday所说的方言指的是相对于作为区域标准语的城区广州话(city Cantonese)而言的珠江三角洲(以下简称珠三角)各地的次方言(sub-dialect)。
本文将沿用这一概念。
方言研究的另一个路向是解释,主要是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对方言的内部特征、社会属性进行理论解释,将文化语境纳入分析视角,探讨方言特征的成因以及这些特征与社会结构、人类的行为活动之间的关系,最终建立起方言的内部特征、社会属性与文化语境间的关系。采用这个路向的研究倾向于将使用方言这一行为视作一种低社会地位和低教育程度的外在体现。这种倾向在英 语 语境中 尤为明显,Haugen(1966:923)就曾指出,大多数人在交际中是不区分“语言”和“方言”的概念的,对他们而言,方言仅仅 是 语 言 在 当 地 的 一 种 卑 微 而 弱 势 的 变 体。
Bernstein(1971)和Labov(1966)所做的社会语言学研究采用的就是这个路向。
Halliday(1978)高度评价了Bernstein(1971)和Labov(1966)在社会方言研究方面所做的贡献。他(1978:
98)认为,Bernstein的理论是对Labov的研究成果所做的必要补充;如果说Labov预设了一个文化传播和社会变迁的普遍性理论,那么Bernstein的语码理论(theory of language code)便是对这一假设的 进 一 步 论 证。
Halliday将 之 称 为 “Bernstein-Labov hypothesis”。在探讨语言的社会性时论及Bernstein和Labov,是因为Halliday相信,当前的社会方言研究过分关注种族问题和社会阶层因素,而忽略了更广阔的社会系统及文化语境。这一点关系到方言研究的发展方向,将在后文做更详细的论述。
在Halliday看来,只有Bernstein和Labov才是“trulyoriginal thinker”,两人的理论对革新方言研究的视角与范式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两人的理论都存在被误读和曲解的部分,值得重新审视。
当然,许多研究都会将这两种不同的路向结合,兼顾描述性和解释性。例如,陈渊泉(2001)就用优选论对上海崇明年轻人说的新崇明话进行变调分析,使结论更具解释性。但如桂诗春、宁春岩(1997:6)所说,“以描写概括事实的广度为最终目标的理论,即使含有解释性理论色彩,仍旧是描写性的理论;而以解释事实成因为最终理论目标的理论,即使含有必要的描写性理论色彩,仍旧是解释性理论”。
3.Halliday的粤语方言研究与思考
Halliday认为方言作为一种语言变体,其“内部特点和使用方式与社会结构、不同阶层的态度和人类行为 系 统 之 间 有 着 十 分 紧 密 的 联 系”(朱 永 生2001:F27)。因而,在Halliday看来,方言研究的最终目标应当是为方言的内部特征建立一个解释性理论。这也符合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语言视作社会符号的立场,即关注人们是怎样使用语言并通过语言来进行社会交往中的各种各样的活动的。
Halliday有关粤语方言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是1949年至1950年(这是他在中国师从王力先生进行粤语方言研究实践的时期)和1950年后(特别是1955年前后在英国对粤语方言研究进行理论探索的时期)。
1949年,经国立北京大学(今北京大学)罗常培先生推荐,Halliday到广州师从岭南大学的王力先生,系统地学习方言学理论和调查方法。当时,王力先生正在进行珠三角粤语方言的语音学调查,这是我国方言调查史上的第二次粤语方言调查(参见彭宣维2007)。
Halliday便在王力先生的指导下,对粤语方言的语音和词汇语法特征做了细致的研究。作为研究总结,Halliday在“Some LexicogrammaticalFeatures of the Dialect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一文中详细说明了研究方法的确定、具体调查过程、调查对象及调查材料的选择与获取等,并主张用等语线来描绘方言分布的连续性。同时,Halliday还对北京话、城区广州话与珠三角各次方言进行了语音、词汇语法特征的对比分析,对句法和语义方面的差异也有所涉及。
回到 英 国 后,Halliday依 然 保 持 着 对 汉 语 方言———尤其是粤语方言———的研究兴趣。这一时期,Halliday(1955,1956a)先后推介了英国学者Whitaker(1954a,1954b)的两部作品,分别是Structure Drill inCantonese,First Fifty Patterns和Cantonese SentenceSeries。在书评中,Halliday依旧关注方法论和语言对比的问题,介绍了方言研究的一般原则和具体方法,提及北京话与城区广州话在句法上的一些差异。
延续这两大话题之余,Halliday(1956a:198)还探讨了语言对比在粤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价值,强调由于粤语的口语化特征,学习粤语即意味着学习口语。
2013年7月,由 国 际 系 统 功 能 语 言 学 学 会(ISFLA)主办的第40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在中山大学举行。
Halliday在大会开幕式上做了题为“That‘Certain Cut’:Towards a Characterologyof Mandarin Chinese”的主题发言,期间论及了普通话与粤语方言在音系、词汇语法方面的差异(Halliday2014)。
4.讨论
具体来说,Halliday有关方言研究的探讨有以下几个重点:(1)方言研究的一般原则和具体方法;(2)方言特征的描述与解释视角;(3)方言研究的应用价值和研究方向。下面我们将对这三个方面逐一进行讨论。
4.1 方言研究的一般原则和具体方法
作为一个普通语言学理论,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体现了语言研究的客观性、系统性和清晰性。系统功能语言学以真实、自然的语篇为研究对象,基于实验数据和事实来验证理论假设;它有一套完整、严格的音系/字位-词汇语法-语义系统,各层次之间是体现与被体现的关系;且它对理论的概念、范畴、术语、规则等都做了清晰的解释。如前文所述,Halliday在王力先生指导下进行的粤语方言调查正是以母语者的语篇为基础,从语音、词汇语法和语义三个层面,对珠三角各次方言的内部特征进行系统描述。值得一提的是,王力先生的语音学调查仅关注孤立的语音,并未试图研究粤语方言的词汇或句法特征。这一做法在粤语方言的研究中是可行的,因为在粤语里,以句子作为修饰成分的情况要比普通话或其他方言少得多(Halliday 1956b/2007:226)。
但在实际操作中,Halliday不仅根据王力先生的要求,收集了13个方言区次方言的语音数据,并且向同一批受试收集了词汇和句法数据。在特征描写中,Halliday也同时对语音、词汇语法和语义三个层次进行描写。这样做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粤语方言中,个别孤立的语音与词素在句子中的发音仍有差别(Halliday 1956b/2007:226),但王力先生的语音学调查并未涵盖这一部分的特征描写;二是Halliday希望能够补充有关粤语方言的词汇、句法研究;三是Halliday(1950:252)相信,在描述词汇、句法特征的过程中,能够揭示出一些语音方面的新特征。尽管该调查属于Halliday早期的语言学实践,在论述中仍有诸如“句子”、“句法”等概念,语言的层次性也尚未得到明确阐述,但他对调查视角的调整已经反映出他的系统语言观意识。
在收集语音数据时,Halliday使用的汉字列表包含1150个汉语单字,是王力先生基于赵元任教授在1936年进行湖北方言调查时所用的汉字列表修改而来。受试根据要求逐一朗读这些单字,Halliday同时进行录音和转写,对个别不确定的汉字读音进行确认后,便得到调查数据。但在收集词汇语法数据时,Halliday强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对语言选择的重要性。为了确保所收集的数据是各地次方言,而非带有当地口音的区域标准语,Halliday首先用城区广州话向受试描述一个语境,借以引导受试用家乡的次方言复述所描述的语境。例如,Halliday希望了解次方言中“瞥见”(目交)一词的使用,描述语境时,他故意用较为模糊的“看见”(睇)来引导受试自然地说出“我瞥见他来了,便躲了起来”。相比于直接问“‘瞥见’在你的方言中怎么用”,这种方法允许受试根据语境做出自然的语言选择,对答案的限制性较小;而相比于纯粹自由的谈话形式,该方法则能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有效的数据,这也符合当时调查时间有限的实际情况。
就研究视角而言,Halliday强调方言研究应当关注语言的层次性和各层次之间的体现与被体现关系,将方言视作一个系统。就具体的研究方法而言,Halliday强调语境对语言选择的重要作用。语言系统作为一个丰富的意义潜势,不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语篇都不能脱离特定的语境。
Halliday的语境意识从他收集词汇语法数据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中可见一斑。此外,在有限的时空条件下,Halliday还对多个调查方法的可行性、适用性进行论证,以确保实验数据的完整、客观与准确,这是他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承认事实、尊重事实的科学意识的最佳体现。
4.2 方言特征的描述与解释视角
作为适用语言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它突显了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下的语言特征,从而揭示语言在任何特定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发挥的作用(见Halliday 2009:ⅶ)。
从适用语言学角度理解系统功能语言学,就是要展现在解决实际、具体的语言问题时涉及了哪些层面的因素。
如上文所述,除了具体的研究方法,Halliday对语境的强调和重视也体现在他对方言特征的描述与解释中。在这里举一个有关词汇特征对比的例子(参见Halliday 1956b/2007):【表1】

如表1所示,英语中的“take”和“use”往往可以用汉语中的同一个词表达,比如北京话中的“拿”。
但在语法上,这些汉语词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限定动词来表达“take”的意思;另一类则以从属动词来表达“use”的意思,作用类似于介词。这是因为虽然“use”在英语中是动词,但其更常被理解成“with”的意思,表示工具。相应地,汉语中的“把”作为纯粹的功能词,用来提示及物动词的宾语提前出现的情况(Halliday 1956b/2007:232),正好呼应了“use”表工具的用法。此外,在城区广州话中,通常用“揾”(to look for)来表达“use”的意思。珠三角次方言在这里以台山-新会地区的次方言为例。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列的情况是该地区的一般情况,不排除个别次方言在发音和词汇语法层面的盖然率(probability)方面的差异。例如,在新会,“擰”作为“take”的用法很常见,但在其他地方则很少见;“拖”在江门也可以表示“use”的意思,在其他地方则较少见;某些地方,“扌戒”表示“with”时发k’ai音,而表示“use”时发hai音。
除了文化语境的影响,对应同一个英语词汇的不同汉语词汇所使用的情景语境也不尽相同。以城区广州话中的“擰”和“攞”为例:同样表示“take”,人们可以说“我去攞”(我去拿),但不可以说“我去擰”;可以说“我擰嚟”(我拿来),但不会说“我攞嚟”。类似的差异也存在于“扌戒”和“拖”中,前者的用法类似于“擰”,后者类似于“攞”。大致而言,“擰”类似于英语中的“bring”或“take”,而“攞”类似于“fetch”(Halliday 1950:262)。
就方言特征的描述而言,Halliday突出了语言的层次性和系统性,从音系/字位-词汇语法-语义多个层次来审视粤语方言。每一层次为低一层次的单位提供语境,并由一个或多个低一层次的单位来体现。如在广州的“边缘地区”,“扌戒”的语音特征就取决于它的词汇语法特征,即表示“with”时发k’ai音,而 表 示 “use”时 发hai音。就 解 释 视 角 而 言,Halliday依然强调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对语言选择的作用,即在特定的交际语境中,某一语言交际单位(语篇)是怎样和为什么能够表达它所表达的意义,以及相较于其他交际单位,为什么这一交际单位就其使用目的而言是有效的,这是Halliday适用语言学意识的最佳体现。
4.3 方言研究的应用价值和研究方向
对Halliday而言,创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最主要目的是为潜在的语言学“消费者们”解决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提供一个理论(Coffin 2001:94)。
Halliday一贯重视语言理论的实际应用,尤其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而方言研究作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语言教学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汉语语言间的共性恰恰揭示了语言对比的重要性,因为这种对比能够让本族语者和方言学习者更好地理解、把握方言的内部特征。同为汉语,普通话是一种声调与语调相融合的语言,较少使用句末语气词,因而其小句的人际功能主要是由语调来体现;相反,在粤语方言中,小句的情态和人际意义主要由大量的句末语气助词和声调来体现,语调的使用则非常有限(Halliday 2014)。此类对比不仅能够帮助本族语者及粤语学习者解决粤语教学、使用中的实际问题,亦对粤语教学的目标、教材编写和教学方法的选择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这里所讨论的粤语教学主要是指对外城区广州话的教学。
相对而言,粤语是一种较少被写成书面语的方言,具有明显的口语化特征。这一点使得粤语教学带有明确的实用性目的,以“向学生展示如何最好地用粤语表达思想”为教学目标(Halliday 1955:386)。
普通话教材侧重展现普通话书面语丰富的意义潜势,语篇分析作为主要的教学方法被广泛应用于课堂教学当中。而粤语教学则倾向于使用英汉对比和交际法,侧重口语训练,在学生熟练掌握粤语之前,引导学生用母语的思维对语境作出反馈。此外,由于许多口语式的粤语词汇没有对应的书面语表达,亦或书面语表达鲜为人知(Halliday 1956b/2007:231),在粤语教学中,书面教材一般通过口语式广州话与口语式普通话的对比来解释粤语的某些句法特征。
Halliday(同上:225)曾认为中国人不需要掌握普通话就能够完成教育。时过境迁,如今国内的课堂教学大多使用普通话,这就要求人们必须掌握普通话才能完成教育。然而,普通话的推广使得方言的使用领域和频率正在大幅减少。方言衰亡的背后是本土文化的消逝,迫切需要重视对方言的保护与传承。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方言研究带有强烈的社会性特征,能够更深刻地揭示方言作为本土文明载体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价值,亦能指导更为科学的方言保护与研究。
胡壮麟(2007:1)认为,作为适用语言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长期目标是“建立语言的意义发生系统……以社会理据来解释和描写语义发生”。Halliday(1978:98)也指出,社会方言的研究视角应当超越种族和社会阶层的限制,在更广阔的社会系统语境中来审视这些亚文化群体。诸如“黑人与白人英语间的差异”、不同社会阶层间的语言差异等探讨是不足以充分解释社会方言的内部特征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内的方言研究,其发展目标和意义应当是展示方言系统丰富的意义潜势,解释方言在社会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挖掘方言作为文化遗产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价值,在更辽阔的文化语境中,重新解释方言的内部特征和各个亚文化群体。
5.结语
Halliday的粤语方言研究与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回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新视角。
Halliday早年跟随王力先生所开展的珠三角粤语方言的语音学调查显示,早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建立之前,Halliday的普通语言学意识、适用语言学意识、语言的层次性、系统性和社会性等观点便已经开始指导着他的语言学研究。而随着1956年“GrammaticalCategories in Modern Chinese”的发表,这些早期的观点和意识逐渐发展成为系统的语言学理论,并体现在他(1955,1956a)同期的两篇有关粤语方言研究的书评中。此时的Halliday已不仅仅关注粤语方言内部特征的描写与解释,而是更多思考方言研究的应用价值、意义与方向。
1978年,Halliday在《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中回答了“方言研究该向何处去”的问题,揭示了方言研究背后宏大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图景。这一观点不仅是对方言研究发展方向的展望,更是对语言学领域内方言研究范式的革新。它要求语言学家在方言研究中摒弃狭隘的社会阶级和种族观念的束缚,赋予纯粹的语言特征描述以人文关怀和文化视野,重新审视那些散落在社会系统当中的亚文化群体:方言如何对庞大的社会系统的运作产生影响?方言又何以创造和维系亚文化群体内部的稳定?
2013年,Halliday回到中山大学,在第40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开幕式上谈及粤语方言,在更为成熟、完善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内解释粤语方言的内部特征。时光荏苒65年,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如今已是功成名就的学者,当年散落于字里行间的观点如今已成为一个完整、系统的语言学理论。
然始终不变的,是他构建一个普通语言学和适用语言学理论的信仰与追求,是今生与康乐园、与粤语的不解之缘。这一段缘分,以人文的眼光看来,充满诗意又令人感慨万千;以学术的眼光看来,对当前的粤语方言研究、汉语方言研究,乃至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内汉语分析体系的构建都颇有启发。
0前言本文讨论的是九江方言中的介词跟.笔者从小在乡下长大,所说方言比较地道,在做相关调查时也尽量选取当地使用最早或是最多的音.其中有些不确定的语料均以当地常住居民所讲方言为准.1介词跟的语法意义及用法(1)跟1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对象介词跟、和、同...
大同市位于山西省北部大同盆地的中心,曾为三代京都、两朝重镇,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优秀的人文历史、灿烂的文化艺术、丰富的煤炭资源名载典籍,扬名中外。大同地区曾是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交汇的地方,其方言、文化、风俗习惯等各方面都融汇了汉民族与少数民...
语法就是词的构造、变化的规则和用词造句的规则,是语言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语法是组织语言材料的结构工具,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是决定一个语言基本面貌的最为稳定的部分,因此研究昆明方言语法的生动形式能对昆明方言有一个系统性的认识。一、构词法的...
一、方言与方言节目的兴起方言,俗称地方话,是某一区域内人们使用的交际工具。语言会随着社会的统一而统一,随着社会的分化而分化,而方言正是社会分化的结果。在各种方言之上有民族共同语作为各地域人们共同的交际工具。因此共同语和方言在一段时间或长...
在现代汉语中,各人一词为代词,在大多数情况下可略为各一个音节,有较明显的实义,即自己、每个人的意思。它在普通话和北方方言的绝大多数区域中通常只能代名词,而且主要指人,有时单独充当句法成分,有时与人称代词合为同位语结构共同充当成分。如:咱们...
一、宁波方言与宁波方言中的时间隐喻词汇宁波话属于吴语太湖片(北吴)甬江小片,主要分布在宁波市六区、奉化、象山、宁海、余姚东南部、慈溪东部,舟山大部分地区,使用人口约700万,各区的土语非常接近,除了音调和个别词汇的区别,在使用上高度一致。宁...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在交流沟通的过程中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事实上,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呈现为一个兼容并蓄的开放式体系。方言作为语言最广泛的存在形态,其形成受到地域、历史、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交流沟通的过程中,...
语气词是表示语气的虚词,常用在句中或句尾停顿处表示各种语气.语气词的使用与句类、语法是有密切联系的,因此语气词的研究对补充语法研究的完整性、系统性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对方言语气词的探讨不但能促进地方方言的研究,为探索语言的发展历史提供活的依据,也...
近年来,随着方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方言词汇的研究.每种方言都有自己的词汇特征,这主要通过各个方言区的方言词体现出来,而最能表现方言词汇特征的就是方言特征词.方言特征词的研究是方言研究领域中新兴的分支,是现代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目前国...
自李荣先生将晋方言从官话中分立出来成为一个与官话平行的方言大区之后,晋方言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就目前看,虽然对晋方言能否成为一个与官话平行的方言大区仍有不同的看法①,但多数学者及其着作、教材、论文、地图中已经采用李荣先生十大方言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