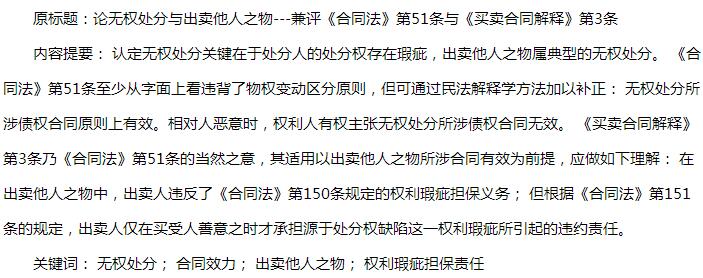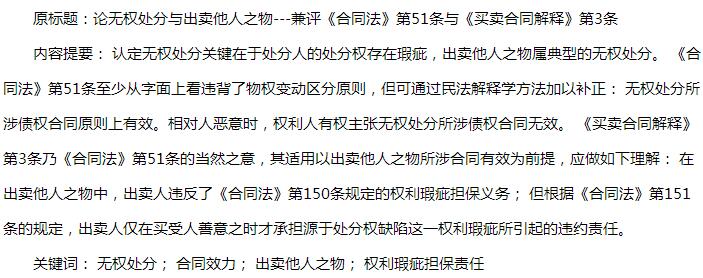
无权处分是民法上非常复杂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其涉及到合同效力、物权变动等诸多民事基础理论〔1 〕,“我国合同法于第51条规定无权处分后,备受争议。”〔2 〕《物权法》第15条对物权变动区分原则的确立,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买卖合同解释》〔3 〕的施行,对理论界与实务界关于无权处分的既有见解造成了一定冲击,并再次引发了理论和实践上的争论。本文将从法律解释学视角来对我国现行法律中的无权处分规则加以分析,并就司法解释的适用提出全新的看法,以期能对理论研究与司法实务有所裨益。
一、学界关于《合同法》第51条的主要争议
就无权处分问题而言,我国现行《合同法》第51条首次以法律形式做出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在此之前,仅最高人民法院就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效力问题以司法解释或批复形式加以了规制,且均直接认定买卖关系是无效的。〔4 〕一般认为,这种学说以“给付不能论”作为其解释的理论基础,即认为在缔结出卖他人之物等合同的场合,因为处分人对处分标的物不具有处分权,属于以“不能履行的给付”为合同标的的情形,故理应无效。但这种观点遭受了强烈的批判: 首先,将出卖他人之物等无权处分情形划属传统民法理论中自始不能的无效合同本身就不恰当; 其次,以履行不能作为判断合同效力的标尺也并不科学。〔5 〕显然,无效说明显欠缺法理基础,其所谓的合理性似乎只能说这种观点比较符合国民观念,是一个容易为一般民众所认可的结论,也是我国司法实务曾经长期所持的立场。〔6 〕自《合同法》颁布之后,这种曾在实务界占据主流地位长达半个世纪之多的观点已经销声匿迹。纵观学界关于《合同法》第51条的争论,从宏观上分析,本文认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派: 一些学者认为对《合同法》第51条应当持肯定态度,虽然其内部的解释理由不尽相同,但均建立在对《合同法》第51条反面解释的基础之上,一般称之为“效力待定说”.另一些学者坚决认定《合同法》第51条存在立法错误,但其理由又根据解释原理之不同而有所差别,这其中又以通过物权行为理论来否定“效力待定说”为主,批判者们主张无权处分所涉合同无论相对人主观是善意还是恶意均一律有效、效力待定应指无权处分所涉的物权变动效力。
( 一)“效力待定说”的分析检讨
就肯定《合同法》第51条之规定无误的见解而言,“效力待定说”曾一直是我国学界的通说理论,因为根据《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在“权利人追认”和“无处分权人事后取得处分权”的情况下,无权处分合同有效,故论者们认为只要没有上述两种情况出现,则无权处分行为所涉的债权合同无效。〔7 〕作为通说的“效力待定说”,其实是针对《合同法》第51条的字面规定而做出的反面解释〔8 〕,但是其可视为是针对“无效说”所作的修正,在本质上可归为“无效说”〔9 〕。换言之,“依体系解释,在权利人追认前或者无处分权的人取得处分权以前,该合同处于效力待定状态”.〔10〕
持“效力待定说”的论者主张《合同法》第51条所言的“合同”即为债权合同,与物权变动结果无关,也即《合同法》立法并未采纳将“物权合同”与“债权合同”二分处理的德国物权行为理论。就此,梁慧星教授曾撰文指出,《合同法》立法时就是将无权处分所引起的物权变动结果包含于债权合同中的,应视标的物所有权变动为买卖合同发生的直接后果,也即合同包含了引发债权债务关系、导致物权变动的双重含义,从而认为《合同法》第51条所涉债权合同效力待定乃应然之意。〔11〕崔建远教授也曾做出过类似表述,其以买卖合同为例,认为我国《合同法》上的合同兼具了德国民法上物权行为的效力。〔12〕
但是,上述作为学界主流观点的“效力待定说”遭到批判者来自以下几方面的质疑:1.在并无充足法理依据的情况下,在无权处分这一法律制度中“赋予非合同当事人享有确认合同是否有效的权利”的立法模式违背了合同相对性的基础法理。2.不利于善意第三人的保护。虽然从表面上看其保护了真正权利人的权利,但是其对相对人的保护却非常匮乏,若权利人不加追认或事后处分人未取得处分权,当善意第三人不能依据善意取得成为相应物权人时,此时第三人只能根据缔约过失制度保护自己的相关权益,但缔约过失责任并不一定能够适用且其保护力度不及违约责任的救济力度。更有甚者,即使无权处分相对人可善意取得相应物权,若出现了交付瑕疵等情形,其权利救济仍只能借助缔约过失责任制度。3.将影响交易的安全,这在连环买卖中将更为明显。4. 《合同法》分则规定了若干具体的无权处分情形效力为有效,虽然可以根据分则的特殊规定优于总则适用而使制度间得以协调,但从体系解释角度而言,保障法律制度内部的协调统一是更为合适的选择。〔13〕
面对上述质疑,主张“效力待定说”论者中有人就“是否违反合同相对性”与“是否破坏民法体系的完整性”予以了一定的回应: 第一,就赋予权利人确认无权处分合同有效的权利是否违反合同相对性的问题,崔建远教授以无证房屋买卖为例,主张由出卖人决定无权处分合同有效与否彰显了对所有权的尊重,体现了“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14〕依笔者之见,这种解释结论显得牵强,因为“尊重所有权”与“合同的有效性”实乃两个完全独立的问题,认定合同有效并不会损害所有权人的权利; 且当“对动态权利的保护”与“对所有权这种静态权利的尊重”这两种价值发生冲突之时,近现代法律规则原则上是倾向于保障动态安全的,这在善意取得制度中即可得到体现。第二,就《合同法》第51条与《合同法》第150条这一权利瑕疵担保义务条款在体系上是否因为存在冲突而破坏了民法体系完整性的问题,肯定《合同法》第51条立法无误的崔建远教授针对将无权处分规则适用于买卖合同带来的种种弊端,另辟解释思路认为应当将《合同法》第51条的“处分权”理解为“处分能力”,提出处分能力乃基于对出卖人一般财产能力所进行的判断,而不是根据出卖人对所出卖的特定标的物是否享有处分权能予以判定,也即其从解释论上巧妙地得出了“出卖他人之物”之类无权处分情形中只需要从外观上判断出“处分人处分特定标的物不违反其财产能力”,则该行为即可被评价为有权处分,以此解决了批判者认为《合同法》第51条与第150条等规则冲突的问题。〔15〕本文认为这种解释结论确实很精巧,但这种解释思路确实与“处分权” 的通常理解相去甚远、难以服众,并不存在法理基础。除此之外,诚如反对者所言,崔建远教授的这种基于一般财产能力判断处分能力的理论在客观上很难操作。〔16〕梁慧星教授则在肯定“出卖他人之物”属于无权处分的前提下,针对批判者们所认为的《合同法》分则第150条与《合同法》总则第51条相冲突的观点做了如下回应: 其认为《合同法》第51条与第150条并不矛盾,《合同法》第51条正是属于第150条所规定的但书条款“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适用情形,也即出卖他人之物的情形中出卖人不需要向买受人承担权利瑕疵担保责任。〔17〕概言之,上述肯定《合同法》第51条并无立法错误的论者均认同出卖人承担权利瑕疵担保责任以合同有效为前提,且均认为从表面上看出卖人出卖他人之物确实违反了《合同法》第150条所确立的权利瑕疵担保义务,但论者们均通过解释学的方法从不同层面阐述了《合同法》第51条与《合同法》第150之间并不冲突的见解。
值得一提的是,也有论者在假定“效力待定说”合理的前提下主张对无权处分的适用范围做必要限制,以期通过法律解释学的方法对善意买受人的交易安全作更全面的保护,但最终得出了“给予买受人的保护仍然是不周延的”的结论,从而否定了“效力待定说”.〔18〕
综上所述,“效力待定说”不仅违背合同相对性这一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影响交易安全、侵犯无权处分合同善意相对人的权利,且造成了《合同法》体系上的不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