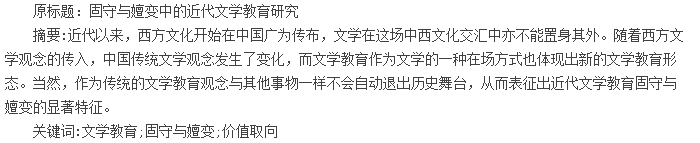
恩格斯在给友人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曾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对于中国历史进程来说,近代史无疑是一场灾难。西方列强凭借坚船锐炮强行打开国门,从根本上摧毁了中国原有统治秩序,开启了近代民主革命的先声,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化也开始在中国广为传布。文学在这场中西文化交汇中亦不能置身其外。随着西方文学观念的传入,促逼了中国文学观念的转变。文学教育作为文学的一种在场方式,开始从传统的“载道”功能中挣脱出来,转而关注现实,面向底层民众,试图通过文学,教育民众,启迪民智,改革社会,从而体现了历史进步的必然性。当然,一切陈旧、没落的东西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总是表征出固守与嬗变的显著特征,近代文学教育观的转变同样是这样。
一、固守:传统文学教育的困境
近代以来,西方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洗礼,开启现代文明的进程,然而,晚清政府不但没有紧跟世界潮流适时推进变革,反而逆潮流而动,妄图继续承接传统儒家之道和宋明理学作为立国之基,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以维护岌岌可危的封建秩序。虽当时西方文化通过传教士已经开始进入中国,但他们拒绝接受这一先进文化。清初杨光先在《不得已》一文中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月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于积薪之下而祸发无日。”甚至在雍正年间实行“教禁”。雍正皇帝在召见外来传教士时就说:“朕不需要传教士,……儒教与尔等之教相距甚远。”他们惧怕封建君权受到西方神权观念的冲击而危及他们的统治,仍坚守着以传统儒学和宋明理学作为政治统治思想和文教政策,实行教化政策,维护旧有秩序。
与拒绝西方文化相对应的就是进一步推行儒家文治传统。宋朝以来,程朱理学曾作为官方哲学长期占据独尊地位,但到明中叶后,受到王阳明心学挑战,致使心学一度成为显学。到清康熙年间因其尊崇理学,又恢复了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这一哲学体系之所以受到青睐,是因为程朱理学的核心就是为了维护封建制度,并通过思辨的形式论证其存在的合法性和不可侵犯性,这正切合了挽救封建王朝遭遇危亡的心理而受到极力推崇。康熙曾说:“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篡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统治者面对政治危机,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试图回到过去,寻求精神支撑。此时文学的评判标准就是承接“文以载道”传统“返经尊祖”,继续倡导文学的政教、德教的功能观,并以此教化民心,施行纲常,重振政纪。
“返经尊祖”的复古倾向成为当时许多封建文人的自觉追求。他们要求回到传统儒学立场上重新整治日益衰败的文学景象,重振文学教育作用,出现了像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魏禧等学者,他们“皆莫不呼吁文人回到古学,尤其是经学的立场上来审视文学的价值、意义和功能,确立文学批评的标准。”因此,文学教育就十分强调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钱谦益说得更加明确,文章要遵从儒家经典,“《三百篇》,诗之祖也;屈子,继别之宗也;汉、魏、三唐以迨宋、元诸家,继祢之小宗也。六经,文之祖也;左氏、司马氏,继别之宗也;韩、柳、欧阳、苏氏以迨胜国诸家,继祢之小宗也。”(《牧斋初学集·袁祈年字田祖说》)甚至顾炎武在返古的路上走得更远,他说:“著书不如钞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
(《顾亭林诗文集·钞书自序》)崇尚复古思潮的还有格调诗派。他们要求论诗必须回到诗歌源头处,才能确立诗歌标准,其实就是重拾诗教传统。薛雪在《一瓢诗话》一开篇就指出:“趋庭之训,首先及诗,而曰:'不学诗,无以言。'则诗之时义大矣哉!夫诗以道性情,感志意,关风教,通鬼神;伦常物理,无不毕具。……昔人已有诗亡之叹,况今日乎!有志者要当自具只眼,溯流而上,必得其渊。”只有回到先秦诗教观念中才能触及诗歌真谛。
这种试图返回到儒家典籍和经书中追根寻源,获取儒学真义,加强思想教化,同样受到统治者的肯定。沈德潜在论诗中因注重道德伦理教育,迎合了乾隆的治国方略,就很受器重。他在《说诗晬语》开篇就指出:“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他继承古代诗论传统,注重诗歌教育作用,极力推崇儒家“诗教”,认为“诗之为道,不外孔子教小子教伯鱼数言,而其立言,一归于温柔敦厚,无古今一也。自陆士衡有缘情绮靡之语,后人奉以为宗,波流滔滔,去而日久矣。选中体制各殊,要惟恐失温柔敦厚之旨。”(《清诗别裁集·凡例》)同样,深受考据学派影响的翁方纲所提出的“肌理说”其根底仍体现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教色彩。他指出:
“诗必研诸肌理,而文必求其实际。”而他所说的“肌理”就是“义理”,“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为此,他强调诗必须以“肌理”为准则,指出:“士生今日,经籍之光,盈溢于世宙,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他正是以此为标准认为明代文学的衰败就是因为没有“真才实学”,而清朝诗歌的兴盛是因为依靠经学和学问才出现繁荣的原因。
“至我国朝,文治之光,乃全归于经术,是则造物精微之秘,衷诸实际,……斯文元气复还于冲淡渊粹之本然,而后徐徐以经术实之也。”然而终因当时的学风和教风严重脱离现实,缺失了对现实社会的深度关切,没有从实际中找寻到解决清王朝面临危机的根源,而是想回到传统儒学中以获取精神资源挽救其命运,特别是想借助文学的政教、德教传统,加强思想控制,其结果必然是不但不能挽救清朝覆灭的命运,反而加速了灭亡的进程。
二、嬗变:近代西方文学观念的引进
在16~17世纪之交的明清之际,就已经出现了西学东渐的势头,但由于封建统治者惧怕西学危及自身统治,到清朝中后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却被阻断。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闭关锁国的大门终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的打开,使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华民族的落后以及国家的危机,从而激起他们学习西方科技文化、振兴国家的热情。此时,西方文学观念开始传入中国,促使文人志士对文学教育功能的新认识。
较早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的是传教士,也是中国了解西方的重要渠道。他们的传教活动大多围绕针砭中国社会的弊端,试图促进中国推行改革。1895年传教士傅兰雅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求著时新小说启》中提出:“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道。”他强调运用小说来推行国民教育,改变中国封建落后的现状。日本使臣森有礼的《文学兴国策》一书经由传教士林乐知翻译为中文并传播开来,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本书原是日本使臣森有礼向各国征询兴国之策,译者在这本书的序言二指出:“欲变文学之旧法,以明愚昧之人心,而成富国之国势,此《文学兴国策》之所译也。”指出译该书的目的,而在文中传教士潘林溪回复森有礼的咨询时说:“且苟知文明之人必籍文学以牖其明,即可知通国之人无不当籍文学以牖其明矣。”还认为:“有教化者国必兴,无文学者国必败,斯理昭然也。即如三百年前之西班牙,实为欧洲最富之国,嗣因文学不修,空守其自然之利益,致退处于各国之后而不能振兴。此外各国,亦多有然。”这里的文学泛指文化,但也揭示了文学对启迪民智、振兴国家的重要性。
由传教士传入的西方文化以及文学观念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使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认识到文学具有革除旧弊、启迪民众、开启民智的重大作用,这对晚清兴起的借助文学教育推进社会改良的作用不可低估。
真正对中国文学观念变革产生影响的则是西方小说在国内的盛行。由于当时西方特别是18世纪以来启蒙文学的兴起,出现了大量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小说,小说成为文学的中心。这些文学作品大多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现实,积极倡导社会改革,体现了强烈的实用取向,甚至在日本还出现了“政治小说”,作家自觉地借助文学以唤醒民众、推进政治变革。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一经接触西方文学,尤其是小说,就意识到文学对民众的巨大教育作用,认为文学能够教育民众、开启民智、促进社会改良。这正切合国内仁人志士寻求救国救民的愿望,所以,他们对西方文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翻译小说的兴起就是这种愿望的最好表达。林纾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他一生翻译了一百七十余种外国文学作品,涉及英法美等多个国家。翻译小说的出现,有利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更便捷地接触西方文学,其中大量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带有明显的批判社会现实的倾向,它们大多描写底层的社会生活状况,直面广大民众,针砭社会时事,这对中国传统文学中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体裁直接提出挑战,同时也引导中国文学创作的转向,开始关注普通民众、关注社会现实。
西方文学观念真正对中国近代文学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则是,由梁启超倡导的以“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及“戏剧改良”等为理论标志的近代资产阶级文学运动。
梁启超提倡的文学革命,就是以西方和日本文学艺术为榜样,要求写诗要有“欧洲之意境、语句”、“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尤其是进化论的思想为近代文学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要求文学适应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反对厚古薄今,更反对一味崇尚古人。梁启超说:“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几及。余生平最恶闻此言。窃谓自今以往,其进步之远轶前代,固不待著龟,即并世入物亦何遽让于古所云哉?”
(《饮冰室诗话》)他表达了文学要面向现实,适应社会发展推进文学的改革。
特别是梁启超将小说定位为“文学之最上乘”,也标志了中国文学谱系的新的变化,颠覆了小说一直被认为是“小道”之学的传统。中国文学历来以“载道”为己任,这一变化也隐喻了小说在另一个层次上肩负起新的载道功能。
其主要有两个原因促成,首先,维新变法失败,他们意识到,要想革命成功,必须依靠大众力量,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以唤醒民众,而要唤醒民众最好的方式就是小说。再者,他们看到西方的先进,不仅在技术上、观念上优于中国,而且在文艺上也优于中国,而其小说居于首位,按照国人惯有思维,小说也必有载道功能。这也体现了时代的特征,因为在古代文学中诗文载道的教化总是呈现出自上而下、温文尔雅的做派,小说则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而切合时代的心理需要。
三、取向:近代文学教育的双重变奏
在传统文学教育步入困境、西方文学观念传入的交织中,终于催生出新的文学教育观念,其中占主导的是试图通过文学来教育民众、启迪民智、推进社会改革、带有明显功利性质的文学教育观念。同时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的引入,在文学教育中也开始关注文学的审美品性,注重文学对人的心理、情感以及精神领域等影响,从而又体现了近代文学教育非功利性的取向。
(一)文学教育的功利取向
注重文学教育的功利性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随着国家存亡、民族危机的加剧,大批能人志士自觉地关注现实,主张文学要为社会和政治服务,将文学作为“经世致用”的“教科书”,即便曾是古文派的学人也有意识地矫正以往脱离实际、流于空疏的不良学风。被胡适誉为“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曾国藩也提出要将“经济”融入到“义理、考证、词章”之中,说“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其“经济”即为“经世济国”。
突显文学经世致用教育观的当首推龚自珍。
他提出“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龚自珍全集·乙丙之际箸议第六》),甚至认为研究经史也要同现实结合起来。“人臣欲以其言裨于时,必先以其学考诸古。不研乎经,不知经术之为本源也;不讨乎史,不知史事之为鉴也;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孰急、孰可行、孰不可行也。”(《龚自珍全集·对策》)他强调学术研究要注重“致用”,要能够“通乎当世之务”,同样,在文学研究上更是注重“致用”这一主张。他说:“曰圣之的,以有用为主。炎炎陆公,三代之才。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同年吴侍御杰疏请唐陆宣公从祀瞽宗,得俞旨行……》)这里所说的“斯”就是指“致用”,文学要为社会现实服务,要以“有用”为主。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以及《海国图志》等论著都是这一文学教育观念的体现。他曾明确指出:“文之用,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文之外无道,文之外无治也;经天纬地之文,由勤学好问之文而入,文之外无学,文之外无教也。”(《默觚》)他将“道”、“治”、“学”、“教”统一于“文”无不体现文学经世致用之功能。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龚自珍、魏源等人所力主经世致用文学教育观,虽与传统文学教育有承接的一面,但之间又有明显区分。在传统文学中,儒学占据主导地位,文学成为载道的工具,“文”仅是“道”的载体和确证,文学的“经世致用”主要是一种政教功能,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和道德教育,遵命于统治者的思想意志,最终纳入到“道统”范畴,不带有具体的开启民智、改革社会的现实功用。而近代以来所倡导的经世济用则与之截然相反,是对“文以载道”在内涵层面上的超越。一方面是用来批判现实,而不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政治统治为目的;另一方面主要是用来宣传社会变革,主张改良社会,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工具而出场,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与经世致用文学教育观紧密关切的是培育新民的启蒙教育,也体现了文学教育功用性的另一面。“经世致用”更多的是在形上层面上确证文学的教育作用,那么主张新民、启迪民智则是在形下层面上体征出文学的教育作用,特别在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时认识到,日本之所以在明治维新后国家迅速强大,是与民众的觉醒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他认为要救国首先必须开启民智,唤醒民众觉悟,其中文学的教育作用功不可灭。他说:“于日本维新之运大有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饮冰室自由书》)他认为通过文学教育民众,能够驱除人们的愚昧思想,而其最好途径就是通过小说进行教育,培养新民。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直接指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需。”那么如何造就“新民”?
只有通过小说才能实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在梁启超等人的倡导下,文学特别是小说成为“开启民智”、“造就新民”的工具和拯救国家于危难的法宝。他们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口号,确立了文学新民、救国的价值定位。为此,他还将日本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翻译介绍到国内,这也是在中国第一次出现“政治小说”这一概念。虽然这类小说缺乏艺术旨趣,甚至趋向于政治说教,但是切合了中国启蒙教育的需要而受到普遍欢迎。
小说之所以受到青睐,是因为小说通俗易懂,易于传诵,能够迅速而便捷的得以传播,它所发挥的教育作用是其他任何文学样式所无法比拟。梁启超等人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充分肯定了小说在开启民智、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尤其长期受封建道统观影响,民众旧有观念根深蒂固,对于振奋民众精神,开启民众智慧,提高民众觉悟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文学教育的非功利取向。
近代以来,由于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以及当时中国特定时代的客观诉求,文学开始从作为道德载体的圣坛上走下来,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并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从而鲜明体现了文学注重实用的取向,自觉承担起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但作为人类心灵和情感家园的文学却没有为塑造人的精神留有空间。即使这样,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不仅深受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西方哲学、美学等思想的影响,在注重文学对人的影响与教育上出现注重实用取向的同时,也出现了超功利的文学教育观念,诸如梁启超的移情说、王国维的超功利说以及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等,这些文学观念对文学教育作用的认识才更加逼近文学的本质。他们都注重文学对人的教育作用,并借助于文学艺术塑造国民精神,给予国民以心灵的慰藉,使人超越现实功利的限制,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非功利的情感联系,从而拓展人生存的自由空间。在这里我们选取王国维、蔡元培等作为观照,试图从中窥见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人们对文学教育认识上的不同取向。
王国维作为近代著名的文论家,深受康德、叔本华等西方哲学家、思想家的影响,他认为中国没有宗教,艺术匮乏,人们的精神慰藉无以依靠,从而缺失了人生存的精神支撑,这样各种社会问题也就应运而生。因此,他认为拯救国民于水火之中必须依靠文学艺术。
与主张文学重实用取向不同的是,他认为文学是不具有功利色彩的。他对当时文学肩负救国使命,将文学沦落为“有用”的工具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他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指出:“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如果“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他认为文学具有其自身价值,不能将文学与政治混为一谈,如果文学的价值被政治家所替代,文学本身的价值也必将丧失。他指出文学教育真正价值在于人的精神塑造,在《文学与教育》中鲜明提出这一主张:“夫物质的文明取诸他国,不数十年而具矣,独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养与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而言教育者不为之谋,此又愚所大惑不解者也。”甚至疾呼:“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他强调文学只有发挥对人的精神培养,才能真正体现文学拯救人的作用,而这种文学教育的发挥又是超越时空,具有恒久性,不带任何功利性质,如把文学作为“实利”来看待,其实是对文学价值的消解。所以文学艺术带给人的精神之真理才是“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正是基于这样认识,他对文学教育中的功利主义及传统文学教育中的教化功能给予猛烈抨击。他认为,长期以来儒家道统坚持教化、惩劝、美刺的文学功能,导致文学艺术受到侵扰,导致小说、戏曲、美术、音乐及人没有地位,而切合儒家教化要求的诗教传统的艺术及诗人却被提到很高地位。
王国维进一步认为文学教育的精神价值其根本体现就是给人带来情感之慰藉。“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岂不以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感情哉。至于生活之欲,人与禽兽无以或异。后者政治家及实业家之所供给,前者之慰藉满足非求诸哲学及美术不可。”(《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在他看来,文学教育的作用就是给人以精神的慰藉,如果人丧失精神之根柢,情感之滋养,也就丧失人之为人的特性而沦为物。而对感情的慰藉就必须依赖于宗教和文学艺术。只有通过宗教和美术才能给人以慰藉和情感的疗救,使人的精神高尚起来,情感丰富起来,自然远离不好的嗜好。
王国维的文学教育思想展现了与当时截然不同的新的范式。他的这种以对人的精神关怀为旨归的文学教育取向,无疑是对中国古代和近现代以来注重文学教育实际功用的强力反拨。注重文学教育非功利性的还有蔡元培。由于他受康德道德哲学中“人是目的”的影响,他把“完善之人格”作为文学教育的价值起点。他认为美育(即文学艺术教育)在培养健全人格中具有重要性,但不能直接体现为实用功利。
1912年1月,他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提出以军国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和美育为一体的教育主张。在他的影响下将“美育”作为“五育”之一写进当时的教育方针,“美育”的提出宣示了包括文学教育在内的文学艺术教育得以重视。他对“美育”解释道:“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他注重美育即文学艺术教育,就是因为通过美育可以培养人的情感,陶冶人的性灵,使人摆脱现世的困惑而进入一个精神实体的世界,从而使人高尚起来、崇高起来。他进一步指出,美育“既有普遍性以打破人我的成见,又有超脱性以诱出利害的关系;所以当紧要关头,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甚至有'杀身以成仁'而不'求生以利害'的勇敢;这是完全不由于知识的计较,而由于感性的陶养,就是不源于知育,而源于美育。”(《美育与人生》)正是由于美育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的双重特性,即能归入到人与人关系的群体之中,打破人我之见,祛除在现象世界中种种利害冲突,但又具有超越现象世界的特性,使人生境界得到提升,甚至使人在生死攸关之时表现出舍身忘我的人格尊严。
蔡元培的文学教育思想真正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则是他提出“美育代宗教”的著名命题。
他认为一切宗教对现实人生来说并不具有积极意义,只能对人生产生消极影响,但因宗教又具有美学价值,所以这也是宗教具有欺骗性和危害性所在,即使这样,但两者是截然不同的:“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在这里他区分了文学艺术教育与宗教的不同,将文学教育引向新的高度去认识,突出了文学教育在人的精神、信仰上的重要性以及对人生的重大意义。因此,他在批评宗教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的同时,使我们看到了加强文学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虽然他简单地用美育取代宗教,并没有对宗教和美育之间内在的更深层的文化关系的把握以及缺乏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不过重要的是他的这一提法能够促进我们增强对文学教育作用认识,特别是其论述了文学的审美属性,使我们认识到文学教育作用的审美途径,只有在审美中,人才能进入文学所营构的意境,从而摆脱现实的限制,走向人的精神自由。
王国维、蔡元培他们试图借助文学艺术塑造国民精神,给予情感慰藉,提升人生境界,揭示了文学教育的真谛。但历史没有选择他们,因为这与救亡图存、经世致用的时代潮流不相吻合,而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却影响了整整一个世纪,直到今天仍依稀可见。当今天回望这一风云跌宕的历史时,我们却感到他们对文学教育的论述是如此的珍贵而富有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2]孙培青,李国钧:《中国教育思想史》3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3]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
[4]陈伯海:《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上海:东方出版社,1997年。
[5]王运熙等:《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6]顾俊:《中国历代文论选》下,台北:木铎出版社,1981年。
[7][日]森有礼:《文学兴国策》,林乐知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走向衰亡,晚清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引入西方的政治学说来改造中国,随之而来的是臣民观的瓦解和新的民族国家观念的诞生.严复所引进的天赋人权、契约立国、进化论等学说以及梁启超宣扬的民族国家学说都深刻影响了世人.20世纪初的人们已经开始...
绪论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中国近代文学在八十年的时间里非常困难而又快速地走完了它的全程,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迈出了第一步。中国近代文学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继续发展和光辉终结,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孕育阶段和先声先导,并指引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
在中国近代史上,湖南人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他们不仅参与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在风云激荡的时代更迭中留下矫健的身影,也给湖南带来了各种社会思潮,改变了湖南的社会结构、民间风俗。...
近年来,普通民众通过舆论渠道,表达扞卫国家利益和主权以及重新厘定文化身份的渴求.而官方和民间双重推动下的国学回潮,以及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宣传等,亦可看作为这场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浪潮的一种显现.从某种程度上,它是长久以来西化追求之后的精神返乡[1]...
伪满洲国文学的研究中,古丁是最大的难点之一,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笔者问津这样一个难度很大的话题,主要是出于下述所想:首先,截至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为止,所有关于古丁的评价,都是在沦陷区文学研究的框架下进行的,无论是对古丁持何种评价观...
《点石斋画报》1884年5月8日(光绪十年四月十四日)创刊于上海,由英国商人美查创办。采用连史纸石印,每期刊载图画新闻八幅,每月上中下旬各出印一次,随《申报》附送,也单独发售。因由点石斋石印书局印刷,故得名《点石斋画报》。1898年8月停刊(...
当前对近代至民国旧体诗词社团研究的成果不多,仅有袁志成、查紫阳、万柳、马大勇以及笔者的相关论著。①又钟振振教授与笔者所从事的民国时期诗词学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项目,因限于篇幅、体例等问题,仅专门收录了南社、如社、须社、沤社、国风社、变风社、...
李光洙(1892-1950)是韩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巨匠。他一生创作了60余部长篇小说,30余部短篇小说和300余篇(首)诗歌、散文、杂文等其他作品,被公认为是自20世纪10年代韩国启蒙主义起,在韩国文坛最具行动,最彷徨的作家,在新文学50年历史上拥有读者最多,给予感动和...
陈洵(1870-1942),字述叔,别号海绡,广东新会潮莲乡(今广东江门市潮莲芝山)人。陈洵少有才思,爱好填词。少时随父亲至佛山经商,拜吴道镕门下,补南海县学生员。后欲随叔父陈昭常仕宦关外未果,辗转至江西瑞昌知县黄元直家当了十多年塾师。客居江西...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成立初期,要求作家们参加示威游行、演讲集会、写标语、散传单、出墙报、办夜校等政治活动,而且不允许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参加,因为“不参加革命就是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