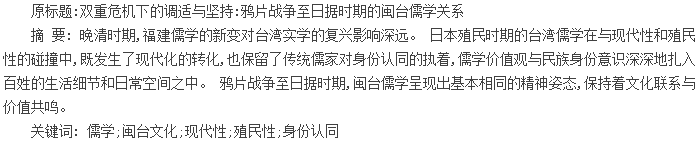
清朝为中国历史提供了最后一个虚幻的鼎盛帝国形象,康乾之后,中国实际上已在世界工业化的进程中被远远抛下。 工业发展与殖民扩张之间的必然联系,使得西方先发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充满了贪婪的好奇。 中国近代史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中拉开帷幕,而闽台就是列强进犯首当其冲的区域。 民族家国危机出现时,作为真理代言人和主流意识形态价值支柱的儒家学说无力对此做出有效的回应或解释,其合理性也遭遇到空前危机。 儒家学说阐释世界体系的天朝模式濒临破产,儒家化的制度难以维系,儒家学说对人伦纲常的解释权遭遇西方文化的挑战,这一切在客观上迫使儒家学说必须做出反应。 闽台儒学在民族家国危亡和学说体系危机的双重困境中,既表现出顺应时代潮流的调适一面,也保留了传统儒家对身份认同的执着。 在新变与执守中,明末以来关联性极强、一体化色彩浓厚的闽台区域儒学,也因政治历史的因素而逐渐走上不同的发展方向。
一、福建儒学的新变与台湾实学的复兴
鸦片战争划出了清晰的历史分界线, 对于闽台尤其是台湾而言, 历史进入了多事之秋。
1840 年之前,英国商人即常潜入福州、厦门、鸡笼、鹿耳门、淡水等港口,在私售鸦片的同时搜集情报,为日后军事侵略做准备。 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多次进犯厦门、台湾,遭到闽台军民坚决抵抗。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福州、厦门被列为通商口岸,台湾府城、淡水、鸡笼等地也被迫开港开埠。 1874 年日本设立“台湾事务局”,侵台之心昭然若揭。 同年 5 月,牡丹社事件爆发,台湾民众浴血抵抗日本侵略军的进犯。 1884 年,法国入侵基隆未果后攻击福州,驻扎马尾的清军南洋水师在半小时中全军覆没。 法军随之再攻台湾,在基隆、沪尾、淡水、澎湖等地都遭遇到刘铭传领导的台湾各界军民的抗击。 闽台军民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机动能力等军事因素全面落后的情况下仍坚持舍命抗战,这既表明传统儒学在民族气节、道德正义的教化方面的成功,也折射出传统儒学对世界体系认识的失败和自我力量评估的严重不足。 作为清帝国政策的制定者、阐释者、执行者的儒家知识分子,显然对此有所触动。 儒家知识分子的反思在闽台两地,共同表现为经世致用之学的再度复兴, 但闽台两地经世致用之学的复兴并非在同一时间节点上并行展开,其基础条件也并不完全一致。
福建实学的兴起与朱子学经典化之后不可避免的僵化有着逻辑关联, 它不完全属于民族危亡的刺激反应,某种程度上说更是一种学说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自我调适。 相比较于理学对义和理的重视,“经世致用”之实学则希望兼顾义与利、道理与事功。 乾嘉时期的意识形态高压政策客观上促使汉学考据之风大盛,朱子学则因其僵化趋于没落,汉学强调以严谨的态度求扎实之考据,这与“经世致用”之学有某种逻辑上的相似。 清中期福建儒学重提经世实学的源头,时常追溯到福州人郑光策。 郑光策被视为清代福建从复兴理学转向“经世致用”之学的关键性人物,生平最喜欢“读经世有用之书”,乾隆朝末期就曾上书福建当局议论时政,力倡关注商、民利弊的社会改革,所有条陈皆被福建当局者采纳,是开嘉道时期全国经世致用风气之先的人物。
嘉庆二年郑光策受聘主讲鳌峰书院时,提出以“经邦济世”之学作为书院教育的根本宗旨,是福建书院教育史上的重大改革。 福建长乐人梁章钜是郑光策的门生和女婿,在主政地方时勉力践行郑光策的“经邦济世”之学。 郑光策“经世致用”的思想,还至少在四个方面对福建经世实学的代表人物林则徐产生了具体影响:统筹全局的议政思想、因势利导的变法思想、解决南北两困的漕政改革思想、重视理财之道和用人之法的思想。
有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之称的林则徐,在其多次出任封疆大吏的的官宦生涯中,在农业、漕务、水利、救灾、吏治各方面都做出过成绩。 当然,林则徐“经世致用”思想最为人所称道的地方,还在于其在禁烟和抗英方面的功绩。 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关注到了军事力量背后的文化背景,清醒地意识到文化交流与文化理解在外事上的重要性,开启了了解西方、重视西方、研究西方、学习西方的风气。 林则徐组织人员翻译西文书报,派人收集西方各国情况,试图在更为全面地了解西方的层次上有效地抵御西方的入侵,他组织编译的资料包括《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是中国近代最早译介的外国文献之一。 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其嘱托,在《四洲志》、《瀛环志略》和其他资料的基础上编纂成世界地理历史书籍《海国图志》,鲜明地反映了实学色彩浓厚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 从郑光策到林则徐,晚清儒学在福建率先完成了重视实学的转变,清末儒学的“经世致用”鲜明地指向了适应世界发展潮流的目的。 在此意义上,晚清福建儒学“经世致用”思潮的出现,可称儒学在双重危机中求新求变的一种努力。
郑光策之学影响到了其女婿梁章钜和其门人林则徐, 而林则徐的实学倾向同样影响其女婿沈葆桢,沈葆桢则以经世致用之精神策划开发建设台湾的实践,这种实践在刘铭传那里又得到了承继和深化。 从思想传承的脉络上看,台湾实学的复兴与福建儒学的新变有着紧密的因果关系。
沈葆桢在赴台之前, 就已经在福建实施了新政色彩十足的政治举措。 1867 年, 沈葆桢以“总理船政大臣”身份经营福建船政局,福建船政局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军舰生产基地,所造舰只以木质、铁质兵船为主,也是东亚地区当时最大的造船厂。 沈葆桢认为,船厂在为富国强兵提供重要保障的同时,也能益民惠商,有利于地方经济民生。 考虑到海军人才自我供给能力的培养和海军队伍的长远发展,沈葆桢还在左宗棠筹办的“求是堂艺局”的基础上兴办船政学堂,派学员留学英、法等海军强国,学习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船舰驾驶技术和工业造船技术。 船政学堂所设的“制造”、“航海”两班,要求合格学员具备能按照设计图纸制造舰船和指挥驾驶舰船能力。 福建船政局及船政学堂带有明显的实学色彩,是近代福建在儒家官员主持下的现代化的重要尝试,对近现代闽台局势和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都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沈葆桢抵台驱逐日军进犯之后,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快速有效地发展台湾,使之与福建的现代化进程相衔接,增强闽台一体的经济交往和军事防御能力。 身为儒家知识分子的沈葆桢,其开发建设台湾的政治举措包含了行政管理、实业兴建、增进汉族民众与原住民的认同感等诸多方面。 在行政管理上,沈葆桢向慈禧和光绪提出台北“拟建一府三县”以强化行政控制的建议:“台北口岸四通,荒壤日辟,外防内治,政令难周,拟建府治,统辖一厅三县,以便控驭,而固地方”。
为在政令上保障台湾建设开发的空间,沈葆桢在《台地后山请开旧禁折》中指出原有对台禁令之于台湾发展的弊害, 希望清廷能废除阻碍台湾发展的诸项禁令:“盖台湾地广人稀,山前一带虽经蕃息百有余年,户口尚未充牣。 内地人民向来不准偷渡,近虽文法稍弛,而开禁未有明文,地方官思设法招徕,每恐与例不合。 今欲开山不先招垦,则路虽通而仍塞;欲招垦不先开禁,则民裹足而不前。 ……际此开山伊始、招垦方兴,臣等揆度时势,合无仰恳天恩,将一切旧禁尽与开豁,以广招徕,俾无瞻顾。 ”
在台湾实业的兴建方面,沈葆桢大力推动台湾交通设施的建设,并着重发展以煤矿为主的矿产开发。 《台煤减税片》详细陈述了台湾煤炭资源的丰富及其在市场竞争上的优劣势,提出减税以保障台煤市场竞争力的措施。 “垦田之利微,不若煤矿之利巨;垦田之利缓,不若煤矿之利速。 全台之利以煤矿为始基,而煤矿之利又以畅销为出路。 ……今欲分东洋之利,必将台煤减税以广招徕。 洋商计较锱铢,闻风而至。 以后税则虽减,而总计税入仍不至悬殊,于民间生计当有起色。至船局所用台煤,向系免税,不在定则之内。今拟请将出口台煤,每吨减为税银一钱。 ”
在增进与台湾原住民的沟通、增强民族认同与民族感情的方面,《番社就抚布置情形折》反映出了订立规矩与文明教化并行的施政策略:“曰遵剃发、曰编户口、曰交凶犯、曰禁仇杀、曰立总目、曰恳番地、曰设番塾……于枋寮地方先建番塾一区,令各社均送番童三数人,学语言文字,以达其情;习拜跪礼让,以柔其气。 ”
沈葆桢治台摆脱了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清议传统,注重政策的实效,不拘泥于儒家在长期的制度化中形成的各种框架条文。 从福建巡抚任上改任台湾首任巡抚的刘铭传,则继续将这种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投入到台湾建设的实践中。 刘铭传主导的台湾现代化建设至少包括以下八个方面:一是建立近代化军事体系,建机器厂、设军械所和火药局;二是建设铁路和创办中国最早的邮政业务;三是兴办包括煤务局、硫磺厂、机器锯木厂、煤油局等在内的新式企业或机构;四是设立轮船公司发展对外商贸;五是安抚原住民,继续垦荒;六是清丈田亩,整顿台湾税赋;七是兴办西式教育,培养现代科学人才;八是扩大儒学教育范围,维持闽台儒学一体化的格局。
从内容、形式、人员关系等诸方面来看,沈葆桢、刘铭传等人振兴台湾的施政措施都可以说是福建近代化尝试的一种延伸。
二、现代性与殖民性的纠葛与压迫:闽台儒学在困境中的演变
1894 年清廷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签订《马关条约》导致了澎湖列岛和台湾的割让。 从 1895年开始,台湾失去了自主发展的权力,沈葆桢、刘铭传等人主导的台湾现代化建设也随之被迫终止。 日占台湾之后,清代的儒学教育体系被废止,台湾籍的考生也无法再到福州参加乡试,闽台自明郑时期开始长达两百多年的传承与交流被迫中断, 因此,“闽台儒学渊源到日本占据台湾后就基本结束了。 ”
然而,从“长时段历史”的角度来考量,两百多年的闽台儒学交流对台湾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变迁均产生了不可忽略的重大影响。 日据后的台湾脱离了福建的区域管辖,但闽台儒学仍面对着同样的历史语境:民族家国的危亡和学说体系的危机,而从台湾面对双重危机之时所倚仗的文化资源、所表现出的身份意识、所凸显的价值立场、所经由的反应机制等多方面来看,都能在自明郑到晚清这两百多年闽台儒学的传承与交流中找到根由。 因此,鸦片战争或是日据之后的台湾儒学,仍然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反映出它和福建儒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如何处理西方船坚炮利所带来的“现代性”与“殖民性”,是鸦片战争之后闽台儒学界所必须要解答的问题,但因闽台于 1895 年之后所处的历史语境不同,对现代性与殖民性的纠葛与压迫的反应也各不相同。 在清代后期和民国初年的福建,以陈寿祺、陈乔枞、郭尚先、严复等为代表的儒家学者主张在新形势下不能再抱定程朱理学不放, 而应该以更为开阔视野提升儒学的实用性。 显然,这一批学者在如何应对“现代性”的问题上与以刘存仁、林春溥、陈庆镛、郑星驷等儒家学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然而,身处福建的儒家学者对于“现代性”和“殖民性”的复杂纠葛,及其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压迫感,还是与台湾儒士们的体验有着较大的差异。 有学者认为,台湾的现代化进程在日据之前已经迈上了正规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日据台湾斩断了台湾自主现代性发展的进程,将殖民掠夺强加于台湾的发展进程中,从而使台湾的现代化发展走上了与福建不同的“殖民现代性”路径。 在此情形之下,“现代性”与“殖民性”以一组悖论的形式呈现于台湾知识界面前,有研究者指出,这组悖论已经成为台湾知识界理解与阐释日据台湾史、台湾思想史复杂的矛盾运动的至关重要的范式之一,但这组悖论同时就是“殖民现代性”幽灵附体的一种精神症候。 “陈芳明的《殖民地摩登:现代性与台湾史观》基本上使用了这个阐释模式。陈芳明一再表述了这一观点:‘台湾若不追求现代化,就必须接受被支配的命运。不过,现代化并非是从台湾社会内部自发性产生, 而是由日本人以强制性手法加诸台湾人身上。 因此,殖民地知识分子,已深深体会到文化上的两难。 如果台湾人要抵抗殖民统治,就连带要抵制现代化;如果要接受现代化,则又同时要接受殖民统治。 ’……陈芳明所描述的‘两难’逻辑或‘困境’ 论述中可能隐含着一个可怕的结论: 没有殖民主义的扩张就没有第三世界的现代性。
……赖和的作品则提供了殖民地知识分子超越‘殖民现代性’悖论的两种方式:以左翼现代性和民族自我认同以及本土文化思想重构来瓦解和对抗殖民主义与现代性的共谋。 ”
“现代性”与“殖民性”的纠葛是台湾历史中的重要问题,但它不是历史的唯一面相,更不是理解历史的唯一途径。 从身为传统文化阵营一份子的台湾儒学的角度来说,要看到它在殖民文化、新文化、传统文化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之间,所展现出的内涵丰富的演变。
台湾儒学对“现代性”与“殖民性”的反应并不相同。 “殖民性”所引起的台湾儒学反应相对单纯,文化“殖民性”试图冲击并瓦解自明郑以来两百多年中闽台儒学共同发展过程里在台湾建立起来的价值底线和身份认同, 除部分儒士因种种诱因而转向对日本殖民当局的歌功颂德之外,大多数儒家知识分子则积极或消极地表明了对日据当局文化殖民的反抗立场。 对于包括了“新文学”等内容的庞杂的“现代性”,台湾儒学在与之对话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进行自我调适,对于“物质现代性”、“启蒙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价值现代性”、“美学现代性”等现代性不同层面的内容,儒学的对话程度与交流深度也各不相同。 总体上看,“台湾汉人在日本人同化政策的压力之下,反而对本族文化的存亡有较强烈的危机感,因此并未出现全盘西化的理论。
结果造成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在 20 世纪上半叶,台湾是全中国最现代化的地区,但也是维护旧文化最有力的地区。 似乎这样一个基调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 ”
如果说“西化”是清末民初包括儒学界在内的福建文化界的主流思潮,那么与“新学”的对话和“现代转化”的努力则是日据时期台湾儒学的主要演变方向。 “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反儒学并没有走到截然对立的地步,而是在新旧之间找到了许多共通的空间。 ……事实上,在台湾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新旧思想截然对立的现象有之,认真商讨比较的情况有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通交流亦有之,甚至出现在彼此的主要刊物上互登文章的事情,比如在高举新文化旗号的《台湾民报》上就曾发表连雅堂以文言文形式撰写的 10 多篇文章。 此外,台湾文化领域的文人在文化观点的对立与民族意识的对立二者之间的主次问题上,一直有明确的立场,即抵制日本文化或反对日本殖民当局对文化论争的利用的明确态度,要优先于新旧文化的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新旧文化论争提供了交融互动的因素。 ”
从此也可以看出将“现代性”与“殖民性”盲目捆绑的粗陋性。 台湾儒学在师法福建儒学的过程中,被唤醒的民族身份意识在抵抗着日本当局的文化殖民企图, 而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则促进了儒家文化与西方新文化的沟通尝试。
儒家诗学就在新旧文化的论战中,实现了与西方诗学的对话与交融。 “在‘现代转化’方面,新旧文学的辩难促成了儒家诗学和西方诗学的对话。 ……在诗歌发生学、诗歌社会学方面,儒家在两千年前形成的看法, 也经得起近代西方文学理论的考验。 20 年代台湾知识分子意外地发现儒家诗学对新文学运动的推展非但不是阻力,甚至还是助力。 而从儒家的立场而言,新文学运动所启动的现代性、西方性的挑战,为其诗学提供了攀登另一思想高峰的起点。 ……在新文学运动的挑战之下,传统诗学在文学基本原理上和西方诗学接轨,证明了儒家诗学包含很高的普世性。 ”
对儒家诗学的回归,在台湾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张我军身上也体现的非常明显。 张我军新文学思想的形成与其在福建的经历密切相关,“在厦门的两年生活, 堪称张我军‘一生的转捩点’”,而在与持传统儒家思想的连横的论战中,张我军的诗学观也在不断地发生自我调整。 “张我军在与连横论辩之后,不仅表现对传统诗学的回归,而且还从一种类似中西比较文学的角度去重新肯定中国诗学的价值;另一方面,在把新旧文学之争导向真假文学之争的时候,张我军事实上承认了旧文学中也有真正的文学,而不必反对,甚至传统诗学中主张‘真正的文学’的儒家诗学,也可以是新文学的理论基础。 ”
正是在与新文学、新文化的不断碰撞和接触中,台湾儒学也在不断地进行自我的更新。 儒家民本思想也在与殖民主义的交锋和与现代文化的对话中,释放出传统的价值魅力。 “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在理论上,儒家民本思想如何为20 年代台湾人提供传统的泉源;更重要的,我们看到了在社会实践上,经过了这些站在最前线冲锋陷阵,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奋战不懈的知识分子的武装,儒家思想成了对台湾社会最具有解释力、改造力,对现代台湾人具有激勉作用的传统。 ”
现代性与殖民性的纠葛与压迫,在福建和台湾引起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反应,但在保持民族气节、尝试在与现代文化的接触中进行自我调整的立场上,闽台儒学却呈现出基本相同的精神姿态,这也应该被认为是日据时期闽台儒学之间的一种精神联系与共鸣。
三、认同的坚持:闽台儒学与台湾身份意识的执守
面对日本殖民政策及其带来的现代化可能, 台湾民众保持了长时间的抵制与反抗。 这说明,晚明以来“以闽为本”的儒学教化已经深度融入了台湾民众的日常观念之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自明郑到此时,儒学在台湾经历了长达两百多年的移植与发展,已经融入了庶民生活,更是士大夫阶层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 儒学在庶民生活中表现为尊师重道、孝敬父母、重视家庭、重视祭祀等等习惯,这在海峡两岸始终相同。 在割台之后,这种庶民儒学比士大夫阶层的精致化儒学存活更久,成为维系汉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力量。 ” 从甲午战后,刘永福率领黑旗军赴台守卫开始,五十年间台湾民众反抗日本殖民侵占的怒火始终不曾停息。 1895 年“台湾民主国” 坚持了五个月的武装抗日;1896 年台湾太鲁阁土著奋起抗日;1907 年蔡清琳率众起义;1912 年刘乾等人袭击林圯埔警察支厅,“林圯埔事件” 爆发;1913 年同盟会会员罗星福组织起义,史称“大湖事件”;1914 年罗臭头等于台南袭击日本警察派出所,不甘被俘自杀身亡;1915年余清芳、江定等人领导西来庵起义,日本殖民当局以欺骗、集体屠杀、秘密处决等方式残杀数千名台民;1930 年雾社起义爆发,总人口不过 2100 人的台湾赛德克族同胞,有 900 余人在这次起义中战死或自杀;1944 年台湾光复前期,台北“帝国大学”学生蔡忠恕等两百余人秘密集会酝酿反日起义,事败后蔡忠恕惨死狱中。
不同阶层、不同族群前赴后继的反日武装斗争表明,由明郑至清中期以来的儒家教育已经唤醒了台湾同胞的民族身份的自觉。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即有意识地强化了台湾儒学学堂的建设。 在闽台儒学教育一体化的背景之下,光绪之后的台湾儒学学校迅速增加,清代台湾 13 所儒学学校中,雍正四年(1726)前建成的共有 5 所,从雍正四年到光绪二年(1876)的 150 年中只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增加了一所新竹县儒学,而光绪二年之到光绪十六年(1890)的 14 年间台湾儒学激增了 7 所。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清政府在列强环伺中对台湾身份的重视、警觉与危机感。
闽台儒学在清末列强觊觎台湾之时,其气节和身份的内容空前高涨,压倒了学说体系中的其他内容。 一个醒目的例子,即清廷在意识形态上对于郑成功的承认和褒奖,这也增进了台湾民众的中华身份自觉意识。 沈葆桢以“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的身份节制福建所有镇、道,赴台筹办防务后,在以实学开发台湾的同时,对唤醒台湾民众的民族身份意识格外重视。 身为福建人的郑成功在台湾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沈葆桢请朝廷对郑成功加以追祀,从而将闽台儒学对汉民族气节与身份的重视发扬光大。 《请建明延平王祠折》着重强调了郑成功一生的“忠义”色彩,以及这种典型的儒家人格之于彼时台湾身份觉醒与共识凝聚所无可替代的意义。 沈葆桢在奏折中说,“奏为明季遗臣、台阳初祖,生而忠正、殁而英灵,恳予赐谥建祠,以顺舆情、以明大义事。 ……有功德于民则祀,能正直而壹者神。 明末延平郡王赐姓郑成功者,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人;少服儒冠,长遭国恤,感时仗节,移孝作忠。顾寰宇难容洛邑之顽民,向沧溟独辟田横之别岛;奉故主正朔,垦荒裔山川。 传至子孙,纳土内属。 维我国家宥过录忠,载在史宬;厥后阴阳水旱之沴,时闻吁嗟祈祷之声,肸蠁所通,神应如答;而民间私祭仅附丛祠,身后易名未邀盛典,望古遥集,众心缺然! ……臣等伏思郑成功丁无可如何之厄运,抱得未曾有之孤忠,虽烦盛世之斧斨,足砭千秋之顽懦;伏读康熙三十九年圣祖仁皇帝诏曰:朱成功系明室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敕遣官护送成功及子经两柩归葬南安,置守冢建祠祀之。 圣人之言,久垂定论。 惟祠在南安,而台郡未蒙敕建;遗灵莫妥,民望徒殷。 至于赐谥褒忠,我朝恢廓之规,远轶隆古:如瞿式耜、张同敞等俱以殉明捐躯,谥之‘忠宣’、‘忠烈’。 成功所处,尤为其难;较之瞿、张,奚啻伯仲。 合无仰恳天恩,准予追谥;并于台郡敕建专祠,俾台民知忠义之大可为,虽胜国亦华衮之所必及。 于励风俗、正人心之道,或有裨于万一。”
于台湾建郑成功之祠并“赐谥褒忠”,就是意在凸显家国危难之际儒家“忠义”观念的重要性,“俾台民知忠义之大可为”。沈葆桢还为郑成功祠亲写对联一副:“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 ”沈葆桢之后治台的刘铭传,在参拜郑成功祠时也撰写对联道:“赐国姓,家破君亡,永矢孤忠,创基业在山穷水尽;复父书,辞严义正,千秋大节,享俎豆于舜日尧天。 ”
以郑成功为代表的明郑遗臣所表现出的“忠义”、“千秋大节”等儒家核心价值,在家国危亡的时代背景里,在清政府的褒扬和追祀下,迅速地升华为对中华民族身份的一致认同。 “割台初期,儒生阶层是抗日武装部队的主要成员。 儒生抗日的精神基础接近明末抗清的前现代思想格局,即华夏民族不受异族统治的思想。 ”
这种身份认同因其渗透入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伦理而显得无比强大而坚固,为反抗日本对台湾的占领、殖民、掠夺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与能量。 日本学者承认,握有军事力量绝对优势的殖民当局对台湾的非法占领,始终遭到台湾民众的坚决抵抗:“台湾住民中之汉族,多半对日本人怀有民族对立之情绪,所谓以中华之民臣服於夷狄治下之耻辱,为此激励之敌忾心所冲动,以义民之名义下响应”。
“台湾民主国”的武装抗日历程,是台湾民众为免于被割让 、执守中华民族身份的典型表现。 曾任台南崇文书院、台湾府衡文书院、嘉义罗山书院主讲的光绪十五年进士丘逢甲,在多次联合台湾绅士向朝廷发出“废约抗战”的吁电未果之后,倡议建立“台湾民主国”以图保台。 “台湾民主国”虽然称“国”,却处处强调这个“台湾民主国”是中国的一部分,它的出现是无奈时局下的权宜之举。 “台湾民主国”的“全台布告”详细表明了“台湾民主国”成立的背景与缘由,以及台湾民众执守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要求守土抗战的必死决心:“我台湾隶大清版图二百余年。
近改行省,风会大开,俨然雄峙东南矣。 乃上年日本肇衅,遂至失和。 朝廷保兵恤民,遣使行成。
日本要索台湾,竟有割台之款。 事出意外,闻信之日,绅民愤恨,哭声震天。 ……台民惟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国,作何办理。……惟台湾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预。 设以干戈从事,台民惟集万众御之。 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 ……此非台民无理倔强,实因未战而割全省,为中外千古未有之奇变。 台民欲尽弃其田里,则内渡后无家可依;欲隐忍偷生,实无颜以对天下。 因此槌胸泣血,万众一心,誓同死守。 ”
“台湾民主国”的国旗“蓝地黄虎旗”就是它身份自我定位的象征。 “蓝地黄虎旗”明显是对清朝“黄地蓝龙红日旗”的呼应,这幅旗帜用蓝底色对应清朝皇室的黄底色,用虎对应龙,旗上不出现代表正统的红日,虎首仰望西北方向,旗上图案的色彩、内容与布局都表明“台湾民主国”不敢僭越的“臣属身份”,也表现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国家意识。 “台湾民主国”改元“永清”,更是直截了当地宣告自己“永远忠于清朝”,重复强调自我的定位与身份。
“不论从传统或现代的角度,从台湾或中国大陆的角度,此书之价值皆不可磨灭”的《台湾通史》,是祖籍福建漳州龙溪县的台湾史学家、诗人连横于 1908 年至 1918 年完成的台湾第一部按照通史体例撰修的史书。 这部史书继承了传统儒家史学的基本精神,可以看做是闽台儒学经由两百余年发展之后沉潜的结晶。 《台湾通史》洋溢着“继绝存亡”的民族意识:“夫春秋之义,九世犹仇;楚国之残,三户可复。 今者,虏酋去位,南北共和,天命维新,发皇蹈厉,维王有灵,其左右之! ”
结合其时台湾日据的时代背景,这篇《告延平郡王文》显然意在寄托驱逐日寇、光复台湾、回归中华的愿望。 日本殖民当局实行文化殖民统治期间,企图通过推行日本文化而从根本上瓦解台湾的文化传统与文化根基, 消泯已然融入台湾民众日常生活观念中的朱子学价值观。 台湾儒生与民众也随之采用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力图保存中华文化传统的观念血脉和身份意识。 正是在这种文化反抗中,闽台儒学教化所埋藏下的爱国激情与身份自觉,通过许多不同方式或隐或现地表现出来,主要包括了办书房以传承儒学、结诗社以砥砺气节、开鸾堂以崇祀儒教、建祠堂以彰显宗族等方面,从而在不同的文化维度上将儒学价值观与民族身份意识融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细节和日常空间之中。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台湾回归祖国怀抱。 不久国民党政权退入台湾,闽台两地又再次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国民党当局在退守台湾之后大力提倡传统文化,并对社会实行儒学化的文化包装。作为儒家学说在新历史语境中的发展,“新儒家”学派于 1958 年在港台成形。1966 年11 月,由孙科、王云五、陈立夫、陈启天、孔德成等一千五百人联名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将台湾社会的“儒家化”再次推向一个高潮,而隔海相望的祖国大陆,儒学的发展则陷入了停顿期。 闽台儒学再次正面交流,则要等候两岸关系正常化的春天来临。
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走向衰亡,晚清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引入西方的政治学说来改造中国,随之而来的是臣民观的瓦解和新的民族国家观念的诞生.严复所引进的天赋人权、契约立国、进化论等学说以及梁启超宣扬的民族国家学说都深刻影响了世人.20世纪初的人们已经开始...
纵观中英混血儿、当代英语小说家毛翔青(TimothyMo,1950-)的小说,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故事主人公无一不处在中西跨文化情境中,无一不在努力追问并建构新身份,却无一不为一种深深的存在焦虑所困扰。《酸甜》(SourSweat,1982)主人公丽丽陈在二战后的...
以物喻志,借景抒情是中国诗歌的传统。一些植物早已经成为世代相承的诗歌植物,如梅兰竹菊号称四君子,松、竹、梅又有岁寒三友之谓,千百年来不断成为诗词歌赋吟咏书写的题目。仅仅据《全唐诗库》检索系统统计,在收录的全部42863首诗歌中,咏松的就占3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