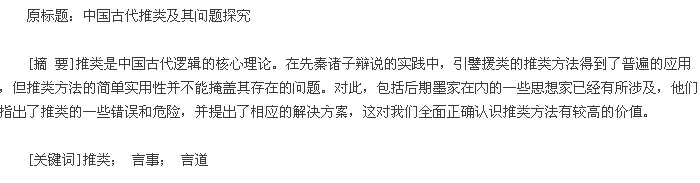
一、推类的理论与实践
推理基于人们对事物类的了解和掌握。在我国古代,在类思想基础上进行的推理常常被称为“推类”.关于中国古代的“类”这个概念,许多研究者都有比较深入而广泛的研究。“类”的概念是逻辑学赖以产生和建立的基础,在中国逻辑传统中,“类”的概念更是推理理论和实践的核心概念。
古人将事物或现象相似、相同、相从、相召的关系称为类关系。如孟子认为: “凡同类者,举相似也。”( 《孟子·告子上》) 而在中国逻辑传统中,将“类”赋予逻辑含义的是墨子及其学派。对于“类”的概念,后期的墨家给出了言简意赅的定义: “有以同,类同也。”( 《墨经·经说上》) 同时,也给出了什么是“不类”的定义: “不有同,不类也。”( 《墨经·经说上》) 在此,墨家主要是从概念的内涵方面,即从概念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特有属性方面去把握类的规定性。“类”是一种“有以同”的关系,凡是具有相同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的事物就可以是一类,否则就“不类”.这种对“类”的定义表明墨家对逻辑上的类的概念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根据类关系进行推类,在古代被大多数思想家所认可和推崇。孔子所谓的“举一反三”其实就具有推类的意味,“一隅”与“三隅”是同类,所以“举一隅”就可以推知另外“三隅”的特点; 荀子主张“听断以类”( 《荀子·王制》) ,“以类度类”,因为“类不悖,虽久同理”; 墨家主张“以类取( 证明) ,以类予( 反驳) ”( 《墨经·小取》) ,“辞以类行”( 《墨经·大取》) ; 《吕氏春秋》的《召类》篇明确提出“类同相召”,即同类可推;《淮南子》也推崇“以类而取之”( 《淮南子·说山训》) ; 王充说: “……以推类见方来……”( 《论衡·实知》)总体说来,中国古代的推类就是建立在类的基础上的推理。中国古代思想家倡导“察类”“知类”和“明类”,将事物区分为不同的种类,是为了“以类取之”进行推类。具体说来,“所谓推类就是两种不同事物( 现象、命题) 依据类同的属性,由一种事物( 现象、命题) 具有某种属性,推出另一种事物( 现象、命题) 也具有这种属性的推理”.它是中国古代广泛应用的一种推理论说形式和思想方法,是思想家们用来阐发思想和主张的重要手段。在先秦文献中,推类方法在辩说实践中有大量的应用,《淮南子》之《要略》篇将这种论说现象概括为“言事以言道”.在言事与言道的过程中,推类所依据的就是“事”与“道”在某一点上的共同之处,即它们的类同关系。“事”和“道”常常是指跨领域的事件,其相同之处更多的是有某一同情同理,这种“同”,即“理同”.尽管“事”与“道”在类种包含关系上并不沾边,但古人仍认为它们是一类。
因而这种推类在论辩、立说时具有更为广泛的适应性。实际上,推类的过程就是建类的过程: 从一般说来毫不相干的事物中寻找它们共同或相似的特征或本质,通过这些特征或本质将这些事物相互联结、贯通。因而在具体的言事与言道的论辩过程中,就习惯于以那个浅显的“事”的特征或本质与所言之“道”相比附,从而达到说明和论证所言之“道”的合理性的目的。正所谓,一方面,“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以使人知之”; 另一方面,“见者可以论未发”.
二、推类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古人根据他们所理解的类概念的意义和建类的思想,在思维实践---辩说、立说中以事言道,乐此不疲。但这样的推类方法并非总是完美无瑕,古代思想家对此也有所认识: 随意的推类往往会产生谬误,因此建类、推类要慎重。那么如何才能正确地进行推类呢?
墨家告诫人们,“推类之难,说在( 类) 之大小。”( 《墨经·经下》) 推类的困难,在于类的范围有大小,超乎范围,就陷于谬误。另外,《墨经·小取》认为: 由于“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不是而然; 或一周而一不周,或一是而一非。”“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辞之侔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 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 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因而“辟、侔、援、推之辞,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失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类、异故; 则不可偏观也。”
《吕氏春秋》认识到“物多类然而不然”( 《别类》) ,以至于在思维实践中就会出现“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 《察传》) 的情况,所以“是非之经,不可不分”( 《察传》) ,类不可必推。
《淮南子》也认为“类可推,不可必推”,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可必推”的原因: 其一,“物类之相摩近而异门户者,众而难识也。”( 《淮南子·人间训》) 即有些事物看起来很接近,其实不同类,这种情况很多而又不容易区别辨认。例如,“狂者东走,逐者亦东走。东走则同,所以东走则异。”( 《淮南子·说山训》) 真正疯了的人往东跑,他的亲朋为了追他回来也向东跑,二者虽然都有向东跑这一共同属性,但实际上原因各异,前者是“疯跑”,后者是“有意图的跑”.
其二,“物类相似若然而不可以从外论者,众而难识矣。”《淮南子·人间训》) 客观事物由于某些属性相同而归为一类,因为不同的属性而区别为不同的类。
所以相同不是绝对的同,相异也不是绝对的异,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如“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面,而皆说于目。梨、橘、枣、栗不同味,而皆调于口。”( 《淮南子·说林训》) 因此,任意地从事物中摄取一定关系或属性作为分类之根据往往会导致谬误。其三,物固有似然而不然者,亦有似不然而然者。在社会领域中,为了自身或阶级利益,制造种种伪装,竟施诈伪,事类之难区分就更甚。如,越王勾践为吴王夫差所败,勾践则请身为臣,妻为妾,礼甚卑,而辞甚服。
而实际上,勾践这是卧薪尝胆,以待来日复仇的一种权宜之计。
既然推类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么如何才能提高它的可靠性,从而使得言事以言道更加有说服力,这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先秦思想家对此也有一定程度的涉及。
墨家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提出了“异类不比”的原则,要“知类”“察类”才能“明故”.主张战争的人为了替其侵略行为辩护,举“禹征有苗,汤放桀,武王伐纣,此皆为圣王”来反驳墨子的“攻伐为不义”,证明“攻伐”的合理性。墨子则认为,禹、汤、武王这三王征伐是“诛”,而侵略别国的行为才是“攻”,这是不同类的事件,不能进行类比。可见,墨子强调以概念内涵的根本不同之处区别不同的类,“诛”是正义的,而“攻”却是非正义的。
《吕氏春秋》为此而提出的办法是: “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 《吕氏春秋·察传》)考察事物的实际和大多数人的看法,因以此作为依据,进行推类。这个方法综合考虑到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固然不错,但并未抓住根本,且太笼统。
《淮南子》则较为明确地提出: “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 得呙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适。”( 《淮南子·说山训》) 考察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以找出事物得以产生的原因,进而了解事物的属性以及这些属性得以发挥或发生作用的时间、地点等条件,只有掌握这些,人们才能在各种实践活动( 包括思维实践的论辩) 中少犯错误,正确地进行推类。强调通过寻求事物的因果联系以解决何类事物可推类,何类事物不可推类,《淮南子》比《吕氏春秋》的认识更深刻。
三、评价与思考
先秦所谓的“推类”与我们现在所说的“类推”并不完全一致。我们一般认为类比推理是这样一种推理: “它根据两个( 两类) 对象在一系列属性上是相同( 或相似) 的,而且已知其中的一个对象还有其他特定属性,由此推出另一个对象也具有同样的其他特定属性的结论。”
而中国古代的推类依据的也是事物间的相似、相同之处,因而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类比推理。类推主要是一种认知方法,这种认知方法是或然的,在现代逻辑中被归为归纳推理的范畴。推类则主要是一种论辩方法,用以揭示宇宙中普遍的“道”,具有演绎的性质。“道”的存在是哲学的本体观,似乎天经地义,言事以言道而推类的方法只是揭示被掩盖或蒙蔽的真理而已。所以,尽管古人对推类推崇备至,但实际上这种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已沦为伦理、政治和哲学的附庸。因为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政治伦理思想和世界观,且都可以使用推类的方法言自己独特的道,这必然会使得通过推类而取得的结果---“道”的真理性大打折扣。例如,孟子曰: “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博而跃之,可使过颡; 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 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就是也。”( 《孟子·告子上》) 这个推类论证在孟子看来是妥当的,但在后期墨家看来,这个推类是极其错误的,因为违背了“异类不比”的推类原则。但问题在于,什么是同类?
什么是异类? 标准是什么? 按照《墨经》中所举的例子,它似乎求助于本质主义,本质不同则不相类。可孟子却认为二者本质相同,因而进一步的问题就是:
如何去判别本质? 这将是哲学的探讨。难能可贵的是,有些思想家意识到了推类的困难和问题,并进行了有意义的分析,这比单纯地使用这种方法显然要理性得多。可见,在言事与言道的论辩、立说的思维实践中,推类究竟有多大的逻辑力量,并不仅仅取决于这一方法本身。
中国古代逻辑理论重内容分析,而轻形式考察;注重实际的推理经验,缺少严密的形式逻辑和形式化的数学思维。尤其是其中的类概念是较之一般科学中的属种关系要广泛的多的范畴。相对于推类的逻辑价值,先秦思想家们更注重推类方法的效果。游说、劝谏等等就是为了让对方接受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而实际情况也表明,推类方法的确效果显着。
先秦是百家争鸣、文化激荡的时代,各家各派为宣传各种各样的“道”而运用推类以事言道的现象比比皆是,而这种辩说方式所带来的立竿见影的效果使得这种推类的思维方式逐渐为人们所习惯和认可,并形成一种思维传统固化下来,以至于在后来人们辩论和着书立说的活动中一直发挥着作用。比如,我们经常会使用喻证法、类比法,用一个浅显、生动、易于为听话者所理解的事例来说明一个比较深奥、抽象的道理,从而增强论辩的说服力、感染力。尽管这种方法有某些局限性,如论辩强于认知,效果优于手段等等,但作为一种独特的言语交际的逻辑方法,其生命力依然旺盛,对此,我们应当给予公正的评判。
[参 考 文 献]
[1]张晓光。 中国逻辑传统中的类和推类[J]. 广州大学学报,2002,( 5) .
[2]董志铁。《淮南子》推理论[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1) .
[3]吴家国,等。 普通逻辑( 增订本)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12.
现代意义的辩证法和形式逻辑都是西方哲学的产物,于20世纪初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文化思潮被正式引介到中国。它们的传入具有共同的时代背景,那就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为了救亡图存,实现民族振兴,一些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有感于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落后,...
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中国的逻辑是否存在?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困难是什么?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出路究竟是演绎化还是归纳化?这些重要问题近年来逐渐成为逻辑学界和哲学界争论的热点。在这里,我们将基于逻辑与文化的关系,从归纳逻辑、非形式逻辑等视角探讨...
思维的发展无论是从作为整体的人类思维发展史来说,还是从作为个体的个人思维发展史来说,都可以分为两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的阶段,可称之为形式思维;第二阶段是从思维抽象到思维中的具体的阶段,可称之为辩证思维。以往进行中国逻辑史的...
“推类”一词最早见于《墨子·经下》“推类之难,说在之大小。”可见,“推类”乃建立在“说”的基础上。又《墨子·经说上》“方不,说也”,又知“说”其实是以“类”为基础,是一种“见者可以论未发”式的概括。...
第二章白马非马问题在中国的命运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的命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白马非马这一命题有着十分丰富的逻辑内涵。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为我国逻辑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和思维财富。在中国逻辑学发展史上,公孙龙白马非马这一...
结论中国的逻辑思想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初。然而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很多学者通常把西方逻辑和中国古代的逻辑联系在一起进行比较,甚至更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并没有逻辑,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认真的研究中国的文化背景。在我国,逻辑学...
摘要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一直以来都以智者的面目示人,从古至今为人类留下的文化遗产更是数不胜数,从物质性的四大发明到非物质性的思想类建树都推动着时代的进步与人类的前行。然而,在提及中国古典文化之时人们更多的时候都将关注点放在儒家主流思想之上...
欧阳中石先生生于1928年,山东泰安人。他于1950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哲学系,1951年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专业,师从金岳霖、王宪钧、汪奠基等诸位先生,专攻逻辑学,主修中国逻辑史,1954年毕业。[1]早在1957年,欧阳中石先生就在《光明日报》上发...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文化与逻辑的发生有着内在的关联,它们的发生都是特定文化群体内的人们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的体现。它们不仅仅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定的社会生活使然。因此,认知先秦推类法式的发生、发展,需要从历史和逻辑两个角度展开。按此,...
中西方的类概念,中国的推类思想,西方的类比推理可以统称为一种逻辑思维,类思维。类思维在逻辑史中占有重要位置,西方逻辑史讲类比,中国逻辑史讲推类。要推类或类比,首先得知类,中国古代的这个类概念和传统形式逻辑中的类概念不尽相同,但两者对于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