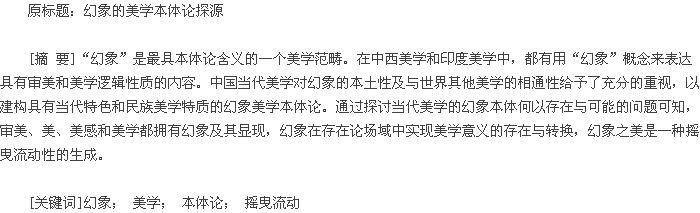
“幻象”一词,可被用来发掘和阐释中国美学史的逻辑本质,美学幻象也是最具有中国本土性的、向现代理论开放的阐释性概念,它在世界其他美学理论系统中能找到对应物,是最切合于当代美学本体论的阐释与整合的美学范畴。
“幻象”一词由“幻”与“象”组合而成,“象”作宾词,指具象性的一切,表象、形象、意象、图像、形状、形式等。幻与象相合,便是一种宾谓涵摄。具体说,凡是存在的象,都是在呈现和变化中的,貌似虚幻不真,唯其形貌、状态、图形、形式真切鲜明。在这里,“象”是特别适宜于描述视觉对象的“象”,但在审美和美学研究中,“象”的所指又是极其宽泛的,包括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类似佛教所谓“色声香味触法”皆可以有象。
“法”是轨持性的,可以包括意念、情感等恒持性存在,但它们也是可以有象的。而“幻”一词,本身表现的是一种动态性的状态,但这一词的含义非常微妙,一是它仿佛在动态前后瞬间切入,非此非彼,显得很不真实,没有自体性; 二是“幻”有相对的隐义,这个隐义就是不幻、真、实象之类,它与“幻”相对,而对幻象是否真的存在造成否定、解构作用; 三是“幻”一词具有色彩感,这种色彩仿佛是七彩的融合,赤橙黄绿青蓝紫,没有一种色彩可以在“幻”之中不被青睐乃至舍弃的,唯其色彩丰富,称为“幻”才更显存在的过程、动态与形态充满张力。因此,幻象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宾谓涵摄的美学思维,使幻象不仅作为物象、心象可以极呈其幻现流动之美,而且幻象在其自身作主词呈现时,其幻化、幻变、幻如的“谓词性”存在,也使其与异常丰富的意义场域相衍摄和关联,使“像”、“如”、“仿佛”、“似”这一类拟状词作为幻象的特殊标记,召唤着美的内在质蕴的幻现,从而在幻象的美、审美、美感和美学意义上都能够发掘某种共通的质性。这种共通质性通过“像”、“如”、“仿佛”、“似”这类词语获得本体论意义最为基础和普泛的确认,那便是“空”、“有”、“无”、“中”等,每一种本体论维度都能得到所期望的表达方式。当然,这种表达最终一定要落实到某种语句范式。但不管怎样,幻象毕竟是幻象,任何谓词性关联或衍射,无非是“像”、“如”、“仿佛”、“似”的幻现而已,美的存在依然是幻象,审美对象场域也依然是幻象,美感的蓬勃葱郁依然是幻象,美学的繁富诠释也终究是幻象。幻象是美的,它无始无终,确定和不确定,既为对象又自主呈现,既显现共通的与自在的美学质性和含义,又将这一切都幻化于非实体性的美的自由、超越与愉悦。总之,幻象是美的根本存在方式,是人与宇宙、世界的生命本质的存在、交流、转换和投放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人与世界排除来自任何一方面对“自我”、“他者”设置的烦恼和遮障,让人在宇宙中获得无须寄托身心而身心俱得其所的自由感与幸福感。
一、“幻象”的美学资源
幻象的美学资源极其丰富。以欧洲大陆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注重幻象的理性分解和语言诠释系统的“逻各斯”完善,在史前神话时期即体现出鲜明的幻象理性色彩。但正因此之故,相对僵化的分解模式限制了西方美学幻象理论,使得美学本体论维度从自至今一直具有强烈的独断论和形而上色彩。当代西方美学尽管在存在主义、现象学和符号阐释学的推动下,美学幻象愈来愈倾向于对差异化审美场域的意义呈现,但文化的总体性格并不因为这种人为的自觉努力而发生根本性改变。
在中国和印度,幻象理论资源积累可谓最为深厚。
中国巫术文化是士人文化和官方文化的母体,其一大特点就是对“象”的操作,从而由很早的模拟性象思维发展到商末周初时期形成了系统的卦象理论。卦象理论初步建立起幻象逻辑。汉代的“易学”是幻象理论高度知识化的发展期,周易的“象数学”和“义理学”都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东汉谶纬炽热,“谶”指预言、卜兆,“纬”是与“经”相对之纬,指在“六经”之外的书籍,包括伪托为圣人所造的经书。谶纬的一大特点是要观“象”,把自然与现实中各种正常的和怪异的现象当作可以预兆重大事理的征象,用非常正统的官方学说,包括儒道易学及阴阳五行学说等加以窜解,形成了关于“观兆验迹”的丰富美学资料。现在有关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都保存了当时人们的观察录刻和丰富想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重心向南迁移,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对于“幻象”的理解。在这个时期,“幻象”概念吸收了佛教思想转身出来与中国原有的“幻化”概念凝合为一。但在美学上,这一时期关于幻象的意义发掘成为理论关注的重点。
关于幻象的呈现及其存在论场域的关联性研究,因为佛教文化的进入而暂时缓下脚步,使得有关幻象的美学本体论推进反而不及关于幻象的意义诠释进展大。
这并不奇怪,当时属于文化变革动荡时期,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交锋乃至融合,首要关切的是整个文化系统的核心价值理念的冲突与融合问题,“幻象”本应是这一问题的核心构成,但因美学上还没有把“象”与“幻”作为一体性的存在来对待,故理论上不可能形成关于幻象的系统美学理论。隋唐是中国幻象美学理论发展的鼎盛期,一方面,佛教美学关于“幻象”的独特理论构成被中国化了,它们被融化在以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流派体系中; 另一方面,儒学和道家学也在幻象本体观念方面汲取了佛教思想,使其自身原有的幻象美学观念有了新的发展。例如,儒家的“比德”说以“德”和喻象相对应,强调内在品德的象征性具化,它在唐代与佛教观念结合后,“以象喻德”说与“德象和合”说互为表里,融入更宽容、博大的意境,呈现更为开放、旷达的胸怀和气度; 道家则在原有的重视自然之“象”,以朴拙为至理的观念基础上,吸收了佛教的“假名”、“相”( 象) 为方便说的观念,使道家的“象”理论更加系统化。唐以降,宋代复兴易理的“象数学”,并以理学巩固关于幻象意义的价值系统性,使中国美学的幻象理论在此后被贯彻到各个方面,发展为既重视内化于人格、心理的陶冶,又重视幻象的理性底蕴的严谨而深邃的理论体系。
印度的幻象美学资源主要存在于般若范畴及般若学之中。般若学是研究般若范畴之学,在印度文化发展史上并未形成明确的般若之学,但从原始宗教后期奥义书哲学时代算起,到公元 13 世纪佛教衰落为止,无论哪一个学术派别的兴起,都围绕着对般若范畴的不同理解而产生不同的体系学说。因此可以说,存在着一种事实上的“般若学”.般若范畴最鲜明的特征是具有突出的美学特性,这主要通过般若幻相显示出来。
“般若”,汉译为智慧,指超常的、特殊的智慧。“般若幻相”包括实相和假相二种,均由智慧而衍生。“实相”指虚妄之相,义同实义,其实是“无相”; “假相”借名言而存,可以有四万八千种法门变现,也就是说方便之相是无限的。那么从“实相”到“假相”是否有一个中间的过渡之相,在佛教来看,任何确定的、执着的意图都是危险的,因此,确定实相和假相的分别本身就是虚妄,这样便无所谓实相与假相之分,般若幻相也走向了现象学存在论美学,只不过是归结于智慧本体论维度的幻相论美学。
“幻相”与“幻象”基本上可以等同来看。“象”重视整体的由内到外的圆成,“相”则侧重于由内而达外的显现,但两者都是某种呈现或澄明,其意义存在某种一致性。印度原始宗教、原始佛教之小乘佛教、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都涉及到般若理论,自然也涉及到“幻相”范畴。大体说来,原始宗教以幻相为本体的变现,可以从中幻现,亦可以幻化为本体。本体与幻相的存在场域,在智慧根义上是一体的,但在变现上是有分离的。小乘佛教重视对人生现象的观察,幻象主要是指对各种世俗以为是实相的“幻象”本质的认识。如女性之美,年轻时容颜姣好,体态窈窕,韵味魅人; 但年纪大时再美的女性也要发秃齿豁,皮肤干瘪,眼神呆滞,再无丝毫诱人之处,可见女性之美是一个幻相,是不真实的。小乘佛教因此而主张由人生之苦谛、集谛的寂灭而入道谛。道谛注重实相,于变现之相甚少论到。部派佛教关于般若幻相的认识,主要是相信人的灵魂有三世轮回之实体,那么从“幻相”自般若智慧而出讲,也可以使人生诸相成为一个轮回,十二因缘其实就是人生的幻相。这个解释更具体了,但根本的问题是,人生的价值意义与幻相本身其实是分离的,并不是在每一个人生幻相阶段都能呈现美和美的智慧。大乘佛教则不同,它专门创造了一个菩萨概念,让其居于不变的、终极性的佛与世谛的众生相之间,使幻相理论又归复了“三性”之论。而菩萨是可以成佛、通常又下居在众生之间的,这样,菩萨就成为人的理想和情志的一种施设。依菩萨道,有关幻象的中道观便渗透到大乘佛教的各种理论系统当中,发展成美学境界、场域和其表现的价值意义都能变幻无穷,又能始终明确所指向的一种特别精致、完善、全面的佛教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般若作为核心范畴筑就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因其鲜明的美学特性而成为世界美学最重要的资源之一。
二、“幻象”与美学本体观
( 一) 幻象与中国美学本体观
幻象与中国美学本体观的关系在于二元本体论维度里的“幻”和“象”是互化的。《周易》“卦象”以“天象”( 天文) 、地象( 地文) 幻化而成为人象( 人文) ,无幻则不化,“幻”原始含义即是变易。周易《易传·系辞上》有“立象以尽意”之说,估计成于汉代,在象的背后隐有“情志”,此说直道象与意的联系,与《尚书》“诗言志”的命题似出一格,都在强调“言”表达出的东西在于其后面有内在的“志”驱动,“情”和“意”都属此类。若由此来看,“立象尽意”的命题似乎具有文化原生性,应该很早就有了,因为它强调了由内而外的“化”意。那么,这个由内而外的“化”与天地和合之“化”是否为同一种“化”呢? 显然不是。天地和合,人文化成,是由天地造化而生成人文之美; “立象尽意”或“以诗言志”则是由人文之教而化成其“人”其“物”.美的人格都是教化的产物,这种美的源始性力量是自然所赋予人的阴阳( 道家) 和心性( 儒家) ,这是一种根本。后续历代美学都本着这样的原则,将美的象幻化到人和器物的方面。
需要注意的是,“气”在二元美学本体论当中的作用。“气”是中国民间文化最根本的驱动力量,属于美学存在论的本体。巫术之象固然模拟天地造化,以导出人文之意,但巫术操作的过程,始终被认为是有神的气息贯注于所施行的对象当中的,因此,才有不可解释和不能不相信的神秘力量仿佛主导、操弄着情感意志的发动。但是,“气”在中国美学中,即便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未能依照气本体形成系统的理论,《淮南子》用“阴阳”二元论把“气”分解了。魏晋玄学确定的“气”是玄游之气,生命真实的气韵被抽空了。汉末至南北朝以前的气论,将“气”范畴从抽象本体含义向具体的物理之气、人的性格秉赋等靠拢,并以气为促成人文形式的重要构因,在思想上有大的推进。但“气”的构成和肌理却始终未能形成系统、清晰的认识,因而在气与象的结合方面,未完全与道、性、心等范畴很好地结合。因而,有关二元本体维度应当理解为不是源于同一种本体之气衍生、运行的结果,而是从二元之气辩证运动,讲究相反相成、顺逆相应的一种美学本体理论。
二元美学本体维度在宋代得到了周密而详尽的理论解说。周易的“象数”学在宋代复活,通过象的演绎变化,把性、情、理这些注重伦理或生命价值意义的概念统合起来,构建起中国古代最为庞大和严密的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理”被推崇为至高无上的本体,但“气”的概念仍然存在,属于机制性的驱动性概念。在宋代理学一元的遮罩下,二元论的美学本体观仍然有其具体的场域,这种不同元构成本体维度的美学交融与交叉,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是经常出现的情况。因而在宋代理学体系被推崇的时代,存在同样的情况是毫不令人意外的,只是理学总体上对美学的幻化采取抑制态度,从而宾谓涵摄的情形在宋代并不平衡。作为存在论的美学场域,只是在理学的局部领域有其发挥的天地,至于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和本体观念仍然是理性支配直觉的本体论形态。
在哲学传统之中,真善美是人类孜孜不倦追求的三个维度,三者相互联系并统一。而当集中在真与美的关系上时,大体会置于哲学与美学二者之中。一般而言,真是哲学的基本规定性;而就广义而言,我们可以将美学理解为以美为考察对象的哲学,这样,真的规定性便进入到美学...